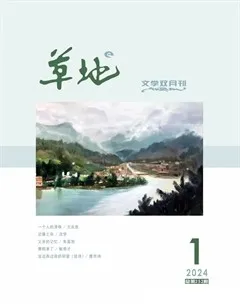小金記憶:松茸
五月,寫論文時查閱資料,偶然看到《末日松茸》一書,書的封面中心是一朵乖巧肥厚的松茸,傘形的菌蓋端正地撐起來,菌根又微微地探向左邊,嫩白的底子上面一層潮濕泥土的顏色,像是剛剛從厚厚的櫟樹林子里被帶出來,帶著山林的氣息。萬分親切——松茸啊,老家阿壩州小金縣盛產的一種山珍。如今我身在蘭州,對一切與老家相關的事物都特別上心,于是打算認真研讀一下這本書,聊慰心里那片往故鄉飄蕩的浮云。作者羅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是美國加州大學的人類學教授,對文化政治、多物種人類學、女性主義等話題頗有研究,她對松茸從山林菌絲到精美商品路程中牽連起的商人、采集者、資本主義世界、人類世概念、生態危機問題等等事物一一考察、梳理、描繪,有微觀的田野調查,也有宏觀的視閾分析,其實算是不錯的學術著作了。但這本與松茸相關的學術書籍卻讓我這個自詡“以學術為志業”的人覺得不滿足,我一度以為是因為譯本不夠好,故又找了英文版本來讀,卻依舊覺得這本書沒有寫到我的心坎里,中英文版本各草草讀了一半,就把書放下了,對老家更為惦念。
直到七月底,偷得半月清閑,回了老家,這正是松茸在山林瘋長,老老少少全都涌入山林與松茸偶遇的時節。我突然又想起了《末日松茸》留給我的遺憾,瞬間釋然,心里也有了答案,不是因為譯本不好,也不是作者描繪不夠細膩,而是因為我對松茸有太多溫暖柔美的記憶,大概是任何人都沒法將其恰如其分扣動的絲絲心弦。在老家,“蘑菇”就是松茸的獨特稱謂,“松茸”應該是商業時代的觸角伸到中國各個山區之后留下的名字——它們為我們的蘑菇命名了。其他的各種野生菌各有自己的名字,青杠菌、鵝蛋菌、雞油菌、老婆子菌、刷把菌、馬蹄菌、大腳菇、油辣菇……每個名字背后都是涌動的故土記憶啊!還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菌子,有的有毒,也就不敢去摘,在林子里遇到它們,燦爛安靜地長著,這本身就很美好。
小時候,每年暑假都會被父母放到親戚家去待一段時間。其中,讓我歡喜的就是去三姨家里,三姨個子很高,身形健碩,長臉豐唇,干活麻利又硬札,絕對不輸任何團轉四鄰八鄉的青壯小伙子。但三姨是個溫柔的人,特別是對我們這些小孩子,母親常說三姨愛“墊腳”。三姨的家在小金縣美沃溝高高的山上,雖然現在已經修了水泥路,但是取勢險峻,我是根本不敢開車上去的。當年去三姨家,先要坐車沿狹窄的河谷走上很長一段路,車子停在一個窄小的橋邊,于是開始步行往山上走。太陽在天上毫無畏懼地曬著,幾坨干凈的云縮在比山頂更高的地方,對這炎熱的人間避之不及。埋著頭一直走,突然回頭,就看到縣城已經變得手掌那樣大小,被幾座山兜起來,而前面的路還望不到盡頭,再走過幾個山坡,兜兜轉轉,不斷用雙腿將自己抬升到山的高處,這才能遠遠看到三姨的家。那時候,三姨家的幾間房子圍起一個方方正正的院落,房子周圍都是田地,暑假那段時間,地里的玉米、胡豆、豌豆、白瓜正是成熟的季節,莊稼茂盛地躥出農田,幾乎淹沒了田間小路,撥開莊稼前行,隨手摘一把胡豆或豌豆,青嫩又帶點澀味的口感,在沒有小賣部的山上,這就是最甘甜的味道了。離房子再遠一點點,就是深密的樹林,那些林子就是我最鐘愛的地方,有杉樹、松樹、柏樹、樺樹、柳樹……它們以自然的方式各自擇了一塊合適的土地生長,掉葉子,或者倒下、緩慢地腐朽。林子里有太多好玩的東西,而我最喜歡逛的地方是青杠樹灌叢(多年后我在翻看一本關于川滇植物的圖集時才知道,學術上,它們被稱為川滇高山櫟)。在我們小金,松茸大多長在青杠樹灌叢里。青杠樹低低矮矮,先是一叢一叢地匍匐在高山陽坡的路邊,繼而連接成一片,在陽光下遠遠望去,整片山起伏著一團一團的青褐色,群山竟也呈現出曼妙的曲線。可一旦鉆進青杠樹灌叢,那就絕對不是溫柔的體驗了,青杠樹葉大概是成人拇指指腹大小,邊緣有細細的刺,每次進林子都必須穿厚實的長袖長褲再加上帽子,但從林子里出來的時候,腿、胳膊、脖子,或者臉頰基本會帶上密密麻麻的細細傷口,汗液浸在傷口上,滋味難以言說。加之七月陽光炙烤,或偶爾來一場瓢潑暴雨,青杠灌叢毫無仁慈可言。就在這樣的林子中,在這樣炎熱潮濕的七月,松茸在落葉腐殖質里靜靜生長著。它像是有魔力一樣,一言不發,但自有一群人為了尋找它鉆入密密的灌木叢中。
去林子里找松茸,首先得有一個趁手的蘑菇鉤,其實就是一截木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則折出一個九十度左右的弧度。有弧度的那端是為了撥開青杠樹厚密的落葉,很多松茸的頭沒有冒出厚厚的落葉,可以用這種方法找到它們,尖尖的那端是用來撬松茸的,插進松茸根部附近的泥土,輕輕一撬,松茸就出來了。事后還要把撬過的泥土平整一番,用蘑菇鉤有弧度的那頭培一培土,再把剛才刨開的落葉鉤回來。你看,一個小小的蘑菇鉤都是這么講究。在很多撿松茸的老手那里,蘑菇鉤基本用出了包漿,那是長年進出山林的明證,不過真正的高手也許隨便在林子里折一段樹枝都能輕松發現松茸。而我們這些暑假到林子里混時間的孩子,頻繁更換蘑菇鉤,理由是用得不順手,找不到松茸。
第一次去找松茸,腳下一雙破舊的黃膠鞋,身上穿的是三姨找出來的不合身的舊衣服,頭上一頂遮陽帽子,斜挎一個在年代劇里經常看到的軍綠色挎包,包里裝著兩三個包子或者饅頭,或者蒸熟的洋芋。手持一根蘑菇鉤,不管能不能找到,這身打扮是非常到位的。再學著大人的模樣,走上坡的時候雙手背在后面,走下坡的時候曲著膝蓋側步往下,活脫脫就是一個找松茸的好手。但是進了林子,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對我這種青杠林里的混子來說,撿松茸是件有趣的事情。可能因為我從小笨拙,行走在林子里,首先要保證的是不摔倒。林子太密了,基本是三十度以上的斜坡,青杠樹橫生蠻長,樹枝樹葉交錯緊密,與城市規劃公園里看到的那些由木樁支撐的樹不同,它們自由喧鬧,絕對不考慮人類如何行走其間。我幾乎回到了四足爬行的年歲,這也得是那種高出人頭的林子,如果是稍微矮一些的林子,我只能保證自己能穿過這片林子,絕對不可能俯身去看樹下有沒有松茸生長的痕跡。腳下有時還有蔓生的樹根、碎石藏在松軟的落葉層下。當然,松軟潮濕的地面就是松茸最好的生長點了。第一次自己“找到”松茸,也是三姨爹帶我第一次進林子,他能在那種密不透風的林子里大步流星,我們則在后面爬行,突然他回頭叫我和弟弟妹妹,我們便加快速度爬上去,三姨爹用蘑菇鉤指著腳下一塊地,說“你們看,這里有蘑菇。”可我們都看不見,我使勁揉了幾圈眼睛,也只看到一塊稀松平常的土地,落下的青杠樹的葉子已經泛白,有幾株細細的草,然后就是泥土,哪里有什么松茸。三姨爹笑我們說“蘑菇長得你眼睛底下你們都看不到。”然后用蘑菇鉤的尖尖輕輕在地上指了一下,那里居然有一個小小的裂縫,那么小!他輕輕刨了一下裂縫上的土,下面竟然就是一個松茸頭,白白嫩嫩,嬌羞的樣子令人生氣——這種找松茸的技術,我大概這輩子都學不會了。
偶爾運氣好,我也許能碰上一群紅彤彤的青杠菌,那也是令人開心的事情,白嫩的菌腳支起圓潤的菌傘,一團一團趴在樹腳下。雞油菌也是很好的,有特殊的馨香,它們大多在林間的空地上,青草鮮嫩的地方,黃酥酥地歇在那里,雞油菌很小,至大也不過手指長短,但如果被我遇上,那不管多小都會摳起來,視若珍寶地放在袋子里。回到家展示的時候,三姨總會笑著說“咦,這么小的兒兒你都不放過,不過還是夠炒一盤了。”最令人欣喜的還是鵝蛋菌吧,算是菌子里的俊男靚女,個子碩大,空心的菌腳能長到二十厘米左右,菌傘也闊大,關鍵是鵝蛋菌口感鮮嫩,炒著吃是最鮮香不過的了。肥厚的大腳菇也是好的,肥嘟嘟的菌腳在地面鼓出來,像是一個被施了定身術的胖和尚。最常遇到的是各種“爛菌子”,都是很艷麗的樣子,紅紅黃黃,燦燦爛爛,長得熱熱鬧鬧,找不到菌子的時候,看著它們都來氣,一一敲過去——碎落一地。
三姨和三姨爹找松茸都很厲害,他們進入青杠林子里,幾乎隱沒其中,像是一條青龍扎入波浪滔滔的深海,只看到他們進入林子的地方樹枝微微晃動,再有點硬挺的青杠葉子和刮著衣服發出的唰唰聲響,沒過一會兒,他們可能就已經在對面山坡上和什么人攀談了起來,聲音響亮,像是有用不完的勁。直到下午,太陽西斜了,他們又出其不意地從林子里鉆出來,帽子可能已經斜著戴了,胸前的挎包里鼓鼓囊囊,臉上有疲憊,也有高興。這時候,大路邊已經聚集了一群人了,帶著秤的收松茸的販子,帶著裝滿各色小零食的背篼的販子,還有其他撿松茸的人。年輕的人相互調笑,老的有坐在路邊抽煙的,也有揣著手到處看熱鬧的。三姨他們走到大路邊的時候,那些收松茸的販子都會笑盈盈跟他們打招呼,問他們今天撿了多少,他們也笑盈盈地回,沒撿到什么,今年的蘑菇長得不好。直到走到他們熟識的松茸販子那里,他們才盤腿坐下來,把蘑菇鉤放在身邊,打開挎包。這時候,周圍的人都會圍上來,他們一一拿出自己的戰利品。一般來說,一個塑料袋,裝著一些小松茸,只有手指大小,這些算不上品級,價格不高。另外的就是精品松茸了,他們會用松軟的葉子將這些松茸一一裹起來,再扯一根細細長長的草將葉子扎起來,這樣包裹后,既保護又保鮮。他們在販子面前拆開那些小包裹,曼妙的香味逐漸清晰,個個都是漂亮安逸的,個個都是標致伸展的。這些就是販子嘴里說的“打得起等級”的松茸,品相好,價格會比那些小松茸貴上四五倍,它們會再次被挑選、包裝,送上飛機,飛到全國各地,甚至飛出國門,去日本、美國、歐洲,然后被精心烹飪,出現在那些像三姨和三姨爹這樣的采集者可能永遠不能到達的高檔餐廳里。但三姨他們好像也沒有想過那么多,每年撿松茸的收入是一大筆錢,這筆錢攢下來蓋新房子、給孩子買衣服、交學費、給老人看病……都是極好極好的事情。
三姨爹是家里最小的兒子,三姨嫁過來之后,也就長久地在這個地方生活下來,他們的生計和土地緊密相關,高山草甸地帶適合放牛,于是家里就有了一群牛,黃牛、犏牛、牦牛,都有,春天趕上去,霜降之前收回來,期間時常得上山去清點一下牛的數量。草甸下面的林子里有各種菌子,季節到了就去林子里撿菌子、撿蘑菇,能掙不少錢,這些林子周圍還有茂盛的野草,于是家里也有一群羊,早上打開圈門,它們熱烘烘的氣息撲面而來,太陽西沉時,他們又回到房子周圍。雖然偶爾會有人在山坡上大聲提醒:“羊子下地了!”在家里守著的老人或者小孩就立馬跑出去驅趕“誤入”莊稼地的羊。房子周圍的田地種各種莊稼,小麥、青稞、玉米、胡豆、豌豆、土豆,更好一些的地就當菜園子,白菜、卷心菜、黃瓜、四季豆……在這些生物的環繞之下,莊稼和人都在隱秘生長的年年歲歲里。
今年回老家時,原本說再去山上撿松茸,卻又小病一場,被父母按住了去林子里的沖動,于是每天晚上去松茸市場湊熱鬧。因為七八月正好是旅游旺季,老家縣城窄窄的一條街每天下午五六點開始禁止車輛通行,人行道上全是各色山珍,松茸、各色菌子,甚至是山林里的野果子都被拿出來販賣,熱鬧非凡,用我母親的話來說,這是“軋斷街的鬧熱”。回老家的日子,每天吃飯都有各色菌子,或燉或炒,大快口腹之欲。
這就是自然富饒的山林給我留下的小金記憶。
又說回到曾經讀到的那本《末日松茸》,書里說在日本廣島受到兩枚核彈攻擊之后的廢墟中,最先恢復生機的就是松茸,也許松茸就帶有最原始的生命動力吧。我這個在外求學的人,幼年時關于松茸的記憶,也是那樣從容而難以被打敗。寫到這里,又把阿來的《蘑菇圈》翻出來讀了幾頁,從《末日松茸》到《蘑菇圈》,我也不知道為什么,當我離開老家之后,我從書里面讀到的她是那么動人,而我生活在那里的許多年,不管是山脈慢慢青綠蘇醒的春天,還是河流逐漸消瘦澄澈的秋天,我居然不為所動,甚至責怪歲月漫長,何時才能長大,何時才能離開這里,何時才能衣錦還鄉,這都是少年時候的幻夢。當我離開老家,多年生活在四川盆地,又一路北上到蘭州,在這個順著黃河拐彎的地方建起來的城市里,我的枕頭下面流淌的是一條不知名姓的河,她在冬天澄碧枯瘦,她不斷打濕我夢中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