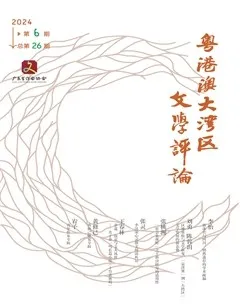中國新文學的精神機能和歷史位置
摘要:相比小說本身“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魯迅更加看重其“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的閱讀效果,這意味著,以《狂人日記》為代表的新文學內涵著某種獨特的精神構造。基于此,當下研究尤其需要從精神史徑路入手,考察新文學如何以現代身體為媒介對“受攖”這一生理機能進行呈現。就文學自身來說,這種“受攖”不僅成為新文學著力聚焦的特定現實,也使它成為一種特殊的、無法被經典文學化約的獨特形態。就二十世紀中國而言,這種文學誕生于革命行動陷入困境的歷史時刻,它通過對社會政治危機的顯影、對革命失敗的涵納嵌入歷史最核心的位置,并在這個位置上完成了重鑄革命動機和重塑革命主體的使命。
關鍵詞:新文學;精神史;生理機能;革命
在1935年給《〈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所做的序言中,魯迅對自己的小說創作作出如下自我評價:
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地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然而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一八三四年頃,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經寫了《狂人日記》;一八八三年頃,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蘇魯支(Zarathus-tra)的嘴,說過“你們已經走了從蟲豸到人的路,在你們里面還有許多份是蟲豸。你們做過猴子,到了現在,人還尤其猴子,無論比那一個猴子”的。而且《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L.Andreev)式的陰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雖然脫離了外國作家的影響,技巧稍為圓熟,刻畫也稍加深切,如《肥皂》,《離婚》等,但一面也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1
在這段文字中,“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曾被頻繁提及和反復征引,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構成了魯迅研究傳統中兩個最基本的路徑。所謂“表現的深切”涉及思想分析、社會分析和現實主義文學觀念,它也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被視為從馬克思主義理論進入魯迅文學的入口;而所謂“格式的特別”則關聯著形式和語言分析,在新時期魯迅研究那里,它愈發成為主流的方法,并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魯迅研究的“文學本體”意識。但少有人注意的是,“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原文中被打上了一個雙引號。這意味著,這段被頻繁提及和反復征引的說法或許別有出處,甚至不排除魯迅征引他人評論的可能。這當然不是也不可能否認魯迅對此一說法的認同,而是想強調,“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這個說法或許并不構成魯迅自我評價的重心,毋寧說,他真正看重的是這種文學品格產生的效果,即“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盡管魯迅也宣稱“這激動,卻是向來怠慢了紹介歐洲大陸文學的緣故”,但無論是“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的判定,還是“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的描述,都意味著以《狂人日記》為代表的新文學內涵著某種獨特的精神構造。這種獨特的精神構造以及令“青年讀者”群體“激動”的社會影響力并不能在“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內部得到充分解釋,甚至從他小說創作的整體歷程來看,兩者之間還存在緊張的抵牾。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才會說《肥皂》《離婚》這類“技巧稍為圓熟,刻畫也稍加深切”的思想藝術佳作反而“減少了熱情,不為讀者們所注意了”。
無論是“憂憤”“熱情”還是“激動”,都明示著,以魯迅小說為代表的“新文學”隱含著某種有待開顯的精神史意義。在身歷二十世紀歷史變革的新文學作家、批評家和讀者那里,這種精神史其實形成著某種籠罩性的氛圍,而對不少老一輩中國現代文學和魯迅文學研究者而言,這種精神史也成為一種基本的、前提性的感覺意識。當然,由于他們置身于歷史之中,這種感覺意識并沒有被學術研究充分對象化,更沒有顯影為清晰的知識形態和歷史面貌。而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已然過去的當下,新文學那種在精神史意義上不無激進的“新”更變得語義含混乃至無從辨識。在很多時候,它甚至只能在理論、觀念層面予以高度抽象地表達(如所謂“戰斗性”“激進性”),而在某種以實證主義方法為主的歷史分析中,它甚至被不假思索地忽略、過濾,最終成為缺乏“事實”支撐的空洞話語。正是在這種情境之下,如何揭示新文學及其精神史的面向,如何用準確而生動的語言重新為這種“精神”賦形也就顯得至關重要。
當然,新文學獨特的構成以及動態的存在方式意味著它不可能被輕易捕捉、把握和充分表述,由此,以學術研究的方式展開這種賦形的工作必然是一個充滿張力的過程,而學術研究自身的視野、方法尤其是語言都要被這個尚未彰顯清晰邊界的對象所反向規定。
對新文學精神史的研究,當然不能忽視“精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源遠流長的脈絡,但除此之外,還需要對“精神”概念本身作出一個貼合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和新文學自身的理解。以魯迅為例,他筆下的“精神”就有非常特定的知識意涵。魯迅把自己的文學稱之為“為人生”的文學,這里的“人生”不是一般的修辭,在其1909年抄撰的生理學講義《人生象斅》中,作為標題的“人生”已經明示出生理學知識的淵源。同樣是在《人生象斅》中,出現了從生理學角度對“精神作用”明確的知識界定:“設體表受攖,則其處之神經杪末,為之僨興,次由求心性,傳諸中樞,爰生感覺。”1從這里能夠清晰地看出,晚清魯迅“攖人心”文學是以生理學知識為基礎的,“攖”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古語詞,而是意指著“體表受攖”,即外物對人體神經系統的“刺戟”。此前的研究多有對魯迅文學“痛感”的討論,也對其具身性的生命政治意義有所關注,而回到新文學及其發生的歷史情境,它們都能夠落實到生理學這個在晚清時期有著廣泛影響的知識媒介上。由此,對魯迅文學有關“身體”的討論不能僅僅對應當下知識界廣泛采用的西方理論話語,而是要注意,魯迅筆下的“身體”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它不是指涉某種整全意義上的身體,恰恰相反,所謂“身體”是一種被現代生理學知識規定、描述乃至參與塑造的“身體”,它被偏至地描述為以神經系統為體、以精神作用為用的生理機能。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到的“精神的絲縷”,在《野草》中所說的“頹敗線的顫動”,都是對神經纖維形態的文學表達,而他的文學中頻繁出現的“夢”“醒”“睡眠”“死亡”等也常常是作為神經官能得以顯影。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那些最具激進性的新文學文本中,常常存在著和魯迅文學深度相通的特質——郭沫若的《天狗》和《夜步十里松原》、巴金的《滅亡》乃至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等等,都能夠看到類似的情形。從某種意義上說,那種以神經系統為體、以精神過程為用的生理官能可以視為新文學著力聚焦的特定現實,也是它整體性的精神特質。和中國傳統文學及其深受影響的域外文學相比,以五四發端的新文學又有其特殊性:
第一,新文學的精神并不是一個自成一體的精神范疇,更不是一個封閉的、令主體沉浸和耽溺其中的精神世界。就生理學而言,所謂神經系統處在身體和外物交接的位置,由此,精神發生作用的方式也就突破了所謂“內面性”,它是通過對外物觸受產生的“及身性”確立了自身。所謂“及身性”意味著文學通過對神經這一肉身界面的摹擬建構起“心”與“物”彼此抵牾、摩擦、磕碰、撞擊的界面,當然,它也是通過引發劇烈痛苦的抵牾、摩擦、磕碰、撞擊將近代中國因經學瓦解而斷為兩截的“心”與“物”重新扭合為充滿內在動勢的、現代性的身體。
第二,這種因外物觸受產生的“及身性”隱含著某種被動情態。魯迅本人曾經提及,“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1。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學界直接挪用晚清時期的“攖人心”來描述魯迅文學的特質是不準確的,毋寧說,“五四”時代誕生的魯迅文學乃至新文學整體更是一種“受攖”的文學。相比“攖人心”而言,“受攖”的文學產生于“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2的覺悟,也意味著新文學在根本上拒絕了那種以既定知識思想為前提的啟蒙理路。新文學的緊張感正來自這種“受攖”,由此產生的不是一個施設假立的行動主體,而是一個行動陷入困境甚至行動無法展開的肉身,除了以“肩住黑暗的閘門”被動地承受以外,這個肉身似乎無所作為。這正是新文學產生的歷史時刻,它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這個無所作為的肉身、用顫栗的神經纖維“反應”(而不是“反映”)現實社會嚴酷的運作機制。
在二十世紀中國的革命歷史中,聚焦于神經系統的生理機能為新文學賦予了極致緊張的精神強度,也使它和它所表征的精神狀況與激進革命構成深度的關聯。首先,新文學強化了社會整體和個人肉身之間的沖突,它也通過將神經反應具象化的方式將其轉述為精神和現實不可調和的沖突,由此,個人在社會情境中的日常生活也就成為“不能忍受的生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才成為革命持續展開的前提性要素,它是作為一種帶有身體性的倫理動機被制造出來。其次,發生于革命挫敗時刻的新文學蘊含著對革命挫敗的深度省思,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通過新文學的形式創造,革命挫敗才掙脫了它作為革命終局的命運,由此,近代中國的革命想象得以突破晚清時期以“自殺”“暗殺”為核心場景的瞬時性構造,進而成為一個得以在長歷史周期中反復重現、持續展開的過程——神經系統陣發的顫栗、痙攣為這種深層的革命發生機制賦予了清晰、鮮明的形象。最后,在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新文學互相內在于彼此的連帶結構中,也暗含著某種緊張的對峙。一方面,經由新文學神經機能激發和形塑的、以知識青年群體為代表的歷史主體固然蘊含著強勁的精神勢能和革命動機,但這種“精神/現實”二分的認識結構常常令他們執著于二者甌脫地帶的“斗爭”,而無法真正穿透現實表層的障壁,進而在真正意義上予以現實整體性的提領和重構。另一方面,當新文學及其相關的歷史主體真正被涵納在革命實踐內部,兩者的張力會進一步凸顯出來,革命展開的過程本身也會在“受攖”的身體反應中得以顯現,在很多時候,魯迅“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1的說法正是這種內在矛盾的寫照。
就當前學術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而言,新文學及其精神機能并不是一個自明的、有清晰邊界的文學史對象,它需要從歷史和文學的雙重維度上予以把握。
新文學首先是歷史的存在。具體而言,它不是任何一種既定的文學類型,毋寧說,它是通過文學的方式(尤其是語言和形式)對中國現代轉型危機的捕捉和賦形——它從倫理層面明示出革命必然且必須發生的根源,也從社會現實方面警醒著革命者與其革命對象之間錯綜復雜的糾纏關系,更在一種頗為嚴苛的文化政治意義上顯影出挫折之于革命不可或缺的構成性。因此,在新文學研究者這里,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并不能化約為某種學院意義上的歷史材料和歷史學知識,更不能在當下流行的文學認知理路中等同于作為“內部研究”預備的“外部研究”方法,而是要注意,新文學對社會政治危機的顯影、對革命失敗的涵納本身就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發生和展開不可或缺的環節。作為某種結構性社會危機的癥候,新文學是無法通過某些既定的社團流派、作家作品將其從文學史的整體序列中框定出來的。在一個整體結構中,即使是同一個作家乃至同一部作品的激進性、革命性也會呈現出一個彈性的伸縮幅度——在某些特定的狀況中,那些本身并不具有“革命性”的作家作品(如老舍、冰心)也會“通向革命,引向革命”(王蒙語);相反,如果社會整體結構發生了變化,那么原本和革命深度扭結的激進文本也會發生變異,1950年代新中國青年群體把巴金作品讀為張恨水式的通俗戀愛小說即是一個典型案例。因此,新文學研究不可能局囿于文學文本乃至文學史的內部范疇,需要特別注意這些文本在歷史構造中生成的過程及其對特定群體發揮作用的機制,這就需要將歷史維度納入進來。
對新文學作為歷史存在的強調自然不意味著對文學性的簡單否定。但必須承認的是,作為一種特定歷史形態的新文學可能并不具有中國和西方經典文學的藝術價值,除了魯迅等少數作家之外,未來的經典文學史書寫可能會無情地刪汰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的大部分作家作品。但是,如果懸置文學的范疇,如果試圖把握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構造和中國社會轉型的現代化過程,那些為數眾多的新文學文本卻是難以忽視的。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很少有像二十世紀中國這樣把文學推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的,也很少有文學以如此的深度嵌入革命的結構內部并參與了革命的發生、展開。當然,在朝向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開放自身邊界的同時,恰恰要在文學和文學史意義上收束新文學的范圍,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新文學的研究需要注意新文學這一對象的“狹義性”。洪子誠先生在《“當代文學”的概念》中曾經提及,1949年之后的文學史“使用的‘現代文學’概念,是在劃分多種文學成分的基礎上確定主流,達到對‘新文學’概念的‘減縮’和‘窄化’。”1這種描述昭示出概念在不同歷史時期意涵上的差異——在十七年時期表征著“減縮”和“窄化”的“現代文學”恰恰在1980年代以后成為豐富、多元的文學圖景的前提概念。因此,本文所使用的“新文學”并不僅僅是沿著洪子誠先生提示的歷史過程做一個反向的話語還原,正如洪子誠先生所說,“劃分多種文學成分”的做法是不必諱言的意識形態操作,但是“多種文學”之間的差異、張力以及這些文學對自身和他者的定位卻是內在于新文學整體歷史結構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所謂“狹義性”的強調絕不是要返回基于僵化的政治觀念而結構的“一元”文學史圖景,更不是重新確認以“左翼文學”為標識的所謂“主流”。事實上,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隱含著革命基于自身邏輯對文學的敘述,這種敘述最核心的部分在于它始終承認且凸顯新文學內部矛盾的存在,如果回到革命史的語境中來看,這也是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和左翼文學的突出特點,它們的根本意義并不在于所謂“主流”的地位,而是在于它們比其他很多社團、流派更能把新文學從整體上理解為一個緊張的論爭結構——帶有悖論意味的是,只有通過這個結構,新文學的各種要素才能以相互對峙、拮抗的方式深度連帶為一個整體。相比那些帶有自明性的作家、作品、社團、流派而言,這種整體性、根本性的緊張結構無法通過實證意義上的材料直接顯現,而只能通過精神史研究的方式予以把握。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以“五四”肇端的新文學遭遇了來自各個方面的嚴厲質疑:以新儒學復興為標志的保守主義為其貼上了“激進”的標簽,“當代文學”則將其視為革命在深入過程中需要超越的對象物,而自新世紀以來,它更被視為某種與“日常生活”脫節并喪失了發展動力和前景的話語形態。盡管這些討論帶有不同立場和思路,但他們對“五四”和新文學、新文化共同的批評態度卻構成某種癥候。問題在于,他們所質疑、批判或解構的“五四”和新文學更多是指1980年代占據思想主流位置的“五四”話語——一個可以用“啟蒙和救亡”話語指稱其全部內涵的“神話”。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對“五四”和新文學的批評,不過是1980年代以降知識話語自我的運作,因為那個作為歷史的“五四”以及新文學不僅不會被真正觸及和認真對待,反而會在所謂“話語”意義上被徹底懸置。但如果回到歷史的情境中,“五四”和新文學這個試圖被多方否定的形態恰恰顯現出它和這多方之間的扭結和連帶。從和傳統的關系來看,新文學的發生是對近代儒學窳敗的回應,魯迅充滿具身性的文學正是對失效儒家倫理的意志化改造;從二十世紀革命和革命文學進程來看,新文學不僅生發出革命的動機,更成為革命挫敗時“革命再起”的媒介;而從新世紀以來中國眾聲喧嘩的思想文化界來看,新文學作為一種把握時代、現實的方式仍然有其意義,那些試圖在所謂“日常生活”中宣告新文學“終結”的討論并沒有意識到“終結”的后果是什么——在復雜多變的現實狀況中,“嚴肅”的社會現實命題依然存在,而那些話語解構式的狂歡書寫根本無法承載和把握它們。因此,即使是作為一種歷史存在物,新文學的經驗仍然需要理解、把握和轉化,這不只是為了歷史本身,而更是為了能夠重建一種有力把握現實的契機和有效結構當下的能力。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