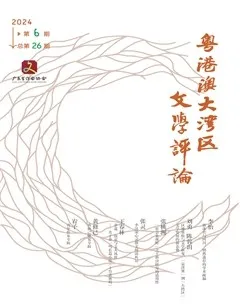梁啟超文學批評話語的古典轉化及其主體意識
摘要:梁啟超是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開拓者與奠基者,中國古典“詩教”傳統及其詩學資源是梁啟超文學批評話語建構的基礎。梁啟超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一方面在于其以“小說”與“群治”這一關系,創造性地闡釋了“新小說”與“新中國”之間的深層關聯,并以“中國文學”為中心對中國文類的歷史秩序進行重構,從而創造了功利性與審美性相統一的小說批評觀念,實現了對中國古典“詩可以群”與“文章經國”批評思想的話語轉換;另一方面在于他以情感教育為基點,通過對儒家“盡性主義”和“仁的人格”的思想轉化,將藝術的價值與藝術家的人格力量聯結起來,構建了人格—藝術—情感—形式一體的情感詩學及其詩文批評的邏輯方法。梁啟超文學批評的古典轉換及其主體追求所蘊含的豐富經驗,對于今天我們探索中國古典文論的現代轉化、構建中國文學批評的話語體系具有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詩教傳統;文學批評;梁啟超;小說群治;情感詩學
一、“詩教”傳統:梁啟超文學批評
的精神資源
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在他筆下涌現的西方人物和思想可以說開了中國近代域外精神視野的一扇大門,比如盧梭、斯賓塞、伯倫知理、孟德斯鳩、伏爾泰等等。在梁啟超創辦的《新小說》報上的插圖欄中,也出現了英國詩人拜倫、法國作家雨果和俄國作家托爾斯泰的頭像和介紹,但是在洋洋大觀的梁啟超的著述中,卻幾乎沒有看到梁啟超談論西方的文學思想的論述,僅有的對于日本政治小說及其西方淵源的表述,也充滿著各種中國式的誤讀。結合梁啟超日本流亡期間的經歷,我們同樣很難發現梁啟超文學批評思想的確切的外來精神資源。盡管日本啟蒙思想家對于梁啟超文學思想的轉變確實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種作用在夏曉虹和日本京都大學的梁啟超研究計劃中都被揭示,但是從其根本上言,梁啟超文學批評思想的真正精神資源,卻是傳統的“詩教”思想。
作出這一判斷的依據首先在于,終其一生,梁啟超對中國傳統“詩/樂教”的傳統情有獨鐘。無論是前期的小說批評思想還是后期的情感詩學思想,他都特別重視古典“詩/樂教”精神資源的作用。早在《飲冰室詩話》中,梁啟超就認為“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在他看來,《詩》三百都是樂章,《楚辭》諸章也應弦赴節,而唐代絕句、宋詞元曲都是通音律的文學,并且因為他們都由士大夫主持,因此并不鄙俗,對于老百姓的精神教化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本朝以來,則音律之學,士夫無復過問,而先王樂教,乃全委諸教坊優伎之手矣。”這正是中國國民性墮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他看來,只有重新恢復詩樂合一的傳統,才能夠實現文學啟蒙的目的,他尤其重視通過音樂與詩歌的結合以創造新的“樂歌”1,而在后來創辦的《國風報》中,他更直接以“國風”的“詩教”思想來闡釋其思想文化啟蒙的思想依據2,而生命后期從政治轉向學術之后,他傾力于審美教育,在《孔子》《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不斷地倡導儒家“樂教”思想。
事實上,梁啟超對小說“不可思議之力”的肯定,也正與其對音樂與心理作用的理解相似,是從心理的層面來強調詩歌、音樂的教化作用,強調文學變化氣質、改造國民性的重要功能,而這正是教育的基本任務,同時也突出了審美教育與政治之間的關聯,顯示出梁啟超后期審美教育思想與其前期文學啟蒙思想的某種一致之處。正是這種一致性,使我們對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話語的本質的理解必須始終注意到政治與審美、啟蒙三者之間的復雜關聯,同時也很鮮明地顯示出梁啟超自身并不是一個審美主義者,而有些論者卻因為其提“趣味主義”而認為梁啟超后期體現了西方無功利的審美主義美學的精神,很顯然,這正是沒有充分地解讀梁啟超文學批評思想的結果。由梁啟超與中國古典“詩教”“樂教”的這種精神淵源,可見他的文學批評思想的真正底色。
二、從“詩可以群”到小說群治:
梁啟超小說批評的話語轉換
梁啟超是中國現代小說批評話語轉型的奠基者,也是20世紀中國小說批評理論范式的開拓者。文學批評本質上是對文學的審美評價,文學批評觀依賴于評論家的文學觀。梁啟超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的地位,首先在于其通過對中國古典小說觀的重建而對中國傳統文學觀進行了重構。誠如日本學者齋藤希史所言:“梁啟超小說論的意義正在于其打開了重建文學的突破口。”3 1902年,他在日本橫濱創刊《新小說》雜志,并于第一期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這篇成為中國現代文論經典的文獻,連同他主編的《新小說》的編輯實踐,共同建構了他的小說觀、文學觀和小說批評的基本思想。
小說作為一種通俗和娛樂文體的功能在晚清得到了知識界的重視。夏曾佑在《本館附印說部緣起》高度肯定小說的作用,“夫說部之興,其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幾幾出于經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風俗,遂不免為說部之所持”4。這種從小說與傳統經史教育的效果對比中,來突出小說對于普通老百姓的民智開啟的意義,是當時小說論述的主調。梁氏對小說的早期認識,并沒有脫離這種論調。他在《變法通議·論幼學》中就從語言與文字合一的重要性論述了小說通俗語言與文體的教化意義5,在《〈蒙學報〉〈演義報〉合敘》中也從通俗教育的角度肯定俚歌與小說的價值。6《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后簡稱“《論》文”)在中國現代小說批判理論史上的價值,就在于突破晚清小說通俗教育論的一般認識,而以“小說”與“群治”這一關系,創造性地闡釋了“新小說”與“新中國”之間的深層關聯,從而以新國民主體的重建為中心,統一了小說的功利性與小說的審美性。
“群”是梁啟超這一時期思想中的一個關鍵概念。在發表于同一時期的《說群》《論佛教與群治之關系》中,梁啟超從民族國家的層面論述了“群”的含義,并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中,將小說與國民的關系進行了連接。人們普遍注意到《論》文中梁從“熏”“浸”“提”“刺”等心理學層面對“小說不可思議之力”與“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等審美層面所作的論述,但這篇文獻的重要價值還在于從“群”的層面上闡釋了“中國小說”的內涵。受日本政治小說及其“民權=國權”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1,梁巧妙地轉化了中國古典傳統中的“小說”內涵:既從小說非“子”非“史”的異端性所包含的混亂和恐懼中轉化出士人階層對小說進行“革命”的必要性;又從《漢書·藝文志》中關于“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的論述背后所蘊含的小說作為“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民語”中,嵌入小說與民權的民族主義內涵。 由此,梁在“國者,積民而成”的觀念下重建“民”的主體性,又在傳統“民”與“小說”一體的觀念下,建立了“小說”與“中國”之間的關聯,使“中國小說”概念成為“民”與“國”關系的一種隱喻,以及對以民為主體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呼喚。因而,“小說界革命”也就意味著,要通過對“小說”在傳統社會中所具有的象征秩序的“革命”性顛倒,獲得小說作為文學之最上乘的地位,從而確立小說與現代中國之間的想象關系。然而,在這一強烈的“斷裂”視野之下,中國傳統的舊小說無非“誨淫誨盜”之物,梁所召喚的“新小說”是一種需要被重構的對象,一種用以建構新的“國民”共同體認同的文學類型。如他在紹介《新小說》宗旨時所言:“本報宗旨,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勵其愛國精神。”2政治小說是梁所構想的實現這一目標的小說類型,而在他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這部“《新小說》之出,其發愿專為此編”的未竟小說中——正蘊含著他關于政治小說的設想,即以虛構為基礎,展現對中國未來藍圖的建構和對民族共同體的展望。這與他在《論》文中所描述的舊小說中的有著種種腐敗的“老大中國”的圖景構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在《新小說》中的“歷史小說”一欄中,梁啟超還通過策劃刊發他國歷史的小說來隱喻中國的命運,以他者的“建國”與“亡國”的命運的小說書寫,來形成中國主體未來建構的一種認同方式。
實際上,在梁啟超提出“中國小說”概念的同時,他也提出“中國文學”的表述。如“本報所登載各篇,著、譯各半,但一切精心結構,務不損中國文學之名譽”3“吾輩僅求之于狹義之詩,而謂我詩僅如是,其謗點祖國文學,罪不淺矣”4等。與“中國小說”所蘊含的強烈的斷裂性不同,“中國文學”始終是與榮譽聯系在一起的,并且傾向于文學的“精心結構”“處處皆有寄托”“風格筆調”“趣味盎然”等審美層次上的內涵,充滿著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歷史接續與審美傳承的意識。正如梁的“史界革命”意圖通過重構歷史作為國民意識的基礎一樣,“中國文學”概念及其蘊含的歷史與審美意識,是他通過對中國文學的重新敘述來為“新小說”建立根源的行為:其一,從俗語文學進化的視野,強調包括小說在內的一切文體向俗語文學進化的必然性;其二,從文體進化的視野,強調文體進化由簡到繁的趨勢,從中以戲曲為中介,將戲曲與詩歌聯系起來,突出戲曲在表現功能上相對于詩歌的優勢,建立戲曲的至高位置,從而在廣義的詩歌的意義上將戲曲納入中國詩歌系統之中,確立戲曲在中國文學中的至高形態;同時將戲曲的表現力與小說的感染力聯系起來,從而將戲曲納入小說的視野之中,確立小說在文類上的總體性。由此,確立了《桃花扇》作為歷史與現實交接的最佳點、文學認同的最佳時刻以及民族精神最為飽滿的時刻的獨特地位。“作為‘國民文學’,它既是文類最高點的呈現,擁有無愧于‘文學’的方面,又是民族國家認同的最佳代表,其本身就蘊含代表著強烈的民族精神。兩者在建構民族的尊嚴和榮譽上聯結在一起,民族認同意識和民族權利精神在這里得到最深刻的呈現。民族精神最為飽滿的時刻,則是藝術構造最為獨特的時刻,審美性與民族性正由此而發生。”1
梁啟超對小說與一國文明之關系,以及“小說界”建立的實踐,其精神資源來自古典“詩可以群”的思想。正如孔子所說,“不學《詩》,無以言”。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對《詩經》的運用,外交與內政場合的“引《詩》”“賦《詩》”行為,既是一種政治行為,同時通過“詩”又建立起政治階層共同體。從周孔時代對“禮樂”制度的向往可知,孔子所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從其本來意義上看,說的正是借助《詩》的興發而達到“禮”的秩然有序,“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正是以情感作為起點抵達秩序井然而和諧融融的理想政治的存在狀態的描述。孔子的“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正是個體在政治共同體中的一種理想狀態。因而“詩可以群”以其個體性與集體性的交融對后世文學創作追求“集體性、功利性和交際功能”2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即使在強調文學獨立觀念和作家創作個性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在社會上仍廣泛存在著唱和、公宴、探題賦韻、賦得、聯句等多種集體形態。在《新民說》中,梁啟超就是以中國現有的內治和外交所處的狀況來呼吁中國“新民”的必要,“新民”的核心內涵就是以西方現代政治為模型的“公德”——群治——觀念。“小說”與“群治”的結合,正是古典詩學“詩可以群”的意義的進一步延伸,而“小說界”的建立又是小說實現其“群治”目標的必要前提。梁的小說批評理論的核心訴求在于建立小說界共同體,從而為其小說啟蒙奠定創作主體的基礎,小說界共同體的實現,又必須發揮著文學集體性的理念——也即“詩可以群”曾經所具有的歷史形態。而這一切的實現,在梁啟超所展開的啟蒙邏輯中,依賴著對于“英雄”借助其“煙士披里純”以“籠絡人心”的手段和“歷史人格者”所具有的“浸染”“擴大”的力量,群體心理成為建構小說界共同體,轉移人心風俗的必要憑借。而這也就為現代文學社會化提供了契機。從根本上言,梁啟超所建立的“小說界”,無論是其主體的中層性、內容的政治性、目標的合群性,還是其形式的共同體特征,都是中國古典“詩可以群”的政治功能的有效發揮和現代演繹。
作為古典詩教思想的“文以載道”和“文學經國”觀念,同樣化身為梁啟超啟蒙文學思想的新的形式。如他對于“中國文學”觀念的論述,其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政治性和文學最高榮譽的審美性的結合,卻由于其強烈的政治性和精英性的色彩,而帶著“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古典“文學經國”觀念的深深印記。歷來對“文學經國”觀念的理解存在較大分歧,“文學經國”觀念既被視為曹丕功利主義文學觀的體現,又被視為中國古代文學自覺的標志。如果我們拋開這種紛爭,直接從原文來理解,可以發現,曹丕提出文學可以作為“經國之大業”和“不朽之盛事”,其著眼點一方面在于改變人們視詩文為小道的認識,一方面又要強調“立言”之于一身的不朽性。但兩者都與曹丕的政治境遇具有重要的關聯。魯迅在《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與酒之關系》中,就指出曹丕倡導文學經國與不朽,正是針對其弟曹植給好友楊修的信中提到詩賦“小道”的觀點,為了警惕和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曹丕大倡“文學經國”之觀念,樹立文章所具有的“經國”的政治功績。又有學者認為曹丕意識到“立言”的重要性,只有文章詩賦才能記錄和留存其豐功偉績,因此大力鼓勵人們進行詩賦創作,以實現其“政治功績”的不朽。這兩者盡管都存在著假設猜測的成分,但是在中國古代儒家政治事功的價值引導下,不管出于何種目的,文章地位的提高都無法脫離與政治的關聯,這一點卻不得不被承認。實際上造成人們對曹丕“文章經國”觀念的認識分歧的,正在于沒有意識到曹丕“文章經國”觀念所蘊含的政治性與審美性之間的獨特結合,而試圖以或審美或功利的現代立場來衡量。梁啟超確立“精心結構”與“民族主義”相結合的“中國文學”典范,重視“中國文學”所蘊含的民族主義審美意識形態的內涵,事實上也正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所揭示的政治與美學重合的結構的體現。正如齋藤希史所言,我們從現代的觀念上斷定梁啟超的文學觀念為功利主義是失之妥當的。1梁啟超關于“中國文學”觀念的這種政治性與審美性的吊詭結合,使我們也需要對其文學觀念性質的定位進行調整。曹丕鼓勵人們改變文章小道意識,注重文章之不朽價值,從而投身創作這一邏輯,與梁啟超突出小說家的政治家身份和小說的政治價值,進而強調小說不朽性何其相似!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介紹《新小說》時對小說“藏山之文,經世之筆”的“不朽性”的提倡,不正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千年回音!
三、從儒家德性到情感詩學:
梁啟超詩文批評的思想轉化
如果說梁啟超的小說批評觀念主要是通過理論話語的建構,和以《新小說》作為陣地開展的文學變革活動來體現,呈現出鮮明的文學政治批評的取向;那么在疏離政治回歸學術和教育的生命后期,梁啟超則以“教育家”的身份,通過學術著述和講學的方式來進行文學批評,形成以情感詩學為中心的文學批評特色。《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兩篇文章批評和《屈原研究》《陶淵明》《情圣杜甫》三篇的詩歌作家論,正是梁啟超情感詩學批評的主要作品。
梁啟超后期對情感詩學的闡發,源于1918年至1919年他在歐游中對歐洲現代文明的反思。在他看來,歐洲近代思想中的“生物進化論”和“自己本位的個人主義”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推波助瀾,“科學萬能之夢”所造成的現代精神的危機是歐洲現代性文化危機的根源,只有對“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調和”和“個性與社會性之調和”才能拯救這一危機。對梁啟超而言,儒家以“仁”為核心的情感哲學思想,正是調和矛盾克服危機的精神資源。為此,一方面,他以戴震將“性”從宋儒束縛下解放出來,從而肯定人的情欲的思想為中介,對《中庸》的“盡其性”進行重新闡釋,從而打開了盡性主義所展現出來的美善合一的美學內涵,以之作為克服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沖突的精神資源;另一方面,他將人格感通視為“仁”的心理學基礎,以對“仁”的 “相人偶” 的闡釋,來實現個體人格與普遍人格的匯通,從而形成基于“仁”的情感人格感通的美學思想,以之作為調和個性與社會性沖突的美學基礎。“‘盡性主義’ 是以以情絜情的方式使個性的發展不脫離普遍德性的目標,而‘仁’的人格則以愛的人格交感的方式,通過‘感通、關切、融合的精神狀態’實現個體性與社會性的溝聯。”1在他看來,“仁”的世界的建立,是以“仁”的人格的實現為前提,而“仁”的人格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情感的作用。他認為樂教是孔子人格教育的精意,其成功就在于對藝術情感力量的重視,“就一方面看,音樂是由心理的交感產生出來的,所以某種心感觸,便淀出音樂;就別的方面看,音樂是能轉移人的心理的,所以某種音樂流行,便造成某種心理。而這種心理的感召,不是個人的,是社會的,所以音樂關系到國家治亂、民族興亡”2。因此“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就是藝術”3。在《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出來的情感》中,梁對情感與文學藝術的關系進行了集中的論述。他指出,“情感的性質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質是現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現在的境界。我們想入到生命之奧,把我的思想行動和我的生命迸合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眾生迸合為一,除卻通過情感這一閾門,別無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間一種大秘密”4。 這一論述,顯然已經超越了《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的境界超越的層面,而綜合了盡性主義與“仁”的人格的觀點,“現在”與“超現在”,“生命”“宇宙”與“眾生”的合一,是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統一,感性與普遍德性的統一。與此同時,延續對《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關于小說情感力可被善惡利用的觀念,梁在強調情感作用的神圣的同時,指出情感的本質也存在著惡與丑的方面,需要通過情感教育揚善汰惡5,而藝術作為實現情感教育的基本方式,藝術家自身人格的完善與情感的修養就顯得尤為重要:
藝術的權威,是把那霎時間便過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隨時可以再現;是把藝術家自己“個性”的情感,打進別人的“情閾”里頭,在若干期間內占領了“他心”的位置。因為他有恁么大的權威,所以藝術家的責任很重,為功為罪,間不容發。藝術家認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該知道,最要緊的功夫,是要修養自己的情感,極力往高潔純摯的方面,向上提潔,向里體驗。自己腔子里那一團優美的情感養足了,再用美妙的技術把他表現出來,這才不辱沒了藝術的價值。6
由此,梁啟超從情感教育轉向情感詩學,并在情感詩學的層面上,將藝術的價值與藝術家的人格力量聯結起來,從藝術德性人格的建構層面,形成人格—藝術—情感—形式一體的批評邏輯,從而將以美為中介,將誠的情感與善的德性統一起來。1在《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和《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中關于對文學情感及其表達方式的探討,以及對屈原、陶淵明和杜甫三作家的批評,就正是在這一邏輯下開展的。詩人“人格”與情感之“真”因而成為梁啟超情感詩學的兩個突出特征。
一方面,梁啟超以人格美作為評價詩文價值的重要尺度,如荊軻的《易水歌》和項羽的《垓下歌》是“千古不磨的杰歌”,就在于前者“把北方民族武俠精神完全表現”而后者“把他整個人格活活表現”2,同時注重通過時代和人生經歷探討作家的人格精神與其表情方法。他曾指出:“批評文藝有兩個著眼點,一是時代心理,二是作者個性。”3如對屈原的評論,就以屈原的自殺作為起點,分析屈原的人格與社會的沖突及其文學表達。在他看來,屈原是“一位有潔癖的人為情而死”,其腦中含有“極高寒的理想”和“極熱烈的感情”兩種矛盾的原素,在哲學上有很高的見解,但不肯耽樂幻想,把現實人生丟棄。他一面是達觀天地的無窮,一面是悲憫人生的長勤,因而對現實社會不是看不開而是舍不得。他認為人類道德的墮落是社會痛苦的根源,下決心和惡社會奮斗,但惡社會勢力太大,所以最后只好潔身自殺。4在梁看來,屈原性格中的這種不調和的極端性,其根源在于“屈原是情感的化身”,他對于眾生的苦痛有著感同身受的同情心5,因而他的自殺,是“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的“魄力和身分”,而這也就使其作品“添出幾倍權威,成就萬劫不磨的生命,永遠和我們相摩相蕩。”6他對陶淵明和杜甫的評論,也大體如此,如通過肯定陶淵明“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喪掉”7的精神,來評價其文學價值在于“沖遠高潔”8的人格所帶來的毫無矯揉造作地保全自然之美。9他將杜甫推崇為“情圣”10,原因就在于杜甫不僅是一位極熱腸,富于同情心的人,也是最能寫情的人。11在梁啟超看來,杜甫《佳人》中那位身份名貴、境遇可憐、情緒溫厚、性格高亢的佳人,正是杜甫人格的象征。12從梁啟超對屈原、杜甫和陶淵明的創作人格和藝術人格的評論可以看到,注重歷史社會與詩人人格的互動、強調藝術人格的審美價值和道德價值的統一,正是梁啟超詩文批評的方法和取向所在。
另一方面,注重從藝術情感的真實自然的層面,來評價藝術家的表情方法、創作個性及其藝術價值。在梁啟超看來,“情感越發真越發神圣”13,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序》把其“求官、棄官的事實始末和動機赤裸裸照些出來,一毫掩飾也沒有”,是其人格最忠實的表現,這樣的人才是“真人”,這樣的文藝,才是真“文藝”。1在他看來,寫實的作品必須遵循“真事愈寫得真,真情愈發得透”的“真即是美”的道理2,但這并不意味情感的抒發必須一覽無遺,這是因為人類對某種社會現象的批評有共同的心理,“作家只要把那現象寫得真切,自然會使讀者心理起反應。若把讀者心中要說的話,作者先替他傾吐無余,那便索然寡味”3。如杜甫的純寫實詩作《麗人行》,雖不著議論卻完全是情感真摯的文學,比白居易的《新樂府》高出一籌。而對于想象的作品則需要能“從想象力中活跳出實感”才能算極文學之能事4,比如屈原的創作之所以是“有生命的文學”,在于其不僅想象力豐富瑰偉,也在于其情感真切自然5。在梁啟超看來,研究一位文學家的個性就要在他作品中獲得“不共”和“真”兩種條件。“不共”是使作品完全脫離模仿的套調,而“真”則使作品絕無一點矯揉雕飾,能把作者的實感全盤表現,而不是涂脂抹粉把真實面目隱去。6這種認識,實際上與王國維的“不隔”具有相通之處,借用葉嘉瑩對王國維“不隔”的“真切之感受”“真切之表達”7的定義,梁啟超對情感的“真”的要求,同樣是從情感的內涵與表達兩個方面著手。但要注意,梁的“真”的情感,從情感教育而言,既指個體情感的自然之真,還指不“私”、不“偏”的德性情感,這就與王國維稍微不同。屈原、陶淵明、杜甫的人格與情感,正是這樣一種德性情感,他們對社會的惡濁極為痛苦,并進而反抗,追求生命的自由與正義,追求社會的公平與合理,追求與自然的融合與默契。因此,這里的真就是善與美。它是梁啟超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也即是“盡性主義”與“仁”的人格。情感教育與人格教育在本質上也就同一,因為真的情感、善的人格與美的文學,在這里不再存在功能與目標的差異。正如對戴震的“以情絜情”、孔子“仁”的人格交感的闡釋一樣,以文學進行情感教育,情感相通,人格交感,個體性與社會性的調和也就自然完成。
結語
臺灣學者柯慶明在《梁啟超、王國維與中國文學批評的兩種趨向》一文中,指出“梁啟超之于言志傳統;王國維之于神韻傳統,都能以其各人獨到的豐富廣泛的文化學術背景,迎接西方思潮的刺激,對于上述兩大傳統,作了承先啟后,踵事增華的發揚”8。他將梁啟超的文學批評方法概括為“歷史傳記法的文學批評”,并將之視為對《毛詩序》詩歌批評傳統的傳承與發展:
利用歷史傳記的背景本事解詩,在中國自是肇始于《毛詩序》,而所謂“影響說”其實正是亦正是“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等等主張的變象發展;此外梁啟超文學觀念之核心的“情感”理論,基本上亦是“詩大序”的:“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啖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的主張,因此我們確實可以說梁啟超的文學批評其實是“毛詩序”的各種主張精益求精的發展,因此就是“言志”傳統的近代型態。1
通過梁啟超后期詩文文學批評的“情感”論與中國傳統“言志”詩學之間的發展,正可以看到梁啟超文學批評與中國古典詩教傳統之間的深刻關聯。只是這種關聯,除了《詩大序》的“言志”傳統之外,實際上也是對儒家“盡性主義”與“仁”的德性人格思想的詩學轉化,并因此作為一種德性情感應對現代文化所引發的精神危機。而這正是梁啟超從前期小說批評話語對于以國民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想象與召喚,向后期以情感詩學的批評實踐來拯救現代精神危機的取向的轉變。梁啟超文學批評對古典詩教傳統的話語轉換和思想轉化,正是基于這種對中國文化現實的深刻關切。梁啟超對中國古典詩教話語的現代批評轉化,既是其時代與個體的文化語境使然,也正是其在“新民”的啟蒙思想背后的深刻的文化主體性意識所帶來的批評話語的選擇的結果。對“新小說”與“新國民”的召喚并沒有讓梁啟超拋棄傳統,而是在對文學歷史的重構中重建中國古典文學的新傳統;對歐洲精神危機及其調和的動機,使梁啟超重新發現了中國儒家思想及其情感人格的獨特價值,進而將其轉化為文學批評的詩學話語。盡管梁啟超的文學批評并沒有簡單地挪用中國文學批評的古典概念,卻反而能夠深層次地觸及中國古典詩教與詩學傳統的文化思想內涵,并在其“新民”的啟蒙目標與古典“詩教”之間完成了一種話語的傳承與轉換。梁啟超文學批評的古典轉換及其主體追求所蘊含的豐富經驗,對于今天我們重新反思古典文論的現代價值、探索中國文學批評話語的現代轉換,以及構建中國文學批評的話語體系和學術體系等,都具有重要的啟示。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