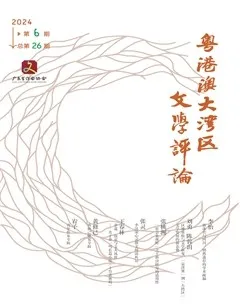兒童、 親屬與愛欲
摘要:魏微善于書寫傳統的家族親情、血緣倫理,在“70后”作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其作品既富有明晰的時代感,又有著鮮明的性別意識。她善于從女童及少女的視角出發,揭示一個特殊時間段內中國式家庭內部的性別秩序與運作模式,聚焦于身處其中的“女兒們”所遭受的生理及心理創傷。在講述個人的記憶、經驗、情緒的同時,也嘗試容納更多的歷史、時代信息,在一個寫作日益“私人化”的時代,致力于開拓更為深遠的社會/歷史想象空間。
關鍵詞:愛欲;時代;家庭模式;親屬關系
身為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魏微成名于20世紀90年代。千禧年之后,其作品愈發成熟,逐漸形成獨有的風格,在70后作家群體中獨樹一幟。她并不注重豐富生動、引人入勝的情節與故事,而是刻意營造一種情緒或心境,在文本世界中建構了一個憂郁與沉思性主體,帶有強烈的主觀情感。她的代表作在平實沖淡的表象之下,往往有著反潮流的叛逆沖動,有條不紊地拒絕了一系列既定的敘述模式。在同時代的其他作家衛慧、綿綿、周潔茹、朱文穎等刻意彰顯,放大頹廢、時尚、縱欲的后現代生活樣態,與市場、消費主義文化合流之時,身在其中的魏微反倒回過頭去打量自己的“來路”——鄉村、小鎮、小城,這逐漸構成她重要的文學空間。在其作品進入成熟期后,還凸顯出某種反全球化的意義與價值。從都市到小城、鄉村再回到都市,當年寫出《煙霞里》的魏微,早已蛻變為一個資深作家。但不變的是她對于物質生活與日常經驗的執著,以及對于人性及愛欲的深入揭示,尤其是對于家鄉、鄉土、親情的眷戀與執念。在時代的再現這一方面,魏微并不追求歷史深度與時代本質,而是帶有很強的自我意識與理性反省的精神,用飽滿豐盈的情感與思想,寫下屬于個人的經驗與記憶的世界,由于敢于直面世界和生命中那些敏感、尖銳、曖昧的痛楚,其作品往往顯得愈發豐厚、深邃而迷人。
一、兒童的性
作為70后女作家群體中的代表性人物,曾被貼上“美女作家”“新新人類”等標簽,魏微早年的作品《一個年齡的性意識》《喬治和一本書》明顯體現出彼時新銳作家的先鋒追求,技法與想法都有著符合讀者期待的摩登奇巧。雖然篇幅短小,卻另辟蹊徑,顯示出決意走出一條屬于自己道路的創作自覺。《喬治和一本書》以清醒的反諷,決意與米蘭·昆德拉所代表的“他人的話語”保持距離,這在20世紀90年代“千禧年資本主義”的氛圍中,體現出極其難能可貴的自尊、清醒與矜持。《一個年齡的性意識》處理的則是與當時風靡一時的“女性寫作”“身體寫作”間的關系,同樣具有某種“宣言”的性質。魏微寫她剛剛走上文學道路之時所遭遇的巨大困惑時描述到,“對于我們不熟悉的性,真實有太多的話要說。……寫著寫著,就趴在桌邊,想嘔吐,覺得不該那樣,人無論如何也不能那樣。性成了一種支柱,甚至不能不寫。1”那些不得不寫的“性”,那些不斷翻空出奇的性描寫,構成了對于“我”與小容這一代女性寫作者的壓力與壓抑,形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影響的焦慮”。聯系到“講述神話的年代”即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美女作家”構成怪誕且沸騰的文化事件之后,似乎只要身為年輕的女性寫作者,就不能不寫性,甚至于將身體與隱私包裝成奇觀,在消費社會中供人(尤其指男人)獵奇與消費。所謂先鋒時尚、另類新潮的背后仍然不過是老舊陳腐的性別邏輯與欲望結構。
經過深思熟慮與自覺反思之后才開始從事創作的魏微,在下筆寫性之時,該有怎樣的場面呢?作為一個敏感、多情、性別意識鮮明的女性,魏微的寫作并不回避性描寫,但較之前輩女作家林白、陳染、海男、趙枚,及同為70后“美女作家”的衛慧、綿綿、周潔茹、金仁順等,她并不特別熱衷于寫性,甚至是有意與旗幟鮮明的“身體寫作”保持距離,將作品中涉及情欲與性的部分故意寫得素凈寡淡、王顧左右。與其說這是有意為之的“叛逆的叛逆”,不如說魏微要探討的“性意識”有異于通常意義上的欲望想象,比如早熟孩童的性沖動、異性親屬之間微妙的性意識,這些才是她所熱衷于探索的疆域。可以說,這些雖不“時尚”但真正特殊、另類的“性描寫”貫穿于魏微的創作脈絡,甚至成就了她最為優秀的作品序列,如《在明孝陵乘涼》《石頭的暑假》《鄉村、窮親戚和愛情》《姐姐》及長篇代表作《一個人的微湖閘》。
《在明孝陵乘涼》是魏微的早期代表作,開始涉及兒童的性想象及親屬間性心理。小說講述一個成長于南京城的女孩,在盛夏的某一天,與哥哥、好友同游明孝陵時偶然萌動的性意識。明孝陵象征的晚明王朝墮落淫逸的氣息,關于妖冶魅惑、明艷動人的“妃子”的想象令尚處于幼年期的女童心神蕩漾、不能自已,而她性幻想的第一個對象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親哥哥,同行的女友百合則扮演了“情敵”的角色。在十二歲女孩的想象中,南京城是一個奇妙的地下迷宮,“情欲”與“墮落”是這個城市最為寶貴的品格,它輝煌的過去就是積累了幾千年的“性傳統”,而成為一個擁有妖嬈曲線、鮮明性征的身體的主人,一個真正的南京女人,成了少女小芙氣宇軒昂的性宣言。但在文本中旋即毀掉這一切、終結了她美妙生澀又華麗復古的初戀體驗的,則是年輕顢頇的母親一頓毫無來由的侮辱性暴打。在這個頗受歡迎的小短篇中,纏繞并貫穿魏微文學世界的諸多命題都出現了:早熟孩童的性意識與性沖動,投射于家族內部男性成員的欲望,對于血緣親情帶有亂倫想象的迷戀與憎惡,等等。
到了更為成熟的作品《一個人的微湖閘》,作者用整整一個章節的篇幅重新講述了“兒童的性”這一主題,也就是“性的童年”。因為背景放置于江淮之間的小鎮,刪除了《在明孝陵乘涼》中故作風流的浮夸艷異,故而顯得真實細膩、質樸感人。不得不說,寫作《一個人的微湖閘》時的魏微身在其中,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她自幼熟識的,在這個自成一格頗有時代感的小世界,魏微從容地展開為她所關注的文學及人性的主題——兒童的性。“性的童年”中的主人公,早熟的小橘子,只有五歲就習慣于“自娛”,當同樣年幼的“我”撞見她手淫的一幕時,恍若瞬間窺見了“另一個世界”——那是隱藏在具體實在、浮在表面之上的日常生活背后的陰暗角落,一些恐懼著被外人發現的“齷齪的小秘密”。當成年后的敘事人用弗洛伊德的性理論冷靜理性地審視當年那個過分早熟的女孩,感覺到的卻是鋪天蓋地而來的深刻悲憫、憂傷與同情:
我只想告訴你,在孩童的世界里——在某一類孩童的世界里,你可以看見色情和欲望。如果你細心察看,你肯定看得見的。也許在很多年前,你也曾經是這樣的孩子,你受過它的壓迫。你的整個童年黑暗而陰沉,就因為你受過壓迫。那是身體的壓迫,也是快樂的壓迫。
快樂來得早了些,它在你小小的身體里攪得你不安寧,它超過了你那微小的肉體的負荷。你被它壓垮了。你開始覺得這是在犯罪,犯罪感與日俱增地生長在你的體內,它超過了你,它曾經是你的全部,是不是?
你也許覺得,比起那沉重的犯罪感來說,身體的快樂簡直不算什么。它來得如此艱難,也不是時候,總之,你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它簡直要了你的命1。
敘事人用這樣推心置腹的語氣與讀者交流,她迫切地想讓我們明白,那些過早地體會到成人性歡愉的孩童,其實是非常不幸的,因為她要面對與生俱來的羞恥心與犯罪感,而她尚且混沌的心智無法解釋這一切,她還沒有能力為自己的欲望辯護,只能任由毫無頭緒的沖動與隨之而來的壓抑、恐懼吞噬自己尚不充分的活力與生命。但敘事人進而思考,對于那么小的孩子,由性所產生的羞恥感真的是與生俱來的嗎?對于這個問題的思索與追問,構成了寫作者文學創作重要的心理動因:“我不知道羞恥感從何而來,黑暗將把人帶向何方?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后來寫小說了,我猜想,小說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我仍然以為,這是構成我日后寫作的一個重要原因。”2不難發現此處進行的仍然是《一個年齡的性意識》中所延續的思考,即對于20世紀90年代以林白、陳染為代表的女性“私人寫作”“身體寫作”潮流的反思與拒絕。文本中被寫作者刻意設置為“他者”的潛文本無疑是林白的代表作《一個人的戰爭》:“在很多小說里,我看不到這個‘原因’,看到的只是一個女人,在她的童年時代,對自己的身體進行頂禮膜拜。看到的是在一件黑暗的小屋子里,她就要開始致命的飛翔了。看到那些淋漓盡致的場面,怎樣從我們的眼前一頁頁地被翻過。看到對自己隱秘的熱愛和渲染。”3敘事人對于《一個人的戰爭》所代表的女性“身體寫作”思潮的批判,與早年間對于《喬治和一本書》中表達的批判意識一脈相承,即那些看似時尚、先鋒、后現代的表達,實際上早已迷失在他人/西方的強勢話語中,錯把他鄉作故鄉,可悲到連情欲都不是自己的,而需要模仿甚或抄襲他人/西方。同樣,從以《一個人的戰爭》(林白)、《我們家族的女人》(趙枚)等為代表的各種女性自傳體寫作中不難分辨出法國女作家杜拉斯《情人》的影子,或者說《情人》是20世紀90年代流行的“女性寫作”思潮重要的潛/前文本。而文學風格一向低調溫厚的魏微不動聲色地用《在明孝陵乘涼》告知人們,打破少女小芙白日夢與性幻想的,是來自母親無情的巴掌;《父親的來訪》中,讓小玉無法充分享受都市單身女性的性自由的,是無所不在的“父親的聲音”,是對于“父親的來訪”的莫名恐懼與超強戒備——父親與母親共同監控著女兒的身體,時刻管理與約束著她的欲望。東亞父權制社會下的女兒們,早已內化了無所不在的管控與監視,她的身體與情欲早已不屬于自己,而屬于“愛”她的父母。魏微冷靜、理性且憂傷無奈地告之她的讀者們,那個由杜拉斯創造的、浪漫自由、桀驁縱情的法國少女形象只是一個白日夢,并不適合于東亞父權制與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相交織的土壤,這里有的,只是已長成和尚未長成的“良家婦女”。
于是敘事人用既理性克制又溫柔多情的聲音告訴讀者,她拒絕將凡夫俗子的性升華為酣暢淋漓的“致命的飛翔”,拒絕對性做任何詩意化的描寫,因為那不過是凡人的快樂,能有多么大不了呢?更何況,她要讓讀者關注“性”背后的東西,那并不是通常所以為的激情與快樂,而是“悲傷”。《石頭的暑假》就是一則關于性與欲望的最為悲傷的表達,一則“洛麗塔”式的性及人性的悲劇:一個處于青春期的俊秀少年被一個早熟、精靈般的女童吸引,犯下了“強奸”的可怕罪行,夏日的沖動毀掉了兩個花樣的生命。故事的女主人公夏雪就是另一個小橘子,一個只有八歲的“小女人”,一個充滿性意識與焦慮感的女童。對于某些人或某類人來說,她的吸引力是致命的,她喚醒了俊秀干凈的十七歲少年內心的野獸,誘發了可怕的罪行。這樣一個關于性犯罪、畸戀、禁戀的主題,讀來卻并沒有半點聳動、獵奇、露骨的描寫,文風仍然一如既往地低調平實,滲透著淡淡的詩意與憂傷。在善良傷感的敘事人看來,少年和女童之間宿命般陰暗兇險的交纏,其實也是一種“愛情”,只是過早地發生了,就像“性的童年”中小橘子過早發生的性欲,只能帶來黑暗、陰沉、驚悚的壓迫,最終導向無可彌補的消耗與死亡。文本中最有意味的是敘事人身份的設定,它決定了整個故事的基調與走向:“我”是一個暗戀著石頭的小城少女,透過她憂傷、落寞、失意的語調,在傳達出對整個事件的關切、理解、同情之外,流露出失戀少女無盡的感傷、尷尬、痛楚與不甘。這一切決定了《石頭的暑假》不是一個西方化的、洛麗塔式“不倫之戀”的拙劣模仿,如同衛慧的《黑夜溫柔》,而是一個中國小城現代化進程中一則悲傷的“愛情故事”。
二、親屬的“愛”
可以說,在寫性這一層面,魏微走出了自己的路,她看似保守溫和,實際上她所直視、觸摸進而開掘的領域比之叛逆的女性前輩們更加大膽:兒童的性意識與性行為,親屬之間包括叔侄、父女、姐弟之間的“男女”之情,都在其鋪排渲染的瑣碎日常細節中緩緩呈現,在波瀾不驚的講述中暗潮洶涌。可以說,對于中國式家族及家庭關系的深入開掘,對于異性親屬關系的情欲化想象,在這一層面,魏微可謂獨樹一幟。一旦涉及親情、家族、血緣,魏微作品中的筆觸就愈發敏感細膩、百轉千回,比如《鄉村、窮親戚和愛情》《一個人的微湖閘》《家道》《姊妹》,而與之相比,那些純粹寫陌生男女的都市戀情篇章,如《情感一種》《化妝》《蟑螂,你好嗎》反倒顯得過于單薄。《情感一種》與《化妝》中看似時尚的都市女性,在情愛爭逐的過程中,卻始終囿于市場經濟的“賺賠邏輯”,她們看似多情、大度,實則一直在理性且緊張地權衡考量,最終反倒血本無歸。然而一旦面對親情,魏微筆下的女性卻表示可以毫無保留、不計成本地付出與犧牲,她們似乎將親情當成了“愛情”。或者說,在她們看來,親情屬于廣義上的“愛情”,是一種更為深入肺腑、傷筋動骨的聯系:“……我對家族情緣是很敏感的,我的性別意識也很濃厚。有一點是真的,那就是我愛他們,我是把自己當作一個女性,而不僅僅是他們的孫女、女兒、侄女和姐姐。或者說,這兩種愛是混雜的,它們緊密地絞在一起了。我只是分不清它們。”1
但是綜觀魏微所有的作品,不難發現其筆下的父女關系是異常緊張且尷尬的,在《姐姐和弟弟》《在明孝陵乘涼》《一個人的微湖閘》《煙霞里》等作品中,她用傷感的散文筆調,詳細描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小城鎮中典型的家庭模式與親屬關系。那個時代的父母對于子女的教育極其簡單粗暴,甚至對于青春期的女兒也是動輒打罵、罰跪,美其名曰“棍棒主義”:“他們打我,用棍棒,用鞋底,用剪子和刀。他們打我,曾經抽斷一根皮帶。”2這樣來自至親的、頻繁的暴力嚴重損毀了少女的自尊,毀掉了她對于浪漫情愛的憧憬,被迫開啟陰郁、暴力的成長史,逐漸成長為一個冷漠、擰巴、暴戾的少女。她青春期常做的噩夢,是與拿著菜刀的母親仇恨地對峙,是發現與素來并不親近的父親睡在一張床上。并且當她容忍并習慣了來自父母的暴力之后,轉而開始了對弱小弟弟的持續性暴力輸出。這就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小城小鎮中常見的家庭模式與親子關系——外表是現代的核心家庭,由父親、母親與未成年子女組成,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小家庭”,但其與傳統親屬關系網絡仍然聯系緊密——鄉下的“窮親戚”經常進城,七大姑八大姨走動頻繁,爺爺奶奶也會過來同住。且雖然是現代性與城市化的產物,“小家庭”卻并沒有任何寬容民主的氛圍,父母仍然擁有絕對的權威,教育方式粗暴隨意,將“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封建糟粕奉為圭臬。套用毛尖老師的說法,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式原子家庭,究其實質是“半封建半社會主義”的樣式。而魏微對于當代城市文學的貢獻,也許就在于她用文字的形式為中國式“原子家庭”的“父權”本質做出了真實詳盡的文本記錄,猶如一冊業已發黃但珍貴的影集,因而具有某種“文獻”“檔案”的社會學價值。
從這個角度,可以將魏微的作品序列理解為一部特定時期的家庭史及成長史,其中《一個人的微湖閘》《煙霞里》這樣準自傳式的、關于女性成長的小說,既富有明晰的時代感,又有著鮮明的性別意識。魏微從一個女童及少女的視角出發,揭示出這一特殊時間段內中國式家庭模式內部的性別秩序與運作模式,聚焦于身處其中的“女兒們”所遭受的生理及心理創傷。“半封建半社會主義”式的家庭模式究其本質仍然是父權制的,雖然社會主義的“男女平等”保證了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與受教育的權利,但家庭對于女兒的身體、性及純潔的要求與管控仍然延續了前現代宗法制家族的諸多傳統與規約。那些或明或暗、五花八門的規矩包括但不限于:父母對于絕對服從的苛求及暴力的身體規訓,奶奶悉心傳授的專為女孩們訂下的規矩,弟弟對于姐姐身邊出現的所有異性充滿敵意的防范,叔叔伯伯當著女孩的面與弟弟開著男人們才能懂的玩笑……《姐姐》中尚處于幼年的弟弟對于剛剛出落為少女的姐姐全天候、無死角的監控,對于姐姐身邊出現的所有異性的“天然”敵視,令人忍俊不禁之余又有點細思恐極。那些看似純然自發的行為,不僅僅是“血濃于水”的親情與天性使然,父系家族對于女性身體的監管與控制實則體現于稚氣未脫的小男孩那些霸道的舉動中——守護家族女性的身體與貞潔,已經成了家族男性的本能。
在這個意義上,魏微早期的一部并不起眼的短篇《父親來訪》,在其作品序列中其實有著特殊的意義與價值。故事的主人公小玉是一個成年女性,如同《一個人的微湖閘》中經歷了漫長痛苦的青春期,終于長大成人的“我”,開始了少女時代夢寐以求的獨立生活。她一個人生活在大都市南京,自由地享受物質生活和浪漫愛欲,卻在收到父親來訪的消息時瞬間陷入崩潰,在那一刻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從未“長大”。因為經歷了長期被高度管控的生活之后,壓抑已經被小玉深刻內化,自由早已是杳不可及的夢幻,而“父母”則成為她享受浪漫愛與性自由的最大現實及心理障礙。中國式父母那種專制暴戾的“愛”,家庭成員之間既緊張沖突又毫無邊界感的相處模式,使得身處其間的女兒們喪失自我,并逐漸高度內化了父權的規則,被打上了“好女兒”的思想鋼印,然而,一個好女兒注定是“規矩的”、無性的。童年時期被壓抑的性沖動,青春期的陰暗與痛苦,與父母關系的持續緊張與暴力沖突,這似乎構成了魏微小說世界中所有女兒們的共同處境。與其說這是女性成長的主題,不如說始終是關于無法成長的困惑、痛楚與迷茫——女兒終其一生無法成長為一個擁有性魅力的女人,一個在心理上獨立成熟的現代女性。那些被迫中斷的成長,無處安放的欲望,只能繼續投射到家族內部男性成員身上,轉化為對傳統父系家族血緣的迷戀與忠誠,這也許并不是成熟與寬厚,而只是一種被馴化后的無力與無奈。
于是出現了《一個人的微湖閘》中“我”與叔叔的故事,“我”對于叔叔復雜的情感,暗示出親情、美德與情欲之間雜糅交織的復雜狀態。年幼的寫作者最為中意的,就是家族里年輕俊秀的男性長輩——“叔叔”,他“挺拔、倜儻、面容姣好”,性情“敏感、內向、脆弱,骨子里很羞澀”。作為異性后輩,敘事人對他的癡迷,不僅僅是對于父系家族血緣的崇拜,還有對一個富有魅力、“清朗”迷人的異性的欣賞與暗暗的渴慕。通過對叔叔稱不上悲劇的愛情故事的細心跟蹤與記錄,“我”最終要告訴讀者的,卻是“我”與叔叔之間微妙的、超出親屬關系的情感。為了表現青春期時的“我”與叔叔的“愛情”,“我”講述了幾件關于和叔叔相處的小事,比如被叔叔發現生理期時的尷尬,母親當著叔叔的面拿出給“我”新買的內褲時“我”微妙的內心活動,和叔叔單獨相處時兩個人同時感受到的難堪等等。不過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瑣碎小事,敘事人也承認她并沒有把真正重要的說出來,那些復雜的、隱晦的情感都被隱藏了,給讀者看見的,只是冰山一角,“那最難以述說的部分永遠在水下,外人是看不見的”。那“難以述說”的究竟是什么?如何辨認出其間受壓抑的欲望?敘事人在講述“我”與叔叔的故事之前,再次用了很長的篇幅敘述自己叛逆的青春時代與父母激烈暴力的關系——他們強行施加于“我”身心上的創痛,她難堪、陰郁、暴烈的成長史。所以她需要在回憶中一次次回到微湖閘,回到與爺爺、奶奶、叔叔一同度過的安靜平和的時光,以此治愈核心家庭帶給自己的創傷。所以,其后敘事人所詳盡描述的對于年輕俊美、溫柔隨和的叔叔的愛慕,是出于對傳統父系家族血緣的迷戀,還是少女對于年長、有魅力異性的暗戀?這也許隱藏著更深層次的原因,只是對于一個更為理想、溫和、善解人意的“父親”形象的期待與想象,對于一種更為合乎人性與理性的現代家庭關系的向往與希冀。
三、愛欲/時代
魏微的小說具有散文化的傾向。相比于制造戲劇性沖突,她更加善于捕捉、渲染、營造一種情感環境與情緒狀態,并總是試圖捕捉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的氣息與“靈韻”。她對于歷史時間的沉浸式體驗,對于內心情感生活的細膩感受,展現了一個始終在追憶與回憶的主體。這個寫作主體有著憂郁、善感、多情的精神氣質,極度飽滿充盈的情感容量,同時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擁有張愛玲式的用文字定格時間的能力。最難能可貴的是,她講述個人的記憶、經驗、情緒,用文字縫合個人心理傷口的同時,也在嘗試容納更多的歷史、時代的信息,在一個寫作日益“私人化”的時代,致力于開拓更為深遠的社會想象空間。
《大老鄭的女人》是魏微“小城系列”作品中的第一篇,她以個體化的語言和富有情感的意象,傳達出一個時代具有普遍性的氛圍與氣息。改革開放初期的江蘇小城,民風依然淳樸,人們仍然過著簡單、閑適、有規律的生活。但時代畢竟已經不同,漸漸地熱鬧繁華,改革、下海、開放、沿海,已經成為人們的口頭禪。溫州姐妹開了“廣州發廊”,給小城先帶來了一場審美及觀念的革新,然后又帶來了風俗倫理的變革:她們“白天做女人的生意,夜里做男人的生意”,賺得盆滿缽滿。如此地傷風敗俗,小城里的人們卻一笑置之,畢竟他們認為“現在都什么年代了,這事在廣東那邊早盛行了”。溫州姐妹離開之后,卻又冒出了溫州發廊、深圳發廊……人們對這早已見怪不怪。在這樣的氛圍中,外地人大老鄭出場了,作者為他的出現做足了鋪墊,這鋪墊就是時代氛圍。來自莆田的大老鄭在小城做生意,因不堪寂寞,遂找來一個當地女子作“外室”,這原本是一樁不那么體面的風流事,然而,透過敘事人涉世未深的眼睛,讀者看到的卻是歲月靜好、現世安穩——一對“野鴛鴦”將小日子過得有聲有色,且逐漸生出相濡以沫、舉案齊眉的情義來。直到有一天女人的鄉下“前夫”找上門來,這樁“尋常情事”才暴露出不堪的底色,這令人沉迷回味的“歲月靜好”原本不過是“暗娼”的一樁生意。然而對于還是孩子的敘事人來說,大老鄭和那個女人卻是一段美好歲月的見證人,“那是怎樣安寧純樸的時光啊,像我們幻想中的莆田的竹林,在月光底下發出靜謐的光……”為敘事人懷念的其實是那樣一個轉瞬即逝的時代,一個依然“單純、潔凈、古老”,又充滿希望與活力,預示了無限可能與巨大潛力的時代。作者特意標記出了那個年代——1987年,那是改革開放初啟時分的歷史段落,大規模的物質匱乏、嚴酷的政治動蕩已成過去式,逐漸被人們淡忘,一個新時代緩緩拉開帷幕,一切都充滿了希望,一切都還“剛剛好”。經濟體制改革、政企分開、個體經營、鄉鎮企業這些新名詞聽起來還是那樣激動人心,而彼時現代化仍是一個面目不清的巨大召喚,現代性及發展主義尚未顯露出其猙獰的另一副面孔。對于那個逝去時代、那一個“歷史瞬間”無限地依戀與深深地緬懷,使敘事人時刻沉浸在一種懷舊的感傷氛圍中,而敘述語調的依戀憂傷背后是一種政治文化潛意識的流露。
從《一個人的微湖閘》開始,到《大老鄭的女人》《回家》《異鄉》《鄉村、窮親戚和愛情》,寫作者顯示出以特殊的情愛故事抓住一個時代神韻的能力,文本在描述個人情感生活的場景之外,隱隱顯現出歷史與時代的縱深。無論是微湖閘,還是“小城系列”中的“小城”,“風景”里都蘊涵著一個時代中可以稱之為奧秘的東西。新的時代產生了欲望的新形式與新表達,而這一切往往透過一些原本傷風敗德的情事表現出來,這種表達方式總能產生深刻雋永、落葉知秋的藝術效果。《一個人的微湖閘》以一個出軌女人楊嬸的故事貫穿始終,她的形象生動、鮮明、飽滿,充滿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代感,同時又有著超越時代的獨屬于女性的特質。在幼年的“我”看來,楊嬸是微湖閘的靈魂人物,她有著站長夫人的特殊身份,她是微湖閘公認的賢妻良母,她經營的小家庭成為水利局職工群體中的“樣板”,她身上的安穩、和諧、生動是歲月靜好最為貼切的注釋。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物,卻在五十歲的年紀選擇與人私奔,對象竟是一個極為年輕的男子。楊嫂這驚世駭俗之舉不僅毀了自己的安穩人生與完美人設,毀掉了自己苦心經營的家庭與子女的前程,同時還打破了微湖閘整體的氛圍與內在的平靜——一種曾與她同在的光陰、秩序與生活。在敘事人看來,她的私奔帶走了一個時代,一個雖然不夠富足但安穩平靜,滲透著暖老溫貧的氣息的時代,一個遺留著經典的社會主義大家庭氛圍的時代。對于楊嬸的“變節”,文中其實早已設置伏筆,草蛇灰線,八十年代初期,改革開放的步伐已然加快,楊嬸不滿意大女兒門當戶對的男友,原因是對方“太過老實”。面對前來勸說的奶奶,她振振有詞:“奶奶你不知道,現在老實人不吃香了,人還是要靈活,能闖蕩,見風使舵,這樣才吃的開呢。像我們家老楊,就吃虧在這里。”1聰慧的楊嬸已經感覺到時代的風向,察覺站長夫人的光環開始黯淡,丈夫所擁有的鐵飯碗、固定工資、國家干部的身份,已經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了。她的墮落,并不僅僅是因為非理性的情欲,也是因為聰慧、敏感與虛榮,她敏銳地察覺到了時代的變化,發現曾經珍視的一切突然之間喪失了吸引力。所以文本中楊嬸的出走,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預示著一個“純真年代”的終結,預示著一個充滿活力卻縱欲敗德時代的開啟。
作為以《一個年齡的性意識》走上創作道路的女性作家,魏微卻刻意與“性”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她避免露骨地寫性,不負責任地詩化、升華性,她所擅長的,是書寫愛欲。而在資本主義制造的消費社會,愛欲被簡化成了性,“身體”也逐漸脫離埃萊娜·西蘇意義上的反父權色彩,墮落為純粹的色情商品。從哲學的角度看,愛欲究其本質,是與他者之間的關系,是承認他者身上那些不可化約、抹殺的異質性,同時承認自己的無能為力。從這個角度看,代表作《鄉村、窮親戚和愛情》講述的就是在現代都市的語境中逐漸迷失自我的“自戀主體”重新尋找到愛欲能力的故事。“我”出身小城,根系來自鄉土,成年后進入大都市,成為富足精致的中產階級,合格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人,純粹的、分子般的后現代個體。“我”曾經將“未來”視作一切,拼命否定并要堅決消滅自身的“過去”,斬斷與鄉土和窮親戚的所有關聯。久而久之,“我”成了一個典型的自戀主體,對于自戀者來說,力比多都被投注到自我的主體世界,完全感受不到他人身上的差異性,在任何時空中能被一再感知的只有“自我”2。“我”身處的資本主義化的大都市,愛情被馴化成一種即時的消費模式,在欲望爭逐的陷阱中自我消耗,逐漸喪失了正常的知覺與感官,陷入精疲力竭的憂郁狀態,而借助傳統的“遷葬”禮儀,“我”得以重新進入鄉土世界,開始反省自己“無根”的漂泊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我”與表哥看似莫名其妙的愛情,其實是自戀主體自我拯救的表現——“我”要將自我從已經開始彌漫的“憂郁”的牢獄中解救出來,因為愛欲與憂郁是相互對立而存在的,“愛欲將主體從‘自我’世界中拉扯出去,轉移到‘他者’世界”1,它要求突破納喀索斯式的致命的自我封閉。也就是說,“我”對于鄉下表哥突然之間產生的情愫與愛意,不僅僅是某種“尋根”及回歸鄉土的文化隱喻,更是試圖重新與世界、與他人建立起真正的聯系。敘事人在那一瞬間的欲念涌動,是業已麻木的感官重新恢復知覺的時刻,而重新感受并擁有自我,就是來自他者的珍貴的饋贈2。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窮親戚和愛情》是一部非凡的小說,有著以愛欲反都市資本主義的桀驁氣質。
對于魏微來說,用一些普通男女的風流韻事,捕捉一個時代的隱私與秘密,發掘時代中蘊藏的經驗,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反思、闡發潛藏的個人記憶,也是一種介入現實的有效方法。身為70后,作為后革命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們曾自覺放棄了關于整體性的浪漫憧憬與追求,但魏微的記憶卻扎根于特定的歷史、時代及地理環境,顯示出一種與眾不同的尋求連續性、共同歸屬感與身份認同的努力。用蓋爾納的術語來闡釋,她是在用一種“浪漫-有機的”視野反抗全球化時代的“個人主義-原子式的”生存方式,但其筆下浪漫主義與有機感的表達不僅來自一種前現代的鄉土倫理,也內在包蘊著對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社會主義時代氛圍的懷念,及改革開放初期彌散于整個社會的理想主義的歷史記憶,正是多重的歷史經驗與記憶構成了魏微這樣一個寬容平和又始終在反省著的敘事主體以及與之相應的時代特征。
作者單位: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