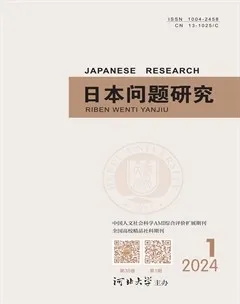日本建構(gòu)“先住民”概念的實踐及其影響
摘要:20世紀(jì)90年代末,“先住民”概念在日本的建構(gòu)以及廣泛傳播是日本土著民族阿伊努人的人權(quán)與自由、文化與傳統(tǒng)等權(quán)利逐漸被納入其國內(nèi)法保護(hù)范疇的過程。“先住民”作為在承認(rèn)文化多樣性的國家和社會里被承認(rèn)和尊重的獨立的民族文化共同體概念,與以彰顯大和民族的獨立性和優(yōu)越性為目標(biāo)的“原住民”概念相比具有進(jìn)步的一面。日本構(gòu)建“先住民”概念的根本目的,是在國家認(rèn)同嚴(yán)重受到全球化進(jìn)程浸染的現(xiàn)代背景下,以重構(gòu)多元文化認(rèn)同來實現(xiàn)國家認(rèn)同的增強(qiáng)。
關(guān)鍵詞:日本;先住民;多元文化共生;國家認(rèn)同
中圖分類號:G13/17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1004-2458(2024)01-0051-09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401006
引言
就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不能單一地存在與發(fā)展一樣,人類社會也不能同質(zhì)地存在與發(fā)展,每一種人類文化都有存在的價值和權(quán)利。國際人權(quán)法一貫倡導(dǎo)保護(hù)文化多樣性和文化平等,并將其理論反映在文化多元化制度與政策上。“Indigenous"Peoples”就是國際人權(quán)法在20世紀(jì)80年代末為保護(hù)文化多樣性和實現(xiàn)文化平等而提出來的概念。隨后,這一概念在國際社會廣為流傳,同時也掀起了討論的熱潮。
20世紀(jì)90年代初,東亞漢字文化圈的一些國家和地區(qū)開始紛紛對“Indigenous"Peoples”做出國內(nèi)譯介工作,但由于所處的社會形態(tài)及語言習(xí)慣等的不同,呈現(xiàn)出了翻譯上的多樣性,如中國譯為“土著人民”,日本先后譯為“原住民(族)”和“先住民(族)”[1]。圍繞“Indigenous"Peoples”對應(yīng)譯詞的甄選,日本人類學(xué)家清水昭俊指出:“由于‘Indigenous’與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有很大關(guān)系,因此,與‘原住’及‘土著’等具有‘原初歷史’含義的詞匯相比,‘先住’更適合做其對應(yīng)譯詞。”[2]從實踐層面上看,日本政府的確從20世紀(jì)90年代末開始傾向于使用“先住民”,并用該詞取代了“Indigenous"Peoples”的原來對應(yīng)譯詞“原住民”。清水昭俊的上述觀點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足以回答日本為何在20世紀(jì)90年代末才以“先住民”替代“原住民”的問題。那么,在當(dāng)代日本語境下的“先住民”包含哪些概念內(nèi)涵,與“原住民”有何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它反映了怎樣的文化建構(gòu)機(jī)制?對此,中國學(xué)術(shù)界很少有考察兩個概念之區(qū)別的研究,而有關(guān)“先住民”與文化建構(gòu)關(guān)系的研究更是罕見。基于此,本文擬主要通過對日本官方文件的文本分析,探討日本對“先住民”和“原住民”的不同理解及其背后深層次的邏輯,以期給國內(nèi)學(xué)界有關(guān)此問題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論視角、方法與經(jīng)驗。
一、“Indigenous"Peoples”的國際機(jī)構(gòu)釋義與日本譯介概況
1985年,聯(lián)合國防止歧視及保護(hù)少數(shù)小組委員會防止歧視及保護(hù)少數(shù)小組委員會于1997年7月27日將其機(jī)構(gòu)改名為促進(jìn)與保護(hù)人權(quán)小組委員會。的下設(shè)機(jī)構(gòu)土著民族工作小組在起草《聯(lián)合國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草案》的過程中,向國際勞工組織提出應(yīng)將國際勞工組織《土著和部落人口公約》(以下簡稱《ILO第107號公約》)中帶有歧視含義的“Indigenous"Populations”改為“Indigenous"Peoples”的建議。國際勞工組織接受該建議,并在1989年通過的《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約》(以下簡稱《ILO第169號公約》)中將“Indigenous"Populations”改為“Indigenous"Peoples”。從此,“Indigenous"Peoples”在國際社會上廣泛傳播,其影響力也不斷擴(kuò)大。而且,《聯(lián)合國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于2007年在聯(lián)合國大會通過之后,該詞不僅成為國際社會對土著民族稱謂的唯一公認(rèn)用語,還被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所接受和使用。這一事實意味著國際社會對土著民族的態(tài)度從歧視到以維持殖民主義體系為目的的關(guān)注,從家長式統(tǒng)治和保護(hù)到鼓勵融合和同化,最后到為全人類的利益承認(rèn)土著民族是與眾不同的獨特民族,并對其予以尊重的變化過程和認(rèn)識上的進(jìn)步[3]。
然而,“Indigenous"Peoples”自20世紀(jì)80年代末成為國際人權(quán)法概念之時起,國際社會對其概念認(rèn)識的爭論就已開始,而其爭論和多方政治利益博弈一直持續(xù)到當(dāng)今。圍繞“Indigenous"Peoples”的定義,國際社會上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不同觀點。比如,國際勞工組織在《ILO第169號公約》中對該詞下定義為:“土著民族因作為在其所屬國家或該國所屬某一地區(qū)被征服或被殖民化時,或在其目前的國界被確定時,即已居住在那里的人口之后裔而被視為土著,并且無論其法律地位如何,他們?nèi)圆糠只蛉康乇A袅吮久褡宓纳鐣⒔?jīng)濟(jì)、文化和政治制度。”國際勞工組織《ILO第169號公約》第一部分“總政策”第一條第一款。同時,世界土著民族理事會對該詞的定義為:“在殖民人口進(jìn)入前就居住在某一領(lǐng)土上,殖民人口在該領(lǐng)土上建立了一個或多個新國家,或一個現(xiàn)有國家或多個國家擴(kuò)大管轄權(quán)將該領(lǐng)土包括,以及繼續(xù)居住在該領(lǐng)土上,并不控制其居住的國家或多個國家的國家政府的人們共同體。”[4]
面對國際社會上針對“Indigenous"Peoples”的不同概念界定,日本政府于1989年與國際勞工組織簽署《ILO第169號公約》之后也開始對這一概念做出國內(nèi)譯介工作。如表1所示,日本政府最初將“Indigenous"Peoples”翻譯為“原住民”(日語音讀為“げんじゅうみん”),然而,《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草案》于1994年遞交至聯(lián)合國人權(quán)委員會接受審議之后,日本將“Indigenous"Peoples”的對應(yīng)譯詞從原來的“原住民”修改為“先住民”(日語音讀為“せんじゅうみん”)當(dāng)前,日本對“先住民”的英文翻譯為“indigenous""peoples”,“原住民”的英文翻譯則為“natives”“aborigines”“indigenes”。。
圍繞“先住民”的概念界定,日本國內(nèi)目前有兩種不同的觀點。首先,日本官方的觀點認(rèn)為:“國際社會上對‘先住民’的定義有各種各樣的不同觀點,但從國家政策實踐意義上講,該詞應(yīng)指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統(tǒng)治波及之前,有著與國家多數(shù)民族的主體文化不同的文化認(rèn)同而定居某一地域的,盡管受到多數(shù)民族文化的支配,但并未喪失其文化獨特性的民族。”[5]其次,研究阿伊努人問題的日本學(xué)者以及大部分阿伊努人卻有著與日本政府截然不同的觀點。他們認(rèn)為,世界上約有3億多人口的土著民族,他們的生活、文化和社會樣式是多種多樣的;盡管還不存在對此概念的通用界定,但"“土著民族是被殖民國家剝奪土地、資源并遭受歷史性不正當(dāng)折磨的群體”的觀點已得到廣泛認(rèn)可,所以“先住民”意指被近代殖民政策或同化政策所否定,以及被剝奪土地、資源、語言及文化的人類群體。部分日本學(xué)者還主張將“先住民”解釋為想給下一代傳承其固有土地、語言、傳統(tǒng)文化及生活方式等的人類群體。表1日本對“Indigenous"Peoples”的語言轉(zhuǎn)換過程資料來源:由筆者根據(jù)國際勞工組織駐日本事務(wù)所及日本聯(lián)合國宣傳中心的資料整理而成。國際勞工組織駐日本事務(wù)所網(wǎng)站:https://www.ilo.org/tokyo/standards/list-of-conventions/lang--ja/index.htm;日本聯(lián)合國宣傳中心網(wǎng)站:https://www.unic.or.jp/activities/economic_social_development/social_development/integration/indigenous_people/。ILO第107號公約
(1957年通過)ILO第169號公約
(1989年通過)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
(1994年起草)原文Convention"concerning"the"Protection"and"Integration"of"Indigenous"and"Other"Tribal"and"SemiTribal"Populations"in"Independent"CountriesConvention"concerning"Indigenous"and"Tribal"Peoples"in"Independent"CountriesUnited"Nations"Declaration"of"the"Rights"on"Indigenous"Peoples日文獨立國における土民並びに他の種族民及び半種族民の保護(hù)及び同化に関する條約獨立國における原住民及び種族民に関する條約先住民族の権利に関する國際連合宣言中文關(guān)于獨立國家保護(hù)和同化土著和其他部落、半部落人民公約關(guān)于獨立國家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約聯(lián)合國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
二、“先住民”的概念建構(gòu)及其內(nèi)涵闡釋
如上所述,從20世紀(jì)9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政府改用“先住民”來稱呼國內(nèi)外土著民族。圍繞日本政府為何以“先住民”取代“原住民”的問題,日本國內(nèi)主流媒體普遍將其解釋為與后進(jìn)的“原住民”相比,“先住民”是一個朝著正義和進(jìn)步的方向發(fā)展的新概念。日本《每日新聞》記者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原住民’里的‘原’字與‘原始人’里的‘原’字一樣有‘野蠻’‘愚蠢’等含義。‘原住民’是帶有社會偏見及歧視的概念,這已是日本社會的普遍共識。”資料來源:筆者于2022年1月初對日本《每日新聞》《朝日新聞》與《讀賣新聞》記者通過電子郵件、電話等方式進(jìn)行訪談的內(nèi)容。
然而,與“土人/土民”原本就帶有明確負(fù)面內(nèi)涵的概念相比,“原住民”的鄙視性內(nèi)涵并非自古便有。在現(xiàn)代國家利益驅(qū)動下,“原住民”與“先住民”同樣是被日本政府有目的、有計劃地主動建構(gòu)的產(chǎn)物。其理由如下。第一,從詞典釋義上看,與“土人/土民”有著“未開化”“愚蠢”“欠發(fā)達(dá)”等負(fù)面內(nèi)涵的概念相比,“原住民”和“先住民”均不含貶義。日本國語詞典《廣辭苑》(第七版)對“原住民”的釋義為:“相較于移居者來說,‘原住民’指的是很早以前就定居在那里的一群人,‘原住民’又稱‘先住民’。”旺文社《國語辭典》(第11版)對“先住民”的釋義為:“相較于征服者或移居者來說,‘先住民’意指原來就定居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nèi)后w,‘先住民’又稱‘原住民’。”第二,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原住民”和“先住民”幾乎在同一時期出現(xiàn)在日本的相關(guān)史籍中,二者的用法也基本相同,兩個概念都強(qiáng)調(diào)歷史上特定地域在時間順序上居先性的特點。在日本國內(nèi),最先使用“原住民”一詞的學(xué)者是史學(xué)家坪內(nèi)雄藏。坪內(nèi)雄藏在1901年出版的《英文學(xué)史》的第一部《上古時期的文學(xué)》中考察了英國的“原住民”與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相關(guān)問題。“先住民”一詞則首次出現(xiàn)在日本學(xué)者江見水蔭在1907年出版的《地底探險記》中。該書的第一章為有關(guān)日本“先住民”的研究,江見水蔭在這一章里主要探討了大和民族的祖先來到這片土地之前哪一種人類群體定居在這里的問題。換言之,“原住民”和“先住民”以相同的意涵出現(xiàn)于同一時期,兩者都意味著(殖民)移居者到來之前已居住在某一地方的人類群體。
由此看來,不管是后進(jìn)的“原住民”概念,還是進(jìn)步的“先住民”概念都是日本政府在同國際社會與國內(nèi)土著民族的互動以及彼此的博弈中,根據(jù)自身所處環(huán)境對其概念的內(nèi)涵做出選擇性運(yùn)用的結(jié)果。“原住民”是相對“先住民”而言的,兩個概念互為存在的前提和條件。其中,“先住民”是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之后,受到圍繞保護(hù)土著民族及其權(quán)利的國際人權(quán)法日趨成熟的國際環(huán)境,以及國內(nèi)各界壓力的影響而被日本政府建構(gòu)起來的概念。具體來看,從國際層面上,《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草案》于1994年首次提出了土著民族作為“Peoples”擁有與其他人民平等的自由決定自身政治地位及謀求自身經(jīng)濟(jì)、社會和文化發(fā)展權(quán)利的自決權(quán)的觀點,這與《ILO第169號公約》盡管承認(rèn)土著民族為集體性的主體,卻否認(rèn)與其相關(guān)的各種權(quán)利,而遭遇國際社會的普遍質(zhì)疑呈明顯對比。圍繞《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草案》在日本國內(nèi)的高度認(rèn)同和積極反響,清水昭俊如此下結(jié)論:“與更多地反映國家‘原住民’政策的《ILO第169號公約》不同,《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草案》勾勒出了‘先住民’權(quán)利的基本框架。”[6]從日本國內(nèi)層面來看,阿伊努人作為土著民族爭取其各項權(quán)利的運(yùn)動日益活躍,國內(nèi)政治、經(jīng)濟(jì)與社會各界以及國際輿論對日本政府的批評之聲也隨之興起。如此國內(nèi)外環(huán)境下,試圖以人權(quán)外交為武器樹立國際良好形象的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呼應(yīng)《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草案》精神的各項措施,其中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將本國土著民族阿伊努人的稱呼從原來的“土人/土民”“原住民”修改為“先住民”,并賦予“先住民”正義之意。與“原住民”是容易遭受國內(nèi)占統(tǒng)治地位民族的剝削、壓迫和邊緣化的概念不同,“先住民”意味著在一個承認(rèn)文化多樣性的國家和社會里被承認(rèn)和尊重的獨立的民族文化共同體概念。針對“原住民”與“先住民”的區(qū)別,清水昭俊在其另外一篇著作中指出,“將‘原住民’與‘國家’‘國民’等概念聯(lián)系起來概括的話,‘國民’里不包含‘原住民’,國家普遍排斥‘原住民’,不將其視為‘國民’。‘原住民’如想成為‘國民’就必須接受統(tǒng)治者的強(qiáng)制同化,而同化帶來的結(jié)果僅僅是國民數(shù)量的增長,從國民構(gòu)成來看并未發(fā)生任何的變化,依然維持著單一性。但是,‘先住民’建立在否認(rèn)國家強(qiáng)制實行‘文化消滅與民族滅絕’的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jié)構(gòu)之上,因此,要將‘先住民’統(tǒng)一到國民范疇里,原來的同化政策將會失去效力,國家應(yīng)重新調(diào)整國民要素,重建多樣化成分的‘新國民’。”[7]
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將“先住民”視為擁有文化特性及其權(quán)利的人類群體,其本質(zhì)建立在將“先住民”看作權(quán)利主體的認(rèn)知之上。換言之,“先住民”突出反映了日本對本國土著民族的認(rèn)知與態(tài)度由“保護(hù)、同化、合并”向“尊重、和解、共生”的方向發(fā)生轉(zhuǎn)變的事實。因此,“先住民”的概念內(nèi)涵可概括為以下兩個層面:
第一,“先住民”是日本政府通過承認(rèn)文化多樣性和塑造多元文化社會來積極應(yīng)對日益增長的土著民族權(quán)利要求的產(chǎn)物,它具有進(jìn)步的一面,但其落腳點并非在發(fā)展土著民族各項權(quán)利的考慮上,而是更多地強(qiáng)調(diào)國民共同體的整合。1994年,以主張土著民族個人及集體的土地、資源、文化等廣泛基本權(quán)利及民族自決權(quán)的聯(lián)合國《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草案》的擬定及其強(qiáng)大的國際影響力,迫使日本政府廢棄持續(xù)一百多年的《北海道舊土人保護(hù)法》日本政府目前僅承認(rèn)阿伊努人為本國土著民族,因此,日本的土著民族政策也僅圍繞阿伊努人問題而展開。,制定了新的《阿伊努文化振興法》。在此新法中,日本政府首次承認(rèn)阿伊努人的土著民族屬性,并對阿伊努文化解釋道:“阿伊努人的民族音樂、舞蹈及工藝和其他文化性產(chǎn)物作為日本獨特的民族文化之一,國家有責(zé)任對其保護(hù)和積極推廣”[日]『アイヌ文化振興法の概要』,公益社團(tuán)法人北海道阿伊努協(xié)會網(wǎng)站:https://www.ainuassn.or.jp/ainupeople/overview.html,2022年1月28日引用。。從此,日本政府對阿伊努民族的認(rèn)知與態(tài)度,由在近代民族國家建設(shè)階段被納入國家的控制與民族塑造之中被賦予“因經(jīng)濟(jì)社會文化的欠發(fā)達(dá)需要被改造的弱勢群體”,轉(zhuǎn)為“在承認(rèn)文化多樣性的國家和社會里應(yīng)被接受和尊重的獨立文化主體”。換言之,與“原住民”曾被“合法地”排除在國際法主體之外,種族滅絕、被迫遷移、土地喪失、流離失所、文化絕滅等成為其共同的歷史經(jīng)歷相比,“先住民”的個人與集體層面上的人權(quán)與自由、文化和傳統(tǒng)等一系列基本權(quán)利能夠得到國內(nèi)的法律保障。然而,日本研究和解決土著民族問題的出發(fā)點并非落在真正恢復(fù)和發(fā)展土著民族各項權(quán)利的考慮上,而是通過承認(rèn)文化多樣性和重構(gòu)多元文化認(rèn)同來實現(xiàn)加強(qiáng)整合國民共同體的目的。阿伊努政策推進(jìn)會議的前任執(zhí)行部長常本照樹曾發(fā)文稱:“1997年通過的《阿伊努文化振興法》為回避各種麻煩和爭論,有意將阿伊努文化僅僅限定在語言、歌曲、舞蹈、工藝等狹義范圍之內(nèi)。”[8]2019年4月19日,《阿伊努民族支援法》盡管首次明確了阿伊努人的土著民族身份,但依然未將其土地、教育、資源及民族自決等核心權(quán)利內(nèi)容反映到法律文件之中[日]「アイヌの人々の誇りが尊重される社會を?qū)g現(xiàn)するための施策の推進(jìn)に関る法律案』,日本參議院網(wǎng)站:https://www.sangiin.go.jp/japanese/joho1/kousei/gian/198/pdf/t0801980241980.pdf,2022年1月20日引用。。對此,日本有學(xué)者稱:“日本政府始終以承認(rèn)先住民族的土地、教育等權(quán)利不符合日本國情為由,將先住民族的權(quán)利僅僅局限在‘繼承和發(fā)展民族傳統(tǒng)文化’這一特殊范圍之內(nèi),這是‘日本型’先住民族政策的本質(zhì)及問題所在。”[9]
第二,“先住民”是日本政府在同國際社會與國內(nèi)土著民族的互動以及彼此的博弈中,為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和工具,也是國家人權(quán)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清水昭俊曾指出:“‘先住民’其實是一個與政治相關(guān)的概念,它在先住民運(yùn)動、國家政策、國際法與國際市民社會等因素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政治過程中發(fā)揮了一種構(gòu)建現(xiàn)實力量的作用。”[10]2007年9月13日,日本政府盡管為保護(hù)世界土著民族各項權(quán)利的《土著人民權(quán)利宣言》毫不猶豫地投了贊成票,但在國內(nèi)實踐層面上對土著民族的態(tài)度極為保守,僅僅承認(rèn)其文化權(quán)利。如圖1所示,目前,日本政府的阿伊努土著民族政策僅僅分為“阿伊努文化的振興及啟蒙”和“阿伊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兩個部分。換言之,20世紀(jì)90年代末,以“北海道阿伊努協(xié)會”2009年4月,“北海道屋塔里協(xié)會”將其協(xié)會名稱重新改回“北海道阿伊努協(xié)會”。為首的阿伊努人獲得國際人權(quán)法保護(hù)和國內(nèi)社會各界的支持,在不斷開展為爭取土著民族權(quán)利的運(yùn)動形成嚴(yán)峻形勢之下,日本政府?dāng)M采取以賦予阿伊努人文化權(quán)利為標(biāo)志的多元文化政策,來開展反映其國家人權(quán)價值的國內(nèi)外活動,其目的就是利用多元文化主義的政治理念及價值觀施展人權(quán)外交,并向國內(nèi)外宣示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為使尊重人權(quán)更加普遍化所做的努力,以便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2009年7月,在“討論阿伊努政策方向的專家研討會”向內(nèi)閣官房長官遞交的報告書中指出:“使先住民族擁有名譽(yù)和尊嚴(yán),并將其文化和自豪感傳給下一代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和潮流,而擁有與國際社會相同的價值觀是21世紀(jì)我國引領(lǐng)國際社會時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11]。對此,國外有學(xué)者稱:“日本政府積極參加關(guān)于人權(quán)保護(hù)的各種國際條約,并在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政策上放棄同化主義,轉(zhuǎn)而推行多元文化主義并向世界表明其對尊重和保護(hù)土著民族人權(quán)的立場與態(tài)度,這是基于國家人權(quán)外交的需要,但客觀上它也起到了保護(hù)土著民族權(quán)利的作用。”[12]"圖1日本政府的現(xiàn)有阿伊奴民族政策體系
三、多元文化共生與文化認(rèn)同重構(gòu)
近代日本以國民的同質(zhì)化為基礎(chǔ)和目標(biāo),在建構(gòu)日本人身份認(rèn)同上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成功地塑造了文化認(rèn)同、民族認(rèn)同和國家認(rèn)同一致的國民身份認(rèn)同,并奠定了戰(zhàn)后日本人身份認(rèn)同的基礎(chǔ)[13]。因此,在統(tǒng)合國民及培養(yǎng)和加強(qiáng)國民意識上,如何將阿伊努人等少數(shù)民族同化成日本民族(“和人”或“和族”)成為日本近代國民國家形成及發(fā)展過程中首要解決的關(guān)鍵問題。然而,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之后,日本對土著民族阿伊努人的態(tài)度由過去的否認(rèn)和歧視轉(zhuǎn)向了肯定和尊重。換言之,如圖2所示,日本將族際關(guān)系的治理模式從文化單一化轉(zhuǎn)向了文化多元化,而其契機(jī)與尋求防止當(dāng)今由民族及族群文化多樣性帶來的制度缺陷以及社會互不信任或相互沖突的蔓延有關(guān)。首先,20世紀(jì)80年代末,圍繞保護(hù)土著民族權(quán)利的國際人權(quán)法日趨成熟的國際大氣候下,阿伊努人爭取土著民族地位及權(quán)利的呼聲和斗爭愈發(fā)高漲和凸顯,促使日本政府反思和重新調(diào)整阿伊努人政策。然后,20世紀(jì)90年代初,隨著冷戰(zhàn)結(jié)束和全球化擴(kuò)大帶來的人口流動的加速發(fā)展,使日本遭遇由國際移民的大量流入帶來的國家內(nèi)部族群文化多樣化的挑戰(zhàn)截至2020年12月,在日本注冊的外籍居民數(shù)量已達(dá)到288萬,盡管其在日本總?cè)丝跀?shù)量中占據(jù)的比例僅為22%,遠(yuǎn)低于美國、加拿大等傳統(tǒng)移民大國水平,但相比過去顯著增多。詳見《在留外國人統(tǒng)計》,日本法務(wù)省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網(wǎng)站:http://www.moj.go.jp/isa/policies/statistics/toukei_ichiran_touroku.html,2022年2月21日引用。。族群文化多樣性成為日本社會的顯著特點,并加快了其文化同質(zhì)性社會的瓦解,這就使得不同民族及族群之間如何和諧相處成為日本重要的課題,同時這一課題迫使日本政府尋找將各族群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共同和諧生活的方法。日本政府開始效仿在加拿大、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中被作為土著民族及跨國移民參與國家一體化的新途徑而提出來的多元文化主義,并根據(jù)自身所處環(huán)境著手制定與西方國家不同程度的多元文化政策。
日本的多元文化政策始于20世紀(jì)90年代末,而該政策針對兩個不同的群體,一個是有關(guān)土著民族的政策(僅限阿伊努人),另外一個是有關(guān)新老移民等少數(shù)族群的政策。首先,針對土著民族阿伊努人的多元文化政策始于1997年《阿伊努文化振興法》出臺之后。《阿伊努文化振興法》強(qiáng)調(diào)了政府要尊重阿伊努人及其文化特性,并致力于保護(hù)國家文化多樣性之一的阿伊努文化與傳統(tǒng),以及應(yīng)做到引導(dǎo)全體日本國民充分認(rèn)識到阿伊努文化的價值所在。然后,有關(guān)新老移民的多元文化政策,則始于2006年3月日本總務(wù)省批準(zhǔn)《在全國范圍內(nèi)推進(jìn)“多元文化共生”計劃》(以下簡稱《多元文化共生》)之后。該計劃的主旨是努力建設(shè)不同國籍和民族背景的人們之間相互承認(rèn)其文化差異和建立平等社會關(guān)系,并作為同一地方的社會成員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社會[14]。"圖2文化認(rèn)同與族群認(rèn)同、國家認(rèn)同之間的關(guān)系
日本的多元文化政策一般被日本學(xué)界稱之為《多元文化共生》,而這一政策在日本總務(wù)省于2007年提出來之后,被廣泛傳播、討論和運(yùn)用。有關(guān)“多元文化共生”的定義,日本國內(nèi)學(xué)界有幾種不同的觀點。日本學(xué)者加藤千香子認(rèn)為,“多元文化共生”是指生活方式不同的人與人之間,相互承認(rèn)對方的自由活動和參加機(jī)會,積極構(gòu)筑相互間關(guān)系的一種社會性結(jié)合,是通過人們共同探索來實現(xiàn)的[15]。日本學(xué)者坂中英徳將“多元文化共生”定義為,在一個社會中,兩種以上不同性質(zhì)的文化集團(tuán),在生活習(xí)慣和文化上相互理解,溝通時相互尊重對方,形成對等關(guān)系的狀態(tài)[16]。日本學(xué)者鍋島祥郎對“多元文化共生”的定義為,為相互間承認(rèn)價值觀和文化,誰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而建設(shè)的社會[17]。然而,“多元文化共生”實則是由“多元文化”和“共生”兩個詞語來組成的概念,它與“共生”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共生”這一概念在20世紀(jì)80年代末就開始使用,它是在血統(tǒng)主義理念之下根據(jù)將國內(nèi)居民劃分為“國民”和“外國人”的單純二分法原則,為使大量移民到日本的巴西人、秘魯人,以及來自菲律賓、泰國的舞蹈演員、藝妓,來自中國、韓國的研修人員等外國人順利融入日本當(dāng)?shù)厣鐣鴱奈鞣絿乙M(jìn)多元文化政策嘗試于解決國內(nèi)文化多元化問題而形成的概念。當(dāng)初,“共生”這一概念建立在將在日外國人看作日本社會的“問題”并從解決“問題”的角度出發(fā)對其實施“管理”的理念之上。日本學(xué)者廣田康生對此尖銳批評道:“‘共生’經(jīng)常被當(dāng)作共存理念來強(qiáng)調(diào),但不能忽視這個概念僅適用于移民或少數(shù)族群被當(dāng)?shù)鼐用衲酥辽鐣刃蛩恼Z境中,它作為政治理念被政府所利用。”[18]隨后不久,日本政府也意識到了把在日外國人當(dāng)作勞動力加以利用或僅從管理的角度予以應(yīng)對,就無法改善由于文化多樣性帶來的各種制度問題及社會矛盾和沖突,便開始重新反思和全面探討國內(nèi)文化多樣性的問題。2005年,日本總務(wù)省成立關(guān)于推進(jìn)多元文化共生的研究會,開始研究文化多樣性及其引發(fā)的問題,并于2007年出臺了有關(guān)《多元文化共生》的政策。該政策主張政府應(yīng)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yè)、民間組織、市民團(tuán)體及居民個人等多主體和“語言、信息等支援”“居住、教育、勞動環(huán)境、醫(yī)療保健、防災(zāi)等支援”“建立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域”“貢獻(xiàn)于地區(qū)發(fā)展和全球化”等多角度推進(jìn)多元文化社會的發(fā)展。可以說,與過去強(qiáng)調(diào)在同化主義理念下迫使異文化的“他者”接受“和人”“和族”文化并融入日本社會的“共生”概念相比,“多元文化共生”概念強(qiáng)調(diào)建立“不同國籍和民族背景的人們之間承認(rèn)彼此的文化差異并建立平等的社會關(guān)系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社會。“多元文化共生”概念的意義還在于國家引導(dǎo)全國國民接受和尊重其他少數(shù)民族文化,以及謀求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如上所述,《多元文化共生》這一政策的背后邏輯是日本政府將本國阿伊努人的土著民族文化當(dāng)作國家文化的一種標(biāo)志物,促使國家文化包含非主流社會或非主體民族的文化元素,以此促進(jìn)多元文化社會的發(fā)展。
近年來,多元文化政策在日本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這在日本國內(nèi)土著民族、新老移民等少數(shù)群體保護(hù)和發(fā)展本民族文化及其權(quán)利上意義重大。盡管如此,日本的多元文化政策有著先天不足之處。比如,日本政府盡管通過立法承認(rèn)阿伊努人為本國的“先住民”,但被賦予的土著民族權(quán)利僅僅局限在傳承和發(fā)展“狹隘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上。對此,日本有學(xué)者批評道:“先住民問題的解決至少應(yīng)與在先住民族的同意下轉(zhuǎn)換國家形態(tài)有關(guān)。具體來說,國家形態(tài)應(yīng)從現(xiàn)在的單一國民國家向復(fù)數(shù)的國民國家轉(zhuǎn)變,也即政府應(yīng)將先住民這一共同體視作一個‘文化國民’來處理國家向多元文化國民國家轉(zhuǎn)換的問題。如果政府在不涉及國家形態(tài)轉(zhuǎn)換的前提下尋求解決先住民問題,那么實質(zhì)上就是在‘多族群國家’的框架內(nèi),將針對移民的多元文化政策適用于先住民身上罷了。”[19]日本還有學(xué)者指出:“在多元文化共生政策的制度框架內(nèi),對于‘先住民’而言,可以借助多元文化主義尋求的權(quán)利僅僅是通過制度框架來尋求語言及文化傳承的權(quán)利,以及實現(xiàn)族群文化認(rèn)同和民族身份的保持,而在西方國家語境下借助多元文化主義普遍可以尋求到的區(qū)域自治、政治代表、土地歸屬等方面的利益保障卻不可獲得。”[20]從日本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實踐來看,日本擬通過文化多元化模式取代文化單一化模式來重新構(gòu)建國家的多元文化認(rèn)同,并以此來提升土著民族及移民等少數(shù)族群的國家認(rèn)同感。日本學(xué)者菊池洋曾指出:“如果將日本的國民構(gòu)成要素看作是多元的,可以將其劃分為阿伊努系日本人、沖繩系日本人、日系日本人以及歸化了的朝鮮及韓國系日本人等。”[21]然而,除了阿伊努人之外,日本政府對其他少數(shù)群體的多元文化措施基本停留在語言及生活支援上,而在教育、經(jīng)濟(jì)、政治上尚未得到實質(zhì)性進(jìn)展。Bantingamp;Kymlicka和Kimamp;Cha的研究表明,日本多元文化政策的能力水平依然處于“新生型”國家類型,而這一類型的特點為國家和國民對少數(shù)者的態(tài)度極為否定和悲觀,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制度化水平極其低下[2223]。
結(jié)論
身份認(rèn)同構(gòu)建是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交往、對話。它所構(gòu)建的主體性既可能是主體的存在,也可能是主體間的共在。前者是一種基于主客體對立的二元論的主體性,強(qiáng)調(diào)主體的特殊性,因為在這種條件下主體可以恣意地“想象他者”,而無須關(guān)心其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的真實性,也可以不受他者的歷史和現(xiàn)實情況的束縛;而后者是超越主客體對立的自我主體與對象主體間的同在關(guān)系,認(rèn)為主體性只有在主體間性下才是其所是,這種主體性受到普遍性或共同性的制約,也因此強(qiáng)調(diào)主體間的統(tǒng)一性、互為性、聯(lián)結(jié)性、共在性等。進(jìn)入20世紀(jì)9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通過建構(gòu)“先住民”概念來承認(rèn)國內(nèi)民族文化多樣性以及強(qiáng)調(diào)建立各民族之間在語言、文化和歷史上聯(lián)系的做法就屬于后者這一類型。
日本曾經(jīng)是一個極其重視民族文化同質(zhì)性的國家,“大和民族主義”曾是日本建構(gòu)近代民族國家的重要思想武器。近些年,在不少歐洲國家紛紛宣布多元文化政策失敗的關(guān)鍵節(jié)點上,日本反而強(qiáng)調(diào)多元文化社會的塑造,是應(yīng)對日益生長的土著民族權(quán)利要求,以及為增強(qiáng)少數(shù)族群的國家認(rèn)同而選擇的制度及政策框架。通過多元文化政策的實施,日本先住民族阿伊努人獲得了維護(hù)和自主發(fā)展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權(quán)利,新老移民等少數(shù)族群也開始擁有保留自身文化及與其他文化和平交流的機(jī)會。這些是日本將族際關(guān)系與民族及國家關(guān)系的治理模式從文化的同質(zhì)化轉(zhuǎn)向多元化的重要成果和表現(xiàn),但是,日本的多元文化政策仍有其局限性。有學(xué)者圍繞日本的多元文化政策批評道:“日本的多元文化政策將先住民的特殊權(quán)利要求變形為國際移民等少數(shù)族群的文化權(quán)利要求。”[24]日本在承認(rèn)和給予本國土著民族應(yīng)享有權(quán)利方面極為保守,阿伊努人被賦予的權(quán)利僅僅局限在非政治性的語言、文化和藝術(shù)等純粹文化意義上,因此,遭到了國內(nèi)外社會“日本從未真誠地對待過國內(nèi)少數(shù)民族問題”的嚴(yán)厲批評。日本通過多元文化政策剛剛邁進(jìn)國內(nèi)少數(shù)族群政策的自我修正和調(diào)整階段,而其最終效果如何還需要歷史和現(xiàn)實的檢驗。
[參考文獻(xiàn)]
[1]姜德順.聯(lián)合國處理土著問題史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52-54.
[2]清水昭俊.先住民の権利と國家および國民の條件[J].文化人類學(xué),"2008(12):371.
[3]廖敏文.為了一個和而不同的世界:《聯(lián)合國土著民族權(quán)利宣言》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9:"261-262.
[4]KINGSBURY"B."“Indigenous"Peoples”"in"International"Law:"a"Constructivist"Approach"to"the"Asian"Controversy[J]."The"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1998(3):"414-457.
[5]內(nèi)閣官房阿伊努綜合政策室.アイヌ政策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有識者懇談會報告書[EB/OL].[2022-01-26].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ainu/dai10/siryou1.pdf.
[6]清水昭俊.先住民と國民の歴史のための序論[J].文化人類學(xué),2008(12):357-358.
[7]清水昭俊.先住民、植民地支配、脫植民地化:國際連合先住民権利宣言と國際法[R].東京:國立民族學(xué)博物館研究報告,2008(2):355-360.
[8]常本照樹.アイヌ民族と『日本型』先住民政策[J].學(xué)術(shù)の動向,2016(9):79-82.
[9]東村岳史.アイヌ政策の分析枠組み:強(qiáng)制された「共生」の構(gòu)造[J].國際開発研究フォーラム,2016(10):6.
[10]清水昭俊.論國際法中的indigenous"peoples[J].云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2(2):12.
[11]アイヌ先住民研究ニューズレター[R]."北海道:アイヌ先住民研究センター,2011(1):1-3.
[12]"[J].,2015(51):325.
[13]向卿.身份認(rèn)同與被創(chuàng)造的民族、文化:以近代日本的文化認(rèn)同構(gòu)建為例[J].中央社會主義學(xué)院學(xué)報,"2020(5):43.
[14]日本總務(wù)省.地域における多文化共生推進(jìn)プラン[EB/OL].[2022-02-20].https://www.soumu.go.jp/main_content/000731370.pdf.
[15]加藤千香子.日本における多文化共生とは何か[M].東京:新曜社,2008:75.
[16]坂中英徳.移民國家ニッポン:1000萬人の移民が日本を救う[M].東京:日本加除出版,2007:13.
[17]鍋島祥郎.共生のための教育は可能か[C]//"野口道彥.共生社會の創(chuàng)造とNPO.東京:明石書店,2003:183.
[18]広田康生ほか.先端都市社會學(xué)の地平[M].東京:ハーベスト社,2008:271.
[19]広田啓子.『北海タイムス』とアイヌ問題[J].地域と経済,2010(7):117-132.
[20]馬渕仁.「多文化共生」は可能か:教育における挑戦[M].東京:勁草書房,2011:66-68.
[21]菊池洋.アイヌ民族の権利に関する二つのアプローチ[J].政経學(xué)會雑誌.2008(78):"147-168.
[22]BANTING"K,"KYMLICKA"W."Is"there"Really"a"Retreat"from"Multiculturalism"Policies?"New"Evidence"from"the"Multiculturalism"Policy"Index[J]."Comparative"European"Politics,"2013(5):577-598.
[23]KIM"B"K,"CHA"Y"K."Clustering"Analysis"Based"on"the"National"Multicultural"Policies[J]."Multicultural"Education"Studies,2017(1):77-100.
[24]中村廣司.日本の『多文化共生』概念の批判的考察[J].日本文學(xué)研究,2014(91):414-415.
[責(zé)任編輯孫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