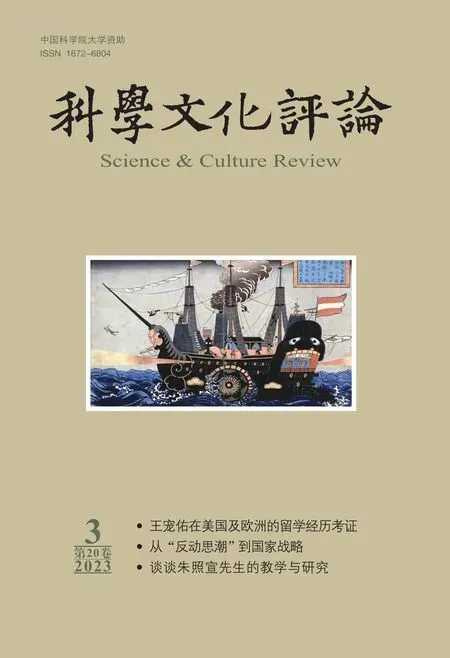從“反動思潮”到國家戰(zhàn)略我國人工智能認知變遷歷程
余春玲 劉 培
一 引言
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發(fā)展一直伴隨著技術(shù)革命論與技術(shù)威脅論的爭議,社會各界對該技術(shù)追捧與抵制的聲音此起彼伏。在技術(shù)紅利與技術(shù)風(fēng)險的矛盾認知下,不少專家學(xué)者試圖從我國人工智能的歷史發(fā)展中尋找技術(shù)前進的規(guī)律與方向抉擇的經(jīng)驗。
現(xiàn)有研究多集中于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人工智能學(xué)科建制化發(fā)展、技術(shù)研究成就、科技政策量化及商業(yè)應(yīng)用成果的梳理[1]。哲學(xué)界也有學(xué)者對我國20世紀80年代人工智能哲學(xué)發(fā)展及當(dāng)下人工智能倫理研究進行了探討[2]。盡管我國人工智能歷史梳理的維度有所擴增,但囿于專業(yè)類別,其研究結(jié)果多呈現(xiàn)出技術(shù)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分離,鮮有從科學(xué)思想與技術(shù)認知的角度分析人工智能在我國的本土化融入過程。
技術(shù)認知是設(shè)計、規(guī)劃、引起技術(shù)活動的思考和行動方式,是一種旨在改造、創(chuàng)建的實踐活動[3]。通過技術(shù)認知的視角可以從整體上把握技術(shù)與社會的互動,已有學(xué)者將其運用在鐵路史[4]、航天史[5]的研究之中。我國人工智能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但社會群體對人工智能所建立的技術(shù)認知早于技術(shù)本身研究,認知變遷的歷程貫穿于我國人工智能發(fā)展史。本文借鑒前人研究視角,將人工智能技術(shù)認知劃分為三個方面的問題:(1)人工智能是什么?(2)人工智能有什么影響?(3)人工智能如何發(fā)展?依據(jù)技術(shù)的雙重屬性,將技術(shù)認知概念分解為對技術(shù)的科學(xué)性認識與社會性認識。科學(xué)性認識包括對技術(shù)的科學(xué)論證與學(xué)科屬性探索;社會性認識主要為對技術(shù)價值及發(fā)展定位的把控。基于此,本文以“一門學(xué)科”和“一項工具”為主要認識視野,對我國不同時期的人工智能技術(shù)認知作解讀,并探究技術(shù)認知對技術(shù)發(fā)展的促進或阻滯作用。最后,本文總結(jié)了人工智能三大研究綱領(lǐng)與社會科技觀在我國人工智能認知轉(zhuǎn)變過程中的建構(gòu)作用。
二 人工智能的“偽科學(xué)”批判(1955—1977)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我國科學(xué)界以翻譯蘇聯(lián)科學(xué)與哲學(xué)文章的方式了解國外先進技術(shù)[6]。我國人工智能認知的形成亦是從引進蘇聯(lián)控制論開始[7]。維納(Norbert Wiener)在《控制論》中提出的“機器思維”觀點是我國學(xué)界對智能形成科學(xué)性認識的起源。這一觀點沖擊了舊有科技觀,學(xué)界在批判中完成了對該智能思想的選擇性接納。這一階段的主要認知問題是:人工智能是不是“偽科學(xué)”?
20世紀50年代早期,蘇聯(lián)學(xué)界認為控制論中機器與人類可類比的觀點是“美國的偽科學(xué)”[8]。1953年后,蘇聯(lián)科學(xué)家意識到將科學(xué)問題意識形態(tài)化、政治化嚴重阻礙了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被批判為“偽科學(xué)”的控制論重新得以審視。雖然稍早時候我國學(xué)術(shù)期刊上就出現(xiàn)了控制論的相關(guān)概念,但引起我國學(xué)者對控制論關(guān)注的主要源自于1955年《學(xué)習(xí)譯叢》上刊發(fā)的兩篇蘇聯(lián)文章《什么是控制論》和《控制論的若干基本特征》,二文糾正了對控制論的錯誤哲學(xué)批判,我國對控制論的引進與翻介工作隨即展開[7]。維納在萊布尼茨所提出的“機械大腦論”基礎(chǔ)上,將隨機的統(tǒng)計屬性引入控制系統(tǒng)中,并打破機器與生物體在行為上的界限,認為二者在理論上都可以表現(xiàn)出相同智能行為[9]。這一創(chuàng)新性學(xué)術(shù)論斷為后續(xù)人工智能各學(xué)派提供了思想源頭。隨著《控制論》的翻譯出版,“機器模擬人類思維”思想在我國學(xué)界傳播開來。因其打破了時人對機器與人類、有機與無機的科學(xué)界限認識,對當(dāng)時所秉持的唯物主義哲學(xué)觀造成沖擊,引發(fā)了學(xué)界對該設(shè)想科學(xué)性的質(zhì)疑。
1956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關(guān)于知識分子的問題報告》中稱“電子自動控制機器已經(jīng)可以開始有條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腦力勞動,人類將面臨著一個新的科學(xué)技術(shù)和工業(yè)革命”[10]。此時國家決策高層雖然對智能及其技術(shù)原理的科學(xué)性認識還比較模糊,但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機器替代腦力活動”的社會革命工具認識。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guān)系交惡后,控制論在我國被貼上“資本主義復(fù)辟”的認知標簽[11]。我國以哲學(xué)界為主要陣地,對控制論展開批判,周總理所提出的這一工具性認識在批判中被淹沒。1963年9月北京自然辯證法學(xué)會籌委會與中科院哲學(xué)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組聯(lián)合召開了控制論哲學(xué)問題座談會。會議前夕,《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發(fā)表文章《圍繞控制論科學(xué)成就的思想斗爭》,批判“機器比人聰明、機器將統(tǒng)治人類”這類謬論是一種“極端的反動思潮”,認為“現(xiàn)代自動機既沒有生命,更不能思維”[11]。在會上,來自數(shù)學(xué)、計算機、心理學(xué)研究所的專家認為“機器對思維的模擬完成的只是特定的數(shù)學(xué)機械工程,并不代表機器能思維”[12]。1965年《人民日報》發(fā)表《機器與思維》一文,稱“機器可能完全代替人腦的說法,在技術(shù)上是沒有根據(jù)的,在哲學(xué)上是錯誤的,并且在政治上是反動的”[13]。這意味著對“機器思維”問題的批判,已從科學(xué)真?zhèn)涡缘膶W(xué)術(shù)層面上升至政治層面。同年中科院數(shù)學(xué)所胡世華在《控制論的發(fā)展》一文中對“智能模擬”一詞注解時稱,“國外文獻也將其稱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按照我們的觀點,有些用語是不妥當(dāng)?shù)摹盵14]。從譯名的選擇上可見,對“機器思維”的批判致使人工智能作為學(xué)術(shù)名詞在我國初期傳播之時并未被接納。
在對“機器可完全實現(xiàn)人類思維”進行猛烈批判的過程中,科學(xué)界選擇性地接納了“機器可部分模擬人類思維”的智能思想。《圍繞控制論科學(xué)成就的思想斗爭》稱“模擬是控制論中廣泛采用的方法,現(xiàn)代自動機對生命和思維進行模擬,代替人腦的某些思維功能”[11]。胡世華將智能模擬定義為“機器模擬人需要用到智能的活動”,并把感覺官能的機器模擬稱為“模式識別”,對其進行了肯定[14]。在研究方向上,科學(xué)界將對高級智能的追求描述為更高級別的自動化控制,并認為有必要對人類更多的生命活動進行研究與模擬,表明智能科學(xué)朝向人類生命體更高層次的模擬得到合法化認可。
在機器延伸人類智力的工具選擇方面,學(xué)界對什么樣的機器可作為人類智力延伸的實體、機器與人類建立智力延伸的方式也建立了初步的科學(xué)性認識。為給“機器可完全實現(xiàn)人腦思維”批判提供論斷支撐,國內(nèi)引進了大量西方學(xué)界有關(guān)“機器思維”問題的觀點與研究文獻。由此,圖靈測試、邏輯學(xué)等人工智能相關(guān)的技術(shù)方法思想得以傳播至我國。通過對圖靈機的了解與討論,學(xué)界更確切認識到計算機是可模擬人類生命活動的機器對象。此外,在實現(xiàn)“機器思維”的路徑上,國內(nèi)也開啟了實現(xiàn)智能的技術(shù)性探索,如1976年發(fā)表的《達到“讓機器能思維”的種種途徑》,提出了“計算機科學(xué)”“邏輯科學(xué)”“數(shù)學(xué)”等六條路徑來實現(xiàn)“機器能思維”[15]。
綜合來看,“機器模擬思維”問題成為學(xué)界后續(xù)建立“人工智能是什么”的認識萌芽,其本質(zhì)是“數(shù)學(xué)機械化”的科學(xué)性認識在我國科學(xué)界初步形成。但是囿于意識形態(tài)層面的批判,人工智能這一學(xué)術(shù)名詞仍未得到認可。在“智能控制”和“智能機器”名詞的替代下,模式識別等領(lǐng)域的研究得以開展,這一做法體現(xiàn)出學(xué)界為發(fā)展智能學(xué)科邁出了嘗試性的一步。
三 人工智能科學(xué)與價值的定性(1977—2000)
我國智能研究領(lǐng)域的突破及頻繁的中西學(xué)術(shù)交流促進了學(xué)界認可人工智能的科學(xué)性,并以學(xué)科為主要視角建立科學(xué)性認識。人工智能屬于什么學(xué)科?研究內(nèi)容是什么?成為此階段主要關(guān)注問題。在學(xué)科認識建立的基礎(chǔ)下,人工智能作為一項技術(shù)工具的社會價值也開始被學(xué)界所認識。
20世紀70年代初期,在“數(shù)學(xué)機械化”思維下部分科學(xué)家已開啟了智能領(lǐng)域研究。作為西方熱議的發(fā)展方向,人工智能概念已傳入我國,但囿于前期對“機器思維”問題的批判認識,部分學(xué)者仍堅持人工智能是偽科學(xué)的幌子。人工智能這一學(xué)術(shù)名詞還未得到解禁。1977年,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研制出我國第一臺手寫數(shù)字識別樣機,吳文俊發(fā)表了幾何定理的機械化證明方法。同年吉林大學(xué)計算機系王湘浩首次對人工智能發(fā)表認可觀點并倡導(dǎo)研究[16]。科研成果的顯現(xiàn)與計算機領(lǐng)域先驅(qū)科學(xué)家的認可,引發(fā)了學(xué)界對人工智能科學(xué)性的再次審視。1979年王湘浩受教育部委托,在吉林大學(xué)召開以人工智能為重點方向的“計算機科學(xué)暑期討論會”[17]。會上邀請了幾何定理證明領(lǐng)域?qū)W者吳文俊,專家系統(tǒng)研究專家陸汝鈐等人作報告。這場被認為是“中國達特茅斯會議”的學(xué)術(shù)討論會提振了學(xué)界對研究人工智能的信心,帶動了高校研究人工智能的熱情,大范圍傳遞了人工智能研究可行性的態(tài)度,削弱了“機器思維”問題引發(fā)的人工智能“偽科學(xué)”認識,人工智能的科學(xué)性得到了初步認可。
然而很快,囿于某些科學(xué)家將人工智能與特異功能、氣功等相提并論,使得人工智能再次陷入了“偽科學(xué)”的漩渦。部分研究者因此脫離人工智能學(xué)術(shù)團體,對人工智能研究不予支持。
進入20世紀80年代,學(xué)界在人工智能科學(xué)探索的道路上繼續(xù)前行。1980年10月,我國人工智能領(lǐng)域科學(xué)家在北京科學(xué)會堂主持召開了全國第一屆人工智能學(xué)術(shù)討論會,并邀請符號主義學(xué)派的創(chuàng)始人西蒙·司馬賀(H. A. Simon,司馬賀是其中文名)在會上作了專題學(xué)術(shù)報告。此次學(xué)術(shù)研討會成為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成立的光明序曲,也為我國學(xué)者對人工智能建立科學(xué)性與價值性認識提供了基礎(chǔ)。1981年2月,在倡導(dǎo)盡快成立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的會議上,與會者對人工智能學(xué)科屬性形成共識,提出人工智能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邊緣學(xué)科。同年7月,哲學(xué)所聯(lián)合中科院自動化所與心理所在北京召開“人工智能哲學(xué)問題”座談會。在有關(guān)人工智能和哲學(xué)與各門具體科學(xué)的關(guān)系討論中,有學(xué)者再次提出:“人工智能是一門跨界科學(xué),與哲學(xué)、心理學(xué)、生理學(xué)、語言學(xué)、邏輯學(xué)、數(shù)學(xué)、控制論、計算機科學(xué)等學(xué)科都有密切的聯(lián)系,它是自然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的邊緣科學(xué)。”[19]邊緣學(xué)科的屬性界定將人工智能研究拓寬至各個科學(xué)領(lǐng)域,強調(diào)出這門學(xué)科的復(fù)雜性,號召多學(xué)科研究者共同參與。在人工智能學(xué)會掛靠問題上,籌備組最初希冀掛靠中科院數(shù)學(xué)所,但因吳文俊對人工智能的科學(xué)性有所保留,轉(zhuǎn)而向中國社科院求助。哲學(xué)所童天湘表示人工智能屬于哲學(xué)研究范疇,因此學(xué)會最終掛靠在哲學(xué)所名下。這一掛靠也促進了后期人工智能哲學(xué)領(lǐng)域的發(fā)展。同年9月,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正式成立,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在開幕式講話中肯定了人工智能是一門新興學(xué)科,強調(diào)應(yīng)該積極支持其研究。于光遠作為特異功能運動的強烈反對派學(xué)者,其對人工智能與特異功能關(guān)系的切割,實現(xiàn)了對人工智能科學(xué)性的正名。人工智能學(xué)會的成立掃清了學(xué)界殘留的“偽科學(xué)”與“反動思潮”認知,標志著人工智能學(xué)科化的開啟。
在眾多關(guān)聯(lián)學(xué)科中,人工智能主要依附于何種學(xué)科也是討論的焦點。各學(xué)科專家對人工智能重要性的認識也有所不同。1982年計算機學(xué)界在學(xué)術(shù)思想上作出了計算機科學(xué)與技術(shù)的本質(zhì)發(fā)展方向是人工智能的學(xué)科定論[20]。這一定論有力地提升了人工智能在計算機學(xué)科領(lǐng)域的重要地位,促使計算機成為我國人工智能研究的主戰(zhàn)場,人工智能逐漸劃歸為計算機分支。在研究內(nèi)容方面,受西方人工智能研究思潮的影響,該階段我國以符號主義為主要研究綱領(lǐng),在該綱領(lǐng)下對人工智能研究內(nèi)核與研究方向作出判斷。1982年第一次全國人工智能學(xué)術(shù)會議對人工智能基礎(chǔ)理論給出了官方定義,即“圍繞如何把某類問題形式化來進行”[20]。在應(yīng)用研究方面,受西方專家系統(tǒng)商業(yè)化應(yīng)用的引領(lǐng),與會學(xué)者強調(diào)專家系統(tǒng)是人工智能最實用的研究領(lǐng)域。此后,以中科院自動化研究所為主要研究單位,我國研制出諸多專家系統(tǒng),如石油測井解釋人工智能專家咨詢系統(tǒng)、地震剖面解釋專家系統(tǒng)、集成電路圖形解釋專家系統(tǒng)等。
隨著人工智能開始從實驗室走向社會生產(chǎn),從抽象理論走向具體應(yīng)用,其科學(xué)性得到廣泛認可的同時,價值性也逐漸凸顯。1999年我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第一屆副理事長涂序彥發(fā)表多篇科普文章,將人工智能定義為“研究、開發(fā)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shù)及應(yīng)用系統(tǒng)的一門新的技術(shù)科學(xué)。”[21]提出人工智能要為“知識經(jīng)濟”服務(wù)、促進“智能經(jīng)濟”發(fā)展,探索“人工生命”[22]。在人工智能領(lǐng)域頂尖專家的指引下,人工智能面向經(jīng)濟服務(wù)的發(fā)展性認識逐步建立。學(xué)界有關(guān)人工智能的認識不再局限于學(xué)術(shù)屬性,技術(shù)的社會價值開始成為關(guān)注焦點。與之相同步,哲學(xué)界也從早期“機器能否思維”的哲學(xué)思辨轉(zhuǎn)向人工智能社會影響研究。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發(fā)行了《人工智能的認識論問題》一書,該書肯定了人工智能的社會意義,并認為人工智能是機器進化合乎發(fā)展規(guī)律的產(chǎn)物[23]。1988年社科院哲學(xué)所童天湘發(fā)表《現(xiàn)代科學(xué)革命與唯物主義的發(fā)展》與《論智能革命——高技術(shù)發(fā)展的社會影響》引發(fā)較大關(guān)注。童天湘在文中對人工智能促進社會革命的技術(shù)價值給予了高度認可,創(chuàng)造性提出智能革命設(shè)想,并從工具論的視角重申了腦力活動機械化的工具性認識[24]。錢學(xué)森在評論中指出“智能革命是又一次文藝復(fù)興”[25]。不難看出,哲學(xué)界對人工智能的認識是以工具論為基礎(chǔ),將人工智能看做機械化工具,具有重塑人類社會生活形式與社會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功能。
在如何發(fā)展人工智能問題上,20世紀80年代西方世界圍繞第五代計算機的科技競賽引起我國科學(xué)家的高度關(guān)注。錢學(xué)森多次在各類會議上將智能機比作戰(zhàn)略核武器,強調(diào)應(yīng)按照發(fā)展尖端科學(xué)技術(shù)的經(jīng)驗來發(fā)展人工智能[26]。在國際競爭態(tài)勢的逼迫下,人工智能被看作是國家實力的有力象征,科學(xué)界認識到發(fā)展人工智能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國家發(fā)展與人工智能緊密聯(lián)系的戰(zhàn)略性認識開始形成。
這一階段我國對人工智能的認識從“機器能否思維”的科學(xué)性批判中跳出,“偽科學(xué)”的論斷被清除,在“人工智能是什么”這一問題上形成了科學(xué)性認識。這場人工智能學(xué)科啟蒙也引發(fā)了哲學(xué)界研究的轉(zhuǎn)向,哲學(xué)家開始以工具為視野,挖掘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社會價值。國際人工智能競賽的態(tài)勢也從外部催生了國家對“如何發(fā)展人工智能”的關(guān)注。綜合來看,這一時期我國對人工智能的科學(xué)與價值屬性形成了較為穩(wěn)固的認識,思想層面對技術(shù)實現(xiàn)了完整的接納。
四 人工智能戰(zhàn)略地位的確立(2000—2020)
進入21世紀,我國人工智能研究轉(zhuǎn)向機器學(xué)習(xí)與聯(lián)結(jié)主義學(xué)派。研究流派的轉(zhuǎn)變重塑了我國對人工智能的科學(xué)性認識。學(xué)界對人工智能成為一級學(xué)科的訴求逐漸強烈,深度學(xué)習(xí)引發(fā)的應(yīng)用熱潮使得大眾對人工智能的社會性認識也在不斷改變。該階段技術(shù)認知聚焦于“人工智能有什么影響”以及“人工智能如何發(fā)展”。
人工智能發(fā)展認識的形成取決于對其社會價值的認可。在這一方面,我國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開啟了人工智能社會價值的認知搶跑。20世紀末期專家系統(tǒng)的式微,致使學(xué)界轉(zhuǎn)向“機器自學(xué)習(xí)”領(lǐng)域,機器學(xué)習(xí)的應(yīng)用使得模式識別、推薦搜索等領(lǐng)域的智能效果提升。2006年,加拿大學(xué)者杰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將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應(yīng)用于機器學(xué)習(xí),推動人工智能走向深度學(xué)習(xí)時代。在新一輪人工智能浪潮下,2010年百度公司率先對深度學(xué)習(xí)布局,認為“深度學(xué)習(xí)帶來機器學(xué)習(xí)一個新浪潮,導(dǎo)致‘大數(shù)據(jù)+深度模型’時代的來臨,將以機器學(xué)習(xí)為主的人工智能帶入加速前進的‘新人工智能時代’”[27]。百度對深度學(xué)習(xí)價值的認知覺醒帶動了國內(nèi)其他科技巨頭對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重視,阿里巴巴、騰訊等國內(nèi)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也紛紛參與進一場世界人工智能爭奪戰(zhàn)。在該技術(shù)創(chuàng)生期內(nèi),我國在人工智能研究綱領(lǐng)完成了從專家系統(tǒng)為代表的符號主義到機器學(xué)習(xí),再到深度學(xué)習(xí)為代表的聯(lián)結(jié)主義的轉(zhuǎn)變。這一轉(zhuǎn)變促進了學(xué)界與產(chǎn)業(yè)界對人工智能形成了以統(tǒng)計學(xué)為基礎(chǔ)的“數(shù)據(jù)+算法=人工智能”的科學(xué)性認識。在應(yīng)用方向上,2016年Alphago在人機大戰(zhàn)中取得的勝利展示了人工智能巨大的工業(yè)潛力,其被認為是改變社會、提高經(jīng)濟效益的重要工具。企業(yè)在技術(shù)價值認識上的領(lǐng)跑與社會大眾對智能技術(shù)的接納無疑為后續(xù)國家確立人工智能戰(zhàn)略地位提供了促進力量。
AlphaGo人機大戰(zhàn)勝利后,多國開始將人工智能提升至國家戰(zhàn)略層次。例如,2016年美國奧巴馬政府成立人工智能發(fā)展研究部門,并在報告中首次強調(diào)人工智能技術(shù)發(fā)展的經(jīng)濟價值[28]。至特朗普政府時期,人工智能不僅是促進社會邁向智能化生產(chǎn)的工具,亦是維護國家安全與霸權(quán)的重要“科技武器”[29]。2018年德國首次將人工智能定位至國家戰(zhàn)略,關(guān)注技術(shù)在工業(yè)制造與人力勞動上的推動作用[30]。2018年日本政府在人工智能技術(shù)戰(zhàn)略會議上出臺了推動人工智能普及計劃,希冀借助人工智能技術(shù)維持并提升日本在汽車、機器人等領(lǐng)域的工業(yè)競爭力,以及解決人口老齡化等社會性問題。我國政府對人工智能戰(zhàn)略認識的形成與德國具有較高的相似性。
我國智能化理念發(fā)端于制造業(yè),伴隨著人工智能在安防等領(lǐng)域的杰出成效,政府最終將人工智能列入國家戰(zhàn)略規(guī)劃之中。整體來看,較之20世紀80年代由學(xué)界自下而上的推動,此時國家對人工智能戰(zhàn)略性的認識更具主動性。在世界信息技術(shù)刺激產(chǎn)業(yè)革命,及我國制造業(yè)亟待轉(zhuǎn)型升級的背景下,2015年國務(wù)院印發(fā)《中國制造2025》,在戰(zhàn)略目標中將智能制造列為主攻方向。智能制造正是人工智能技術(shù)在制造業(yè)賦能的體現(xiàn),此時我國政府對智能技術(shù)的賦能價值及方式初步形成了具象化認識。2015年7月《國務(wù)院關(guān)于積極推進“互聯(lián)網(wǎng)+”行動的指導(dǎo)意見》發(fā)展目標中指出“人工智能等技術(shù)及其產(chǎn)業(yè)化能力顯著增強”[31],并提出“互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概念,強調(diào)“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提供AI公共創(chuàng)新服務(wù),培育發(fā)展AI新興產(chǎn)業(yè)”。但此時的人工智能概念要么依存于產(chǎn)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要么覆蓋在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之下,還未作為一個獨立的戰(zhàn)略方向。至2016年,在各國人工智能戰(zhàn)略認識激增及國內(nèi)人工智能產(chǎn)業(yè)爆發(fā)的態(tài)勢下,人工智能從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規(guī)劃中獨立成為重要戰(zhàn)略方向。同年5月發(fā)改委發(fā)布《“互聯(lián)網(wǎng)”+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強調(diào)培訓(xùn)發(fā)展人工智能新興產(chǎn)業(yè);7月國務(wù)院再度發(fā)文,在《“十三五”國家科技創(chuàng)新規(guī)劃》中提出“重點發(fā)展大數(shù)據(jù)驅(qū)動的類人智能技術(shù)方法”[32]。2017年7月,國務(wù)院頒布《新一代人工智能發(fā)展規(guī)劃》,宣布舉全國之力在2030年搶占人工智能全球制高點。該份規(guī)劃首次將人工智能提升至國家戰(zhàn)略層次,拉開了我國人工智能繁榮發(fā)展的大幕。在該份規(guī)劃中,也明確了對人工智能的科學(xué)性認識:“新一代人工智能是大數(shù)據(jù)基礎(chǔ)上的人工智能,與前60年的人工智能完全不同的階段。”[33]當(dāng)今政府強調(diào)了以數(shù)據(jù)為驅(qū)動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shù)思想,已完全不同于上世紀我國學(xué)界對人工智能建立的形式邏輯認識。這一科學(xué)性認識的轉(zhuǎn)變正是不同時期對人工智能研究綱領(lǐng)選擇的映照。
人工智能作為國家戰(zhàn)略的技術(shù)認知迅速傳播至學(xué)界、產(chǎn)業(yè)界及普通大眾。在一系列政策的指引下,社會各行各業(yè)開啟了智能化轉(zhuǎn)型的熱潮,“賦能”成為大眾對人工智能社會性認識的代名詞,人工智能的學(xué)科地位也得到提升。2001年中國人工智能學(xué)會第九次全國學(xué)術(shù)會議上,鐘義信理事長提議將人工智能設(shè)立的本科專業(yè)命名為“智能科學(xué)與技術(shù)”[34]。2003年12月,北京大學(xué)率先設(shè)立智能科學(xué)與技術(shù)專業(yè)。2009年,鐘義信理事長聯(lián)合多單位向國家學(xué)位委員會和教育部提出設(shè)置“智能科學(xué)與技術(shù)”學(xué)位授權(quán)一級學(xué)科的建議[35]。因該建議當(dāng)時未被采納,2017年李德毅院士帶領(lǐng)學(xué)會及相關(guān)高校對人工智能列入一級學(xué)科又進行了科學(xué)與價值性論證,完成了《“智能科學(xué)與技術(shù)”一級學(xué)科論證報告》,提出一級學(xué)科的設(shè)立不僅是對社會對人才需求的滿足,更將同時促進其他學(xué)科的發(fā)展。2018年4月,教育部印發(fā)《高等學(xué)校人工智能創(chuàng)新行動計劃》,強調(diào)支持高校在計算機科學(xué)與技術(shù)學(xué)科設(shè)置人工智能學(xué)科方向,推動人工智能領(lǐng)域一級學(xué)科建設(shè)。
從最初被認定為“反動思潮”,到“十三五”時期正式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人工智能作為服務(wù)經(jīng)濟發(fā)展的新興技術(shù)動力為經(jīng)濟賦能,已被融入社會生產(chǎn)之中,我國完成了對人工智能認知的顛覆性轉(zhuǎn)變。然而,在人工智能產(chǎn)業(yè)與學(xué)科如火如荼發(fā)展的同時,人工智能應(yīng)用的全面落地暴露出諸多技術(shù)缺陷,大眾的技術(shù)安全倫理意識激增。技術(shù)倫理威脅的影響下,社會自下而上對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提出了種種安全需求,如何健康發(fā)展人工智能成為近些年社會熱議問題。各種場景下人臉識別的強制使用、深視網(wǎng)大規(guī)模的人臉數(shù)據(jù)泄露、“3·15晚會”曝光的人臉數(shù)據(jù)牟利行為等事件使得大眾對人工智能安全產(chǎn)生懷疑。在社會權(quán)責(zé)體系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權(quán)利歸屬、自動駕駛的事故責(zé)任劃分均對現(xiàn)有社會法律體系產(chǎn)生沖擊。面對以人臉識別為首的人工智能應(yīng)用,社會上開始出現(xiàn)抵制技術(shù)的言論。人工智能如何健康發(fā)展亟待國家出臺相應(yīng)的法律法規(guī),人工智能治理逐漸從發(fā)展規(guī)劃的邊緣走向中心位置。在平衡技術(shù)戰(zhàn)略與技術(shù)風(fēng)險問題上,我國政府起初試圖以軟法——人工智能守則的形式進行企業(yè)技術(shù)應(yīng)用的自律的探索。而隨著技術(shù)的應(yīng)用深入,軟法已無法規(guī)制人工智能向善發(fā)展,硬法治理成為社會各界保障人工智能健康發(fā)展的訴求。近些年國家及行業(yè)組織在《網(wǎng)絡(luò)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基礎(chǔ)上出臺多項管理規(guī)制,如《關(guān)于加強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服務(wù)算法綜合治理的指導(dǎo)意見》、《信息安全技術(shù) 人臉識別數(shù)據(jù)安全要求》等,從場景使用及技術(shù)研發(fā)上對人工智能作出限制。在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領(lǐng)域,國家也逐漸加強人工智能企業(yè)在數(shù)據(jù)安全范疇的監(jiān)管,要求企業(yè)將技術(shù)倫理安全納入技術(shù)設(shè)計全流程。
該階段我國對人工智能的關(guān)注以技術(shù)價值和技術(shù)影響為主,企業(yè)和社會大眾不斷的利益博弈促使我國人工智能戰(zhàn)略的完善。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詮釋了“技術(shù)是把雙刃劍”的社會效應(yīng),發(fā)展負責(zé)任的人工智能成為新階段下國家的戰(zhàn)略方向。
五 我國人工智能認知建構(gòu)分析
縱觀我國人工智能技術(shù)認知的變遷歷程,“機器模擬人類思維”是認知建立的源頭。在人工智能“作為一門學(xué)科”的科學(xué)性認識方面,“機器可部分模擬人類思維是一種數(shù)學(xué)機械工程”作為我國智能認識的雛形,指引了早期機器翻譯、機器定理證明等領(lǐng)域的研究。但人工智能的學(xué)科屬性直至20世紀80年代才得到學(xué)術(shù)界的統(tǒng)一認可,并被認定為主要依附于計算機的邊緣學(xué)科。由此,“知識+邏輯推理”成為20世紀80—90年代我國人工智能的代表性認識。至21世紀,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到來促使“數(shù)據(jù)驅(qū)動”成為新的認知焦點,2010年以來深度學(xué)習(xí)的火熱進一步深化了新一代人工智能認識——“人工智能=大數(shù)據(jù)+算法”。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數(shù)學(xué)機械工程”的原始智能認識逐漸蛻化,“數(shù)據(jù)+算法”成為主流。在人工智能“作為一項工具”的社會性認識方面,“腦力勞動機械化”貫穿于人工智能技術(shù)認知建立的整個歷程。控制論傳播初期形成的模糊認識在反修正主義時代遭到批判,至20世紀80年代人工智能作為社會革命動力的工具性認識才得以重燃。在“智能革命論”的認識影響下,人工智能得以蓬勃發(fā)展,最終于2017年正式被確立為國家戰(zhàn)略。同時現(xiàn)實層面的技術(shù)雙刃劍效應(yīng)促使人工智能倫理治理成為保障技術(shù)健康發(fā)展的重要考量。總結(jié)來說,如果以學(xué)科為基礎(chǔ)的科學(xué)性認識是人工智能技術(shù)發(fā)展的風(fēng)向標,那么以工具為導(dǎo)向的社會性認識則是其發(fā)展的動力源泉。
從社會不同群體對人工智能的認識來看,科學(xué)界、哲學(xué)界、企業(yè)與大眾在各階段的互動和主輔地位的消長也深刻影響了我國人工智能技術(shù)認知的建構(gòu)過程:在人工智能技術(shù)早期傳播階段,科學(xué)界對技術(shù)思想的部分否定與哲學(xué)界的唯物批判是人工智能進入我國的第一道藩籬;在兩者對維納“機器思維”觀點進行科學(xué)性的論證過程中,“機器模擬人類思維”觀點被部分接受,“智能模擬”是一種“數(shù)學(xué)機械工程”成為學(xué)界主流智能認識;中西方學(xué)術(shù)交流在破除人工智能“偽科學(xué)”認識上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成果將抽象的智能思想具體化,促進了科學(xué)界與哲學(xué)界的技術(shù)認知轉(zhuǎn)向。在人工智能學(xué)科化階段,哲學(xué)界的技術(shù)價值定論給予了人工智能研究支持,并引領(lǐng)社會對人工智能建立智能革命工具的認識。在人工智能技術(shù)應(yīng)用階段,企業(yè)率先實現(xiàn)人工智能的經(jīng)濟價值變現(xiàn),為社會注入了人工智能可行的工具性認識,也為國家展現(xiàn)了人工智能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的實力,進而促進我國人工智能作為國家戰(zhàn)略的認識形成。在技術(shù)大規(guī)模應(yīng)用之中,人工智能負面影響促使社會群體技術(shù)安全倫理意識激增,社會自下而上推動國家對人工智能戰(zhàn)略加以調(diào)整和完善,最終形成發(fā)展負責(zé)任人工智能的社會性共識。
技術(shù)自身蘊含的科技思想與社會群體的科技觀或許才是人工智能技術(shù)認知形成的根本動力。從技術(shù)發(fā)展內(nèi)部來看,人工智能研究綱領(lǐng)反映了該學(xué)科的核心思想主張,是各界形成人工智能科學(xué)性認識的基礎(chǔ)。20世紀早期人工智能三大研究綱領(lǐng)伴隨西方技術(shù)交流與文獻引進傳入我國。以控制論為核心的行為主義學(xué)派思想在哲學(xué)思辨中完成了在我國的傳播。在認知建構(gòu)方面,“機器代替人腦思維”這一突破性科技思想叩開了我國關(guān)于智能科學(xué)研究的大門,“高級人工智能=機器能思維”的技術(shù)判定標準也成為社會對人工智能可實現(xiàn)性的根本性科學(xué)認識。計算機事業(yè)的發(fā)展成熟使得符號主義學(xué)派思想得以在我國扎根,一方面科學(xué)界建立了以形式邏輯為主的科學(xué)性認識,另一方面符號主義的可驗證性與科技成果商用化掃清了“人工智能是反動思潮”的錯誤思想,引發(fā)哲學(xué)家對智能革命的未來設(shè)想。聯(lián)結(jié)主義在我國的興起源自于深度學(xué)習(xí)的技術(shù)引進,以賦能為核心的深度學(xué)習(xí)技術(shù)在全社會引發(fā)人工智能認識猛增。聯(lián)結(jié)主義算法的不可解釋性致使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黑箱”屬性。“黑箱”屬性降低了技術(shù)賦能的難度,這也是我國得以短期內(nèi)實現(xiàn)人工智能產(chǎn)業(yè)繁榮的一項重要客觀因素。然而技術(shù)“黑箱”也使得聯(lián)結(jié)主義缺乏科學(xué)解釋性,成為大眾對人工智能安全性產(chǎn)生懷疑的原始誘因。
從技術(shù)發(fā)展外部來看,不同時代下的科技觀決定時人對新興科技的接納態(tài)度與認知定位。20世紀50年代國人對來自外界新興觀念抱有較強的敵對審視認知[36],“科學(xué)思想的唯物論”成為評判科學(xué)技術(shù)的標準。受此影響,“機器可實現(xiàn)人腦思維”觀點被貼上唯心主義標簽,指向資產(chǎn)階級。對科學(xué)認識上的差異使得人工智能雛形思想在我國被激進地批判為“反動思潮”。改革開放后,國家要求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要與經(jīng)濟緊密結(jié)合。符號主義以知識為中心的研究思想與國家新型科技發(fā)展觀下尊重知識的認知相匹配;專家系統(tǒng)在中醫(yī)、地質(zhì)勘探等領(lǐng)域展現(xiàn)出的人工智能實用價值契合我國科技發(fā)展導(dǎo)向。因此人工智能在這一時期得以順利融入國家經(jīng)濟生產(chǎn),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必要工具。1996年“知識經(jīng)濟”一詞席卷全球,科技經(jīng)濟高度融合成為世界趨勢。國家對知識經(jīng)濟發(fā)展的重視帶動了計算機等信息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專家系統(tǒng)、模式識別等成果彰顯出人工智能在知識經(jīng)濟中出色的潛能,促進全社會對人工智能建立技術(shù)認可的價值認識。黨的十八大以來,科技作為經(jīng)濟發(fā)展重要引擎與國力綜合體現(xiàn)的科技觀深入人心,社會對新興技術(shù)的接納態(tài)度從謹慎變?yōu)闊崃易非螅斯ぶ悄鼙唤o予變革社會與提升國力的工具性期望,人工智能戰(zhàn)略認識順勢而生。
從“機器思維模擬”到“大數(shù)據(jù)”的算法驅(qū)動,從“反動思潮”到“社會變革重要工具”,我國各界對人工智能的科學(xué)性認識與社會性認識不斷被刷新。人工智能與社會的融入既取決技術(shù)的突破性,也取決社會群體對人工智能所建立認識的深度與廣度,更不能忽視技術(shù)對公眾權(quán)益與社會秩序的沖擊。這應(yīng)該是透過我國人工智能認知變化歷程得出的經(jīng)驗與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