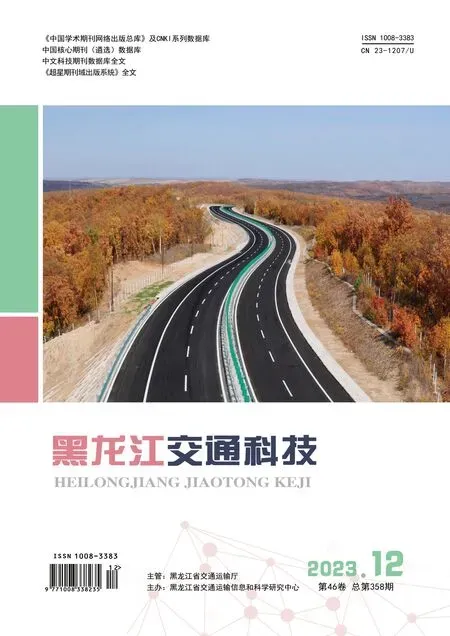曲線盾構(gòu)隧道施工側(cè)穿廊橋樁基施工風(fēng)險分析
方水平
(撫州贛東公路設(shè)計院有限公司,江西 撫州 344000)
城市中地鐵隧道修建采用的方法主要為盾構(gòu)法,盾構(gòu)機掘進(jìn)過程中會對周邊建構(gòu)筑物造成影響,因此確定盾構(gòu)機掘進(jìn)過程中的施工風(fēng)險是工程順利進(jìn)行的重要保證。樁基礎(chǔ)易受周邊環(huán)境擾動,因此盾構(gòu)機掘進(jìn)對樁基礎(chǔ)的擾動分析也是近年來學(xué)者們研究的熱點。王馨霆[1]構(gòu)建了洛陽地鐵側(cè)穿牡丹大橋樁基的三維有限元模型,分析了盾構(gòu)掘進(jìn)過程中樁基礎(chǔ)的內(nèi)力變化情況;路德春等[2]以清華園隧道側(cè)穿樁基為工程背景,構(gòu)建三維數(shù)值計算模型分析了盾構(gòu)施工對樁基沉降、承載力及彎矩的影響;周鑫等[3]運用三維有限元軟件模擬盾構(gòu)開挖施工的全過程,研究開挖過程對地層沉降及鄰近橋梁樁基影響規(guī)律;劉健美[4]結(jié)合三維數(shù)值模擬分析了盾構(gòu)隧道與樁基的相對空間關(guān)系對樁基變形的影響。可以看到數(shù)值模擬方法常被用于分析盾構(gòu)隧道掘進(jìn)對鄰近樁基的擾動情況,施工前期可以通過構(gòu)建數(shù)值計算模型分析并預(yù)測施工風(fēng)險。已有研究中通常只考慮盾構(gòu)隧道沿直線段掘進(jìn)的情況,鮮有研究針對盾構(gòu)隧道沿曲線段掘進(jìn)對鄰近樁基的擾動情況。盾構(gòu)機沿曲線段掘進(jìn)時,施工因素相比沿直線段更為復(fù)雜,對周邊環(huán)境造成的擾動更明顯[5]。
以磁浮快線東延線下穿機場廊橋工程為研究背景,通過有限差分軟件FLAC3D構(gòu)建盾構(gòu)機沿曲線段掘進(jìn)的數(shù)值計算模型,分析盾構(gòu)機掘進(jìn)過程中地表沉降和樁基沉降情況,評價盾構(gòu)機掘進(jìn)過程中的施工風(fēng)險。
1 工程概況
磁浮T2站—磁浮T3站區(qū)間,分為左右雙線,采用兩臺土壓平衡盾構(gòu)機施工,開挖直徑7 180 mm,采用通用環(huán)盾構(gòu)管片,管片外徑6 900 mm、內(nèi)徑6 200 mm、厚度350 mm、環(huán)寬1 500 mm。盾構(gòu)區(qū)間出T2站后,左、右線分別以平面曲線半徑355 m和300 m側(cè)穿T2航站樓南側(cè)E區(qū)登機指廊樁基,共涉及19根樁,樁長12.7~15.8 m不等。調(diào)查資料顯示,在曲線段外側(cè)樁基到隧道的最小距離為2.4 m,在雙線中間,樁基到右線的最小距離為1.3 m,到左線的最小距離為1.4 m。
根據(jù)現(xiàn)場勘探以及已有資料綜合分析,場地內(nèi)第四系覆蓋層主要為人工填土、沖洪積粉質(zhì)黏土及泥質(zhì)粉砂巖組成。其野外特征按自上而下的順序依次描述如下。
雜填土:褐灰色、褐、紅等雜色,松散-稍密,稍濕-濕,主要由黏性土夾碎石(塊石)及磚塊等建筑垃圾組成,表層50 cm為混凝土路面。該層在擬建場地內(nèi)大部分地段分布,平均層厚3.5 m。
素填土:褐黃色、褐紅色,稍濕,松散-稍密狀,主要由黏性土組成,局部夾少量碎石,該層在擬建場地內(nèi)大部分地段分布,平均層厚5.5 m。
粉質(zhì)黏土:褐黃色、褐色,稍濕,可塑-硬塑狀,局部堅硬狀,刀切面稍光滑,稍有光澤,該層在擬建場地內(nèi)局部分布,平均層厚5.0 m。
強風(fēng)化泥質(zhì)粉砂巖:褐紅、紫紅,主要礦物成分為黏土礦物及石英碎屑,大部分礦物已風(fēng)化變質(zhì),泥質(zhì)粉砂結(jié)構(gòu),中厚層狀構(gòu)造,泥質(zhì)膠結(jié)為主,局部鈣質(zhì)膠結(jié),節(jié)理裂隙發(fā)育,巖體破碎,RQD介于0%~40%之間,屬極軟巖,巖體基本質(zhì)量等級為Ⅴ級。該層在擬建場地普遍分布,平均層厚8.0 m。
中風(fēng)化泥質(zhì)粉砂巖:褐紅、紫紅,主要礦物成分為黏土礦物及石英碎屑,部分礦物風(fēng)化變質(zhì),泥質(zhì)粉砂結(jié)構(gòu),中厚層狀構(gòu)造,泥質(zhì)膠結(jié)為主,RQD為70%~80%,屬極軟巖-軟巖,巖體基本質(zhì)量等級為Ⅳ~Ⅴ級。各土層的設(shè)計參數(shù)見表1。

表1 巖土設(shè)計參數(shù)表
2 數(shù)值計算模型
通過大型有限差分軟件FLAC3D構(gòu)建隧道開挖數(shù)值計算模型。由于在數(shù)值計算模型中模擬土層的起伏極為繁瑣,因此選取上部軟弱土層厚度最深的位置構(gòu)建數(shù)值計算模型,最不利截面包含三種巖土體,從上至下分別為素填土、粉質(zhì)黏土以及強風(fēng)化泥質(zhì)粉砂巖,厚度分別為13、10、5 m,隧道埋深為15 m,構(gòu)建的數(shù)值計算模型整體尺寸為60 m×60 m×33 m。模型的邊界條件為:底面為下伏巖土層,不考慮下部巖土層對計算區(qū)域的影響,因此底邊設(shè)置為固定約束,側(cè)面為約束表面法向位移,上表面為自由表面,因此不約束上表面的任何方向位移。
數(shù)值計算模型中的單元包括:土體單元、樁體單元、盾殼單元及管片單元。其中土體單元采用彈塑性體單元,服從Mohr-Coulomb破壞準(zhǔn)則[6],土層的單元參數(shù)按照表1選取;樁體、盾殼及管片單元采用線彈性體單元模擬,參數(shù)取值見表2。

表2 單元材料參數(shù)表
盾構(gòu)隧道實現(xiàn)轉(zhuǎn)彎的過程需要在開挖掌子面兩側(cè)施加不同大小的推力。根據(jù)現(xiàn)場試掘進(jìn)的情況,刀盤內(nèi)側(cè)推力為10 000 N,刀盤外側(cè)推力為13 000 N,通過換算可以確定施加的彎道內(nèi)側(cè)正面推力荷載為560 kPa,彎道外側(cè)正面推力荷載為650 kPa。通過在軟件中定義區(qū)域范圍實現(xiàn)刀盤內(nèi)外兩側(cè)不同盾構(gòu)推力的施加過程。同時盾構(gòu)機在曲線段掘進(jìn)過程中,由于盾殼在彎道內(nèi)外兩側(cè)受到的土層周邊擠壓作用大小不同,因此盾殼上方受到的摩擦阻力也會存在差異,根據(jù)現(xiàn)場試掘進(jìn)的測試結(jié)果,內(nèi)側(cè)盾殼單元受到的摩阻力大小為1 300 kPa,外側(cè)盾殼單元受到的摩阻力大小為1 000 kPa。
數(shù)值模擬的計算步驟為:
第一步:根據(jù)土層模型的埋深情況,賦予不同土體的材料參數(shù),進(jìn)行地應(yīng)力平衡分析步;
第二步:將初始地應(yīng)力作用步計算得到的變形情況歸零,賦予樁體單元并在樁體上表面施加大小為20 kPa均布荷載,模擬上方廊橋荷載,然后進(jìn)行計算得到樁體施作后的應(yīng)力場;
第三步:逐步移除隧道右線內(nèi)土體,并在開挖面左右兩側(cè)施加不同大小的頂推力,同時在盾殼內(nèi)外兩側(cè)施加不同大小的摩擦阻力,每步開挖6 m,右線開挖一共有10個分析步;
第四步:逐步移除隧道左線內(nèi)土體,并在開挖面左右兩側(cè)及彎道內(nèi)外側(cè)盾殼施加不同大小的頂推力及盾殼摩阻力。同樣,隧道內(nèi)土體每次被移除6 m,左線開挖至貫通也一共分成了10個分析步。
3 模擬結(jié)果分析
3.1 地表沉降分析
圖1(a)和圖1(b)分別為隧道右線開挖和左線開挖后的地表沉降云圖,圖1(c)展示了樁基附近地表沉降曲線。

圖1 地表沉降情況
由圖1可知,右線貫通后最大地表沉降約為9.8 mm,地表沉降槽呈“V”型分布,但與直線段的地表沉降曲線分布不同,地表沉降槽為非對稱分布,橫向地表最大沉降位置出現(xiàn)在彎道內(nèi)側(cè),這與鄧皇適等[7]的研究一致,這是由于在數(shù)值計算模型中,對彎道內(nèi)外兩側(cè)盾構(gòu)機刀盤施加不同荷載的緣故。由于樁體上表面作用了豎向荷載,周邊土體處于更加敏感狀態(tài),因此右線貫通后,最大地表沉降位置出現(xiàn)在樁體周邊附近。
左線貫通后,地表沉降槽發(fā)生偏移回歸,最終地表沉降槽以兩隧道中軸線對稱分布,符合雙線隧道開挖后地表沉降規(guī)律的變化特征,最大地表沉降值約為15.3 mm。地表沉降曲線中突變的位置為樁體所在位置,由于樁體上表面存在均布荷載,導(dǎo)致樁體上表面的沉降大于周邊地表沉降,與周邊地表存在沉降差。綜上所述,地表沉降在雙線貫通后最大值為15.3 mm,小于規(guī)定限值30 mm,滿足施工控制標(biāo)準(zhǔn)。
3.2 樁基沉降分析
分別提取了右線開挖第一步(開挖步1),右線掘進(jìn)至樁基平面(開挖步5),右線貫通(開挖步10),左線開挖第一步(開挖步11),左線開挖掘進(jìn)至樁基平面(開挖步15),左線貫通(開挖步20)的樁基沉降情況,如圖2所示。

圖2 樁基礎(chǔ)沉降情況
分析上述結(jié)果,可以得到以下結(jié)論。
(1)在距離樁基平面較遠(yuǎn)位置時,盾構(gòu)隧道開挖不會對樁體造成明顯的影響,在盾構(gòu)機通過后,盾構(gòu)機掘進(jìn)對樁基變形的影響加劇,因此在盾構(gòu)機掘進(jìn)通過樁體后加強對樁基的監(jiān)控測量是有必要的。
(2)右線貫通后,樁體的最大沉降值為8.87 mm,在左線貫通后,樁體的最大沉降值為16.7 mm,右線掘進(jìn)對樁體的影響更顯著,但樁體的最大沉降值處于安全控制范圍,可以忽略盾構(gòu)機施工對樁體造成的施工風(fēng)險。
(3)樁體1的樁頂沉降值明顯大于樁體2和樁體3,這是由于樁體1相比其他兩個樁更靠近右線隧道,因此盾構(gòu)機在右線掘進(jìn)過程中對樁體1的擾動更加明顯,隨著左線開挖的進(jìn)行,樁體2的沉降加劇,在右線貫通后與樁體1的沉降相差不大。而樁體3由于位于兩條線路外側(cè),且與盾構(gòu)隧道的距離相對較遠(yuǎn),因此受到的擾動明顯小于樁體1和樁體2。
3.3 樁基應(yīng)力分析
圖3為盾構(gòu)機掘進(jìn)過程中樁體的最大應(yīng)力值變化情況。

圖3 樁體最大應(yīng)力變化
(1)對于樁1,右線掘進(jìn)至與樁基同一水平面時(開挖步5),樁基的最大應(yīng)力減小,這是由于盾構(gòu)機正面推力和盾殼摩阻力作用的結(jié)果,待盾構(gòu)機通過后,樁體的最大應(yīng)力顯著增加,這是由于盾構(gòu)機通過后引起的樁體大幅度沉降導(dǎo)致樁體最大應(yīng)力增加,樁體最大應(yīng)力值約為800 kPa,相比未開挖前,最大應(yīng)力增加了76%。
(2)對于樁2及樁3,右線的掘進(jìn)導(dǎo)致樁體最大應(yīng)力降低,左線掘進(jìn)后,樁體應(yīng)力顯著增加,雙線貫通后,樁2及樁3的樁體最大應(yīng)力值分別提高了46%、22%。
3.4 樁基水平變形分析
圖4為號樁基水平變形隨盾構(gòu)機掘進(jìn)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到在右線開挖5步時,樁體向水平正向變形,最大水平變形值為1.3 mm,最大變形位于隧道所處位置,樁體產(chǎn)生正向的水平變形是由于盾構(gòu)機正面推力和盾殼摩阻力作用方向為正向所引起。待盾構(gòu)機通過后,樁體的水平變形轉(zhuǎn)變?yōu)榱怂截?fù)向變形,在右線掘進(jìn)至貫通后,樁體的水平變形達(dá)到最大,最大水平變形為3.5 mm,最大水平變形位置位于樁頂,這是由于樁底受到了限制,而樁頂為自由位移狀態(tài),樁的變形曲線類似于懸臂梁狀態(tài),從而最大水平變形出現(xiàn)在樁頂。

圖4 樁體水平變形
4 結(jié) 論
盾構(gòu)機沿曲線段掘進(jìn)時,地表最大沉降位于曲線段內(nèi)側(cè),雙線貫通后地表沉降槽以中心線位置對稱分布,雙線貫通后地表最大沉降為15.3 mm,滿足施工控制要求。
盾構(gòu)機通過樁體后對樁體造成的擾動越大,同時先行隧道開挖對樁體的擾動大于后行隧道,樁體到隧道的距離越近,受到的擾動越大,左右線貫通后,樁頂面的最大沉降為16.7 mm,處于安全控制范圍內(nèi)。
從樁體最大應(yīng)力分布情況來看,盾構(gòu)機沿曲線段掘進(jìn)時對樁體1的擾動最大,樁體最大應(yīng)力值相比未開挖前提高了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