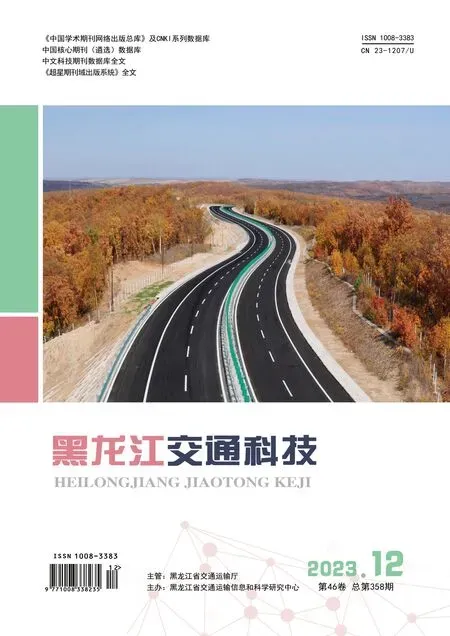軌道交通時代公路客運樞紐的發展
——以廣州市為例
羅 筱
(廣州市交通規劃研究院有限公司,廣東 廣州 510030)
公路客運樞紐是溝通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重要紐帶,依賴于高速公路網及地方公路網實現公路運輸集約化、專業化、信息化的重要節點。同時公路客運樞紐還是實現與水運、鐵路、機場等多種對外運輸方式之間、與城市公共交通、軌道交通等內部運輸方式之間有機銜接的關鍵樞紐。公路客運以服務中長途的對外交通為主,兼有短途客運交通運營,與鐵路運輸競爭關系激烈。
自國家發改委提出“打造軌道上的都市圈”后,近年來,軌道交通建設如火如荼。至2020年,廣東已實現了“市市通高鐵”的目標,廣東省內全域步入了“三小時經濟生活圈”;預計至2025年,珠三角各城市將實現高鐵“一小時通達”。軌道交通的蓬勃發展迅速搶占了中長途距離客運出行的市場份額,對傳統的公路客運交通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推動了傳統公路旅客運輸快速邁入衰退期。公路客運的客源大幅縮減,營收斷崖式下跌,面臨嚴重虧損與大面積客運站關停,這一現象在大灣區更為顯著,公路客運的發展亟待轉型升級。因此,推動傳統公路客運轉型升級,提高公路客運樞紐的競爭力,成為了國內學者近年來研究的熱點。而利用公路客運的獨有優勢引導公路客運與軌道交通適應性發展,錯位構建綜合運輸體系更為可持續。
1 公路客運樞紐的發展現狀
1.1 公路客運量逐漸萎縮
2014年廣州4個鐵路客運站與中心六區公路客運站的旅客發送量基本持平,此后五年公路客運量尚有微小幅度增長,如圖1所示,至2019年鐵路樞紐發送量增長至公路客運旅客發送量的4倍。往后,廣州市公路運輸客運量及旅客周轉量均呈現逐年下滑態勢,且公路客運量占比持續下跌。隨著高速鐵路和灣區城際軌道網的不斷發展,二者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2020年始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各類運輸方式客運量均大幅減少,水運及鐵路下降最為明顯,公路運輸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廣州市公路站場客運量18 054.02萬人次、客運周轉量180.62億人·km,分別比上年下降29.6%和31.3%[1]。

圖1 2016—2020年廣州市旅客運輸總量
1.2 功能單一的公路客運樞紐逐漸關停
自2019年開始,廣州市中心城區公路客運樞紐的搬遷陸續在推進。截止2021年底,除中心城區廣州市汽車客運站、越秀南客運站等6座客運站關停外,外圍城區包括番禺汽車站在內的3座客運站也相繼停止運營。
梳理現狀運營匯總及已停運的多座汽車客運站的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廣州市已關停的汽車客運站的特征
綜合分析廣州市內停運的火車站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問題。
(1)中心城區公路客運站承擔了大量長途線路的運營[2]。如越秀南客運站作為穗港澳專線直達快車場站位于廣州市老城區中心,運營車輛往返不可避免與中心城區內部交通流產生交織,僅在平峰期間中心城區內約7%的行程距離卻需要花近1/5的行程時間。廣州客運站主要運營省內及跨省長距離班線,同樣位于中心城區,周邊存在廣園西路、增槎路、恒福路等多個常態化擁堵點,大幅降低了對外運輸交通的效率。
(2)公路系統和城市道路系統之間缺乏過渡區。如黃埔客運站,公路客運站地理位置與周邊用地出入口相互影響,客流高峰時發車班次可達45班次/h,但客運站周邊存在物流公司,大型居住小區,沿線地塊開口繁多,平均間距僅65 m,相互之間影響大,關鍵通道存在較高的大車混入率,使得道路通行效率大打折扣。
(3)公路客運站與城市公共交通的銜接不緊密。如增城客運站、永泰客運站等與臨近軌道交通站點間距逾2 km,同時常規公交接駁線路不足10條,導致前往旅客需要多次甚至多方式換乘才能抵達客運站,極為不便,客運站和旅客之間不能形成一個良好的黏性關系。
(4)公路客運站設站未能與其他對外交通樞紐形成強大呼應[2]。如白云機場客運站,在軌道銜接失利的情況下,公路長途客運班線卻散布稀疏,15條省內專線僅覆蓋了中山、云浮、河源等粵中8個市區,線網輻射范圍并未拓展至粵東粵西,一定程度脫離了中長途的客運車流。
(5)公路客運樞紐功能單一,僅實現了交通轉換的功能,在后疫情時代頻繁離穗出省受限的情況下,難以維持穩定的客流。當下急需與大型交通集散點,如商業綜合體、貿易綜合體、旅游度假綜合體等深度綁定,相互誘導客流產生。
1.3 伴隨軌道上的大灣區推進建成,省內公路客運線路占比進一步縮減
自《關于粵港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的批復》發布后,城際鐵路建設發展如日中天,大灣區主要城市間1 h通達、主要城市至廣東省內地級城市2 h通達、主要城市至相鄰省會城市3 h通達的交通圈逐步形成。珠三角地區本是廣東公路客車市場的重點區域。伴隨穗莞深城際、廣佛環線、廣清城際等鐵路線陸續開通,原占比超過五成的省內公路客運線路運營直接遭到大幅削減,待廣汕高鐵、廣湛高鐵開通后,長途客運線路運營將再度被截流。
1.4 個性化運輸客流逐年提升,定制專線發展成為新趨勢
自2015年起,廣州市包車客運車輛逐年增長,如圖2所示,4年間包車客運所占比例提升7%,至2018年廣州市開始推進道路客運行業轉型升級,組織改革試點企業圍繞定制互聯網平臺推廣、定制客運線路開通(包含城際專線、校園專班、旅游景區專車等)、交通與旅游創新融合、規范配客點建設等各項目開展試點。2019年“如約城際”開行線路基本覆蓋深圳市、佛山市、珠海市等城市。門到門的個性化服務成為了公路客運發展的新機。在后疫情時代,為降低公共交通的疫情傳播風險,越來越多企業采用包車形式供職工通勤及外出旅游,定制專線受到追捧。
2 公路客運的發展方向
2.1 加強與城市其他交通系統的銜接,打造復合型的客運樞紐
建立便利高效的換乘條件,除了與對外交通樞紐(航空、鐵路、碼頭)的銜接之外,還需要綜合考慮與城市軌道交通、常規公交、出租車與網約車等各類交通方式的銜接,布局盡量緊湊,著力打造“零換乘”的交通體系,從平面空間縮短換乘距離,于立體空間優化換乘流線[4]。建議與空港、鐵路樞紐及相關建設部門聯合規劃、摒棄競爭模式改為協同建設,從上層規劃實現城市交通一體化發展。同時結合周邊地塊綜合開發娛樂、商業等休閑設施,營造商業環境,挖掘衍生客流,形成復合型的客運樞紐[5]。
2.2 調整運力結構,錯位爭取客流
至2021年末,我國鐵路運營里程為15.1萬km,公路運營里程已達528萬km。鐵路運輸雖從時空上拉近了廣州與其他城市中心城區的距離,但高建設成本使之難以輻射至末端的村鎮,公路客運憑借點多面廣、靈活性強的先天優勢,可針對性發展傳統點對點式運營線路,并著力開發點到線式的運營線路。錯位發展的同時,不僅對鐵路運輸范圍進行了延伸,也擴大了客運服務范圍,縮短了最后一公里。
(1)對于中短距離的街鎮散點之間可以發展直達客運線路。廣州市核心對外樞紐雖已將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但大多數外圍區域村鎮搭乘軌道交通、前往鐵路樞紐存在多次轉折換乘,時間將超過90 min。對于中短途的旅客運輸,鐵路運輸在時間成本上的優勢并不突出,公路直達客運線路在便利性和舒適度上都更有吸引力。這使得公路客運樞紐逐步向城市外圍區域遷移,與城市道路形成緩沖區,減少城市內部交通壓力的同時,利好于城市外圍的土地利用以及產業開發,可挖掘城市經濟發展的新活力點[6]。
(2)對于遠距離的村鎮之間可以開發點-線-點式的運營模式。收緊傳統公路客運的對外發送的功能,將公路客運打造為“鐵路+城市軌道網絡”的擴展包,利用鐵路運輸時間穩定且客流龐大的優勢發展鐵路站點延伸向兩端短途接駁客運線路。這使得公路客運樞紐在各個城市軌道交通末端站點發散,遠離中心城區的布局模式減少了對外交通與城市內部交通的交織,減輕了中心城區的過度開發。
(3)緊密聯系景區旅客集散中心形成專線專班。廣州市內已有運營成熟的城區往返景點的旅游線路,但不少景點推薦游覽時間在半日之內,自黃金周改為當下小長假這種節假日模式后,放假期間日均旅游景點數量以及多日游覽景點總數都有了明顯增加,且廣州市外圍景區之間路途遙遠,這就形成了景區與景區之間的旅客輸送需求。不同于旅游公司定制的旅行線路,公路客運在出行時間和線路選擇上都更靈活,給予游客更自主更多元的選擇。且公路客運相比城市公共交通的換乘的不便和空間的擁擠,能在旅途中給予乘客更為舒適的休憩空間。同時還可以將景區周邊,如民宿、美食、特產、紀念品等嫁接到客運體系中,助力營造良好的旅游生態。
(4)外圍區域公路客運樞紐向常規公交場站轉變。交通設施的開發建設或轉型升級均立足于交通需求的變化。現存的公路客運樞紐更新、升級,不斷與新時代更加契合,進入衰退期的公路客運出行需求未來將長期在中低位徘徊不可避免。隨著廣州市外圍城區的土地開發建設,常規公交覆蓋率不足、公交場站短缺的問題,逐漸被暴露出來,而被淘汰的客運站搬遷合并,騰挪出不少建設用地。為了盡多地利用原有基礎設施,縮減建設成本,同時解決公交場站建設不足的問題,建議整合外圍區域公路客運樞紐活化轉變為常規公交場站,助力城市公共交通發展。
3 結 語
通過剖析公路客運發展停滯乃至倒退的成因,結合當下客運發展的需求及特征,探討未來公路客運發展的方向和策略,對引導公路客運樞紐的運營建設適應適應一體化、集約化的發展趨勢,重新激發公路客運發展新活力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