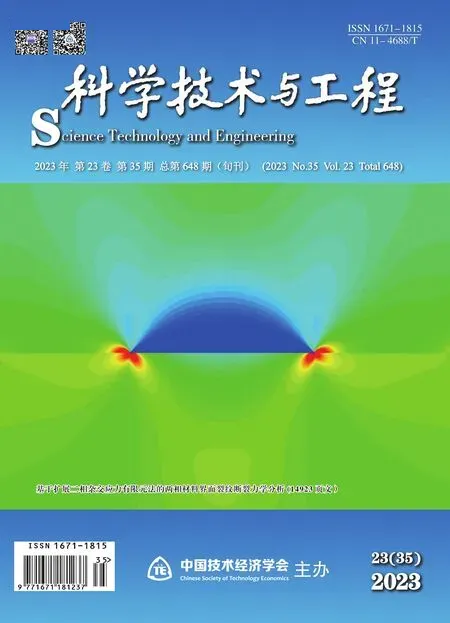基于多源數(shù)據(jù)的城市內(nèi)部空間交互特征:以福州市主城區(qū)為例
真詩泳, 林欽賢, 張露丹, 李嘉政, 林玉英, 陳誠, 潘自寶, 胡喜生*
(1.福建農(nóng)林大學交通與土木工程學院, 福州 350108; 2.福建師范大學旅游學院, 福州 350117; 3.平潭綜合實驗區(qū)交通與建設局, 平潭 350499)
不同功能區(qū)相互組合形成了城市的內(nèi)部空間結構,作為城市人群活動的基本空間單元,城市功能區(qū)是城市規(guī)劃、管理中的重點問題。人群在不同功能區(qū)中的流動行為體現(xiàn)了地理空間要素之間的交互關系[1],并潛在地反映了城市的社會經(jīng)濟、資源分配等狀況[2]。對城市劃分不同功能區(qū)并分析其在城市空間內(nèi)的地位以及人群在不同功能區(qū)間的流動狀態(tài),能夠反映城市熱點功能區(qū)域的時空分布,并為城市交通管理、公共交通規(guī)劃提供參考,從而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
在信息化的推動下,城市內(nèi)部空間可以看作是一個由人和空間要素構成的高速“流動空間”[3],這種人群在不同地理空間中進行移動和信息交換的行為也被稱為空間交互[4-5]。“流動空間”是地理學和城市規(guī)劃學中的重要研究范式,其核心在于通過分析城市內(nèi)部“流”形成的動態(tài)網(wǎng)絡結構[6],來揭示城市空間中的潛在問題。隨著信息科學的發(fā)展,手機信令、軌跡數(shù)據(jù)等大數(shù)據(jù)被廣泛運用到來描述“人流”行為中[7-9]。傳統(tǒng)的人流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相比,交通大數(shù)據(jù)能夠提供小尺度空間內(nèi)的流動信息[10],這為研究城市居民的時空動態(tài)特征提供了幫助[11]。目前,利用交通大數(shù)據(jù)與城市空間結構相聯(lián)系的研究主要包括通勤人群的職住區(qū)位及行為感知[12-13]、居民活動空間及都市圈層級劃分[14]、城市公共服務設施可達性分析[15-16]等方面。然而,這些研究側重于探討單一空間結構的分布模式,缺少對空間結構之間的功能聯(lián)系關系的關注。
城市內(nèi)部因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分化等因素的影響,會出現(xiàn)商業(yè)、居住、公共等功能分區(qū)[17],作為表征城市形態(tài)的和人群出行活動的基本空間單元,功能區(qū)與人群流動的研究熱點主要包括出行時空分布特征[18-19]、出行熱點[20]、功能區(qū)域 對人群出行的影響[21]等方面。如利用多源數(shù)據(jù)對城市功能區(qū)及識別,研究發(fā)現(xiàn)功能區(qū)在時空因素的影響下會影響人群出行的活力[22-25];通過分析人群在不同功能區(qū)之間出行的時序空間特征,研究城市人群在不同功能區(qū)之間集散模式[26-27];通過社交媒體數(shù)據(jù)和POI(point of interests)數(shù)據(jù)對城市功能空間結構進行測量,發(fā)現(xiàn)功能布局會決定城市空間結構和人類的社會活動狀態(tài)[28];對城市功能區(qū)熱點區(qū)域進行地理識別[29-30]等。目前對于功能區(qū)視角下的人流聯(lián)系研究,通常聚焦于時空尺度下的人群聚集特征及影響關系等方面,卻忽略了人流交互網(wǎng)絡所反映出的城市功能區(qū)地位格局及組團特征,城市功能區(qū)的地位格局可以為探究城市內(nèi)部空間結構提供新的視角,并服務于城市交通規(guī)劃及管理。復雜網(wǎng)絡分析方法對于挖掘流動空間中各節(jié)點的網(wǎng)絡結構特征、重要性地位等信息[31-32],因此以信息流、人流、貨流等要素流為研究對象,對較大尺度(如城際、省際)下的流動網(wǎng)絡關系已獲得了較廣泛的應用[33-36]。由于傳統(tǒng)的OD(origin, destination)調(diào)查數(shù)據(jù)樣本少且成本高,難以刻畫城市內(nèi)部功能布局以及空間交互的總體特征,而遷徙大數(shù)據(jù)、人口普查大數(shù)據(jù)等均是對地級市及以上的統(tǒng)計信息,導致以往基于大數(shù)據(jù)對城市內(nèi)部功能進行識別并探討不同分區(qū)之間的空間交互關系的研究鮮見報道。
《2021年度中國城市交通報告》顯示,福州市擁堵程度在全國排名前列,福州市委市政府為緩解城市擁堵,著力開展了治理城區(qū)交通擁堵專項行動。鑒于此,以福州市主城區(qū)為研究區(qū),以交通小區(qū)為分析單元,利用POI數(shù)據(jù)對研究區(qū)進行功能區(qū)劃分,進一步挖掘手機信令大數(shù)據(jù)中蘊含的居民出行信息,對城市內(nèi)部空間交互進行量化表達,分析城市交通小區(qū)之間的空間交互格局;同時,采用復雜網(wǎng)絡分析方法,對功能區(qū)在空間交互活動中的活躍度和網(wǎng)絡地位進行評價;挖掘功能區(qū)之間的出行距離衰減特征。以期為福州市城市公共交通優(yōu)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科學依據(jù)。
1 數(shù)據(jù)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區(qū)域
福州市是福建省省會,位于中國東南沿海,下轄6區(qū)、6縣及1個縣級市,是粵閩浙沿海城市群的中心城市,2021年福州市常住人口約842 萬,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11 324 億元,人均地區(qū)生產(chǎn)總值 135 298 元。《福州城市綜合交通規(guī)劃(2020—2035年)》指出福州市交通現(xiàn)狀仍存在問題,如公交優(yōu)先體系不夠完善,公共交通吸引力不足。同時福州都市圈作為國家級都市圈,以福州市主城區(qū)為核心區(qū)所服務的人口也將逐漸提高,將對福州市城市公共交通系統(tǒng)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本研究以福州市主城區(qū)平原地帶作為研究區(qū)域,包括鼓樓區(qū)、臺江區(qū)、倉山區(qū),以及晉安區(qū)、馬尾區(qū)、閩侯縣的部分行政地界(圖1),是福州市都市圈規(guī)劃中劃定的核心區(qū)域,也是福州市境內(nèi)人口密集度較高的區(qū)域。
1.2 數(shù)據(jù)來源
1.2.1 手機信令數(shù)據(jù)
采用2018年12月10—16日一周內(nèi)的福州市移動用戶手機信令數(shù)據(jù),原始數(shù)據(jù)記錄了包括用戶ID、基站位置ID、時間、事件類型(如開機、通話、切換基站等)、位置坐標等信息。對原始數(shù)據(jù)預處理后,進行用戶出行鏈識別,處理流程如下:①選取夜間

圖1 福州市主城區(qū)區(qū)位及交通小區(qū)概況Fig.1 The location of the main urban area of Fuzhou city and traffic zone
(00:00—05:00)里,在相同基站位置的停留時間在1 h以上且不少于4 d記錄的手機用戶為研究對象,識別手機用戶的居住地的停留;②識別用戶在一天內(nèi)停留時間大于等于60 min的基站位置,作為一天內(nèi)用戶出行鏈中的停留點,將兩個相鄰的停留點之間的記錄視為一次出行;③從市交通部門收集了福州市交通小區(qū)地圖(圖1),在研究區(qū)域內(nèi)共計1 040個交通小區(qū),交通小區(qū)為街道社區(qū)或用地屬性相近的地塊,將手機用戶一天出行軌跡數(shù)據(jù)中的出發(fā)地和目的地匹配至對應小區(qū),得到用戶在交通小區(qū)之間的出行OD矩陣,最終識別出了225 萬個居民用戶的一周的出行數(shù)據(jù)。
1.2.2 POI數(shù)據(jù)
在高德地圖開放平臺(lbs.amap.com)上,利用python爬蟲技術獲取了研究區(qū)域內(nèi)的POI數(shù)據(jù),經(jīng)過坐標轉換和重復點篩除后,共計168 536 個,POI種類包括餐飲服務、購物服務、商務住宅、地名地址信息、政府機構及社會團體科教文化服務等,本研究根據(jù)城市功能區(qū)種類將POI數(shù)據(jù)歸類為6大類,如表1所示。

表1 POI分類結果Table 1 The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POI data
1.3 研究方法
1.3.1 功能區(qū)識別
交通小區(qū)將城市劃分成了眾多面積不等的地塊,為了了解小區(qū)在城市中的功能定位以及區(qū)域內(nèi)主要的活動人群,對交通小區(qū)進行功能區(qū)識別[18]。首先計算功能區(qū)POI的密度指數(shù)Pi,j,計算公式為

(1)
式(1)中:i指交通小區(qū)i;j指第j類POI;Pi,j為小區(qū)i中第j類POI的密度指數(shù);Qi,j為小區(qū)i中第j類POI的數(shù)量;Ai為小區(qū)i的面積。
通過POI分類結果可知各類型POI的數(shù)量差異較大,如商業(yè)服務業(yè)設施的POI數(shù)量幾乎遠高于其他類型POI,為了消除POI數(shù)據(jù)的數(shù)量級差異對功能區(qū)識別結果的影響,對POI密度指數(shù)進行min-max標準化處理,公式為

(2)
式(2)中:Pnor,(i,j)為小區(qū)i第j類POI標準化后的密度指數(shù);Pmin,j為第j類POI的密度指數(shù)最小值;Pmax,j為第j類POI的密度指數(shù)最大值。
最后通過計算小區(qū)內(nèi)各類POI的頻率密度Fi,j,來判斷小區(qū)的功能類型,計算公式為

(3)
式(3)中:Fi,j為小區(qū)i中第j類POI的頻率密度;Pnor,(i,j)為小區(qū)i第j類POI標準化后的密度指數(shù);∑jPnor,(i,j)為小區(qū)i中各類POI標準化密度指數(shù)之和。
最終,若小區(qū)內(nèi)某一類POI的頻率密度>50%時,則將其識別為單一功能區(qū);若小區(qū)內(nèi)有兩類頻率密度值較高的POI處在20%~50%時,則識別該小區(qū)為這兩類POI的混合功能區(qū);若某小區(qū)內(nèi)有兩類以上POI的頻率密度在20%~50%且包含所有POI類型,則識別為綜合功能區(qū)。當小區(qū)內(nèi)存在各類POI數(shù)量均為0時,識別為無數(shù)據(jù)區(qū)域。
1.3.2 空間交互強度
交通小區(qū)之間的空間交互強度能夠反映著居民在不同地域間的出行流動情況,是判斷區(qū)域人流活力和影響力的指標,將小區(qū)間相互出行的發(fā)生次數(shù)之和定義為小區(qū)間的交互強度S,表達式為
S=Sij+Sji
(4)
式(4)中:Sij為由小區(qū)i至小區(qū)j發(fā)生的出行次數(shù);Sji為由小區(qū)j至小區(qū)i發(fā)生的出行次數(shù)。
1.3.3 網(wǎng)絡中心性指標
(1)加權度中心性。加權度中心性表現(xiàn)了功能區(qū)在空間交互中的活躍度和重要性,它代表了功能區(qū)在一天內(nèi)與空間內(nèi)其他功能區(qū)之間產(chǎn)生的交互總次數(shù),由加權入度和加權出度組成。計算公式為

(5)
(6)
W(i)=Win(i)+Wout(i)
(7)
式中:W(i)為加權度中心性;Win(i)為加權入度;Wout(i)為加權出度;Ni為與小區(qū)i有產(chǎn)生空間交互記錄的小區(qū)的集合;δji為由j小區(qū)至i小區(qū)產(chǎn)生的出行次數(shù);δij為由i小區(qū)至j小區(qū)產(chǎn)生的出行次數(shù)。
(2) PageRank中心性。PageRank算法是由Google提出的一種網(wǎng)頁排序算法,目前已被廣泛運用于復雜網(wǎng)絡分析中,它反映了節(jié)點是否與網(wǎng)絡中的其他重要節(jié)點有緊密的聯(lián)系,本研究利用PageRank中心性指標評價福州市主城區(qū)各類型功能區(qū)在空間交互網(wǎng)絡分析中的網(wǎng)絡地位。
1.3.4 空間交互距離衰減效應
距離衰減效應是指交互強度隨著距離的遞增而減弱的現(xiàn)象,目前常用的距離衰減函數(shù)包括冪律型和指數(shù)型,本研究將采用指數(shù)型衰減函數(shù)進行擬合,具體公式為
f(d)=αe-βd,β>0
(8)
式(8)中:α為振幅;β為距離衰減系數(shù);d為距離。
2 結果與分析
2.1 福州市主城區(qū)功能分區(qū)識別
利用式(1)~式(3),對交通小區(qū)進行功能區(qū)識別,共識別出公共用地、商業(yè)服務業(yè)用地、居住用地、工業(yè)用地、科教文化用地及綠地景點用地六類單一功能區(qū)、15類混合功能區(qū)及綜合功能區(qū)和無數(shù)據(jù)區(qū)域(圖2)。
研究區(qū)內(nèi)共識別出單一功能區(qū)、混合功能區(qū)、綜合功能區(qū)及無數(shù)據(jù)區(qū)域共280 個、668 個、83 個、9 個,混合功能用地偏多。其中,以公共及居住相關類型用地為主,兩者合計約占研究區(qū)域總面積的64%。居住類型相關功能區(qū)在空間上分布最廣,約占據(jù)了研究區(qū)域總面積的36%,其中“居住-公共”“居住-商服”是分布較多的混合功能區(qū)類型;公共服務單一功能區(qū)主要為醫(yī)院、交通樞紐、政府機構等公共設施場所,公共服務相關類型功能區(qū)占據(jù)了研究區(qū)域總面積的39%;科教文化單一功能區(qū)以大中專院校和研究機構為主,在倉山區(qū)、閩侯片區(qū)和晉安城區(qū)內(nèi)分布較多,與科教文化功能混合的功能類型主要有公共功能和居住功能;商業(yè)服務業(yè)單一功能區(qū)在空間上分布較少,主要為各區(qū)域內(nèi)的成熟商業(yè)服務業(yè)中心。盡管商業(yè)服務業(yè)設施的POI數(shù)量較多,但經(jīng)過POI密度指數(shù)歸一化處理后,大部分小區(qū)的“商服”功能會與其他功能類型相結合成為混合功能區(qū),其中“公共-商服”“工業(yè)-商服”是主要的混合功能區(qū)類型,兩者共占到了研究區(qū)域總面積的10.2%;工業(yè)類型功能區(qū)主要分布在倉山、鼓樓、晉安、馬尾等區(qū)的工業(yè)和產(chǎn)業(yè)園基地,在空間上通常連片分布,工業(yè)類型混合功能區(qū)以“工業(yè)-公共”“工業(yè)-商服”為主;綠地景點單一功能區(qū)以公園、景區(qū)為主,主要集中在鼓樓區(qū)和晉安區(qū),約占研究區(qū)域總面積的5%,綠地功能主要與公共功能混合;綜合功能區(qū)是功能體系較為完善的小區(qū),約占研究區(qū)域總面積的9%,不同區(qū)位的綜合功能區(qū)內(nèi)部所承擔的主要功能類型有所不同,如臺江、晉安、馬尾內(nèi)的綜合功能區(qū)多依托于“商服”中心或居住集中地,鼓樓、倉山兩區(qū)的綜合功能區(qū)則多以公共功能為主體;無數(shù)據(jù)區(qū)主要位于城市的未開發(fā)地或遠郊。

圖2 城市功能區(qū)空間分布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functional areas
進一步統(tǒng)計各類型功能及綜合功能區(qū)在各行政區(qū)域中的出現(xiàn)頻次(圖 3)。可以看出,鼓樓區(qū)的公共服務功能的出現(xiàn)頻次較區(qū)域內(nèi)其他功能類型明顯更高,共有113 個功能區(qū)具有公共服務屬性;其次,鼓樓區(qū)的科教文化功能的出現(xiàn)頻次在各行政區(qū)中位居前列。臺江區(qū)的商服、公共、居住三類功能的出現(xiàn)頻次明顯偏高,是其他功能類型的5~6倍,此外,臺江區(qū)與其他行政區(qū)相比出現(xiàn)了最多的綜合功能區(qū)。倉山區(qū)由于較廣的行政地界,“商服”、科教文化、綠地景點、工業(yè)等功能的出現(xiàn)頻次相對均衡。晉安城區(qū)內(nèi)的城市功能區(qū)以居住功能和公共功能為主,同時“商服”功能的出現(xiàn)頻次較高。馬尾城區(qū)由于其港口屬性,工業(yè)功能區(qū)的出現(xiàn)頻次在區(qū)域內(nèi)僅次于居住功能。閩侯片區(qū)內(nèi)的功能區(qū)以居住功能居多,科教文化、公共服務、“商服”功能的出現(xiàn)頻次較為相近。

圖3 不同功能類型的出現(xiàn)頻次Fig.3 Frequency of different functional types
2.2 福州市主城區(qū)空間交互強度分析
利用式(4)計算一周內(nèi)工作日及周末各交通小區(qū)之間的平均空間交互強度,將交互強度大于100的交互流線利用自然間斷法分成五個等級(圖4)。一周內(nèi)日均總交互流量從高到低依次為倉山區(qū)(2 218 884 次)、晉安城區(qū)(1 508 036 次)、鼓樓區(qū)(1 468 575 次)臺江區(qū)(725 601次)、閩侯片區(qū)(582 441 次)、馬尾城區(qū)(338 317次)。從工作日和周末的對比來看,工作日各小區(qū)間的交互強度明顯強于周末,這表明在工作日內(nèi),人群在空間中的往來出行需求更高。在周末,可以發(fā)現(xiàn)空間中相鄰或鄰近的小區(qū)之間的高強度交互流線相對有所增加;鼓樓區(qū)及臺江區(qū)的內(nèi)部空間交互流線最為密集且強度相對較高,作為福州市的政治、經(jīng)濟中心,兩區(qū)無論在人流量還是區(qū)域人員活躍度都展現(xiàn)了較大的優(yōu)勢。倉山區(qū)和晉安城區(qū)的空間交互格局則出現(xiàn)明顯的空間不平衡狀況,晉安城區(qū)東部遠郊地區(qū)的空間交互流線遠不及鄰近鼓樓、臺江的老城區(qū)密集,倉山區(qū)的空間交互則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金山奧體片區(qū),東南部三江口片區(qū)的交通小區(qū)之間交互流線則普遍較為稀疏。馬尾城區(qū)內(nèi)部交通小區(qū)之間的交互強度較大,這說明在人群在區(qū)域內(nèi)的流動量很大。閩侯片區(qū)內(nèi)部的存在較為突出的高強度交互流線,片區(qū)南部的空間交互流線較為稀疏。

圖4 交通小區(qū)區(qū)間平均空間交互強度Fig.4 Average spatial interaction strength among traffic zones
2.3 福州市主城區(qū)功能區(qū)中心性評價
2.3.1 加權度中心性評價
為了比較不同行政區(qū)域內(nèi)各功能區(qū)在空間交互中的活躍度和在跨行政區(qū)域空間交互中的地位,結合一周內(nèi)各天的出行OD數(shù)據(jù),利用式(6)~式(8)度量了工作日及周末下各類型功能區(qū)的加權度中心性的平均值以及跨行政區(qū)域交互比例(圖5)。
鼓樓區(qū)軟件園片區(qū)的“居住-工業(yè)”類型功能區(qū)以及五四路周邊的“工業(yè)-公共”功能區(qū)是該區(qū)內(nèi)工作日平均加權度中心性最高的功能區(qū);在周末,鼓樓區(qū)功能區(qū)的加權度中心性整體有所下降,但東街口片區(qū)附近的“商服”及綠地景點功能區(qū)則相反呈上升趨勢,并且大部分功能區(qū)的跨行政區(qū)交互比例均有所上升,這說明鼓樓區(qū)在周末吸引輻射區(qū)外人群的能力更強。臺江區(qū)內(nèi)各類型功能區(qū)的加權度中心性在一周內(nèi)均處于較高的水平,其中“商服”和“科教文化”相關功能區(qū)的地位最高;在周末,臺江區(qū)的商業(yè)服務業(yè)用地的中心性地位出現(xiàn)明顯提升;臺江區(qū)各功能區(qū)的跨區(qū)交互比例普遍較高,其中“工業(yè)-科教文化”的跨區(qū)交互比例更是高達60%,說明臺江區(qū)是城市內(nèi)人群跨區(qū)域出行的集中地。倉山區(qū)和晉安城區(qū)均呈現(xiàn)出了以“商服-科教文化”、綜合功能區(qū)為核心功能區(qū),以居住相關混合功能區(qū)為主體交互區(qū)域的空間交互模式,這表明“商業(yè)服物業(yè)+學校”類型用地和綜合服務用地在城市中的輻射和吸引人群的作用是顯著的。馬尾城區(qū)的“商服”相關混合功能區(qū)和綜合功能區(qū)是人群聚散的熱點功能區(qū),對其他功能區(qū)形成了斷層式的優(yōu)勢。閩侯片區(qū)內(nèi)由大學構成的科教文化用地是空間交互的優(yōu)勢功能區(qū),它所主要服務的大學生群體流動性較強。

圖5 功能區(qū)加權度及跨區(qū)交互比例Fig.5 Weighted degree centrality and proportion of inter-district interactions of each functional areas
2.3.2 PageRank中心性評價
利用Gephi軟件內(nèi)置的PageRank算法對研究區(qū)內(nèi)各功能區(qū)的網(wǎng)絡地位進行度量,并使用自然間斷法將PageRank值劃分成了5個等級,工作日及周末的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PageRank指標空間分布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PageRank index
從空間分布格局上看,PageRank值較高的功能區(qū)在鼓樓、臺江、晉安三區(qū)內(nèi)主要集中在二環(huán)線內(nèi)的核心區(qū),呈小范圍組團現(xiàn)象。而在城市外圍的閩侯片區(qū)和馬尾城區(qū)內(nèi),PageRank值較高的功能區(qū)則有明顯的聚集特征,它們內(nèi)部優(yōu)勢功能區(qū)之間較強的空間交互量是其網(wǎng)絡地位較高的主要原因。周末PageRank值的分布格局與工作日差異不大,但PageRank高等級的功能區(qū)數(shù)量有所下降,說明周末人群的出行熱點區(qū)域相對集中。
統(tǒng)計工作日和周末下,空間中各類型功能區(qū)的PageRank均值及總和(表2)。在工作日,PageRank總和及平均值均較高的功能區(qū)類型包括綜合功能區(qū)、“公共-商服”等,它們在交互網(wǎng)絡中有較高的地位,而綠地景點相關功能區(qū)的總和及均值均較低,除部分著名綠地景點外,大部分綠地景點功能區(qū)在空間交互中的吸引和輻射能力明顯不如其他類型功能區(qū)。在周末,“商業(yè)服務業(yè)”和“綠地景點”相關類型功能區(qū)的PageRank中心性均有明顯提高,工業(yè)及公共相關類型功能區(qū)的PageRank中心性則有所下降。此外,單一功能區(qū)的網(wǎng)絡地位普遍不及同類型混合功能區(qū)。

表2 功能區(qū)PageRank指標統(tǒng)計Table 2 The statistics of PageRank index of each functional areas
2.4 福州市主城區(qū)功能區(qū)交互距離衰減效應分析
利用ArcGIS中的近鄰分析工具度量各功能區(qū)之間的歐氏距離,并統(tǒng)計空間中每公里內(nèi)發(fā)生的交互量,發(fā)現(xiàn)交互強度與距離呈指數(shù)遞減分布關系(圖7),可用式(8)進行擬合并計算距離衰減系數(shù)β。
在工作日,居住用地相互之間的距離衰減效應最為明顯,在2~3 km區(qū)間內(nèi)的累計交互比例即達到了90%;居住用地與科教文化用地、綠地景點累計交互比例達到90%的距離在3~4 km區(qū)間;居住用地與公共用地、工業(yè)用地、綜合功能區(qū)及商服用地之間累計交互比例達到90%的距離則均在5~6 km區(qū)間。在周末,居住用地與公共用地及工業(yè)用地的衰減系數(shù)增長較為明顯,達到累計交互比例90%的距離區(qū)間縮短至4~5 km;而居住用地與“商服”用地及綠地景點的衰減系數(shù)則有所下降,居住用地與“商服”用地之間累計交互比例達到90%的距離區(qū)間延伸至了6~7 km。進一步統(tǒng)計了工作日及周末各類型功能區(qū)在空間交互中作為出發(fā)地及目的地時的平均出行距離(圖8)。可以看出,在“居住-工業(yè)”“工業(yè)-商服”和工業(yè)用地之間出現(xiàn)3個平均出行距離的峰值,且工作日明顯高于周末,平均出行距離均在2 km左右;在“居住-公共”、工業(yè)-公共和工業(yè)-科教文化之間出現(xiàn)谷值,且周末明顯低于工作日,平均出行距離在1.6 km左右。整體結果與距離衰減效應結果相符。

圖7 不同功能區(qū)間空間交互的累計比例曲線Fig.7 Accumulative proportion curve of spa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functional areas

圖8 各類型功能區(qū)的平均出行距離Fig.8 Average travel distance of each functional areas
3 結論與討論
3.1 結論
本研究利用POI數(shù)據(jù)識別城市交通小區(qū)的功能區(qū)類型,并采用手機信令數(shù)據(jù)對城市內(nèi)部人群在交通小區(qū)中的交互行為進行量化,結合功能區(qū)識別結果和復雜網(wǎng)絡分析方法,對城市功能區(qū)的中心性地位及各類型功能區(qū)之間空間交互的距離特征進行了探究,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福州市主城區(qū)類型的城市功能區(qū)以混合功能區(qū)為主,其中,公共和居住相關類型功能區(qū)占比較大,共占研究區(qū)域總面積的64%。
(2)工作日各小區(qū)間的交互強度明顯高于周末。鼓樓區(qū)和臺江區(qū)人流活動最為活躍;倉山和晉安兩區(qū)內(nèi)部空間交互格局存在顯著的不平衡特征;馬尾城區(qū)與閩侯片區(qū)都存在內(nèi)部空間交互較為活躍的小區(qū)。
(3)功能區(qū)在空間交互中的中心性地位因區(qū)位和時間段的影響有所差異:如臺江區(qū)的“商服”相關功能區(qū)優(yōu)勢地位遠高于其他行政區(qū)域的同類型功能區(qū),工業(yè)相關類型功能區(qū)的中心性地位在工作日及周末普遍存在較大的差異,科教文化類型功能區(qū)是聚散區(qū)域內(nèi)人群的核心區(qū)域等。網(wǎng)絡地位較高的功能區(qū)類型主要集中在二環(huán)線以內(nèi),在城市外圍區(qū)域則有明顯的聚集現(xiàn)象。
(4)各類型單一功能區(qū)在工作日與居住用地達到90%累計交互比例的距離從小到大依次為:居住用地>科教文化用地>綠地景點>公共用地>綜合功能區(qū)>工業(yè)用地>商服用地住用地;周末居住用地與公共用地及工業(yè)用地的衰減系數(shù)增長較為明顯,而與“商服”用地、科教文化用地及綠地景點的衰減系數(shù)則有所下降;各類型功能區(qū)在空間交互中產(chǎn)生的平均行程距離反映居住類及公共服務類功能區(qū)的距離普遍較短,“商服”類、科教文化類及綠地景點類功能區(qū)的平均行程距離體現(xiàn)為較為明顯的周末增長態(tài)勢。
3.2 討論
通過分析福州市主城區(qū)的功能區(qū)分布情況,發(fā)現(xiàn)鼓樓區(qū)公共相關的功能區(qū)占比較高,而居住相關功能區(qū)占比相對較低;馬尾城區(qū)工業(yè)相關占比較高而居住相關占比較低,結合各類型功能區(qū)的中心性地位及跨區(qū)域交互比例,可以推斷福州市主城區(qū)的鼓樓、馬尾等區(qū)域存在一定的職住分離現(xiàn)象,應通過完善公共交通的方式達到職住平衡。受地域、時間段等的影響,功能區(qū)呈現(xiàn)出不同的空間交互格局和地位,在城市區(qū)域發(fā)展中,應保持和發(fā)揮區(qū)域內(nèi)優(yōu)勢功能區(qū)的輻射、吸引能力,形成多中心化的城市發(fā)展格局;同時,可對不同行政區(qū)內(nèi)的熱點功能區(qū)域實施有針對性的交通優(yōu)化政策,以提高城市的交通質量和管理水平。還可參考居住用地與其他功能用地之間的距離衰減效應以及各類型功能區(qū)的平均行程距離,進行相應的交通系統(tǒng)優(yōu)化,對于出行距離分布較遠的交互線路之間增加公共交通投入;而對于平均出行距離較低的功能區(qū)則增加設置騎行專用道,引導市民綠色出行,降低交通碳排放。
然而,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手機信令數(shù)據(jù)在描述人群出行目的方面存在空缺,導致混合功能區(qū)之間交互行為相對難以界定區(qū)分,未來應融合多源大數(shù)據(jù),判斷功能區(qū)主要吸引和輻射的人群類型以及人群的出行目標;此外,不同功能區(qū)在面積、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一定差異,未來還需要對各類因素對功能區(qū)活躍度及網(wǎng)絡地位的影響進行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