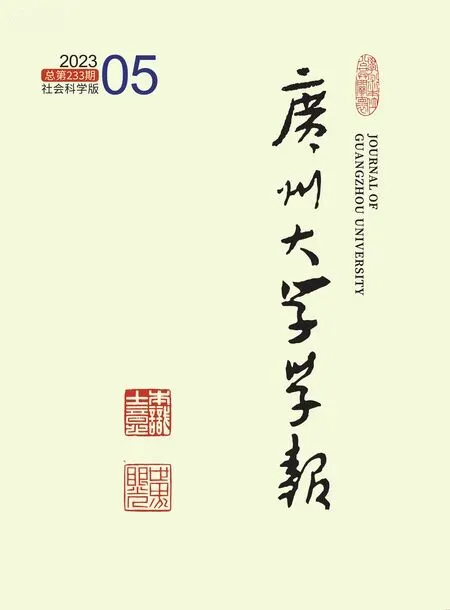彌散:數字日常下的公共知識分子
王 峰
(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知識分子是一種特殊的身份,理解這一身份并不容易。薩義德如此發問:“知識分子究竟為數眾多,或只是一群極少數的精英?”[1]是啊,我們說到知識分子的時候,到底是指眾多具備專業知識的人,還是指那些社會中最頂尖的精英呢?這無疑是一個麻煩的問題,因為我們必須首先限定自己的討論對象,才能知道我們要討論什么。
我們必須承認,知識分子的身份是混雜的,尤其是在時下這個時代。我們在此討論的公共知識分子無疑具有一個很好的限定作用,因為這一指謂直接劃定了范圍,讓我們發現,公共知識分子就是那些對公共問題感興趣并愿意為之發聲的人。在時下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往往指那些具備一定專業技能的人,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獲得學士、碩士乃至博士學位,在社會上普遍受到尊重,但似乎主要是在專業范圍內發揮影響力,一旦踏出專業圈,就可能籍籍無名。知識分子之為公共,就在于他不局限于某一專業,對某些普遍性社會現象發言,并樂于分享自己的見解,獲得贊同。從此而論,公共知識分子只是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在這里,我們可以發現兩個特性:一是對整體性問題感興趣,愿意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入分析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社會整體性價值是其思考的對象,也是直接的動力;二是具備扎實的專業知識和廣博的知識面,他很可能首先是某一方面的專家,獲得尊重,進而對社會問題進行評價,進一步獲得人們的贊同。 公共知識分子的來源非常廣泛,他們可能是專家學者、媒體人、作家、藝術家,等等。
康德指出,啟蒙就是清除強加于自己的不成熟,而其方式就是公開地表達自己獨立的判斷。這說明,知識分子要具備批判思考的能力,不會被政治、經濟或其他利益集團所左右,而是會根據自己的判斷和價值觀來做出決斷,堅持自己的原則,并為此付出努力。公共知識分子往往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愿意思考社會整體性問題,思考人類文明的未來,并通過自己的言論和行動來影響社會,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然而,現代社會發展將啟蒙時代知識分子與公共性天然合一的狀態逐步切分,知識分子的專業性質得到發揚,而整體性關懷開始下降。工業革命以來,專業知識分子開始大量涌現,知識密集型職業逐漸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比如,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著電力、石油等新興產業的發展,工程師、技術員等知識密集型職業應運而生。在這一時期,知識密集型職業主要以機械和技術為主,如汽車制造、電力工程等。20世紀中葉至70年代,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計算機科學、通信技術等領域的知識密集型職業逐漸崛起。這一時期的知識密集型職業以電子和信息技術為主,如計算機程序員、網絡工程師等。
知識真正成為可交換的產品,正是信息技術促成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信息化進程加速,全球化也成為一個顯著的現象,知識分子借助信息化、全球化獲得了此前不具備的傳播力量。21世紀以來,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更進一步推進知識的傳播,整個社會產業逐步變成知識密集型,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知識表達獲得了廣闊的空間,人的表達的自由度和空間大幅上升。那么,我們就要問,公共知識分子在這樣的自由傳達場域中傳播力得到提升了嗎?答案卻并非是肯定的。
不可否認,科技的迅猛發展為知識傳播帶來了巨大助推力。計算機、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等技術的普及和應用,使得信息獲取、處理和傳輸更加高效和便捷。同時,新興技術領域如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和區塊鏈等也催生了更多的專業知識需求。全球化使得知識傳播的范圍不再局限于本地,而是面向全球。這些看起來都是正面的。在互聯網興起之前,知識分子是知識的代言人,在科學領域占據重要地位,同時也是公共領域的發言人。那么,互聯網興起之后,知識的力量應該得到進一步提升,公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也應該進一步上升,但這一預期的情況卻并沒有發生。互聯網初興之時,人們普遍非常樂觀,未來人的未來聯合似乎指日可待,但這一聯合并沒有讓人們變得更理性,出乎意料的是,人們在理性的改進上似乎并沒有什么進步。傳播手段的便捷對于所有人來說,都是同步增長的,而同步增長的結果卻是,反省性的聲音總是偏弱,情緒式的表達所在皆是,知識變成了信息,信息成就了數量,數量造成了團體觀念,團體觀念是流動的、不穩定的,從而,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
數字媒介時代,公共知識分子面對兩個主要難題:一是自身的統一性難題,二是聽眾注意力難題。首先來看自身的統一性難題。如果我們將知識分子與受過高等教育者劃等號,那么,從人口上看,知識分子的數量不斷增長,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加大,獲得知識分子身份的人群數量大幅增加,知識獲得的途徑和知識傳播的方式越來越豐富多樣,但整體性關懷的知識傳播并未得到多少改善。可以看到,公共知識分子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的比例是下降的。從社會對知識的需求來看,知識密集型崗位在大幅增長,但這一增長主要體現在專業型知識崗位上,整體性關懷對于社會需求來說并不是最急迫的,某種程度上也是不必要的。最重要的是,知識的媒介載體不斷變化,知識分子傳播整體性關懷的方式也隨之改變。20世紀30年代,電視、廣播開始在歐美地區流行,并擴展到世界各地,專業知識分子開始借助電視、廣播來傳播自己的思考,應該說,這是一個黃金時期,哪怕這些媒介帶有一些表演性質,但整體性關懷畢竟得到了有效傳達。雖然知識分子數量在增多,公眾對其推重開始逐步降低,但畢竟著書立說并非人人可為之事,公共性表達基本上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互聯網是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一種新媒介,它是一個世紀性媒介形態,在其上產生了大量公共傳播媒介平臺,比如文字性或視頻性社交媒體等,直接帶來傳播方式上的巨大變化。傳播影響力不再是知識主導型,而變成了注意力主導型。新媒介提供了人人可傳遞自己觀念的機會,公共性表達已經不再是稀缺的表達,整體性關懷在公共性表達中的比重不斷下降,因而,從整體上看,新媒介對于整體性關注而言,不能算是一個好消息。
知識傳播與媒介密切相關,不同媒介下知識傳播的原則是不一樣的,堅持整體性關懷的公共知識分子固然大有人在,但由于才能不同,境遇不同,導致具體的內在志趣、知識結構、公共角色也都隨之改變。數字時代,傳統媒介如報紙、雜志、電視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已經從傳統媒介轉向了網絡媒體。這使得傳統媒介的受眾逐漸減少,影響力逐漸減弱,公共知識分子的發聲方式也受到很大的影響。新興媒介如微博、微信、抖音等平臺的影響力不斷擴大,這些平臺具有傳播速度快、互動性強、覆蓋面廣等特點,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和使用這些平臺。對于公共知識分子來說,利用新興媒介進行媒體表達已經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手段。然而,這看似機會,但也暗藏危機。新媒介表達往往是簡單、快捷且有些獨斷,公共表達不免被烙上表演的內核,這不可避免地損害了公共知識分子對整體性意義的表達和追尋。富里迪這樣表達對知識分子的憂慮:“與知識分子連在一起的追求真理這一傳統理想讓位給了新的目標,對思想的追求不再出于任何高遠的目的。不只是慣常認為的無知的平民化庸人對知識分子角色持懷疑態度,許多知識分子發自內心地接受了與他們的活動相伴的實用主義,并堅稱他們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2]
再來看聽眾注意力難題。我們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媒介越發達,表達越順暢,表達的方式越多樣,個體保持內在一致性的力量就越薄弱,這一點不僅對公共知識分子如此,對公眾也同樣如此。
公共知識分子的表達具有天然的契約性(即其表達是一種承諾),而其所對應發聲的公共聽眾卻是彌散的群體,即不具有回應的契約性,談不上承諾,因而,聽眾的注意力天然是渙散的,在各種聲音當中不斷切換,以滿足聽覺上的快感。數字媒介時代的公共表達既是發達的,又是艱難的,公共知識分子自我一致性本身不易保持,為了維持聽眾的注意力,又要變換話題的表達方式,甚至單純的表演性都不足以滿足聽眾的需求,對公共話題的反應速度、外在形象的包裝、媒介場域的熟稔,等等,都成了公共知識分子的必修課,否則,單純整體性關懷的表達總是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不要忘了,還有大量的偽關懷在進行競爭!如果我們比較有公共關懷的知識分子與有知識的憤青對聽眾的影響,就會發現,憤青的知識傳遞影響力很可能更大一些,更容易獲得聽眾的認同,而反省性知識的傳遞反而顯得軟弱無力,無法吸引多數聽眾的注意力。數字媒介越發達,發聲渠道越多樣,公共表達越像是一場生意:對準消費者的喜好,喂給他們愿意接受的言論。公共知識分子的觀念表達無疑也要關注聽眾的胃口,吸引聽眾的注意力,但這樣一來,文化的媚俗又不可避免產生了。而媚俗,又是公共知識分子傳遞整體性關懷的真正的致命傷,相對而言,少有人傾聽或理解反而并不那么致命。
數字化生存易于產生順從數字壓迫的言論,而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卻是批判和質疑。在一個知識大爆炸的時代,非批判式教育產生大量專業性知識分子,他們遠比批判性知識分子更適應這個時代:技術,尤其是新技術的應用創造富豪的速度是這個社會最引人入勝的文化景觀。這是技術奇觀與數字消費相結合的后人類社會狀況。富里迪高喊:“知識分子都到哪去了?”我們可以略帶悲涼地回應:在消費當中,在科技的沖刷當中,在新媒介形態的表演當中。具備整體性志趣的知識分子不是沒有,但在知識、技術、媒介的大合唱中聲音變得嘶啞,不再像以往那樣引人注目,除非某種適合整體性關懷志趣的公共情境再次出現。目前來看,整個社會文化不斷向內轉,這一公共志趣暫時還不具備出現的條件。這個內轉不是指專注于心靈,而是技術向身體和大腦的勝利進軍,比如大量身體設備,智能化穿戴,腦機接口等等;與技術的無往不勝相聯系的是全球政治的向內轉,轉向民族主義化和保守化。這兩者雖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兩者的偶然合拍卻造成技術成就政治壁壘的特殊政治形勢,這也可能造成全球文化政治的大割裂和大對抗。在數字化社會時代,這一數字宰制的威力尤其可怕。
更可怕的是社會加速。社會結構的變化在加速,技術的發展在加速,知識的普及在加速,現在,隨著ChatGPT等大語言模型的崛起,知識結構的獲得也在加速。加速的社會技術結構下,知識形態開始變得動蕩不穩,這必將對教育產生沖突,公共知識分子的表達也隨之飄搖,在公眾的觀看目光中,日漸失去焦點,其內涵變得越來越貧乏,以致無法對其做聚類處理。
當代新媒介和人工智能下的技術加速有這樣的特點:知識易得,技能易得。前者受益于互聯網搜索,后者受益于新崛起的生成式AI。進入互聯網時代,知識迅速數字化,此前不易獲得的知識變得易于獲得,人們只要掌握一定的知識框架,結合搜索引擎進行知識搜尋,就可以獲得相關的知識。但是,我們也知道,這樣的知識基本上屬于局部性知識,知識本身的可靠性還存疑。但是不管怎樣,一個人只要具有了相關的知識和搜索技巧,就可以獲得進一步的深入的知識。這是數字媒介產生之前所不敢想象的。2022年橫空出世的生成式AI更是一個知識的巨無霸,它是一個智能圖書館,可以迅速有效地組織語言,完成知識對答。通過有效提問,生成式AI可以做到知識的可組織化,并且生成適用的知識。此前,這專屬于人類,在時間成本上比較高,從小學算起,到大學畢業,基本達成知識的高效應用,需要16年的時間,而現在,生成式AI只需要幾秒鐘就能完成。可見,生成式AI可以大幅壓縮時間,降低時間成本。這當然不是說不再需要教育,而是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任務:如何最廣泛地獲得基礎性知識,并且創造性與生成式AI合作生成新知識,這一任務會大幅改變人類教育的方式和學生培養的方向。帶來的后果是,知識分子的知識專屬特性廣泛下延,知識屬性與整體關懷的分離被進一步掩蓋。在生成式AI的加持下,普通的知識者也可以獲得專業人員才具有的知識,整體性關懷更是被棄置一旁,乏人問津。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進一步變得失位和尷尬。
數字媒介的不斷推進直接造成知識分子的知識專屬特性的失效,整體性關懷的表達也隨之被大大弱化。在總體安全的背景下,一方面,知識分子的公共功能被徹底弱化;另一方面,知識分子的表演化、娛樂化變得非常突出。社會公眾借助媒介的力量,將文化觀賞視野深入到高校之內,高校的專業人士變為社會媒介場中的觀看對象,也成為娛樂的對象,專業人士的非專業化成為數字媒介下的流量明星,不僅整體性關懷被瓦解,專業知識的嚴肅性在娛樂的侵襲下也變得讓人懷疑。
我們的結論似乎呼之欲出,那就是數字日常下公共知識分子開始彌散無跡。但其實并非如此。彌散只是數字日常狀態,如何應對這一狀態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而應對它的前提就是,必須理解它,解開其中的一些扭結。
任何一個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都面臨獨屬于他的時代境況,數字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言述途徑狹窄嗎?可能并不,數字媒介提供了足夠寬敞的傳播途徑,但公共知識分子在數字媒介時代更像是聲嘶力竭的推銷員;啟蒙時代的公共知識分子言述途徑通暢嗎?也可能并非如此,啟蒙時代的知識分子數量相對較少,其聽眾在民眾中的份額也明顯不足,但有一點是啟蒙時代知識分子獨享的:他帶有一種卡里斯瑪的光環,包括其聽眾中也有一部分人帶有這種光環,這就保證了思想的傳遞具有放大的效應。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不屬于實質的歷史狀況,而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解釋視角:回溯前代公共知識分子總是帶上語言本身加持的賦能光輝,使那些我們所珍視的價值在語言的傳遞中得以增強。這固然是正常的,但指出這樣的機制也有利于我們理解數字時代公共知識分子所面臨的難題以及并不像表面那樣讓人沮喪的效應,畢竟這一稍顯負面的效應可能影響到整體性價值傳達的信心。
具備整體性關懷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占比的確在下降,但是如果我們更關注具體的數量而不去關注比例,那么就會發現,其實,公共知識分子的數量還是在增長,更重要的是,公共知識分子以各種方式找到了發聲的渠道,只是影響力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擴展。也許關鍵之處是,改變對數字媒介時代聽眾的期待。在數字日常情況下,數字聽眾總是注意力渙散的,但這一渙散并不是負面的,它表現了數字生存的真正形態,聽眾總是聽到各種聲音,進行比較,各種聲音彼此雜糅,可能矛盾性地共存于具體個體當中,一旦牽涉具體的公共情境,這一公共關懷觀念就會被喚醒,形成群體的公共關懷。正是在這樣看似彌散的情況中,我們看到公共知識分子的整體性關懷對社會的改變發揮點滴的推進作用。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們就可能離開薩義德所主張的精英化知識分子斷然的邊緣性,而將這一方案視為整體性關懷的一個部分,畢竟數字媒介下,公共知識分子的行動方案也將是多元的,無論是積極性方案,還是看似消極的方案,都可能形成一股合力,哪怕有些猶猶豫豫。彌散,也許不是公共知識分子的墮落,反而給予我們一個機會,去理解數字媒介與知識公共性的新結構、新關聯,從而重尋數字日常下公共知識分子的行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