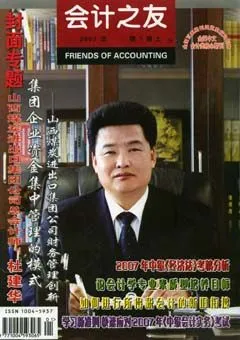期望落差與企業行為選擇:規制俘獲還是研發創新?
孫穗 譚夢卓 朱順和





【摘 要】 醫藥行業是典型的技術密集型和創新驅動型行業,當企業業績不佳時,不僅會依賴對內能力的建設,如研發創新活動,也會通過收買規制機構的官員,采取規制俘獲行動。文章以183家醫藥行業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面板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研究發現,當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期望落差會增加企業的規制俘獲行動,促進企業進行研發創新;而當實際績效高于社會期望,業績期望得到滿足,會減少規制俘獲行為,同時也降低了創新需求。在進一步檢驗中發現,企業營運現金流量強化了期望落差對規制俘獲和研發創新的正向影響作用,而當企業已經獲得了超過市場預期的回報,即使企業營運現金流充足,也不會增加規制俘獲行動和創新活動。這一研究結論對規范醫藥企業合法經營和促進創新轉型具有現實意義和啟示作用。
【關鍵詞】 期望落差; 規制俘獲; 研發創新; 醫藥行業
【中圖分類號】 F27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4)01-0148-08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在新冠疫情的考驗面前,中國新冠醫藥研發活躍度全球最高,國內生物制藥企業為疫情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在復雜嚴峻的內外部環境下,醫藥產業仍處在轉型發展的“陣痛”期,面對諸多挑戰,持續大力投入研發,加速創新成果落地上市,有助于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根據Wind資訊報道,醫藥行業上市公司研發投入不斷擴大,如表1所示,2020年A股373家醫藥公司研發費用總計約603.05億元,恒瑞醫藥以49.89億元的研發費用排在首位,約占總營收的17.99%;與此同時,A股醫藥公司的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卻居高不下,其中上海醫藥銷售費用超過百億元。醫藥企業的費用支出再次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天價費用支出背后其實隱藏著很多灰色利益鏈條,成為商業賄賂的高發區。為了能夠應對制度壓力與市場競爭,企業需要在復雜環境進行決策以達到盈利的目的,而企業如何進行戰略選擇一直是學界和業界共同關注的重點[1]。
來自企業行為理論的研究表明,當企業存在期望落差,管理層在應對不斷下滑的業績時,傾向于通過創新研發這類有長期導向的活動來應對[2-4]。但是,也會有一部分企業將目光轉向了游說、賄賂、財務造假[5-7]等短期冒險活動,期望通過這類行為,獲得非生產性經濟回報,以此快速高效地解決企業業績不理想的問題。但實際情況中,隨著企業業績落差的不斷變化,管理層在做決策時思路與想法可能會發生改變,基于不同行業的特性,企業在行為的選擇上也有很大差異。
目前,我國醫藥行業的營銷體系涵蓋了許多形式和渠道。中紀委官網曾提到,根據公開可查的法院判決文書統計,2016—2020年間,全國百強制藥企業中有超過半數被查實存在直接或間接給予回扣的行為。除此之外,目前藥品采購制度在執行中也有跑偏走樣的現象,成為了醫藥企業在各個領域的準入門檻,這逐漸形成了一個典型的“規制俘獲”問題。由于醫藥行業上市公司在商業賄賂和研發創新的投入上都是巨大的,選擇這個行業進行實證研究,能夠很明顯地找到業績期望對企業行為選擇的影響,使得研究結果更加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基于此,本文將從醫藥行業的角度切入,選取2016—2020年183家A股醫藥行業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業績期望對于企業決策行為選擇的影響。
本文可能的邊際貢獻在于:一是聚焦于醫藥行業,研究發現當實際業績低于業績期望時,醫藥企業既會采取規制俘獲行動,也會增加研發創新投入,而企業的營運現金流量會影響醫藥企業行為的選擇,從行業的角度拓展了期望落差對企業行為選擇的作用邊界。二是探討了醫藥企業之所以會選擇這兩種行為的原因,很大程度是由于醫藥行業的特點和屬性,因此,醫藥行業監管部門要警惕“規制俘獲”問題,并引導醫藥企業在面臨經營困境或業績不佳時做出更科學、更嚴謹、更合理的行為選擇,從而使得市場能夠更健康、更持續地發展。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業績期望落差與企業行為選擇
企業行為理論認為,CEO或管理層會設立一個特定的期望水平,以此作為參考點來評估企業績效,企業的決策是由愿望引導的,愿望建立在企業過去的目標之上,并以同行業組織的績效為基準,低于期望水平的績效被認為是推動企業在市場環境中采取戰略行動的原因[8]。然而,企業可以在市場環境和非市場環境中運作并獲得競爭優勢,前者可以通過內部治理結構變革、創新研發等活動實現,后者通常與政府、媒體或其他利益相關者有關[2],包括游說、逃稅、訴訟或剽竊等行為[9]。
對于非市場行為的選擇,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聯系活動上。糟糕的業績會威脅到公司的正常運作甚至生存,這些結果可以通過增加非市場環境的投資來減輕,旨在保護公司現有的競爭地位[10]。正如許多學者所假設的那樣,企業通過參與政治行動來提高其經濟績效的程度。例如,Thompson et al.[11]發現,為了應對互聯網搜索行業市場份額的下降,微軟利用其在華盛頓特區的游說影響力,成功地采用了各種各樣的政治策略,引導司法部將谷歌與雅虎搜索廣告的合作關系框定為潛在的壟斷,導致了兩者合作計劃的失敗。Rudy et al.[3]采用美國100家大型上市公司數據,探究企業績效期望對市場與非市場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如果一家公司的實際業績下降到期望水平以下,可以預期它會在短期內通過加大游說力度和在未來加大研發力度來做出回應。Eun et al.[12]采用美國輕型汽車制造公司1998—2013年數據,研究發現,當企業的銷售業績低于歷史期望時,企業的決策者有可能通過企業游說來尋找解決方案,當企業高度依賴焦點產品市場時,這一傾向會加強。Xu et al.[10]利用2 224家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研究發現當企業業績進一步低于其期望水平時,其非正常娛樂支出(賄賂支出的隱性衡量指標)會增加,但研發強度不會增加,當公司的業績超過它的期望水平時,企業將有更大的研發強度,但沒有更多的賄賂費用。在我國的市場背景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資源分配不平衡,民營企業業績不佳時,研發投入等創新行為被認為存在較高風險,民營企業主更有可能加強政治聯系活動,傾向于選擇非法性尋租行為[13]。
對于企業市場行為的選擇,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創新研發行動上。因為創新活動在較大程度上受到內生性因素的影響,比如經營業績。當企業收到正面和負面的績效反饋時,它們可能都有意愿增加創新投入[14]。具體來說,一家企業的績效表現超出預期的水平越高,在其創新活動的總組合中,探索性創新的份額就越低;相反,一個企業的績效表現與其預期目標的差距越大,探索性創新在其總創新活動中所占的份額就越高[15]。Huang et al.[16]利用中國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上市的596家公司2009—2017年的數據,探究企業績效低于期望水平對R&D強度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表現不佳的公司比表現良好的同行增加了更大程度的研發強度。李孔岳等[17]通過使用2009—2018年中國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研究發現企業績效期望落差對企業R&D投入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基于歷史期望的期望落差對企業R&D投入存在顯著倒U型影響,但基于行業期望的期望落差與企業R&D投入呈線性關系。
(二)業績期望落差與規制俘獲行為
規制俘獲理論認為,規制是為滿足產業對規制的需要而產生的,即立法者被產業所俘虜,而規制機構最終會被產業所控制,即執法者被產業所俘虜[18]。在醫藥行業,監管部門、醫院、醫生等都可以假定為“規制者”,相對醫藥企業的獲利企圖而言,應當是一道道防線,以保證為公眾提供高質量的產品。而醫藥企業則利用高額的商業賄賂,來俘獲這些規制者,比如從生產批準到患者最終使用的整個鏈條上的人,通過他們獲取壟斷優勢,以獲取壟斷紅利。而壟斷經濟學認為,壟斷企業沒有投入研發的動機,從而導致行業競爭水平下降。
醫藥行業是政策型市場,主管機構自然成為了一些不合規醫藥企業的圍獵對象。有權力,就有權力尋租,既影響市場的良性競爭,也會降低主管部門的監管服眾效力。在逐利心理的驅使下,企業為了獲得超過市場預期的回報,對政府官員或者公職人員采取規制俘獲行為,這必然會導致醫藥行業生產經營活動的扭曲,引致醫藥企業在規制俘獲行為上投入更多,套取資金用于各類商業賄賂,而非藥品研發上。
根據上述理論邏輯和實踐經驗,當企業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時,業績期望落差增加,一般意味著企業出現了管理效率低下、資源分配不當、戰略投資失誤等問題,企業會傾向于通過規制俘獲行為以達到獲得政府補貼、稅收優惠等目的。同時,企業會更重視自身生存狀態,為避免出現生存危機,從事尋租的動機會不斷增加。雖然灰色地帶甚至是違法違規的行為會對公司聲譽有一定的影響,但是在破產危機的籠罩下,規制俘獲這種不需要生產周期與時間的行為能夠快速改善績效不佳的情況,幫助企業擺脫困境。然而,當企業實際績效等于或高于社會期望時,組織會更傾向于維持以往經營狀態,不會增加更多的非市場投入,去開展規制俘獲行動[10]。
由此提出假設1(H1):企業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時,業績期望落差與規制俘獲行為正相關;反之,業績期望落差與規制俘獲行為負相關。
(三)業績期望落差與研發創新行為
企業行為理論認為,低績效和高績效的企業可能從事相同類型的冒險活動,低績效的公司專注于為眼前的問題找到短期解決方案,因此他們更有可能表現出反常的冒險行為,如賄賂、游說等,而高績效的公司則關注在長期內保持其競爭優勢,更有可能從事研究和開發(R&D)等有抱負的冒險行為[15]。
醫藥行業是典型的技術密集型和創新驅動型行業,業績的快速成長不僅源于賽道的選擇,還來自于對研發的投入。相比于國外部分發達國家醫藥企業動輒20%的研發投入,國內醫藥企業的研發投入占比整體偏低。隨著我國加大對企業研發創新的支持力度,出臺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等政策措施,醫藥企業更有加大研發投入的動機。隨著醫藥行業市場競爭壓力的增加,管理層的風險承擔意愿會隨著期望落差的增加而不斷提升,當公司經營業績不佳時,他們投資創新的動機可能是最高的。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企業尋求競爭優勢的首要途徑就是推動創新和加強研發[8]。
根據上述理論邏輯和研究經驗,當實際績效低于期望績效時,企業CEO對企業現狀產生不滿,會認為當前的決策是不合適的,從而引發企業創新,例如增加對現有產品或服務的R&D投入,或是增加新產品、新服務、新項目的R&D投入,力圖使得企業績效達到或超過期望水平[3]。相反,實際績效達到或是高于期望績效,會使得企業對現狀感到滿意,因為一旦要進行創新研發等長期冒險活動,企業將會投入大量的資金、人力等資源,且不會有較大的短期投資回報,反而可能會造成企業出現績效降低的情況。企業會更傾向于維持現行的運行規則,不會有動機去尋求創新投入,從而降低R&D投入強度。
由此提出假設2(H2):企業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時,業績期望落差與研發創新行為正相關;反之,業績期望落差與研發創新行為負相關。
(四)現金流量的調節作用
根據企業行為理論的研究,當企業面臨消極的績效反饋時,擁有過剩資源的企業更可能從事新的研發創新活動,因為這些活動是有風險的,可能不會產生任何回報,或者在幾年后才能轉化為利潤,當企業面臨積極的績效反饋時,一般會保持當前的戰略、操作和常規。而代理理論認為,CEO常常關注自身利益,重視短期業績表現,因此他們往往選擇放棄更具風險、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實現價值增長的業務探索,傾向于采用非常規的市場手段來迅速解決企業的途徑[2]。本質上講,只有當企業的資源有限時,通過短期的非市場投入比長期投入的研發創新活動更受青睞。如果公司有充足的冗余資源,他們可以選擇兩者兼而有之[14]。
因此,期望落差和企業行為選擇之間的關系取決于情景因素,如閑置資源的豐富性、績效不足的持續時間等[1-2]。一般而言,企業高度的財務松弛可能會與企業的行為選擇有一個積極的互動效應[15]。而現金流量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企業的財務松弛度,充足的營運現金流可能代表企業有一定的財務冗余資源,同時,營運現金流量也決定了決策方案是否能夠順利進行,當企業面對較大的業績期望落差,需要決策是否進行規制俘獲或創新投入時,強有力的營運現金流會是其最終做出決策的后盾。反之,將會影響企業決策行為的信心。
由此提出假設3(H3):營運現金流量強化了業績期望落差與規制俘獲行為之間的關系;假設4(H4):營運現金流量強化了業績期望落差與研發創新行為之間的關系。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一)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萬得數據庫(Wind),選取滬深兩市A股醫藥行業的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數據期間為2016—2020年。為確保樣本的可靠性,剔除了被標記為ST、*ST和上市時間不足5年的公司,最終選取183家醫藥行業上市公司樣本。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
(1)規制俘獲行為(RC),參考何晴晴等[6]、Xu et al.[10]的研究,其衡量公式為:
RC=實際管理費用(AE)-預期管理費用(■)
其中,AE表示實際管理費用,通過以下方程估算出未知參數α0,…,α11:
AEi,t=α0+α1Ln(Sale)i,t+α2Levi,t+α3Growthi,t+α4Board
Sizei,t+α5Staffi,t+α6Auditori,t+α7FirmAgei,t+α8LnWagesi,t+
α9HHIi,t+α10LnMargini,t+α11CapInti,t+εi,t
根據以上方程估計出參數α0,…,α11,再計算出預期管理費用(AEi,t):
■=17.675-0.054Ln(Sale)i,t+1.335Levi,t-0.196Grow-
thi,t+0.033BoardSizei,t+0.648Auditori,t+0.040FirmAgei,t+0.028
LnWagesi,t+0.227HHIi,t+0.015LnMargini,t-0.365CapInti,t
(2)研發創新行為(RD)
參考Greve[8]、Huang et al.[16]的研究,采用行業調整后的研發強度來測量,其衡量公式為:
RD=研發支出與營業收入之比
2.解釋變量
業績期望落差 (SA_GAP)參考Greve[8]、Philip et al.[19]、Huang et al.[16]的研究,采用實際績效與社會期望績效的差值進行衡量,衡量公式如下:
SAi,t=[■ROAi,t]/(N-1)
SA_GAPi,t=ROAi,t-SAi,t
其中,SAi,t表示社會期望水平,ROAi,t表示企業的實際經營績效;N表示樣本企業總數,ROAi,t-SAi,t表示實際績效與社會期望績效之間的差值,如果ROAi,t-SAi,t<0,則表示實際業績低于社會期望,產生了期望落差,如果ROAi,t-SAi,t>0,則可以表示實際業績高于社會期望的差距。
3.調節變量
營運現金流(CF)是企業在特定時間內通過常規運營活動產生的現金,代表了企業短期和長期盈利的能力。依據本文的假設,主要考察營運現金流量是否起到強化或抑制作用的調節效應。
4.控制變量
根據前人文獻,本文還選取了企業規模(Size)、兩職合一(Duality)、第一大股東持股例(TOP)、權力距離(PD)作為控制變量,并同時控制了時間因素的影響。
具體變量定義如表2所示。
(三)實證模型
基于選取的各個變量,本文設定了如下模型,并檢驗假設是否成立:
H1:RCi,t=α0+α1SAGAPi,t+α2Sizei,t+α3Dualityi,t+α4TOPi,t+
α5PDi,t+εi,t
H2:RDi,t=α0+α1SAGAPi,t+α2Sizei,t+α3Dualityi,t+α4TOPi,t+
α5PDi,t+εi,t
H3:RCi,t=α0+α1SAGAPi,t+α2CFi,t+α3SAGAPi,t×CFi,t+
α4Sizei,t+α5Dualityi,t+α6TOPi,t+α7PDi,t+εi,t
H4:RDi,t=α0+α1SAGAPi,t+α2CFi,t+α3SAGAPi,t×CFi,t+
α4Sizei,t+α5Dualityi,t+α6TOPi,t+α7PDi,t+εi,t
其中:
RCi,t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俘獲規制行為;
RDi,t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研發創新行為;
SA_GAPi,t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期望落差;
Sizei,t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資產規模;
Duality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兩職合一;
TOPi,t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
PDi,t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數與第二大股東持股數比值;
α0為常數項;
α1,…,α7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估計系數;
εi,t為第i家公司第t年的誤差項。
四、實證分析與結果討論
(一)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
表3為描述性統計與相關性分析的結果:從描述性統計來看,企業規制俘獲行為整體樣本的波動幅度較大,說明醫藥企業之間存在一定差異性。期望落差指標最小值為-0.963,最大值為0.286,標準偏差為0.091,說明了我國醫藥行業上市公司之間在完成績效的能力上有著較大的差距。從調節變量運營現金流量來看,醫藥行業上市公司在運營現金流量上的表現都是處于一個較好的狀態的。從相關性系數來看,解釋變量、調節變量與控制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小于0.7,表示各個解釋變量、調節變量與控制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二)假設檢驗
如表4所示,本文將樣本分為業績期望落差大于0的企業組和業績期望落差小于0的企業組,實證分析結果標明:
從業績期望落差與規制俘獲行為的關系來看,期望落差小于0的企業組,其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期望落差(SA_GAP)對規制俘獲行為(RC)的估計系數為-0.031,由于期望落差(SA_GAP)為負值,表明業績期望落差對規制俘獲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期望落差大于0的企業組,其實際績效高于社會期望,期望落差(SA_GAP)對規制俘獲行為(RC)的估計系數為-1.300,由于期望落差(SA_GAP)為正值,表明業績期望落差對規制俘獲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實證分析結果支持H1。
從業績期望落差與研發創新行為的關系來看,期望落差小于0的企業組,其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期望落差(SA_GAP)對研發創新行為(RD)的估計系數為-0.123,由于期望落差(SA_GAP)為負值,表明業績期望落差對研發創新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期望落差大于0的企業組,其實際績效高于社會期望,期望落差(SA_GAP)對研發創新行為(RD)的估計系數為-0.132,由于期望落差(SA_GAP)為正值,表明業績期望落差對研發創新行為有顯著負向影響。實證分析結果支持H2。
(三)進一步檢驗
如表5所示,本文加入企業的營運現金流作為調節變量,進一步檢驗業績期望落差對企業行為選擇的影響,實證分析結果表明:
從規制俘獲行為來看,期望落差小于0的企業組,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企業營運現金流量對期望落差與規制俘獲行為之間關系不存在調節作用;期望落差大于0的企業組,實際績效高于社會期望,企業營運現金流量強化了期望落差與規制俘獲行為之間的負向作用,估計系數為1.006。實證結果部分支持研究H3。
從研發創新行為來看,期望落差小于0的企業組,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由于SA_GAP是負值,SA_GAP×CF估計系數為-2.724,表明企業營運現金流量強化了期望落差與研發創新行為之間的正向作用。就期望落差大于0的企業組,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估計系數為6.057,表明企業營業現金流量強化了期望落差與研發創新行為之間的負向作用,實證結果支持研究H4。
(四)穩健性檢驗
如表6所示,本文將被解釋變量規制俘獲行為(RC)的衡量方式替換為管理費用與營業收入之比(RC1);將被解釋變量研發創新行為(RD)的衡量方式替換為專利申請數(PAT),進行穩健性檢驗,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與原來回歸結果大致相同,模型比較穩健。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就業績期望落差小于0的企業組而言,其實際績效低于社會期望,企業產生了較大的期望落差,會加劇規制俘獲行為,同時也會促進研發創新活動的開展。在進一步檢驗中發現,營運現金流量對期望落差與規制俘獲行為之間的關系不存在調節效應,而營運現金流量能夠強化期望落差與研發創新行為之間的正向關系,說明現金流充足的情況下,如果公司實際業績未達到社會期望,企業更有創新的動力。
就業績期望落差大于0的企業組而言,其實際績效高于社會期望,企業的業績預期已達標,能夠顯著抑制規制俘獲行為,同時也會減少研發創新活動。在進一步檢驗中發現,企業營運現金流量強化了期望落差對規制俘獲與研發創新的負向關系。也就是說,企業營運現金流充足的情況下,企業已經獲得了超過市場預期的回報,會減少規制俘獲行為,同時也會降低對研發創新的需求。
(二)實踐啟示
一是醫藥行業要警惕規制俘獲行為。醫藥行業受政策影響較大,醫藥企業經常通過收買規制機構的官員,使規制者成為被規制者的“俘虜”。盡管國家相繼出臺法律法規、改革政策,如藥品集中帶量采購制度、兩票制、醫藥代表備案制、建立醫藥價格和招采信用評價制度等,但仍存在一些醫藥行業商業賄賂的現象,因此,必須消除產業的“規制俘獲”問題,例如通過公開透明的程序、嚴厲的司法懲處等,使得醫藥企業真正回歸到競爭狀態,而不是基于尋租獲得壟斷地位。
二是醫藥企業要加強自主創新能力。醫藥企業在面對績效期望落差的情況時,要克服短視心理,以創新為突破口切實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以搶占市場,達到提高績效的目的。雖然我國目前醫藥行業的研發水平距離全球領先國家仍有一定差距,但鑒于我國醫藥外包行業在全球的領先地位,以及龐大的市場,且隨著國家規劃對生物醫藥的高度重視,我國醫藥行業在研發創新方面未來可期。
三是監管部門要進一步規范信息披露。一方面可以抑制醫藥行業的規制俘獲行為,通過明確招待費用、會議費用、差旅費用等可能與尋租行為相關的費用成本信息披露規則,減少企業進行操縱報表、隱藏尋租行為的空間;另一方面,由于醫藥行業研發支出費用化和資本化的會計處理存在較大主觀性,要從細分行業特點或自身研發模式上不斷探索,降低醫藥行業的盈余管理空間,引導醫藥企業更加注重產品的差異化和研發能力,不斷調整、完善相關政策,為我國醫藥企業創新研發營造一個良好的政策環境。
【參考文獻】
[1] 連燕玲,葉文平,劉依琳.行業競爭期望與組織戰略背離——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的經驗分析[J].管理世界,2019,35(8):155-192.
[2] 李健,曹文文,喬嫣,等.經營期望落差、風險承擔水平與創新可持續性——民營企業與非民營企業的比較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8(2):9,140-148.
[3] RUDY B C,JOHNSON A F.Performance,aspirations,and market versus nonmarket investment[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6,42(4):936-959.
[4] DAVID D,WEIHONG C,HAILIN L.Multiple performance pressure inconsistency,resource slack,and the firm’s R&D investment:a behavioral agency theory perspective[J].Business Research Quarterly,2020(1):1-22.
[5] 杜興強,陳韞慧,杜穎潔.尋租,政治聯系與“真實”業績——基于民營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金融研究,2010(10):135-157.
[6] 何晴晴,楊柳,潘鎮.創新還是尋租?業績期望落差對企業風險承擔行為的影響[J].商業經濟與管理,2020(7):71-85.
[7] 連燕玲,劉依琳,鄭偉偉.經營期望落差,管理自主權與企業財務造假[J].上海財經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2):46-60.
[8] GREVE H R.A Behavioral theory of R&D expenditures and innovations:evidence from shipbuilding[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3(11):685-702.
[9] DANIEL B,MICHELE R.RC-Seeking,market structure,and growth[J].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13(7):878-901.
[10] XU D,ZHOU K Z,DU F.Deviant versus aspirational risk taking:the effects of performance feedback on bribery expenditure and R&D intens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9,62(4):1226-1251.
[11] THOMPSON N,VOGELSTEIN F.The plot to kill Google[J].Wired,2009(2):89-93.
[12] EUN J,LEE S H.Aspirations and corporate lobbying in the product market[J].Business & Society,2021,
60(4):844-875.
[13] 呂斐斐,賀小剛,朱麗娜,等.家族期望落差與創業退出:基于中國數據的分析[J].管理科學學報,2019,22(6):21.
[14] 賀小剛,鄧浩,呂斐斐,等.期望落差與企業創新的動態關系——冗余資源與競爭威脅的調節效應分析[J].管理科學學報,2017,20(5):22.
[15] LIN-HUA L,POH-KAM W.Performance feedback,financial slack and the innovation behavior of firms[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9(6):1079-1109.
[16] HUANG L,HE L,YANG G.Performance shortfalls and R&D investment change:aspirations,actions,and expectations[J].Sustainability,2021,13(6):1-21.
[17] 李孔岳,王宇,劉新恒.績效期望落差與企業研發投入——基于廣義傾向得分匹配的再估計[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4(2):16-24.
[18] 杜傳忠.政府規制俘獲理論的最新發展[J].經濟學動態,2005(11):72-76.
[19] PHILIP B,JARED D.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organizational aspiration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4(7):338-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