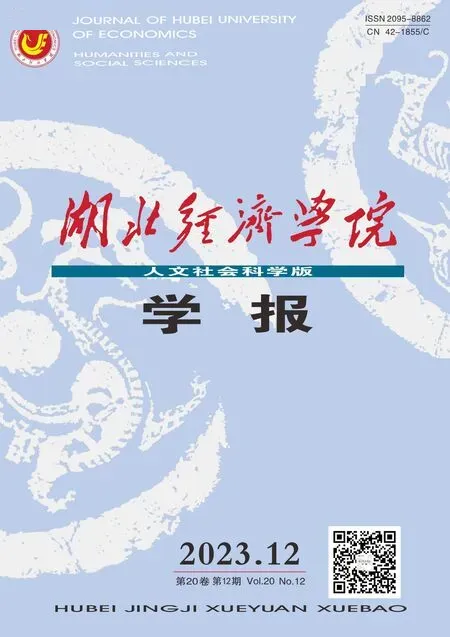“教育數字化”視閾下高校思政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策略探析
李 欽(漢口學院,湖北 武漢 430212)
新時期的科技進步不同于以往,其最主要的表現特征呈現于以智能化為依托的數字賦能。從教育層面剖析,教育數字化不同于教育的信息化變革,而是集合于信息、數據、網絡、人工智能等多要素為一體的特殊階段下的教育變革手段,體現為科技進步對教育進步、發展的科技力量的加持。將教育數字化融合于教師教學能力的鍛造與提升過程中,能夠充分彰顯科技進步視閾下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融合發展。作為推動人文理性發展的重要方式,思政教學立足于人文思想的鍛造,以“立德”而樹“人才”,是新時代新人培育的重要載體、平臺。因此,將教育數字化融入高校思政教師的教學能力提升領域,對推動高校思政教學創新發展意義非凡。
一、“教育數字化”視閾下提升高校思政教師教學能力的邏輯切入
思政教學不同于一般性質的專業課程教學,而是一種兼具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教育活動。對于思政教師而言,教學能力的提升一方面應當考量技術性因素,通過技術加持等方式完善教學方法、方式,并將行為手段放置于科技進步的時代場域之下,推動對數字賦能思政教學的接受力、適應力與應用力;另一方面,應考慮到人文要素,堅持教育對象的人本觀念,樹立數字賦能思政教學的育人根本點上來。要從教學目標、方式、內容等多要素結合的前提下融合“育”與“人”,這些共同構成了“教育數字化”賦能高校教師思政教學能力提升的邏輯切入點。
(一)以“數字化資源”更新并豐富教學資源
數字化時代,通過高效、先進的數字科技,形成了以云庫、數據鏈、AI 等為代表的大數據技術與資源庫,由此基本建立了具有“即時性、廣闊性、互涉性”等特征的數字資源[1]。數字資源不同于傳統數據資源,而是具備高效的傳導性、豐富的荷載性與便捷的采用性等。一方面,數字資源能夠為高校思政教師提供海量充沛的教學素材,使得教學內容能夠實現即時化、與時代進步同行,有利于思政教師利用實時案例、教育文件、教學方法庫等資源提升數字適應力與運用力,有助于思政教師講好“思政話”、教好“思政課”、做好“思政人”。另一方面,數字資源具有較強的專業互涉性,思政教師能夠通過利用數字資源,調動其他專業資源為思政課教學服務,從而培養、提升思政教師在相關知識層面的互涉教學能力,進而做大思政教學平臺、拓寬思政教學眼界,強化思政教學服務技能。
(二)以“數字化思維”強化教學主體的本源地位
教育數字化不僅涵括技術理性還應涵括人文理性,人文理性不同于片面的工具主義,教育數字化的人文理性應當避免以技術為核心本源的機械性思維,而應當強調數字技術服務人的人文理性思維。一方面,數字化思維要求重視思政教學主體的本源地位。任何科技進步都是契合社會變革需求的,是“人”的進化與發展,歸根結底離不開服務“人”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在堅定本源地位的前提下,思政教師能夠通過教學活動的“定向化”“個性化”設計,彌補“一盤棋”式的傳統教學方式,強化對受教個體的關注度,進而增強教學能力[2]。作為受教方的學生,也可以在教師指導的前提下,通過數字化助力,強化求知動能,加強學習自主力,形成“學”“教”雙方的共贏局面。
(三)以“數字化手段”豐富思政教學的手段方式
在數字時代發展中,其傳導速率是驚人的,最主要表現于數字媒介的生活化適用,數字技術所呈現出的表現平臺更具有直觀化、樂趣化,容易被受體接受、認可。一方面,數字媒介的易接受性能夠推動思政教學的參與度。高校思政課的教學受體為青年學生,高好奇心、接受力、適應力是其重要特征。通過數字化教學手段的廣泛適用提升教師的數字應用力,將思政課堂 “線上化”“案例化”“直觀化”“翻轉化”等,能夠有效增進參與度、認可度[3]。另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多樣性能夠轉型思政課的學習模式。數字技術具有較高的情景化與實踐化,能夠將課堂環境實踐化,也能將實踐場景課堂化,這有利于打破學習模式的空間壁壘與資源壁壘,使得即時學習、個性學習得以實現。
(四)以“數字化技術”完善教學能力的綜合評價
數字技術能夠在思政教師能力提升層面有所作為,同樣能夠在綜合評價教師素能提升幅度層面發揮作用。一方面,數字化技術能夠綜合、客觀地涵括“學”“教”雙主體的指標評價。這有賴于數字技術提供的模塊設計、量化分析與結果統計等,從而為教學弱點追蹤、學習薄弱方陣鎖定等環節提供技術支持。另一方面,數字化技術能夠避免過于主觀化的模糊評價。數字化技術能夠在實時追蹤數據的基礎上綜合全過程做出能力強化或者削弱的評價數值,從而克服主觀、機械式的傳統考核手段。
二、“教育數字化”視閾下提升高校思政教師教學能力的現實困囿
數字賦能思政教師教學能力的提升并非一片坦途,現實中在主體認知、基礎支撐等方面存在數字化思維的形成與認知存在偏差、數字技術的供給及適用存在不足、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發展存在沖突等多種困囿。
(一)主體認知困囿:數字化思維的形成與認知存在偏差
數字化思維的培育與提升對思政教師提升能力在重要性上是突出的,作為關鍵的教學主體,思政教師樹立正確的數字化思維是數字賦能的科學化前提。但現實中這種思維上的困囿是存在的,數字化思維未形成或未正確彰顯。一方面,教學主體認可數字化對思政教學的強推動作用,認識到思政教學變革離不開數字化加持。但是部分教師的數字化思維并不完全或者科學。例如,部分教師將數字化思政教學等同于課堂教學的數字平臺使用,認為只要使用了數字媒介或平臺就是數字化。再如,部分教師只注重形式上的數字化,而對數字化背后的人文理性把握不夠,存在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的“完成任務為目的”的“應付式”教學[4]。另一方面,教學主體對數字化思維的認識存在誤解與偏差。例如,有的高校重視引進數字化信息設備而忽略軟件化的思維引導與教師主體技能培訓。有的教師片面注重思政教學的“花樣”,以“眼球吸引”為首要考量標準,雖說收到了參與度但缺乏育人內涵等,這些都不利于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強化。
(二)基礎支撐困囿:數字技術的供給及適用存在不足
在思政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提升語境中,數字技術的供給是基礎、是支撐,是應用數字技術強化教學素能的基礎性要件。首先,數字化的思政教學應用系統并不完備。一方面,受制于經濟差異因素及基建建設因素等現實制約,部分高校并沒有生態化、完整化、鏈條型的數字化教學系統。思政教師在教學實踐中仍然留滯于多媒體教學、視頻教學等初級信息化階段,無法真正享有數字資源,難以真正提升數字資源應用力與數字技術適應力。另一方面,數字平臺缺乏共通性也阻礙了教師技能的發展。實踐中,受制于省際差異及管轄差異等因素的影響,各高校在數字化建設中難以實現系統平臺的同步融通,無法實現高校平臺資源的共享狀態[5]。缺乏共融共通的數字化系統只能停留在狹隘的數據孤島層面。其次,是數字技術在思政教學中缺乏充分適用。先進的技術只用通過運用才能發揮本源價值,而技術適用本身也是技能提升的過程。現實中部分思政教師基于年齡、適應能力等因素,沒有充分接納及采用數字技術,也構成了現實困囿的成因。
(三)素能提升困囿: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發展存在沖突
數字賦能思政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的過程事實上是存進思政教師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融合發展,當然這種融合并非先天具備,而是需要遵循一定的進階規律,但是不論采取何種進階方式,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沖突都是不可取的。首先,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沖突客觀存在,制約教師數字能力的進階。一方面,有的教師主體對數字技術過于遵從,認為但凡數字技術生成下的任何數據都是正確的,都能夠作為衡量教學質量與能力增進的有效指數,而恰恰制約了自身在教學中的評判力[6]。另一方面,有的教師主體缺乏必要的信息篩選力,對數字資源缺乏必要的篩選能力,甚至全盤轉移過來使用,這不利于學生正確思想素養的培育。其次,重技術輕人文的片面觀制約思政教師的“樹人”能力。人文理性與技術理性在思政教學層面最大的沖突在于混淆了 “體”和“用”之間的邏輯關系。有的教學主體將技術使用排在立德樹人之前,顛倒了兩者之間的邏輯與層次,忽略了對學生主體的價值塑造與品德培養,容易導致“樹人”偏駁、“育人”偏向,偏離思政教學的正確路徑。
三、“教育數字化”視閾下高校思政教師教學能力提升的驅強方策
教育數字化賦能思政教師教學能力提升是必要措施、必然方向,但在實際運行中存在數字化思維的形成與認知存在偏差、數字技術的供給及適用存在不足、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發展存在沖突等多種困囿,可以通過強化思維,促進數字思維在主體思想中的真實融入;筑牢基礎,推動數字技術在基建發展中的系統裝備;驅強素能,增強數字技術與人文理性融合發展本領等方策予以策應。
(一)思維上強化:促進數字思維在主體思想中的真實融入
針對數字化思維未形成或未正確彰顯的現實困囿,首先,應當強化對教學主體的數字思維的培育、培養。教師作為思政課教學工作者所肩負的育人職責,需要入腦入心思政內容予學生,同樣的,數字思維也應當在思政教師方入腦入心,以思維強化與真實融入頭腦并進,變思政教師教學活動中為了數字化而數字化的“完成任務為目的”的“應付式”教學為真實融入數字技術的科技化、科學化思政教學,從而推促思政教師能力提升。例如,校方應當制定較為系統的數字思維培育模式,針對思政教師進行專業化、整體化的思維訓練與方向引導,從數字技術本源、數字技術應用、數字科技弊與利、數字技術與教育革新等多方面講解,引導思政教師科學、真實地融入數字思維。其次,教學主體應當提升數字技術的認知力、理解力。數字思維的培育不能只依靠外在力,還應當發展內源力。作為教學主體的教師應當在堅持教育本源的前提下考量數字技術的應用,要明確數字思維不能脫離教育這一活動本體,并將數字思維主動融入到育人目標中去。最后,教學主體應當善用數字思維解決教學難點,推動數字賦能的實現。簡言之,思政教師應當具備依托數字技術解決教學問題的能力。
(二)基礎上筑牢:推動數字技術在基建發展中的系統裝備
針對數字化的思政教學應用系統并不完備、數字化建設中難以實現系統平臺的同步融通,無法實現高校平臺資源的共享狀態的現實困囿,首先,以系統化建設數字裝備為契機,筑牢數字賦能思政教師能力提升的客觀性前提。如果拋開了數字化設施的建設,談思政教師的數字化技能培育是空中樓閣。即便思政教師具備了正確的數字思維,但沒有充分的數字技術設備予以支撐,數字化賦能幾乎是難以達到的。因此,高校應當在數字化技術建設層面強化硬件投入,建設、建成系統化、生態化、鏈接化、整體化的數字技術系統,為思政教師運用數字技術提升思政教學的人文素養筑牢基礎。其次,打破空間層面的技術阻隔,實現數字系統資源的共融共通,強化思政教師在數字領域的適應力與駕馭力。數字化的根源在于信息層面的共享與開放的實際需求,脫離這種需求,數字化甚至是沒有意義的。高校之間即便建成了完備的數字系統、投入專業化的設備建設,但是如果缺乏互相間的聯通與分享,則數字資源的共融共通則是不可能的。因此亟須打破空間上的技術阻隔,建立較為統一性的思政資源平臺,以此提升思政教師發現資源、審視資源、提取資源、運用資源的內在能力。
(三)素能上驅強:增強數字技術與人文理性融合發展本領
針對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的沖突客觀存在,制約教師數字能力的進階等現實困囿,首先,思政教師應當明確數字技術的發展規律及掌握數字技術的實際使用。一方面,技術的發展具有明顯的社會意義與生成背景,技術發展過程同樣是社會進步的發展歷史。作為思政教師應當明確數字技術產生、發展的本質、本源及方向,從而不至于陷入過于迷信技術力量的誤區。另一方面,思政教師應當熟練掌握數字技術,只有熟練掌握該技術才能夠在需要使用時做出較為契合的實際選擇,讓數字賦能思政教學發揮到最優狀態。其次,應當明確思政教學的人文理性,將育人目標穿梭數字賦能始終。無論采用數字技術抑或傳統方法,思政教學的本質目標未變,育人功能不得衰減。數字賦能教學能力提升,所提升的是育人品質、效率。最后,應當強化思政教師融合數字技術與人文理性發展本領。一方面,堅持思政課主要價值觀無動搖,強化正確價值形態的鍛造。另一方面,在運用數字技術賦能思政教學中,要提升教師甄別觀與篩選能力,并輔之以必要的制度規制與機制制約,保障數字賦能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