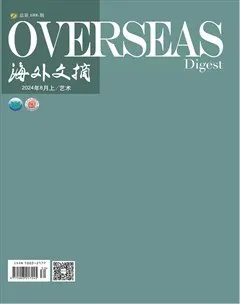信念與言說
蘇軾一生出入三教,于佛教浸潤尤深。其談吐文字,膾炙人口而盛傳士林者,多有直指心性的禪家機鋒語。明人從其文集中輯成《東坡禪喜集》九卷,其篇幅超過許多禪門高僧的語錄。禪宗思想對蘇軾的影響為人所周知,但若具體分析蘇軾的佛教信仰,其構成不只是禪宗,確切地說應是禪凈雙修、導歸凈土,于矛盾中求圓融,于對立中求統一的一種觀念形態。這一形態,貫穿了他整個人生,也映現于其人格與創作。
1 凈土信仰概述
在大乘佛教思想中,凈土代表著身心境界修養凈化的最終完成,所有大乘宗派最后都以往生或成就凈土為目標。各宗的凈土觀念及形態,依自宗的教義各有不同。如華嚴宗有蓮花藏凈土,天臺宗是常寂光土,法相宗是往生兜率凈土,禪宗標榜唯心凈土……然正如天臺宗荊溪大師所說:“諸教所贊,多在彌陀。”在大乘經典中最廣為人知的,是以阿彌陀佛為本尊的西方極樂凈土信仰。一般提到凈土宗,就是特指以阿彌陀佛為本尊,以往生西方凈土為目標的宗派。
在漢傳佛教史上,凈土一宗命運頗為曲折。后漢時期,佛教初入中國,凈土信仰的主要經典就已傳譯流通。在大乘佛教巔峰的盛唐時代,善導大師開凈土為一宗,但不久即遭遇唐武宗時期的滅佛運動。經此一劫,以凈土立宗的論著在中土失傳。此后的凈土信仰,往生西方的宗旨未變,而教義及修行手段則失去獨立性,多寄托于其他宗派,被稱為“寓宗”[1]。
滅佛破壞了依經典立宗的教派傳承,但此消彼長,“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禪宗,在唐以后的發展,則呈一枝獨秀之勢。后世士人與佛教結緣,因此都受到禪宗的影響。而士人的信仰則表現出某種內在的矛盾:就美學趣味而言,禪家之機鋒棒喝,壁立千仞,以自力優入圣域,令人羨慕;但從安身立命的需要出發,則仰仗佛力加護、往生西方的凈土法門,更能保障自己靈性歸宿的安全。于是禪凈雙修、導歸凈土,遂成為一般士人佛教信仰的主流形態。
從蘇軾生平行事作風來看,其信仰形態,正是士人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他深信自己是禪宗五祖戒禪師的轉世,一生好作禪家機語;另一方面,他常于佛教中修行布施,修造阿彌陀佛像,像成多作贊詩偈文;親友亡故,則設水陸道場為其追薦冥福,以西方凈土為愿生歸趣之處。被貶黃州之時,號“東坡居士”,有仰慕追效唐代大詩人白居易之意。白居易晚年歸心凈土,對蘇軾當有啟發,但蘇軾以自身卓越的才華,大起大落的人生際遇,履險如夷的從容風度,獨特的人格魅力,成為后世文人心摹手追的偶像,因此他的信仰風格,對后世文人產生了更加深刻持久的影響。
本文茲據蘇軾年譜行狀及詩文,述其生平行事,以明其心靈軌跡。
2 蘇軾的凈土信仰與禪宗思想的融合
蘇軾深信自己前世與佛教有著不解之緣,這種信念貫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文集中多次提到,自己經常夢到西湖,仿佛那是前世的記憶之地。他對杭州有著深深的眷戀,認為那里是他靈魂的歸宿。所以提及杭州,常用“前緣”“前生”“舊游”等。如《去杭十五年復游西湖用歐陽察判韻》: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余。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疏。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第二次來杭州做官時,杭州府內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武官,蘇軾發現此人好文采,文章很有見地,非常賞識,于是向朝廷舉薦此人脫武轉文。后來,他的兒子何薳寫了一部專門記錄民間奇聞軼事的雜文集《春渚紀聞》,其中第六卷《東坡事實》,專門記錄關于蘇軾流傳在民間的沒有在史料中出現過的奇聞軼事。其中有一則說到,蘇軾在杭州游覽壽星院時,一踏入寺門便感覺似曾相識,能詳細描述出寺院后堂殿、山石的位置。蘇軾曾寫兩首關于壽星院的詩,《西湖壽星院此君軒》《西湖壽星院明遠堂》,該奇聞軼事應是基于這兩首詩所寫。
但是無論這個軼事是真是假,蘇軾在南華寺虔誠地參拜六祖慧能的真身像時,的確不禁淚流滿面,內心充滿了深深的懺悔。他低語道:“云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飲水既自知,指月無復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借師錫端泉,洗我綺語硯。”蘇軾生平達觀、好詼諧,但他自述前生為僧一事,卻鄭重其事,不是出于滑稽戲謔的口吻。在六祖慧能的真身前,他剖肝瀝膽,自覺“我本修行人”,悔恨于“中間一念失”,墮為“綺語”文人,因此“感動淚雨霰”,情發于中,懇切深摯。可見,蘇軾的確是有“前世為僧”的想法的。
上文提到《春渚紀聞》中說蘇軾在杭州時游壽星院,入門即覺自己曾經到過這里,甚至能說出寺內格局的細節。何薳還在書中添了民間相法兇吉一類的細節,說蘇軾后背有很多黑痣——“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為蘇軾形象更增添了神秘色彩。
除此之外,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七,“夢迎五祖戒禪師”也記載了一個關于蘇軾和佛教淵源的故事。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計劃在四月前往高安,而蘇轍則與洞山克文禪師及圣壽聰禪師一同在高安建山寺等候他的到來,準備迎接這位文壇巨匠與佛教信徒。會見前夜,蘇軾與二僧都夢見出城同迎五祖戒禪師。等到與蘇軾相見時,他們說起這個異夢,蘇軾回憶說:“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記其頎然而眇一目。”意思是“我母親懷孕時,也夢見過一位僧人前來投宿,那位僧人身材高大,且有一只眼睛微眇”。洞山克文禪師聽后驚訝地說:“五祖戒禪師正是陜右人,且失去了一只眼睛。他在晚年放棄了五祖寺,云游至高安,最終在大愚山圓寂。”而此時是五祖戒禪師去世五十年,蘇軾時年四十九歲,四人相會于高安,這是時間、地點、人物都能對應上的巧合。蘇軾因此有感,從此“自是常衣衲衣”,經常內著僧衣。惠洪對蘇軾特殊的穿衣行為習慣的細節的記述,強化了蘇軾前身是五祖戒禪師的傳說的真實性。五祖戒禪師,本名師戒,因居蘄州黃梅五祖寺而得名,后人或稱“五戒禪師”,是北宋云門宗高僧。惠洪對蘇軾前身為五祖戒禪師的記述,成為后來叢林語錄與文人筆記習見的掌故。
釋惠洪在《禪林僧寶傳》亦記錄了二僧同夢五祖戒禪師與蘇軾常著衲衣的行為,與《冷齋夜話》細節略有出入。釋惠洪進一步闡釋了蘇軾文學天才的根源,他認為:“蘇軾乃五祖戒禪師之轉世,因其深諳佛理,故而其文章猶如清澈之水,自然流暢,浩渺無邊,其文思亦如水面波紋,自然而成。[2]”這并非單純依靠語言文字,而是源自深刻的哲理。若非從般若智慧中脫胎而出,他又怎能達到如此境界?
自此之后,關于蘇軾前身為五祖戒禪師的說法,在佛教界廣為流傳,成為一段佳話。
前身既為五祖戒禪師,則禪師的行跡,蘇軾也要故地重游。五祖戒禪師最初在五祖寺修行,晚年則遷往大愚山定居。元豐七年三月,蘇軾被貶黃州,內心卻懷揣著對凈土信仰與禪宗思想的深刻體悟。他至五祖山時,不禁感嘆:“問道白云端,踏著自家底。”這句話不僅表達了他對禪宗修行之路的追尋,更透露出他對內心凈土的無盡向往。同年五月端午,蘇軾與三個兒子及弟弟蘇轍一同游歷大愚山真如寺,拜謁大愚禪師,并作詩留念。在這片前生舊地,他一一重歷往事,感慨萬分。蘇軾深知,盡管世事無常,但內心的寧靜與超脫,卻能讓他超越塵世的紛擾。在與大愚禪師的深入交流過程中,蘇軾對禪宗思想的信仰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并且對凈土世界的向往亦愈發深刻。這些游歷經歷與深刻感悟,不僅使得其文學作品蘊含了深邃的哲學思想與禪宗意蘊,而且在逆境中為其心靈尋得了安放之所。蘇軾在與大愚禪師的對話中,不僅汲取了禪宗的智慧,更在禪師的指導下,對禪宗的教義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和體悟。他開始在日常生活中實踐禪宗的“頓悟”與“漸修”,并在詩文中融入了禪宗的“空性”與“無常”觀念,使得其作品在藝術表現上達到了新的高度。
明代小說家馮夢龍在其著作《喻世明言》中,收錄了一篇題為《明悟禪師與五戒禪師》的傳奇故事,結合蘇軾與佛印的傳說,重寫蘇軾的前生故事。他將人地并稱的“五祖戒”一名,訛解為佛門中的“五戒”,虛構出一位以“五戒”為名的禪師。故事講他因一念之差破戒,經同門明悟禪師點化,轉生為蘇軾。明悟禪師恐其墮落,托生為佛印,引導蘇軾了悟前生因緣,成就道業,最后二人同日辭世。這個故事情節精彩動人,雖是虛構,卻成為蘇軾前身為僧一說流傳最為廣泛的版本。
當時士大夫不但醉心禪機,對佛門靈異也很熱衷,知名文士往往多有前生傳說。蘇軾于前生為僧之事自信甚篤,推己及人,對他人自述的前生記憶,蘇軾同樣深信不疑。亦師亦友的張方平,自言前生是受持《楞伽經》的法師,蘇軾為紀念他而手書《楞伽經》刻板流通。
前生曾為禪僧之說,對于文士顯然是一種嘉譽,是對其人格與智慧的肯定;但在佛教的立場,毋寧說是一種退轉和墮落。士人們在為前生的風光自喜的同時,也衍生出對來生去處的顧慮。這種精神拉鋸的結果、禪宗機鋒的興味,在現實利害的權衡下,不得不退守為求歸寧凈土的安心。明代禪宗大師蓮池祩宏總結歷代公案,以蘇軾等人作為修行退轉的典型,云:“戒禪師后身為東坡,青禪師(投子義青禪師)后身為曾魯公(曾鞏),哲禪師(慕哲真如禪師)后身耽富貴,多憂苦。”智慧超群者,仍不免落入輪回;則凈土的安穩易往,當是更加明智的選擇。慧業文人如蘇軾者,當然也想過這個問題。所以趨于晚年,他對念佛求生凈土就越加篤誠,在專修念佛之余,還廣行佛事,為求生凈土的方便。
3 蘇軾凈土信仰的實踐
蘇軾是個文人,一時興至時曾有:“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的感慨。這恐怕是為文造情的趣味,當不得真。當然我們可以更深入一層,理解為他雖向往解脫,但在信念不夠堅定時,對自身歸宿的不安、不確定感,難以消除。于西方凈土的存在,蘇軾本人在感性上深信不疑,且切愿往生,而理性上的探究和思考,則遠不如他在禪宗經典和公案上下的工夫來得深。所以說,他于凈土的信念,其實是外在且被動的。如果說在禪宗,他的身份是如魚得水、機鋒百出的禪師,那么來到凈土的信仰時,蘇軾的表現,更像一位努力做到如愚夫愚婦般誠篤的信徒,而不是揮灑個性的文人。
他頻繁慷慨解囊,捐資鑄造阿彌陀佛像及其他佛教圣像,以表達對佛教的虔誠信仰。每當親友離世都會舉辦隆重的超度法會,廣泛誦經祈福,為逝者超度亡靈,同時也為自己和健在的親人祈求功德與冥福,希望他們能夠積累善因,最終得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此外,蘇軾還常于寺廟中布施財物,支持佛教事業的發展,以此作為自己修行的一部分,這些都是他對凈土信仰的深刻踐行。下文依時間排序,略舉其文集中記錄所行的凈土法事:
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蘇軾身處杭州之際,將已故母親程氏遺留下來的珍貴簪珥首飾慷慨捐贈給了凈慈寺,請工匠造阿彌陀佛像,并作《阿彌陀佛頌》。
元豐四年(1081年)正月二十二日,蘇軾至岐亭,夢一僧面破流血而有所訴。次日路經某寺,見羅漢塑像面目被破壞,為之修葺一新。
蘇軾在擔任杭州知州期間,不僅致力于地方政務,更在精神上尋求超脫與安寧。他深受圓照律師的影響,對凈土信仰有了更深的體悟。圓照律師以其深厚的佛學造詣和慈悲為懷的精神,常常勸導世人歸心凈土,以求來生的解脫與安樂,蘇軾被其言行所感動,決定以實際行動響應圓照律師的勸導。除了舍去亡母程氏遺留下的簪珥首飾,蘇軾還親自監督繪制阿彌陀佛像的過程,確保每一筆每一劃都充滿虔誠與敬意,他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為亡母積累功德,也為自己和眾生種下往生凈土的善因。在造像的過程中,蘇軾還常常與工匠們交流心得,共同探討佛教教義與人生哲理。他深知,真正的信仰不僅僅是外在的布施與造像,更是內心的覺醒與超脫。因此他時常借此機會,向工匠們傳授自己對凈土信仰的理解與感悟,鼓勵他們也走上修行之路,隨著阿彌陀佛像的完成,蘇軾在杭州的凈土信仰實踐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其《阿彌陀佛頌》曰:“愿我先父母,及一切眾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去亦無來。”蘇軾在修行的過程中,一方面積極地實踐著追薦冥福的虔誠供養,熱切地向凈土祈愿,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逝者帶來安寧和福報。另一方面,他的心中充滿了“人人無量壽,無去亦無來”的唯心凈土觀,這種觀念體現了他對絕對平等中道的理想追求。蘇軾在修行中,既注重情感的投入,又強調理性的思考,試圖在凈土信仰的事相“實有”與禪宗智慧理念的“真空”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和圓融。然而,從實際效果來看,蘇軾刻意標舉超越的理趣,反而削弱了個體的深情,使得他的文辭流于口號式的空泛,只是機械地引用經典,缺乏打動人心的力量。
4 蘇軾凈土信仰的深化與轉變
紹圣元年甲戌(公元1094年)閏四月三日,蘇軾被免去定州知州之職,改任英州知州,實則是被貶謫至偏遠之地。遠謫嶺外,蘇軾攜僧道潛(即參寥子)所贈阿彌陀佛像同行。據陳錄《善誘文》記載,蘇軾獄中作詩“有‘魂飛湯火命如雞’之句,神宗聞而憐之,事從寬釋。既而南行,子瞻猶有慊意,乃以阿彌陀佛一軸隨行。人問其故,答曰:‘此余投西方見佛公據也。’”涵芬樓《說郛》卷四十九引《唾玉集·西方出處》亦敘此事[3]。《龍舒增廣凈土文》云:“五祖禪師乃東坡前身,應驗不一。以前世修行故,今生聰明過人;以五毒氣習未除故,今生多緣詩語,意外受竄謫。此亦大誤也。若前世為僧,參禪兼修西方,則必徑生凈土,成就大福大慧,何至此世界多受苦惱哉?聞東坡南行,唯帶阿彌陀佛一軸。人問其故,答云:‘此軾生西方公據也。’若果如是,則東坡至此方為得計。亦以宿植善根、明達過人方悟此理故也。”
上述的文獻都明確記載一個事實:蘇軾被貶嶺南,鄭重其事地帶一軸阿彌陀佛像隨行,視為自己生命寄托。凈土信仰的特點是以情趣入,此時的蘇軾,剛剛從鬼門關撿回性命,如逃出火鑊的落湯雞,驚魂未定,無心侈談理趣,唯有死心塌地,一心倚靠阿彌陀佛。自悔被聰明誤盡一生的蘇軾,此時難得地表現出虔信者樸拙的赤子情懷。到年近六十的晚景,貶謫邊地,蘇軾對凈土的信仰有了一種生死托命的依靠感。而蘇軾隨身帶一軸阿彌陀佛像作為自己往生凈土的保證,也成為一個著名典故,附帶“西方公據”也成了佛門凈土信仰的常用詞。
元祐八年(1093年)十一月十一日,蘇軾還設水陸道場,禮佛以告慰亡妻王閏之(蘇軾的第二任妻子),作《釋迦文佛頌并引》。
紹圣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九日,遵循母親王閏之的遺愿,蘇軾的三個兒子共同繪制了一幅阿彌陀佛像,并將其供奉在金陵清涼寺中。蘇軾親自為這幅佛像撰寫了贊文《阿彌陀佛贊》,并以詩歌的形式贈予清涼寺的長老,以表達對妻子遺愿的尊重和對佛教的虔誠信仰。《阿彌陀佛贊》有:“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之句,蘇軾念佛之精勤與法喜,情見乎辭。但結句“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則又落入理障套話,既欲高揚西方凈土實存的希望,又希冀實證唯心凈土之理想,情與理二者不可得兼。蘇軾并未自覺其觀念與天性的矛盾,在字面上卻分明表現出對立的風格與取向。
紹圣二年(公元1095年)八月一日,蘇軾之子蘇過為母親王閏之追資冥福,抄寫《金光明經》,作為凈土往生的資糧。蘇軾作《書金光明經后》。
紹圣三年(公元1096年)七月五日,蘇軾的侍妾朝云病亡,蘇軾為其超薦,作《惠州薦朝云疏》,收錄于《蘇軾文集》卷六十二。
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三月,蘇軾在虔州主持了一場盛大的超薦孤魂滯魄的儀式,即水陸法會,旨在普度那些漂泊無依的亡靈,作《虔州法幢下水陸道場薦孤魂滯魄疏》。到了六月中旬,他又移師金山寺,再次興辦水陸道場。米芾《寶晉英光集》卷二《東坡居士作水陸于金山,相招。足瘡,不能往,作此以寄之》對此有所記載。
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病重。離世前,蘇軾對守候在病床旁的三個兒子殷切囑托:“我生不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意思是“我一生未曾行惡,死后定不會墮入惡道,你們千萬不要因為我的離去而哭泣,以免驚擾了我安詳的化去。”對自己生命的安頓頗為自信。“怛化”一詞,出于《莊子·大宗師》,他認為孩子們的哭泣會對自己的死亡過程造成干擾。這或許是受到莊子“鼓盆而歌”的影響,但區別于莊子的“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的達觀,蘇軾的表現,似乎未然。最典型的例子,是蘇軾好友米芾《紫金研帖》寫道:“蘇子瞻攜吾紫金硯去,囑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斂。傳世之物,豈可與清凈圓明、本來妙覺、真常之性同去住哉?”紫金硯是米芾最珍愛的硯臺,蘇軾借去后亦愛不釋手,遺囑要兒子將紫金硯一同陪葬。米芾知道后索回,托辭說紫金硯臺乃傳世之物,怎能和人的靈性同去住呢?二人臨終時的一留一取,皆出于文人的愛執。米芾假佛教名相飾其好物之心姑且不論,蘇軾欲強留友人之文房珍玩陪葬,亦非如其自言的那般灑脫。
蘇軾臨終之際,友人維琳和尚提醒其系念西方以求生凈土。蘇軾在逐漸失聰失明之時,從意識深層泛起的,不是曾經傾力踐行過的凈土祈愿,而是生平所好的禪家做派。據《紀年錄》載:“將屬纊(命終),而聞、觀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蘇軾曾任端明殿學士,故有此別稱)宜勿忘!’‘西方不無,但箇里著(力)不得。’世雄云:‘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清波雜志》卷三記載相同,但稍略。
信仰的第一要義是直面生死而超越生死。蘇軾生平確信西方凈土的實在,且親身實踐求生凈土的佛事,以凈土為最后的歸宿。但他一生張揚自我的個性,對禪宗智慧悟境的喜好,是其天性之所偏。于情理之際,他始終不能徹底解決禪與凈、真空與實有、天性與信念的內在沖突。至于他是否真如所說般不執著,是否如愿往生凈土,則給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這一話題的價值不在客觀經驗之真偽,而在信念之有無深淺,及其于人格行事與文辭表現的影響。俗語說:信則有,不信則無。此語細思頗有深義。《說文》釋“信”字曰:“誠也,從人從言,會意。”“信”的本義,不在客觀經驗的征實,而特指人生體驗之真切。“人”的相“信”與“言”說,能造就一種更深刻的精神層面的真實。蘇軾的信仰,他所相信的世界中知性與天性的關系,創造出蘇軾的人格與世界,這才是值得我們觀察和深思的主題。
可以肯定的是,在禪宗的愛好之外,凈土作為一種心靈實在的信念,于蘇軾之為人為文,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跡,有待進一步探討。
5 結語
作為文士的蘇軾,為文化史創造出了永垂不朽的文學作品;作為個體自覺的人及以道自任的士,蘇軾在精神世界示現了古典士人追求圓融、以凈土為歸的信仰。蘇軾禪凈雙修為特征的信仰,其成就與內在的沖突,對立與統一,平衡與失衡,于其創作及人格成就的影響得失,都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反省。■
引用
[1]" 孔凡禮.蘇軾文集[M].中華書局,2004.
[2]" 孔凡禮.蘇軾詩集[M].中華書局,1982.
[3]" 孔凡禮撰.三蘇年譜[M].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作者簡介:黃佳楣(1973—),女,福建寧德人,教育碩士,就職于福建師范大學協和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