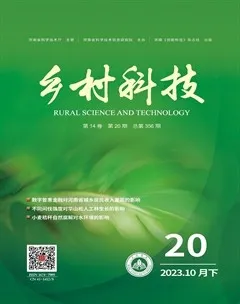小麥秸稈自然腐解對水環境的影響
李兆龍 孫 燕
南京康鵬檢測技術有限公司,江蘇 南京 210038
0 引言
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我國每年農作物秸稈產量在9 億t 左右[1]。農民對秸稈的利用方式多種多樣。例如,在我國南方地區,人們將稻稈曬干儲存,用來編織床墊、掃帚等家用品,還可用作炊事燃料,以及喂養牲畜(牛、羊等)、鋪墊牲圈、漚肥還田等,很少被浪費掉。然而,由于我國近幾十年來煤、電、氣的普及,提供的各種工業制品豐富多樣,致使農村對秸稈的需求減少,大量秸稈的處理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據統計,目前我國被利用的秸稈占秸稈總量的2/3左右[2],其余秸稈被焚燒、丟棄[3],既浪費資源,又污染環境。近年來,相關部門加強了對肆意焚燒秸稈的監管,通過培訓、宣傳等多種方式,提高了農民的環保意識,但隨意拋棄秸稈的現象仍難以杜絕。
小麥種植在我國大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比較普遍,目前關于小麥秸稈處理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秸稈還田腐解、添加催化劑腐解、秸稈氣化發酵等方面[4-6]。尤其是在秸稈還田方面,揭示秸稈在田間腐解的變化特征及其對農作物影響的研究比較多[7-9],而秸稈在自然水體中腐解對水環境造成的影響鮮有報道。試驗模擬小麥秸稈在自然水體中的腐解過程,通過觀測水體中常規水質指標的變化,揭示小麥秸稈自然腐解對水環境的污染特征,為科學制定秸稈離田化綜合利用管理決策提供一定的參考。
1 試驗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試驗小麥秸稈采自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龍袍鎮,含水率為10.43%,灰分質量分數為4.81%,總氮(Total Nitrogen,TN)質量分數為2.52%,總磷(Total Phosphorus,TP)質量分數為0.17%,多糖質量分數為3.42%,木質素質量分數為16.49%,纖維素質量分數為32.45%,半纖維素質量分數為25.82%。
試驗用水來自龍袍鎮田間池塘,pH 值7.4,化學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質量濃度為51.7 mg/L,總有機碳(Total Organic Carbon,TOC)質量濃度為14.2 mg/L,總氮(Total Nitrogen,TN)質量濃度為2.8 mg/L,總磷(Total Phosphorus,TP)質量濃度為0.13 mg/L。
試驗用底泥采自龍袍鎮田間池塘,pH 值6.2,固含量5.6%,TN 質量分數為1.82 g/kg,TP 質量分數為0.73 g/kg,有機質質量分數為46.17 g/kg。
試驗用容器為方形塑料桶(4 只),規格為100 cm×50 cm×30 cm,總容積150 L。
1.2 試驗設計
秸稈腐解試驗在室溫(25±2)℃下進行。在4 只塑料容器中分別加入5 kg池塘底泥(濕),先用大約20 kg池塘水稀釋混勻;然后各添加小麥秸稈250、500、750、1 000 g(分別標記為A~D);最后補充池塘水至總凈質量100 kg(含秸稈、底泥質量,塑料容器質量除外),用扁平的大石塊壓住秸稈,使其完全浸沒在水面以下。每隔1 周采集水樣200 mL,并用池塘水補充至總凈質量100 kg。
1.3 測定內容與方法
采用快速密閉消解法測定水樣COD 質量濃度,用總有機碳分析儀測定TOC 質量濃度,采用過硫酸鉀氧化紫外分光光度法測定TN 質量濃度,采用水楊酸分光光度法測定NH4+-N 質量濃度,采用鉬銻抗分光光度法測定TP 質量濃度,用酸堿度測定儀測定水體pH值,采用稀釋倍數法測定水體色度[10],采用苯酚硫酸法測定多糖質量濃度[11]。
2 試驗結果與分析
2.1 水體pH值變化
在歷時4 個月(16 周)的秸稈腐解過程中,各處理水體的pH 值在5.91~8.56 波動,如圖1 所示。秸稈剛剛開始腐解時(前1 周),A~D 處理水體的pH 值差異不大,且與原水體(試驗用池塘水)pH 值相近,之后各處理水體的pH 值有較大程度的下降,并在第4 周末達到最低點,分別下降到6.57、6.42、6.26、5.91,且秸稈量越大,水體的pH 值越低。在秸稈腐解后期,水體的pH值又緩慢上升,超過初始值,穩定在8.0左右,隨著腐解的持續進行,水體的pH值緩慢下降,且秸稈量越大,水體最終的pH 值也越高。這可能是因為秸稈在水體中開始腐解的初期,可產生少量的乳酸和丙酸[12],使水體的pH 值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隨著腐解的持續進行,秸稈中含氮有機物的分解產生少量的氨氣,使水體pH 值上升,最終導致秸稈腐解末期水體處于微堿狀態。

圖1 小麥秸稈自然腐解過程中水體pH值變化
2.2 水體中多糖質量濃度變化
秸稈的腐解主要是其成分纖維素、半纖維素和木質素的分解,通過觀測水體中的多糖質量濃度變化,可以了解秸稈的腐解動態。由圖2 可知,A~D 處理水體中多糖質量濃度在前4周逐漸上升,基本上都在第4周末達到了最高值,分別為49、72、85、106 mg/L。之后隨著秸稈腐解速率下降,且水體中的多糖被微生物攝食利用,水體中的多糖質量濃度呈逐漸下降態勢,但直至第16 周末,各處理水體中的多糖質量濃度都遠高于起始水平(2.1 mg/L),是起始含量的8~24 倍,且秸稈量越大,水體中殘余的多糖越多。

圖2 小麥秸稈自然腐解過程中水體中多糖質量濃度變化
2.3 水體色度變化
秸稈腐解過程中會釋放一些溶解性物質或膠體狀物質,使得水體呈現一定的顏色。色度是用來表征水體污染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在秸稈腐解前期,水體的色度逐漸增加(見圖3),反映出在此期間秸稈的腐解速度比較快,在第5 周末,各處理水體的色度達到最高值,分別為78、97、113、124 倍,且秸稈量越大,水體的色度越高。而在秸稈腐解后期,水體的色度略有下降并趨于平緩,至第16周末各處理水體的色度為64~99 倍,遠高于起始試驗用水色度13 倍,秸稈腐解使得水體色度明顯增高。

圖3 小麥秸稈自然腐解過程中水體色度變化
2.4 水體中COD質量濃度變化
水體中COD 質量濃度是衡量水體污染程度的重要參數之一。由圖4 可知,在腐解過程中,由于小麥秸稈中的有機物釋放到水體中,水體中的COD 質量濃度在前4 周逐漸增加,在第4 周末A~D 處理水體中的COD 質量濃度上升到最高值,分別為208、336、397、507 mg/L。后期由于水體中微生物的活動,水體中的COD 質量濃度逐漸下降,至第16 周末各處理水體的COD 質量濃度在102~229 mg/L,仍遠高于起始水平(53 mg/L),反映出秸稈腐解對水體造成了一定的污染。

圖4 小麥秸稈自然腐解過程中水體中COD質量濃度變化
2.5 水體中TOC質量濃度變化
TOC 質量濃度是指水體中溶解性和懸浮性有機物含碳的總量,秸稈中40%左右的干物質是由有機碳組成[13]。由圖5 可知,小麥秸稈自然腐解產生的纖維素、半纖維素、木質素等含碳有機物,在第4 周末達到了較高的水平,A~D 處理水體中的TOC 質量濃度分別為63、93、112、149 mg/L。之后由于微生物的利用、降解作用大于秸稈自然腐解作用,水體中的TOC 質量濃度逐漸降低,在第16 周末,各處理水體中的TOC 質量濃度為31~67 mg/L,高于起始水平(16 mg/L)。

圖5 小麥秸稈自然腐解過程中水體中TOC質量濃度變化
2.6 水體中NH4+-N和TN質量濃度變化
氮素水平是衡量水體富營養化程度的重要參數之一。在小麥秸稈腐解過程中,NH4+-N 和TN 的釋放都表現出前期快、后期慢的趨勢。
由圖6可知,A~D處理水體中的NH4+-N質量濃度在第4周末達到最高值,分別為8.0、6.9、6.1、4.9 mg/L。

圖6 小麥秸稈自然腐解過程中水體中NH4+-N質量濃度變化
由圖7 可知,水體中的TN 質量濃度也在第4 周末達到最高值,分別為10.0、12.3、13.2、18.3 mg/L。腐解速率與作物殘體的化學組分有關,其中水溶性物質、粗蛋白物質和苯醇溶性物質分解最快,其次是半纖維素,纖維素次之,而木質素最難分解[14]。在開始腐解的前幾周,秸稈中水溶性物質和粗蛋白物質等能夠較快地進入水體,使得水體中TN質量濃度逐漸上升。由于水體中微生物的氨化作用,將有機氮轉化為氨氮,水中的氮素超出自然水體承受范圍,導致水體富營養化,消耗水體中的氧,造成水體中溶解氧的質量濃度下降,從而導致水發黑發臭。通過水體中微生物自身生長利用及硝化、反硝化等一系列作用,水體中的氮素被逐漸消減。但直至試驗結束,各處理水體中的TN 質量濃度依然在6.4~8.6 mg/L,造成了水體嚴重的富營養化[15]。

圖7 小麥秸稈自然腐解過程中水體中TN質量濃度變化
2.7 水體中TP質量濃度變化
磷是水體富營養化的限制性因子[15]。由圖8 可知,在秸稈腐解過程中,A~D處理水體中TP質量濃度在第4 周末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分別為1.44、1.59、1.77、1.92 mg/L,加劇了水體富營養化程度。秸稈中磷60%以上以離子態存在,由于離子態的磷易溶于水,因此在小麥秸稈腐解初期,隨著水體pH 值的下降,秸稈中的磷能夠較快地釋放到水體中,導致水體中TP 質量濃度在前4 周迅速升高。此外,底泥所釋放出來的微生物可通過富集作用吸收并利用水體中的磷進行增殖生長[16],在第4 周后,隨著時間的推移,秸稈腐解釋放物質的水平降低,其中的離子態磷的釋放接近尾聲,水體中TP質量濃度呈逐漸減少態勢。

圖8 小麥秸稈自然腐解過程中水體中TP質量濃度變化
3 結論
小麥秸稈在模擬的自然水環境里進行腐解,在連續4 個月里,小麥秸稈腐解的特征是前期較快、后期較慢。在前4~5 周水體中的COD、TOC、NH4+-N、TN、TP 質量濃度上升得較快,在試驗條件下,最高值分別為507、149、8.0、18.3、1.92 mg/L,色度達到124 倍。水體中受納的秸稈量越大,水體受污染的程度越高。雖然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隨著時間的延續和腐解程度的減緩,水體中各水質指標值緩慢降低,但仍然均遠高于起始水平。秸稈在水體中自然腐解,嚴重污染了水體,加劇了水體的富營養化程度。因此,建議加強宣傳,增強農戶的環保意識,杜絕肆意丟棄秸稈現象,保護農村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