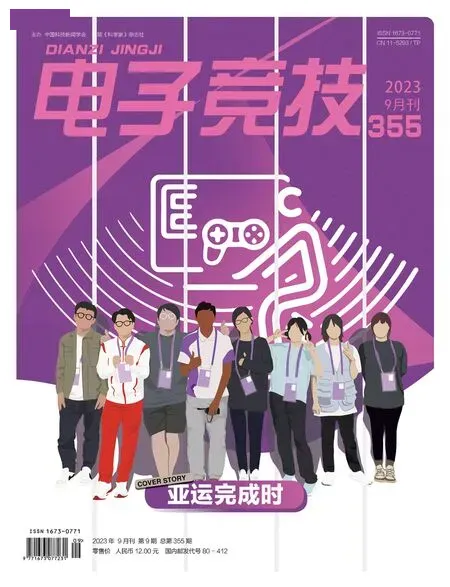北美電競墜落,殘骸也在世界其他地區帶來新生
文 石 翔
5 月20 日的《紐約時報》上刊登一篇名為《The E-Sports World Is Starting to Teeter》的文章,翻譯過來大概是電子競技的世界正在開始搖搖欲墜。文章主要講了北美的兩支英雄聯盟戰隊在售賣自己的席位,并且帶來了一系列的轉向。拳頭的電競負責人也為此發了一篇長博文來回應市場。
之前我們已經討論過拳頭電競負責人的那篇博文,還寫了評論《拉扯了十年之后,竟然正統電競在V 社?》。那篇評論主要是在聊電競和電視體育之間的錯誤的戀情,以及面向互聯網的發展仍然充滿潛力。
這篇想要展開聊聊電競在世界不同地區的變化,以及背后的一些原因。
電子競技在北美整體的頹勢其實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了。疫情開始的時候,我們就看到世界各地的電競觀眾都在增長,可是LCS 和CDL 這兩個北美的職業聯賽觀賽數據始終沒有起色。而且在美國的大學里,電競活動中亞裔的比例也越來越多。
2020 年,大部分關注北美電競市場的業者,大概就知道這種由于在資本市場上過度包裝帶來的心理落差,幾乎已經難以挽回。最近CLG 的退出只不過是正式對外釋放了這種信號。
從2016 年年底開始,又是各個項目版權方發起的特許經營權大潮,的確把電競市帶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樣埋下了禍根。
其一是特許經營權的背后實際上電競體育邏輯下的媒體版權故事,其二是觀眾們的注意力被無休止地綁定在職業聯賽上,這讓大量的玩家沒有時間多參與業余電競比賽,也餓死了大部分不在特許經營權框架里的業余賽事。
版權方的計劃可能是,當市場足夠好的時候,業余賽事的體系只要稍微花一點錢就能解決,可實際上,玩家和觀眾的注意力和時間都是有限的。
北美電競市場是特許經營權模式發端的地方,也是這種改造生效得最為徹底的地方。職業體育電競聯盟就像一場病毒席卷了洛杉磯的游戲公司。一旦資本市場遇冷,泡沫的破碎不過是時間問題,相比于中國,北美甚至于沒有足夠高的競技游戲收入規模,想以游戲貼補電競再堅持幾年,都顯得難以為繼。
特許經營權的搖搖欲墜其實早有征兆,但它的問題并不代表著電競的搖搖欲墜。所以《紐約時報》的視角多少有點管中窺豹的意思,不是北美電競摔了跟頭,世界其他電競也就都沒得玩了。恰恰相反,在世界很多國家,尤其是以“一帶一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為代表,這些在疫情期間迅速邁進移動互聯網大時代的國家都和電競或多或少產生了交集。
它們自知沒有北美優渥的資本市場,也沒有本土的游戲版權方強勢介入,反而孕育出了自己新的模式。

在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蒙古、土耳其等等地區,電競在街區的活動空間,在商場,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光是業余比賽的蓬勃,還有大量的中小型線下觀賽活動。
版權方只做好了自己的職業聯賽,收束自己的權力,一年里給業余賽事留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同時俱樂部經營者的預期也更合理,沒有虛高的席位費,大家只是在職業聯賽的維度上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同時,培育更多的錦標,以“本子”的模式帶動錦標的發展,給俱樂部和選手更直觀穩定的回報。而俱樂部和選手則負責把觀眾留在游戲里。
在PC 時代崛起的電競地域之外,新的以移動電競為主的國家里,觀眾和玩家們沒有明確的身份界定,游戲內給賽事直接帶來收入,賽事給游戲留住玩家。
大量業余賽事和周邊活動,也讓電競的土壤更為扎實。陪玩和業余教練,俱樂部的社區運營,第三方的賽事組織團隊,這些基礎性的工作和崗位從無到有,并且與當地的體育或者文化管理部門在電競發展里共同占據足夠話語權。
在新的市場里,因為先天的不足,沒有走上押寶特許經營權,進而靠版權方的過度投入催熟電競的路徑,反倒是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電子競技在全球范圍之內廣泛受到關注,甚至成為國際交流和文化傳播載體的趨勢并沒有改變。只是過去基于電視體育和美國成熟資本市場催熟的路,目前來看的確無法走通。
在北美電競搖搖欲墜的三年時間里,在世界上更多的地方,借由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電競都在開花結果。各家版權方在拓展新市場的時候,相應地也都做出了修正,擁抱電競賽事和游戲之間的關系,不對立地看問題。
現如今,如何解決好這些過往的遺留問題才是當務之急。在游戲開發商和賽事版權方的眼里,讓職業類的競賽表演活動成為游戲的增值服務,反過來,在真正的行政主管部門或者行業組織中間,創造更大更多的業余電競生態。
從全球市場看,電競充滿了新的活力,也更好地回到了長期主義和注重基礎的邏輯框架之下。
但在特許經營權的先發市場,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誰后放下傲慢,誰就要承擔行業轉彎最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