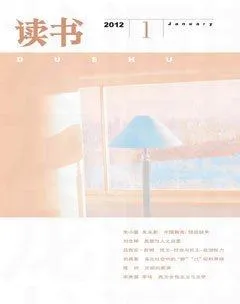從“法律多元”到“世界帝國”
章永樂
“我們是法律帝國的臣民,是法律之方法與理想的信徒,當我們爭論著由此應當如何行事之時,我們的心靈正受著法律的約束。”在其經典著作《法律帝國》(Law’sEmpi re ) 中,美國法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曾如此闡述他心目中的“法治”理想。從法官制度角色極其顯著的普通法實踐經驗出發,德沃金認定“法院是法律帝國的帝都,法官是法律帝國的王侯”。
然而,強世功的《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對這一圖景提出了深刻的質疑。這是一本立足于法律實踐,但又遠遠超出法學領域的學術思想著作,在中國法學界近年的“帝國研究轉向”中居于引領地位。強世功以美國的涉外法律實踐為基礎提出反駁:美國通過司法的“域外管轄權”,將自己的國內立法適用于各種外國實體,迫使后者按照它的意圖而行動,而“域外管轄權”最為積極的實施者是行政執法機構與檢察官,他們運用“辯訴交易”(pleabargaining)制度向外國實體施加壓力,而外國實體擔心漫長的訴訟帶來的不確定性影響到其商譽以及投資人的信心,往往選擇做出讓步,而法官只是對辯訴雙方的“庭前和解”協議做形式上的審查。通過這樣的機制,“司法陷阱”與“經濟陷阱”就實現了無縫銜接。為了更有效地推進“合規”和應訴工作,外國企業不得不選擇那些與美國執法機構具有“旋轉門”關系的美國大型律師事務所。強世功明確地指出:“美國的全球法律帝國統治也是美國法律職業階層的全球統治。”在此,德沃金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法律帝國”概念,被轉化為一個具有強烈支配性和壓迫性的概念。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從“全球法律帝國統治”的具體機制開始,一步步上升到對于“帝國”的理論探討。強世功嘗試在一種中性的意義上使用“帝國”(empire)一詞,將其與思想界熟悉的“帝國主義”區分開來。如果說“民族國家”(nat ion-s tate)強調內部經濟制度、政治法律制度與文化價值觀念乃至種族方面的同質性,“帝國”(empi re)內部保存了更大的差異性和多元性,這迫使帝國必須以更大的力量來獲取成員的“同意”或“默許”,因而比“國家”更強調一種跨族群的文化認同和宗教的作用。在此基礎上,《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斷言,美國絕不是像表面看起來的那樣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具有“世界帝國”的屬性。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將世界歷史進程劃分為“區域性文明帝國”“全球性殖民帝國”與“世界帝國”這三個發展階段。區域性帝國通常是一個區域性文明的擔當者,其自我正當化的話語往往訴諸宗教以及由此衍生的文化價值觀念;“世界帝國”是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產物,其正當性的基礎乃是科學理性、工業社會、自由民主,等等,它用“知識即權力”取代了“知識即德性”,張揚工具理性和欲望的滿足。“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這一標題指向的核心觀點是:“世界帝國”的興起,意味著傳統區域性文明逐步走向終結。“世界帝國”在取得支配地位之后,將自己樹立為“文明”的典范,而將各種基于宗教和道德的傳統區域性帝國視為落后甚至“野蠻”,不僅從外部予以打擊,還從內部促進其瓦解,以將其轉變為全球資本新的“跑馬場”。而這正是一場深刻的“古今之變”。
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將宗教作為界定文明的核心要素,進而從宗教的多元性,推出文明的多元性。而強世功在對“文明”一詞的理解中創造性地嵌入了“古今之變”的視角,他將“文”與宗教、道德相對應, 而將“明”與“啟蒙”相對應。“世界帝國”的興起所帶來的“古今之變”,關鍵就是“文明”中的“明”壓倒了“文”,乃至重新定義了“文”。于是在“世界帝國”帶來的對于“文明”的理解中,欲望、工具理性和權力,成為“文明”的核心要素,宗教與道德失去了原有的位置。亨廷頓判定,隨著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衰落,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群之間的沖突將走向前臺,他提醒美國精英不能被種種關于西方文明普世性的論述沖昏頭腦,而應當在國際上更尊重與其他文明的邊界,在國內警惕族群的多元化帶來國內版的“文明沖突”。而強世功則通過對“文明”的重新界定,改寫了亨廷頓“文明沖突”的故事:在現實中最為關鍵的“文明沖突”,并不是各個區域性文明在一個空間平面上相互沖突,而是美國所代表的“世界帝國”對于各個區域性文明的侵蝕與打擊,以及各個區域性文明對于“世界帝國”的反抗。
強世功從“古今之爭”的角度來重新界定“文明沖突”,得益于近二十多年來中國思想界對于列奧·施特勞斯(Leo St raus s)與沃格林(Er ic Vogel in)等“尚古”的西方思想家的譯介和討論。但與許多因此而轉向古典學的思想界同仁不同,強世功并不認為直接回到傳統的區域性文明的立場就能夠回應“世界帝國”帶來的巨大壓力。他認為,中國已經深刻地參與了“全球化”,并已有能力對“全球化”施加積極影響,塑造一種“新型全球化”。由于國際體系中保守力量的強大,中國對“全球化”的重塑,不能不關注對“世界帝國”不滿的各種力量,其中既有各國主張經濟與社會平等的社會主義與平民主義力量,也有像伊朗、俄羅斯這樣在正當化話語中將宗教與道德置于樞紐地位的區域大國。在強世功的這一理論框架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式現代化”與“文明交流互鑒”話語所針對的國際聽眾范圍的豐富性與包容性。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尤其強調了“中國文明的世俗性和儒家文明所奠定的求變、求新、求智的文化精神和學習品格”,而這與強世功之前從宗教和道德角度對于區域性文明的一般界定,不無細微的差異。要調和這一差異,也許可以采取這樣一種理論路徑:中國文明是各種傳統區域性文明之中具有較強“創新性”和“適應性”的一個,而且正因為“與時俱進”的“創新性”,因而在歷史上保持了較強的“連續性”,并在面對近代的“全球性殖民帝國”與當代的“世界帝國”的時候,體現出強大的自我調適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能夠積極地選擇性接納、消化和吸收外來經驗,更新自身的文明,同時也生長出了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現代文明類型。中國的近代故事,因而不是一個“文明終結”的故事,而是一個“文明更新”的故事。
那么,強世功是如何從人們所熟悉的狹義的法學研究,走到《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這一宏大的跨學科思想計劃的呢?他的“帝國研究”的起點是對于“法律多元主義”的法學理論思考。一九九六年,蘇力出版《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其對《秋菊打官司》與《被告山杠爺》兩部影片的探討,集中引發了針對“國家法”與“民間法”之間關系的學術討論。梁治平譯介了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法律人類學理論,并從“法律文化”的角度總結中國古代的“法律多元”格局。強世功早期的學術思考深受這些學術討論的影響,他甚至參加了翻譯日本學者千葉正士《法律多元》一書的青年學者團隊。在其關于鄉村基層司法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法律多元主義”現象的濃厚興趣。不過,在一個美國單極霸權確立不久,中國還在努力申請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年代,少數敏感的中國學者對于“法律多元主義”的關注,并不足以導向對于“世界帝國”及其支配體系的全面反思。
二十一世紀初,強世功轉向對于“一國兩制”與港澳基本法的研究。他在這一領域看到了更多的“法律多元”現象:無論是清代中國,還是英帝國,都是“法律多元”的秩序,二者之間的碰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強世功在這一領域推出的《中國香港》一書多次重版, 并已有英文版本。而在晚近十年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強世功一方面以《秋菊打官司》引發的法學思考為例,將國內學者對于西方主流法治模式的批判納入批判法律理論的譜系;另一方面,進一步以“帝國”為方法,對“法律多元”問題進行了新的處理,認為當代西方法治的主流模式可以概括為以“形式法治”為特征,以“國家法中心主義”為基本立場, 將“法律”限定為“國家法”,而中國古代的“禮法并行”本身就是一種“法律多元主義”,當代中國同樣具有豐富的“法律多元主義”現象,如“黨規”與“國法”的協同并行,更不用說“一國兩制”的豐富實踐了。這些論述隱藏著對于“法律帝國”論述的回應:德沃金式的“法律帝國”論述對于帝國的“法律多元”缺乏關注,但又恰恰在價值觀上體現了“世界帝國”的支配精神。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在理論層面對“從帝國到民族國家”這一敘事模式進行了徹底否定。強世功力圖在一種中性的意義上使用“帝國”這一概念,認為“帝國”始終是人類政治活動的常規主體,而主權國家只是近代以來的新生事物,甚至主權國家的政治活動也往往是以帝國秩序為擔保的,而“全球化”既是帝國競爭的產物,又是帝國的一種特殊形態。這一主張可以在哈佛大學的簡·伯班克(Jane Burbank)與弗雷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兩位歷史學家合作撰寫的《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Empires inWorld History :Power and the Politicsof Difference )中獲得積極的響應。不過,只要從受到層層制度保護的學術研究領域進入大眾傳播的領域,我們也許就不得不直面“帝國”這一概念身上沉重的“歷史負擔”:首先,經過二十世紀的反帝反殖革命洗禮的當代讀者一看到“帝國”兩個字,就很容易想起帶有強烈負面色彩的“帝國主義”或“殖民帝國”,這一點對于那些具有殖民地經驗的全球南方國家知識分子而言,尤為明顯;其次,“帝國”內部成員身份的多樣性、差異性、等級性,長久以來一直是“人民主權”與“民主”理論批判的對象,被視為缺乏“自下而上”的正當性。比如說,當許多西方史家將清代中國稱為“清帝國”的時候,其往往是以“殖民帝國”的研究范式來認識清代歷史,區分所謂“中國本部”與邊疆地區,其潛臺詞是從“人民主權”與“民主”理論出發,認定中國的“大一統”不具備“自下而上”的正當性基礎。
但不管“帝國”概念在大眾傳播中呈現出多么復雜的局面,《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將中國法學界早年對“法律多元”的思考,上升到對“帝國”與“文明”的系統思考與論述,可謂美式全球化與中美“貿易戰”給中國思想界帶來的最為深刻的思想作品之一。作者對于“民族國家”與“帝國”等概念的反復推敲,也為其思考介于高度松散多元的政治單位與高度同質的政治實體之間的“多元一體”政治共同體形態,提供了知識與思想的準備。《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不是一個句號,而是一個大寫的冒號。它開啟的討論,正在吸引更多學術思想界的“后浪”走出狹隘的學科領地,奔向未知的思想遠方。
(《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美國建構的全球法秩序》,強世功著,香港三聯書店二0二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