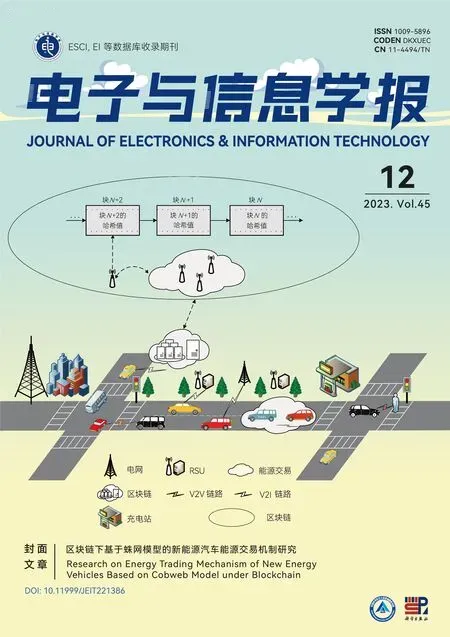一種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檢測和抑制方案
張 霞 余道杰 劉廣怡 白藝杰 王 鈺
(戰略支援部隊信息工程大學 鄭州 450000)
1 引言
作為變革未來戰場作戰模式的重要力量,無人機蜂群在戰場偵察監視、電子干擾對抗、協同突防等方面有巨大應用潛力。相比于傳統作戰手段,它具有費效比高、信息收集全面智能、系統生存能力強等優勢[1-3]。在灰山鶉、小精靈、郊狼[4,5]等項目推動下,無人機蜂群技術日趨成熟,并在作戰行動中嶄露頭角。
為應對無人機及蜂群的潛在威脅,各國積極推進反制技術研究,現有工作集中在反制單個無人機。根據毀傷度可分成硬殺傷和軟殺傷。硬殺傷是指利用高功率射頻信號毀傷目標、尤其是其通信相關器件。文獻[6,7]研究了寬帶高功率電磁脈沖對典型無人機的通信接收機和GPS的毀傷。文獻[8]建立非線性干擾模型,在給定平均干擾功率和峰值干擾功率條件下分析了脈寬、重復頻率對干擾性能的影響。軟殺傷指通過發射虛假信息欺騙或干擾目標系統正常通信,雖不一定毀傷無人機實體,但嚴重影響其功能,而且由于干擾行為更靈巧、隱蔽,具有廣泛實戰應用前景。
然而,反制單無人機技術并不完全適用于蜂群。這是因為蜂群對個體失效有容錯能力,毀傷部分個體往往不能從根本上遏制其作戰效能。例如,美海軍模擬“伯克”級驅逐艦應對蜂群攻擊,包含8架無人機的蜂群系統中平均有2.8架突破防御系統,但是仍對宙斯盾構成實質性威脅[9]。有研究者提出從破壞無人機蜂群網絡拓撲和系統狀態的角度設計反制策略[10-12]。無人機蜂群作戰中常需要個體達到飛行同步,即各單元運動速度方向一致、速率相近,同時避免碰撞[13]。達到飛行同步前,系統處于無序狀態,防御能力低;達到飛行同步后,系統抗毀能力則顯著提升。可見,飛行同步的構建過程是系統較為脆弱的階段,這是反制無人機集群的有利時機。為達成飛行同步,無人機蜂群系統內需要信息交互,例如,個體通告其位置、速度等,這通常用無線通信完成。由于無線信道的開放性,該過程易受干擾[14,15]。文獻[16,17]從反制無人機蜂群協同飛行的角度提出反制方案,將“蜂群”協同飛行描述為有涌現性特征的復雜系統,建立基于f散度[18]的“蜂群”涌現性度量模型,并首次建立了干擾條件下蜂擁控制的失效判別模型。通過實驗分析了干擾強度、時機對抑制“蜂群”蜂擁涌現行為效果。這一工作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鑒。但是存在如下問題:首先,對飛行同步反制的研究缺乏蜂群運動模型的支撐;第二,對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涌現行為的評估關注于單個屬性,易出現誤判;第三,強對抗條件下,反制方單純提高干擾強度將可能被目標系統發現而導致反制失敗,應在降低被發現可能性的前提下研究反制行為,進而評估效能。
針對以上問題,本文主要工作如下:(1)針對典型無人機集群飛行同步運動模型,提出了一種基于雙閾值涌現判定算法,通過聯合檢測速度和網絡連通性,提高識別準確率;(2)建立了平均強度約束的射頻反制行為模型,對比分析了不同占空比、低強度持續干擾和高強度間歇干擾、隨機干擾和固定干擾等多種干擾模式的效能;(3)針對不同作戰意圖設計了反制方案,并通過仿真說明其有效性。
首先給出本文基本假設。假定無人機蜂群包含100個節點,在0 s由長機釋放,到第10 s時完成節點釋放,在第11 s啟動飛行同步。節點具有一套無線收發裝置,通信半徑為R;由于無人機之間通信遮擋物少、距離近,相對運動速度較小,其無線通信受噪聲和干擾的影響,將無人機之間的無線信道假定為加性高斯白噪聲信道,噪聲的單邊功率譜密度為n0[19];無人機蜂群帶寬為B;由于無人機蜂群中個體飛行高度相近,下文僅考慮無人機在平面上的位置。
2 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的識別
2.1 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模型
研究者提出了多種無人機集群飛行同步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Vicsek Model(VM)”[20]。假定系統有N個節點,記作V={i|i=1,2, ···,N}節點具有相同速率,記為v0;初始時刻節點速度方向和位置隨機分布。在飛行同步過程中,節點周期地更新自己的位置和飛行速度。假定在第t秒節點i的位置記作Xi(t),速度方向記作θi(t),其中,θi(t)∈[-π,π),則速度表示為Vi(t)=[v0cosθi(t),v0sinθi(t)]。那么,在第t+1秒時,節點i位置采用式(1)的方式更新
VM模型下,通過信息交互,節點將速度角設置為鄰域內其余節點速度角的均值,實際中,受測量精度限制存在同步誤差ξi(t),其服從均值為0、方差為σ2的高斯分布,即
其中,〈.〉Γ表示對Γ集合內的項求平均,Γi(t)是t時刻以i為中心、通信半徑R內的節點集合,其定義如式(3)所示,也把R稱為“同步半徑”。
文獻[19]指出,網絡連通時所有節點速度將趨于一致,即達成飛行同步。若tsuc,對任意i,j ∈V滿足
則認為群體達到了理想同步。其中ε>0,描述了同步誤差。把從啟動飛行同步到tsuc所經過的時間定義為同步時長,記為Tsuc。
2.2 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涌現的判定
2.2.1 現有判定方法及其分析
準確判定目標系統飛行同步,是對其實施反制的前提。根據已有研究,本文將無人機蜂群的飛行同步看作復雜系統的涌現行為,已有的對涌現的判定方法主要是觀察“涌現強度”,典型方法有基于熵差的和基于散度的兩種。
基于熵差的方法。把集群的某屬性(如速度角)看作隨機變量。把t時刻熵記為Ht,則以熵差描述涌現強度,如式(5)
若E >0,則判定發生了涌現;E隨時間增加;當E曲線趨于平緩則判定涌現達成[21]。
基于散度的方法。散度可描述隨機變量之間概率分布差異,包括KL散度、f散度等。文獻[22]從可度量性、收斂性和靈敏度角度對比,認為Hellinger散度(簡記為Hel散度)更優。Hel散度定義為
其中,P(x), Q(x)分別是X在時刻t1,t2的概率分布。計算Hel散度的核心是估計概率分布。設X={xi},i=1,2,...,N是觀測樣本,則隨機變量X的概率密度函數估計可采用式(7)方法:
其中,h是窗口寬度,K(·)是核函數,可采用高斯形式,即
計算初始時刻和第t秒的Hel散度作為涌現強度Ek;若Ek超過閾值則判定為發生涌現,當Hel曲線達到最大并趨于穩定,則判定為涌現達成。
對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涌現的識別問題,單屬性難以準確反映系統狀態,基于單屬性容易發生誤判。通過下面實驗加以說明。同步半徑R為50 m和25 m兩種情況下,采用上述方法的識別結果如圖1。

圖1 兩種現有方法下目標系統的涌現強度
從圖1(a)可見,熵差隨時間先增加而后趨于穩定。這是由于飛行同步過程中,節點根據同步半徑內節點的平均速度調整自己的速度,節點速度趨于一致,個體的速度熵變小,而熵差增加;當系統中個體速度不再發生顯著變化時,熵差趨于穩定。R取50 m和25 m時熵差曲線形態類似,根據“基于熵差的方法”可認為兩種情況下均發生了涌現。圖1(b)是利用Hel散度的方法的結果,情況與圖1(a)類似。
然而,若同時觀察節點分布區域(見圖2),可發現R取50 m和25 m時系統狀態的差異。當R取50 m時,實驗終止時(見圖2(a))節點的分布區域為X軸上從-870~950 m、Y軸上從-120~-30 m。雖然節點分布區域有所擴大,但網絡仍處于連通狀態,因此,此時系統達成了飛行同步。當R取25 m時,實驗終止時(圖2(b))系統分裂為6個不連通的簇,系統未達成飛行同步;此時熵差趨于穩定,是由于在各獨立的簇內均達到飛行同步,而簇間距離超過R,無法相互影響。

圖2 不同同步半徑下系統在仿真結束時的位置分布
可見,由于缺乏對系統連通性的監控,已有算法無法準確識別目標系統的飛行同步。
2.2.2 基于雙閾值的飛行同步涌現判定算法
針對上述不足,提出一種基于雙閾值的飛行同步涌現判定算法。
用圖G=(V,E) 表示無人機集群,其中V是無人機個體構成的集合,節點數記為N=|V|,E是由個體間通信鏈路構成的邊集,假定邊是無向邊。連通分量NC是指,任取i,j ∈NC,至少存在一條i到j的路徑[23]。把NC中包含的節點數記為NC。時刻t蜂群可能分裂為若干個彼此不連通的分量(t),記其中的節點數為,滿足
為描述系統的連通情況,引入瞬時連通度的定義。
瞬時連通度C(t)定義為t時刻最大連通分量節點數占總節點數的比例,即
當發現無人機蜂群目標時,監測速度角熵差和連通度兩個指標;把速度角的熵差大于0的時刻作為涌現開始時刻,把熵差增速下降時刻判定為涌現達成。與此同時,監測C(t),若C(t)<1-δc,判定為涌現失敗。其中δc >0,它反映了對不連通度的容忍程度。
基于雙閾值的涌現判定算法如算法1所示。
3 無人機集群飛行同步的干擾方法及其效能分析
針對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過程,釋放帶內射頻信號干擾節點間的信息交互,在目標系統“無感”的情況下破壞飛行同步。如何設計干擾行為才能更有效?已有工作針對典型通信系統研究干擾導致誤碼率提升、通信容量下降等[24,25],但較少涉及干擾行為對系統狀態的影響。本節建立射頻干擾圖案模型,通過對比不同干擾行為效能,為反制方案的設計提供依據。假定R為60 m;連通度不低于85%,即δc取0.15。
3.1 射頻干擾行為建模
把基本脈沖記為s0(t),其持續時間T0,具有單位平均功率,如式(11)所示
干擾信號是由s0(t)基本脈沖經過延時和功率放大得到的脈沖序列
其中,M是一次干擾包含脈沖數,ai是第i個時隙是否實施干擾,ai取1表示有干擾,否則表示無干擾; 0≤di ≤1,是占空比;Si是脈沖的功率。
監測目標系統在滑窗M內平均功率,若平均功率高于閾值Sth即認為有干擾。為了避免被發現,對干擾信號平均強度PI有式(13)約束

算法1 基于雙閾值的涌現判定算法

3.2 干擾行為效能分析
本節通過仿真對比研究典型干擾圖案下干擾行為的效能。由于用熵差和Hel散度度量飛行同步時效果相近,后續以熵差度量涌現強度。
3.2.1 等強度不同占空比干擾效能
固定干擾信號強度Si,對比不同占空比下的干擾效能。實驗中,令占空比100%時β為1。圖3給出了占空比為0(即無干擾),25%, 50%和100%時目標系統的涌現強度和連通度變化。

圖3 固定強度、不同占空比的干擾效能對比
無干擾時,涌現強度先增加然后趨于平緩,在t取15時達到穩定,且始終保持95%以上的連通度,同步時長Tsuc約為5 s。施加干擾時,涌現強度先增加然后趨于平緩,干擾信號占空比越高,則涌現強度的穩定值越低,連通度越低。占空比為25%時,系統達成了飛行同步;而占空比為50%和100%時,系統連通度降低到82%和80%,未達成飛行同步。這是由于,干擾信號影響了目標系統的內節點之間的無線通信,干擾信號強度較低時(即占空比為25%時),系統中的個體仍然能夠通過無線通信交互飛行速度、狀態信息,據此調整個體飛行速度;但是,干擾信號強度較高時(即占空比為50%,100%時),個體間難以通過無線通信有效地獲得鄰近個體的飛行速度,而仍然以原有速度飛行,未達成飛行同步,導致系統分裂。系統分裂使得系統飛行同步更為困難,熵差更小,分裂程度加劇。
進一步對比無干擾和占空比25%的情況(圖4),可以發現,干擾遲滯了目標系統的飛行同步過程。無干擾時,Tsuc為5 s;占空比25%時,Tsuc為25 s。施加干擾信號延長了同步時長約5倍。這意味著,低占空比反制行為雖未破壞目標系統的飛行同步,但是延長了這一過程,這為反制方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3.2.2 給定平均強度,不同干擾圖案的反制效能
給定平均干擾強度,通過實驗對比低強度持續干擾和高強度間歇干擾的效果。實驗中,令β為1,β為1,固定Si和di之積,取如下干擾圖案:①Si取1,di取100%;②Si取2,di取50%;③Si取4,di取25%。
如圖5所示,隨時間增加,目標系統飛行速度一致性提高,熵差增加;3種情況下連通度都低于閾值,即反制成功;相比于高強度間歇性干擾(干擾圖案②),中等強度持續干擾(干擾圖案①)下,熵差最低、系統連通度最低、網絡拓撲最分散。這是因為,高強度間歇性干擾下,兩次干擾間隔時間長,利用這段時間系統達成局部同步;而中等強度持續干擾下,目前系統通信始終被干擾而難以實現飛行同步。

圖5 固定平均干擾強度、不同干擾模式的效能對比
3.2.3 給定平均強度、隨機和固定干擾圖案的效能對比
給定平均干擾強度,通過實驗對比隨機干擾和固定干擾的效果。設隨機干擾信號是均值為Si、方差為1的高斯隨機變量,隨機干擾重復周期M設為10;固定圖案取占空比100%、強度為Si。
(1)中等強度干擾。設定β=1,圖6是仿真結果。從圖中可以看到,兩種干擾模式都反制成功。從最終連通程度看,采用隨機圖案1的連通度更低。進一步對比干擾強度(圖6(c))發現,開始反制時采用強干擾比弱干擾更能有效破壞目標系統的飛行同步。這是由于,涌現啟動時,節點位置分布集中,節點利用無線通信獲得鄰近節點的速度,進而調整自己的速度;在此時施加干擾,個體之間難以與周圍其余個體同步,而隨時間增加,個體按原有速度飛行,其位置上更加分散,同步也更為困難。

圖6 中等強度條件下的隨機和固定圖案干擾對比
(2)低強度的干擾。設定β=0.25,圖7是仿真結果。低干擾強度下,固定圖案下反制失敗,但目標系統達成飛行同步的時間大大增加。隨機圖案下的反制效果有一定隨機性,圖中給出了一次反制失敗(圖7中“隨機圖案1”)、一次反制成功(圖7中“隨機圖案2”)的結果。
進一步對比干擾強度(見圖7(c))發現,隨機圖案1在開始反制的4個時隙內均施加高強度干擾,而根據復雜系統涌現現象的特點--從啟動到達成過程強度變化迅疾,高強度干擾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隨機圖案2在開始2時隙施加干擾后干擾強度降為0,喪失了反制機會。
4 無人機集群飛行同步反制方案
對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的反制,從意圖上,可分成破壞和遲滯兩種。前者旨在破壞目標系統,使之分裂為多個彼此不連通的部分;后者旨在延長目標系統達成飛行同步的時長。根據第3節實驗結果,為破壞飛行同步,可采用中等強度、占空比100%的干擾圖案;為遲滯飛行同步,可采用低強度、占空比100%的干擾圖案。同時注意到,應增加干擾信號功率以克服從干擾方到目標系統的路徑損耗的影響。
4.1 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反制方案
設計一種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反制方案,如算法2所示。
本節設計一種針對飛行同步的反制方案,通過設置不同參數,達成相應作戰意圖。
4.2 反制方案的仿真分析
4.2.1 以破壞飛行同步為目的的反制
根據作戰意圖,確定參數設置如下:β為1、采用等強度占空比100%的干擾。圖8是涌現強度和連通度的仿真結果。

圖8 以破壞目標系統飛行同步為目的反制策略的效果
實驗中,第11 s判定目標系統啟動涌現,立即啟動干擾;第19 s目標系統分裂為3個簇(如圖9(a)),連通性低于閾值,因此,反制成功,終止干擾。此后,盡管不釋放干擾信號,節點獨立地按原方向飛行,目標系統分裂程度加劇,從圖9(b)看到,終止干擾后10 s時,目標系統已分裂為5個獨立的簇。

算法2 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反制方案
4.2.2 以遲滯飛行同步為目的反制
根據作戰意圖,設置反制算法參數如下:β為0.25,占空比100%。實驗結果如圖10所示。反制方在t取11 s時啟動反制行動,目標系統在t取20 s時達到了飛行同步,干擾失敗,Tsuc=9 s。對比未釋放干擾的情況,目標系統在t取17 s時達到了飛行同步,Tsuc=6 s。可見,反制方通過釋放低強度干擾的方式延長目標系統同步周期50%,達到了預期效果。從圖中還可以看到,釋放干擾信號后,系統同步過程收斂慢,且最終熵差較小,這意味著最終的同步誤差較高。

圖10 釋放和不釋放干擾時系統熵差的變化
此外,還對比了在是否存在干擾條件下目標系統達成飛行同步后的拓撲,如圖11所示。無干擾時,目標系統分布在X軸上180~290 m、Y軸10~140 m范圍內;有干擾時,目標系統分布在X軸160~340 m、Y軸-20~240 m范圍內。這意味著,干擾使目標系統分布更為分散、脆弱,對網絡穩定性有破壞作用。

圖11 干擾和不干擾時達成同步后的網絡拓撲對比
5 結束語
本文研究了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的反制問題,提出了一種雙閾值的飛行同步涌現判定算法,通過監測飛行同步和網絡連通度,準確檢測涌現的開始、達成和失敗,為抑制算法提供了前提。從降低信道容量的角度建立帶內干擾行為模型,通過實驗分析了不同干擾圖案對目標系統飛行同步過程的影響,研究認為持續低強度干擾可有效延遲目標系統的同步過程,且不易被對方發現;中等強度的干擾就可以破壞目標系統的飛行同步。這些為設計反制方案提供了依據。根據延遲和破壞兩種不同作戰意圖設計了無人機集群抑制方案,通過仿真驗證了有效性。文中假定通過防御方可以完美地獲得目標無人機集群的位置和速度信息,然而實際中受雷達的感知精度制約,所獲信息精度受限,因此進一步要研究噪聲條件下的無人機蜂群飛行同步的識別和干擾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