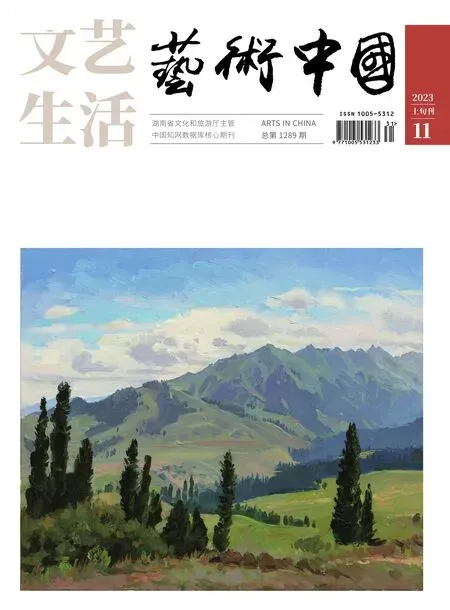此中有真意
——呂啟瓊繪畫創作側記
◆薛元明(南京)
回顧啟瓊兄和我的交往,時光的相機必須打開長焦距才能看到全景。時間太久了,但記憶依舊清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得益于市場經濟的推動,整個社會煥發出強大的生機,表現在藝術方面,各類協會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當然,也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以致真假難辨,一時喧囂。時至今日,真假已辨。能夠堅持到現在的,就是真;曇花一現的,就是假。就在這樣一個熱潮中,我和啟瓊兄因為“中南民族藝術家協會”的成立而相識。說是相識,其實至今二十多年了,未曾晤面。然而,這些年當中,只要彼此需要互助的,必定是心照不宣。
啟瓊兄給我的第一張名片,我至今仍保存著。雖然經歷了漫長的光陰,名片已經發黃,盡管現在人們已經普遍習慣了微信的電子名片,但這種紙質名片,猶如紙質書帶給人的感覺一般,特別溫暖,更主要是它寄托了時間的年輪,見證了歷經歲月霜河的真摯友情。
雖然彼此之間的交流不是特別頻繁,但我對他的關注卻從未停止,見證了啟瓊兄一步一步從成功走向成功。啟瓊兄是土家族人,從進入中書協再到中美協,走進專業院校進修,多年來仍然本色不改。這讓我時常想起那位令我極其崇拜的土家族大作家沈從文。沈從文的經歷跌宕起伏,雖歷盡艱辛,文字卻永遠從容悠游,讓人讀起來有一種攝人心魄的魔力,十分著迷。無論是作為大師級人物的沈從文,還是作為小人物的啟瓊兄,都得益于湘西文化。文學主要依托于文字描述,文學的表現更令人浮想聯翩,有更大的想象空間,書畫則相當直接、直觀,寫真、寫實、寫意和寫心,將心目中的“圖騰”融入筆觸之中。
湘西位于湖南、貴州和川渝的交界處,交通閉塞,處于邊緣地帶,曾是“百越”的發源地之一。這是一個靜謐、緩和、永恒的美麗世界,優美迷人的自然風光,蘊藏了人們對生活本真的態度,對真善美的擁有和關注,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這里的文化資源給啟瓊提供了獨特而豐富的能量。盡管世俗化的影響極為深入,時至今日談及湘西文化,依然有某種“神秘性”,有特別的深邃之美。誰能想到,這里曾經悍匪橫行,還有那神秘的趕尸人。對于啟瓊兄來說,土家族的信仰、巫術和祭祀,不僅有悠久的歷史,而且與神秘文化相互交織,恰恰構成“實驗水墨”的現代性基礎。啟瓊兄擁有湘西人的質樸、純真和敏銳的特質,喜歡追求新鮮事物,拒絕一成不變的生活。雖然去了北京進修,但他始終“不忘本”,讓湘西文化成為自己童年乃至一生的記憶,成為他創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人情美”和“人性美”是湘西文化的特質。面對優美、寧靜、自然和古樸的湘西,批判物欲橫流、野性丑惡且不乏人性扭曲的現實世界,借助現代水墨來表現,可謂再合適不過。在借鑒湘西民間文化元素的創作中,啟瓊兄常常借助象征來暗示或寄寓特定的人事與事理,表達情感和寓意,引發聯想,獲得意境。在電子信息化時代,書畫家主體作為感覺敏銳的一類人,因為新觀念的介入,在思維引導和情感表達方面,會很自然地求索新穎的、合理的視覺空間。“水墨”視覺效果的創新,不僅在于圖式和色彩等元素的創新,更在于追求多種彼此之間關系的創新。當個人深入了湘西這片獨有的民間文化藝術環境,充分了解了地域文化屬性,發掘富有民俗及傳統等雙重性的文化資源,努力突破原有的形式而進行的創新,就會成為一種自覺。
啟瓊兄的繪畫創作,如果要嘗試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真”,真實的自然、真實的筆墨、真情實感,真誠地面對一切。這也是我們這么多年雖未謀面卻相交甚歡的原因。與“真”相對的是“假”,是“偽”。毋庸諱言,在書畫圈有太多的假大空風氣,偽情、偽裝和偽劣,致使風氣敗壞。藝術創作浮躁膚淺,自然無法表現厚重的湘西文化。啟瓊的民族身分和民間身分皆有助于他對本土文化的理解與描繪。這當中似乎存在某種沖突——即古老神秘的文化如何演繹為“現代水墨”。因為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傳統與現代常常是對立起來的。不能不說,非此即彼的觀點誤人深重。殊不知,此二者本身是有機統一的,尤其是表現在啟瓊身上,使他的創作厚積薄發、游刃有余。

擦肩而過 紙本水墨 呂啟瓊

趕鄉集 紙本水墨 呂啟瓊
所謂的“現代性”,在啟瓊的水墨創作中通常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人”的主體性,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再是“自然”和“天”,“人”成為主題和核心,強調追求與眾不同的個性,每個人具有獨立而不可替代的價值。二是對“新”的追求和強調。“現代藝術”打開了“創新”的大門,門類和思維不斷拓展,不乏一些離奇古怪、光怪陸離的成分,已然不滿足于舊瓶裝新酒的簡單舉止,需要有一些更大的突破。然而,作為積淀極為深厚的中國傳統書畫藝術,不是說想擺脫就能擺脫的,考慮傳統淵源始終是必須依賴的資源。三是“反思性”特征,對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予以關注,雖然有時不免存在泛化的主題,但另一方面積極表明,取決于在多個社會領域的批判性反思,對社會現實的參與,不會止步于“逃離”,在創作上就不會是無源之水。
毫無疑問,要了解“現代水墨”,應該稍微追溯一下水墨畫的歷史。縱觀水墨畫的形成,最初是在唐代。唐代是中國歷史中最為強盛的王朝,儒釋道的融合,畫家主體內生的世界觀發生了自覺的變化。其中,禪宗對于水墨畫的影響首當其沖,將內在的哲學思維和思想借助技法表現出來,體現文人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水墨畫作為主要憑借單一“墨色”的畫種,主要在于水的妙用,產生濃淡干濕的變化。水墨畫技法中的濃淡干濕處理,疏密聚散、對稱與不對稱、均衡與不均衡,可以超出傳統繪畫所形成的一種“極限”,因為有時采用“現代構成”的方法,拓展了筆墨層次,不僅有筆墨形態,更有筆墨形態的組合,既呈現平面構成,又彰顯立體效果。這是技法層面的要求。更高的要求在于對人的要求。水墨畫的本質是文人畫,因為畫家主體是文人,要有文人的胸懷與修養,正如郭若虛《圖畫見聞錄》中所強調的:“人品既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水墨畫的審美側重個人主觀世界和內心世界,關聯內心精神和藝術樣式。
不難發現,傳統水墨講究詩情畫意,注重神韻和氣息,尤其是意境之美不可或缺。“現代水墨”顧名思義,要的就是一種“現代感”,但又有內在的傳統積淀,比如最典型的“墨分五色”要求,同樣要注重意在筆先,畫心中之象,寫胸中之意。無論營造怎樣的風格,強調立足本土資源,才能談得上繼承與發揚。“水墨”不再是單純的物理形態,而被賦予了太多的文化內涵。當代藝術精神強調人的創造力,借助畫家的主體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個藝術家來看待的。傳統水墨屬于人與自然的融合,畫家主體一定要歸屬到自然情境中,即人與自然的融合,更高境界則是天人合一。當代水墨畫既要求有傳統功力,同時對現實自然與社會要有敏銳的感知力、表現力。水墨畫一直是中國傳統文人所崇尚的,是傳統文人精神與人格理想的載體。在當代文化背景下,傳統的“文人群體”已然消失,代之以當代形形色色的藝術家,山川樹木變成城市森林,生存環境和思想理念的改變,必然改變水墨畫創作與鑒賞的意識,進而影響到創作風格。當代水墨可以是一種“實驗”,在這樣一種“文化實驗”的進程中,將傳統文化與對當代社會的反思結合在一起,側重自我精神的理解和詮釋。由此而言,當代水墨更接近一個開放的文化場域,水墨本身有時只是一種媒介,創作過程則是一個不斷發現、質疑和自我釋放的過程。
“現代水墨”帶有強烈的實驗性,在心靈與現實世界的碰撞中建立對當代世界的反思與批判。啟瓊兄的系列創作,無一不打上對當代喧囂世俗的質疑與批判的明顯烙印。水墨畫具有“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雖然不同于文學,卻與文學有類似的特質,也由此形成內在的美學與文化脈絡,包括水墨材料的突破和嘗試,讓觀眾在欣賞時能夠與作者形成共鳴,也就真正達到人文關懷的目的。毫無疑問,啟瓊兄的作品,其筆觸的細膩與塊面的沉重,畫面的飽滿與虛靈做到了有機統一,色彩與內涵充分與形神交融統一起來。擁擠的人群、老舊的汽車、有意沉悶的色調、壓抑與釋放的激烈碰撞、偽裝與真實的心靈呼喚,使人想到曾經的年代。水墨畫的未來趨于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審美取向的多元化、毛筆功能的藝術化,無一不使得水墨畫更多側重個人情感的表現,回歸個人心靈,本體化獨立的特征越來越明顯。這就使得水墨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把傳統文人畫一些具象的要求進行抽象演繹,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將畫家個人的審美呈現出來,甚至有效地吸收西方繪畫的某些技法,具有特別的開拓性。這就是讀啟瓊繪畫能產生震動與思考的原因,甚至對當代社會和當代文化產生一種聯想。在當代的社會生存經驗中,困惑、矛盾和質疑等心態使得心理產生不平之鳴,要求畫家必須具備敏銳的感知力,進而通過變形,甚至大膽出格的筆墨,以情緒化的筆觸,創作出極具視覺張力的作品,同樣符合“筆墨當隨時代”的主張。從這個角度來講,呂啟瓊的創作實驗和當代絕大多數畫家一樣,將當代水墨發展成一種“新傳統”:即一種新的方式、一種新的視角和一種新的精神境界。
可以說,啟瓊兄以個人視角針對當代水墨畫的建構與解構、題材的隨意性和隨機性,在詮釋人性異化與自然的別樣理解中,都有特定的作用。這種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融合,需要設身處地去完成。除了人生經歷之外,在藝術成長過程中,前期的各種嘗試與積累,都必須從傳統走來。任何一種風格都不可能是橫空出世,最終仍歸結為兩點:一是個人氣息,二是筆墨精神,都是比較自我的,強調“外師造化,中得心源”,需要內外兼修。這一切使得他的水墨畫常常煥發出時代氣象,這種氣象同時具備了濃郁的湘西本土文化內涵,從個人藝術語言層面對水墨系統觀念做出近乎哲學層面上的思考和詮釋。
但凡畫家、書法家,在中年或晚年實現風格突破,必定包含某種不為人知的特定因素,這才是不可復制的。我對啟瓊兄充滿期待。

問墨盤古 紙本水墨 呂啟瓊

澧水河邊的故事 紙本水墨 呂啟瓊

湘西風情 紙本水墨 呂啟瓊

湘西非遺之一 紙本水墨 呂啟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