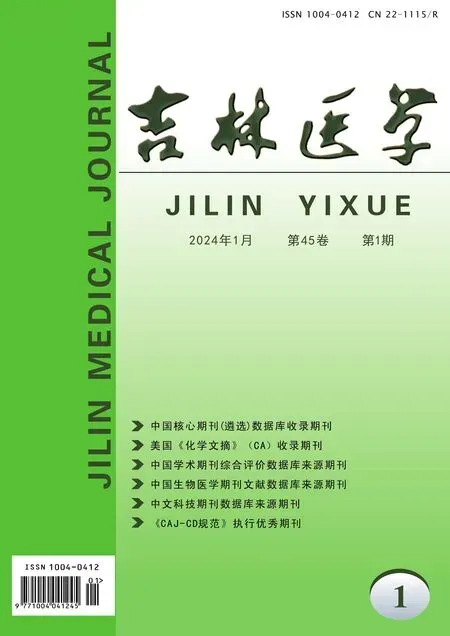PGC-1α基因及其單核苷酸多態性與糖尿病腎病的相關性
申正日,劉 鵬,李 平
(1.北京中醫醫院順義醫院腎內科,北京 101300; 2.中日友好醫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免疫炎性疾病北京市重點實驗室)
糖尿病(DM)最常見的微血管并發癥是糖尿病腎病(DKD)[1],30%~40%的DM患者可能發展成為DKD,DKD是導致終末期腎病(ESRD)的主要原因。隨著現代生活方式向久坐習慣、高脂肪和高果糖飲食轉變[2],脂質代謝紊亂越來越普遍。長期的脂質代謝紊亂也是導致DKD發展的主要因素。遺傳和環境因素在DKD的發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輔助激活因子(PGC)-1α是脂代謝的關鍵蛋白之一,在脂質氧化中發揮著關鍵作用[4]。PARGC1A基因可調節PGC-1α表達,而PGC-1α可以調節脂質分泌、脂肪酸代謝和胰島素敏感性。因此,PGC-1α基因是研究DKD血脂代謝異常的候選基因。這種基因的遺傳變異已經被確認,并且由于其對幾種健康狀況的潛在影響而具有科學意義。在這些變體中,Gly482Ser多態性,也稱為rs8192678,特別值得注意。這種變體的特征是G到A核苷酸的轉變。這種變化導致外顯子8中482位的甘氨酸(G)氨基酸被絲氨酸(S)取代[5]。這種蛋白質結構的改變可能會影響PPARGC1A基因的功能。研究發現PPARGC1A的rs8192678 A等位基因可能是DM的危險因素之一[6]。此外,一項針對馬來西亞人群的研究發現rs8192678與DKD相關[7]。然而,還沒有關于DM和DKD患者之間PGC-1α及其單核苷酸多態性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檢測DM患者和DKD患者rs8192678的多態性,結合DM患者和DKD患者血液中PGC-1α mRNA表達,探討rs8192678與DKD的相關性,并觀察了DKD不同中醫證型間 rs8192678 等位基因及基因型頻率分布。
1 材料與方法
1.1基本資料:本研究于2022年10月15日~2023年9月15日在北京中醫醫院順義醫院腎內科和內分泌科進行,包括DKD患者(n=200)和DM患者(n=200)。年齡在18歲及以上的個人從門診和住院單位招募。在招募時,收集相關的臨床和實驗室數據,包括總膽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此外,從所有參與者處采集6 ml EDTA抗凝全血樣本并保存在-80℃下。本研究方案獲得了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批準文號:2022SYKY007-01),并獲得了所有參與者的書面知情同意書。該研究在中國臨床試驗注冊中心注冊,編號為ChiCTR2200064703。根據世界衛生組織1999年標準診斷DM[8],同時遵循國家腎臟基金會腎臟疾病結果質量倡議(NKF K-DOQI)指南來定義DKD[9],參考中華中醫藥學會腎病分會于2007年頒布的《糖尿病腎病診斷、辨證分型及療效評價標準》對DKD進行辨證分型。每位患者經2位腎病中醫主治以上醫師共同辨證,當辨證一致時方可確認證型。
1.2DNA提取和基因分型分析:使用FlexGen血液DNA試劑盒(Mei5bio,中國北京)從外周血淋巴細胞中提取基因組DNA。SNP檢測中使用的所有引物均購自Applied Biosystems。為了驗證基因分型的準確性,使用TaqMan基因分型,并對選擇的PCR產物進行測序確認結果。用于PCR的引物序列是rs8192678,5′-ATCACTAAGTCAACCACCTCAA-3′(正義鏈)和5′-CATCACTCCCAGCCCTCTAA-3′(反義鏈)。
1.3RNA提取和定量實時PCR分析:使用全血總RNA提取試劑盒(Mei5bio,北京,中國)從外周血淋巴細胞中獲得基因組RNA,逆轉錄后在7 500快速實時PCR系統(Applied Biosystems,Waltham,MA,USA)上進行定量實時PCR分析,引物序列:PGC-1α正義鏈5′- TCTGAGTCTGTATGGAGTGACAT-3′,反義鏈5′-CCAAGTCGTTCACATCTAGTTCA-3′;β-actin正義鏈5′-AGGCATCCTCACCCTGAAGTA-3′,反義鏈5′-CACACGCAGCTCATTGTAGA-3′。
1.4統計學分析:使用SPSS22進行χ2檢驗。SNP的Hardy-Weinberg平衡分析和SNP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頻率使用χ2檢驗。在DM人群中,rs8192678與DM易感性和DKD易感性之間的關聯通過三種遺傳模型(加性、顯性和隱性)進行評估,采用多變量邏輯回歸,校正年齡和性別。三組間定量臨床數據的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而兩組間比較采用t及χ2檢驗。
2 結果
2.1DM與DKD組臨床特征、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頻率比較:DM組與DKD僅在血肌酐(Scr)、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頻率方面有顯著差異(P<0.01),其他指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DM與DKD組臨床特征、基因型分布與等位基因頻率比較
2.2PPARGC1A rs8192678多態性與DKD發病率的關系:我們通過三種遺傳模型(顯性、隱性和加性)研究了rs8192678多態性與糖尿病患者DKD發病率之間的關系。在加性模型中,以GG為參照,GA基因型的DKD風險顯著降低(OR,2.636;95%CI1.201~5.788,P=0.016)。在加性模型中,以GG為參照,GA+AA基因型的DKD風險顯著降低(OR,2.914;95%CI1.922~4.419,P=0.000)。在隱性模型中,AA與GG+GA相比的OR值為1.804,95%CI為0.835~3.896,P=0.133,組間無統計學差異(P>0.05)。根據表2中的性別和年齡進行調整后,結果保持不變。

表2 PPARGC1A rs8192678多態性與DKD的發病率關系
2.3DM組和DKD組GG、GA和AA基因型PGC-1α mRNA的表達:在DM組和DKD組中,AA基因型患者的PGC-1α mRNA水平顯著高于GG基因型患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見表3。

表3 DM組和DKD組GG、GA和AA基因型PGC-1α mRNA的表達
2.4DKD中醫證候與 PGC1-α基因rs8192678多態性的交互作用
2.4.1不同中醫證型在性別、年齡的分布:DKD患者中氣陰兩虛證所占比例最高(34.5%),其次為脾腎氣虛證和陰虛燥熱證,陰陽兩虛型所占比例最低。不同證型間的性別、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性別、年齡在中醫證型分布上均無明顯差異。見表4。

表4 DKD中醫證型在性別、年齡的分布(n)
2.4.2不同DKD中醫證型間 rs8192678 基因型及等位基因頻率分布:三種基因型,在各中醫證型中 GG 型占比例最高,GA 次之,AA 所占比例最低;在等位基因中,各中醫證型中 G 等位基因頻率均較 A 等位基因頻率高。脾腎氣虛證與陰虛燥熱證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36,P=0.045);陰陽兩虛證與陰虛燥熱證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6.434,P=0.011);陰陽兩虛證與脾腎氣虛證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390,P=0.066);其余各證之間兩兩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該位點中醫證型之間各基因型頻率兩兩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PGC1-α 基因 rs8192678 位點不同中醫證型及等位基因頻率分布
3 討論
遺傳因素在DM和DKD的發展中是重要的,已有研究顯示與DKD相關的幾種基因組基因變異,如LXRα、ABCA1、MYH9和APOL1[10-11]。本研究表明DM人群的rs8192678 GG基因型頻率低于DKD患者。在加性、顯性和隱性遺傳模型中,發現GG基因型患者的DM發病率較高,這表明G基因型可能是DKD的危險因素之一。這可能與PGC-1α是一種調節脂質代謝的核受體激動劑有關。PGC-1α可以上調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PPARs)和肝臟X受體(LXRs)的活性,從而逆轉膽固醇轉運及促進脂肪酸氧化和氧化磷酸化,加速甘油釋放[12]。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中,肝臟PGC-1α表達減少40%,導致異常脂質積聚、線粒體功能障礙和胰島素抵抗[13]。在DKD中,PGC-1α mRNA水平降低[14]。在對小鼠進行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降低特定組織(如脂肪組織、肝臟和肌肉)中PGC-1α的表達會導致葡萄糖耐量和胰島素敏感性下降[15]。這支持了在對胰島素敏感的組織中PGC-1α表達減少會增加糖尿病風險的觀點。在患有DM的個體中,脂肪組織和肌肉中的PGC-1α mRNA表達下降[16]。胰島素敏感性降低與脂肪組織中PGC-1α的蛋白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17]。本研究中發現,GG基因型的DKD患者PGC-1α mRNA表達下降。因此,任何影響PGC-1α表達的遺傳變量都有可能導致DM和DKD等疾病的發生和發展,且本研究發現PGC1-α 基因 rs8192678位點DKD中醫證型中氣陰兩虛證分布最多,其次為脾腎氣虛證,陰陽兩虛證最少。PGC1-α 基因rs8192678等位基因中,各證型中 G 等位基因頻率均較 A 等位基因頻率高。DKD患者中醫證候由陰虛燥熱證逐漸轉向陰陽兩虛證過程中,患者 GG 表達占比逐漸增多。陰陽兩虛證患者GG表達最高,AA表達最低,且G 的等位基因頻率也最高。
總之,這項研究表明PPARGC1A rs8192678的風險相關G等位基因與DKD相關。PGC-1α mRNA表達的降低以及PPARGC1A多態性rs8192678的風險G等位基因可能在DKD的發展中起作用。PGC1-α基因 rs8192678 多態性位點與中國漢族 DKD患者中醫證候分型有內在關系,PGC1-α基因 rs8192678 多態性位點的等位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中國漢族 DKD患者的中醫證候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