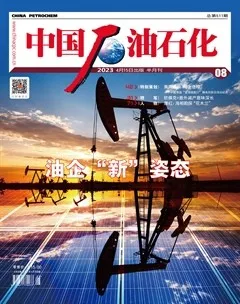沙特伊朗復交,中國協調者角色
清泉

從1943年的80年來,沙特和伊朗經歷了三次斷交和復交的“恩怨游戲”。
3 月10 日,中國成功促使沙特和伊朗這對中東地區“千年冤家”再次恢復外交關系、并發布《中沙伊三方聯合聲明》。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日漸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家,中國在多雙邊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別是最近十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在全球徐徐展開,中國與中東建立起了基于能源合作、基礎設施建設、金融與科技、以及綠色低碳等全方位的經貿合作關系。這種關系必然要影響到政治和外交領域。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自2016 年年初中國國家元首成功實現對埃及、沙特和伊朗訪問以來,無論在中國與中東、中國與阿拉伯國家、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海合會,GCC)等“1+N”的多邊機制框架下,還是在中國與沙特、伊朗、阿聯酋等“1+1”的雙邊關系上,均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所以,才有了《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協議》等重大合作政策文件的釋放,才有了2022年12 月中國與沙特聯合舉辦“中國—阿拉伯國家”“中國—海合會”“中國—沙特”這樣的元首“三環峰會”,才有了今年2 月伊朗總統萊希的成功訪華,也才有了此次中國成功協調伊朗和沙特這對“老冤家”再次成功復交的大好事、大喜事。
脆弱關系
我們知道,沙特和伊朗目前分別是伊斯蘭“遜尼派”(遜尼派中的瓦哈比派)和“什葉派”(什葉派中的支派——十二伊瑪目派)的領頭羊,這兩派均宣稱本派才是真主默罕默德之后正宗血統的繼承人,兩派教眾互相攻伐千年之久,可以說伊斯蘭教興起后的中東史,必有遜尼派和什葉派的斗爭史。
二戰以后,美國成為影響中東地區的最大外部力量,為遏制蘇聯,美國與伊朗和沙特同時交好;而且,伊朗和沙特進入全球幾個最大的油氣資源國、生產國、出口國之列,與美國形成了“資源與市場”的互補,伊朗和沙特也逐漸成為美國在中東的“雙支柱”,特別是伊朗,甚至扮演起美國的“中東警察”角色。彼時的伊朗和沙特關系以合作和交往為主。
1979 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國和伊朗互為敵人。隨著美國加大對中東的介入,進一步拉攏沙特,“石油換安全”“石油美元”等政治經濟和金融關系的綁定,使得沙特成為美國在中東的鐵桿盟友和跟班小弟。這變相加大了伊朗和沙特之間的矛盾。沙特和伊朗的關系由此變得非常脆弱,稍有不如意或小事件發生,其放大效應導致兩國經常出現斷交甚至擦槍走火的重大事件;或者,通過也門這樣的第三國,大打代理人戰爭。
近二十年來,沙特和伊朗之間的矛盾,一直是中東亂局的主旋律之一,與長期以來的阿以(阿拉伯以色列)沖突、伊朗以色列沖突、以及也門沖突、伊拉克和敘利亞亂局、庫爾德獨立運動等一起,成為中東地區幾大矛盾點、風險點之一。
恩怨游戲
如果說以上時期沙伊關系比較脆弱,在此之前1943 年以來的80 年來,沙伊關系真正經歷了三次斷交和復交的恩怨游戲。
第一次斷交與復交:1943年12 月11 日,沙特處死了一名前來朝拜的伊朗人,理由是他向麥加的克爾白天房潑灑臟污。但伊朗人表示不服,說是當時在酷熱的環境下引發了嘔吐,情有可原,并不是故意的。但沙特仍然處死了這名年輕人。1944 年3 月,伊朗宣布與沙特斷交,并且禁止伊朗公民再去沙特朝覲。1945 年2 月,就在二戰即將勝利前夕,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地中海的軍艦上接見了沙特國王伊本·沙特,兩國建立了盟友關系。到了1950 年代,伊朗的巴列維王朝也與美國建立了外交關系,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另一個盟友。在這一階段,伊朗和沙特恢復了外交關系,雙方相安無事。
第二次斷交與復交:1980年2 月,沙特的什葉派聚居區發生了大規模暴亂,緊接著又爆發了兩伊戰爭。兩伊戰爭期間,沙特站在伊拉克一邊,伊朗和沙特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惡化。1987 年7 月31 日,在沙特麥加大清真寺朝覲的幾千名伊朗人突然發生示威,沙特的警察進行了干預,導致402 人死亡,其中275 人是伊朗人。次年(1988 年)4 月沙特宣布跟伊朗斷交。這是第二次。1991年12 月,蘇聯解體,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隨之改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沙特和伊朗恢復了外交關系。
第三次斷交與復交: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和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意外”幫助伊朗消滅了左右兩個遜尼派死敵,伊朗在本地區迅速做大,其典型表現就是伊核問題浮出水面,伊朗不斷增強的核能力引起了以色列、沙特等國的擔心和不滿。2015 年7 月, 奧巴馬執政時期,伊朗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簽署了伊核協議(JCPOA),但對伊朗的核能力發展并沒有做出嚴格的規制,這進一步引發了沙特的不安和憤怒。2016 年1 月2 日,沙特將一名批評王室的知名沙特什葉派神職人員尼姆爾(奈米爾)和其他46 名什葉派教眾斬首,接著沙特駐德黑蘭大使館爆發了大規模騷亂,沙特使館人員出現死傷,第二天,兩國宣布斷交。兩國此后陷入了從也門到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巴林,甚至是沙特阿拉伯東部省(石油重鎮)的持續沖突,其中也門戰場是雙方間接對抗的代理人戰爭。后來,巴林、阿聯酋和蘇丹等遜尼派國家也宣布與伊朗斷交或降低外交關系級別。雖然近年兩國的關系似乎在逐漸升溫,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雙方都有很多東西可以給對方,但相互間的猜疑卻非常深。
水到渠成
水到渠成的是,此次在北京,作為最后一輪也是“最后一公里”的關鍵談判,在中國的斡旋協調下,終于達成和解,并簽署復交協議。可喜可賀。或者說,兩國把最終“一錘定音”的高光時刻放在了北京進行,是對中國示好。
然而,對于中國成功勸和伊朗沙特這件事,美西方是抱著嗤之以鼻和酸溜溜的態度的。畢竟,他們還不太適應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調停者的作用,還不太適應中國“日漸走進世界舞臺中央”這件事實。在他們眼里,大國協調、地區斡旋等在國際舞臺上“長袖善舞”之事,從來都是歐美諸大國的分內之事。
即便如此,據筆者了解,美歐的一些頂尖智庫的專家對中國此舉還是表示歡迎的。還有,筆者近日與華盛頓和美國的一些同行進行交流。對方認為這將有助于地區和平與安全,其中一位智庫的伊朗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扮演了一個良好的協調者角色”。
責任編輯:周志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