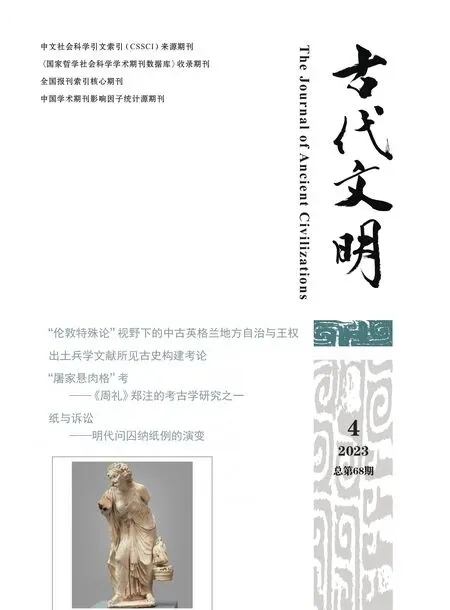出土兵學文獻所見古史構建考論
張 帆
提 要:以往傳世兵書中的古史記述較少,常常受到忽視。今對出土兵學文獻進行考察,可以找到相當體量的古史資料。這些古史敘述一方面能補充現(xiàn)有諸子古史系統(tǒng)的缺環(huán),另一方面也展現(xiàn)出兵學文獻獨特的古史構建方式:如銀雀山漢簡《黃帝伐赤帝》較《孫子·行軍》篇增益了“一帝二王”故事,反映出戰(zhàn)國時期兵學文獻喜談近世和天下視野的特點;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設備》構建了“圣人作兵”的兵器發(fā)明傳說,與清華簡《五紀》等“蚩尤作兵”的敘事不同,是對“寢兵說”的對抗;銀雀山漢簡《地典》即是《尉繚子·天官》批評的“黃帝刑德”類文獻,黃帝形象的沖突表明兵學文獻之間亦有分歧;上博簡、安大簡《曹沫之陳》體現(xiàn)出不片面非古、不全然復古的古史觀,與儒、法兩家皆不相同,具有獨特性。
古今中外,文明的起源、發(fā)展和傳播與戰(zhàn)爭常常形影相隨,文明史與軍事史密不可分。《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子罕言:“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圣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1杜預注,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38,襄公二十七年春,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336頁。已經意識到歷史記憶中國家的廢興存亡都與“兵”有關。事實上,無論是黃帝還是三代圣賢,他們的古史傳說里總免不了戰(zhàn)爭的記述;而后人在進行軍事活動、闡述兵學思想時也常常追憶古史,以先王之道為資。古史系統(tǒng)與兵學思想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互為資源,也互為議題。
經過多年耕耘,目前大多學者已形成共識:古史傳說具有時代性、地域性,也具有一定的學派性。2如李銳先生認為兩周時期古史系統(tǒng)的變化存在4個階段,不能堅持“唯一的古史”的預設,其中戰(zhàn)國時期古史系統(tǒng)體現(xiàn)出地域、學派之別,并指出“春秋之后的古史系統(tǒng),牽涉多端,如果分時段、分區(qū)系、分學派來深入研究,應該能有不少新發(fā)現(xiàn)”。參見李銳:《上古史新研——試論兩周古史系統(tǒng)的四階段變化》,《清華大學學報》,2016年第4期。諸子皆言古史,且存在不少差異,但過去學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儒家、道家、墨家、鄒衍等,兵學文獻中的古史記述往往受到忽視。3長期以來,學者在剖析或恢復古史系統(tǒng)之時往往更重視儒墨道等“顯學”中的資料,而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兵書中的材料。如顧頡剛先生曾提出設想要“一部書一部書”地考辨古史系統(tǒng),但實際上這個設想并未能完全實現(xiàn),顧先生自己也說工作中“漏舉了許多書籍”“以儒家為中心”。王樹民先生曾將戰(zhàn)國時人的古史系統(tǒng)概括為6種,包括韓非、孟子、風胡子等,然亦未及兵書。參見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自序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6頁;王樹民:《戰(zhàn)國時人對于上古史的總結》,載氏著:《曙庵文史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77—88頁。這一方面是因為傳世兵書中對古史的追述簡短而分散,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部分兵學文獻時代不明,相較于其他諸子,似乎很難判定兵學文獻在古史構建和傳播過程中起了何等作用、有何等意義。然而,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銀雀山漢簡、張家山漢簡、上博簡、安大簡等新材料相繼出世,不少珍貴的兵學文獻得以重光,這為我們認識和發(fā)掘兵學文獻中的古史敘事提供了新資料、新契機。
目前出土的兵學文獻數(shù)量蔚為可觀,既有與傳世古書可對應者,如《吳孫子》十三篇、《尉繚子》等;也有已經失傳亡佚的文獻,如《曹沫之陳》《孫臏兵法》《蓋廬》等。據筆者統(tǒng)計,古史敘事在《曹沫之陳》《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太公》1銀雀山漢簡中與今傳本《六韜》相關的內容,整理者公布時直接以《六韜》為名。李零先生指出:“銀雀山漢簡的這一部分,它們未必就是《六韜》,或全部都是《六韜》。”從內容來看,銀雀山漢簡確有今本、中古本《六韜》無法對應的文字,今從李零先生意見,稱以為《太公》。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第400頁。《尉繚子》《蓋廬》等出土兵學文獻中皆有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敘事材料的情節(jié)和結構有明顯的襲取痕跡,可能直接使用了當時普遍流行的傳說,可稱之為“公共資料型”敘事;一類材料可以看到是出于作者或編纂者有意地二次加工而成,體現(xiàn)出帶有學說色彩的獨創(chuàng)性,可稱之為“二次加工型”敘事。其中尤以“二次加工型”敘事為多。本文嘗試通過對數(shù)則出土兵學文獻材料的分析,考察兵學文獻與其他諸子不同的古史敘事,以及兵學文獻之間存在的差異。進而探究在這種種差異現(xiàn)象的背后,兵家是如何通過構建古史來立言著書,又如何在汲取傳說時代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特的古史觀。
一、銀雀山漢簡《黃帝伐赤帝》的“一帝二王”敘事
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佚篇《黃帝伐赤帝》有:
孫子曰:“【黃帝南伐】赤帝,【至于□□】,戰(zhàn)于反山之原,右陰,順術,倍(背)(沖),大烕(滅)有之。【□年】休民,孰(熟)谷,赦罪。東伐□帝,至于襄平,戰(zhàn)于平□,【右】陰,順術,倍(背)(沖),大烕(滅)【有之。□】年休民,孰(熟)谷,赦罪。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戰(zhàn)于□□,右陰,順術,【倍,大烕有之。□年休民,孰谷,赦罪】。西伐白帝,至于武剛,戰(zhàn)于【□□,右陰,順術,倍,大烕有】之。已勝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歸之。湯之伐桀也,【至于□□】,戰(zhàn)于薄田,右陰,順術,倍(背)(沖),大烕(滅)有之。武王之伐紂,至于遂,戰(zhàn)牧之野,右陰,順術,【倍,大烕】有之。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之□、民之請(情),故……”2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2頁。
此篇以孫子之言追溯了“一帝二王”——黃帝、湯、武王得天下的原因,都是“得天之道、□之□、民之情”。關于《黃帝伐赤帝》篇的性質和成書時間,在發(fā)表之初曾引起熱烈討論。由《孫子兵法·行軍》篇中有“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3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188頁。此句銀雀山漢簡殘,尚存文字作“凡四軍之利,黃帝之……”整理者指出《黃帝伐赤帝》篇與“《孫子》十三篇”中的《行軍》篇有關,是《孫子》佚篇。4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7頁。李零先生進一步說明這是孫子后學對《行軍》篇“黃帝之所以勝四帝”的解釋,屬于戰(zhàn)國以來流行的“五行”學說。5李零:《<孫子>古本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12、296頁。近年又有學者提出《孫子》逸篇看不出是后學所作,《孫子》全書都“可能是一次意圖明確的偽托”。6關萬維:《<孫子兵法>成書時間新證》,《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22年第5期。關于成書時間,鄭良樹先生由文中提到“五色”“五帝”,結合《史記·封禪書》漢高祖設立黑帝祀的記載,認為此篇成書要在漢高祖二年(前205)后。7鄭良樹:《竹簡帛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9頁。宋會群先生則以《管子》《墨子》《逸周書》等文獻中有五行觀念為據,認為此篇成書不晚于《管子·幼官》,與《行軍》篇時代接近,至遲在戰(zhàn)國中期前已經完成。8宋會群:《論臨沂漢簡<黃帝伐赤帝>的著成年代》,《河南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何炳棣先生也認為“四帝”“五色”在《墨子·貴義》中已有體現(xiàn),更提出《黃帝伐赤帝》篇具有春秋屬性。1何炳棣:《中國現(xiàn)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歷史研究》,1999年第5期。
上述不少說法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者眾多,目前以李零先生的后學解釋說最為流行。但從古史構建的角度看,這一篇佚文與《行軍》篇只提到黃帝的情況并不相同,不是簡單的文義闡釋,較之《行軍》篇不僅加入了新材料,更體現(xiàn)出空間視野上的古史觀。
首先,《孫子兵法·行軍》篇“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對于黃帝和“四帝”之間的關系并未有具體論述,從《行軍》篇前文來看,黃帝戰(zhàn)勝“四帝”的原因是“四軍之利”,即善于利用不同地形部署軍力。而《黃帝伐赤帝》篇將此句描述為黃帝征伐赤、黑、白、青(據文義補)“四帝”的故事,不吝重復地說明黃帝戰(zhàn)勝的原因是“右陰,順術,2私以為“順術”當讀為“順行”,張家山漢簡《蓋廬》篇有“左水而軍,命曰順行”。參見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62頁。龐壯城指出,銀雀山漢簡《地典》篇簡1117“右水而戰(zhàn),氏(是)胃(謂)順□”中的缺字也當補為“行”,“左水”“右水”的差異是思想流派不同導致的。參見龐壯城:《北大漢簡<節(jié)>“地有五則”“地有七死”探析》,載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河南大學甲骨學與漢字文明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33輯),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412—416頁。背沖,大滅有之。□年休民,熟谷,赦罪”,與《行軍》篇單一地強調地利因素相比,文本和思想都有較大改動。前半部分整理者已經指出是與天象、方位有關的數(shù)術思想,3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33頁。后半部分是以德治民,也就是所謂的教民、養(yǎng)民之術。黃帝等古史傳說,以及方位數(shù)術與“五帝”的結合,并不是一家的獨創(chuàng),但在《黃帝伐赤帝》篇的鋪陳下,一帝二王取得勝利,是因為既合于天時、地形,又合于民情,戰(zhàn)術、民心、財力盡皆完備。這一部分明顯是出于編纂者的發(fā)揮和構造,看不出與《行軍》篇的聯(lián)系,《行軍》篇所強調的“四軍之利”反而被淡化了。就此點來看,《黃帝伐赤帝》篇展現(xiàn)出濃厚的學說色彩,不宜將其直接視作單純的《孫子》闡釋類作品,其是否正確表達了《孫子》的思想主張,也值得懷疑。
第二,《孫子兵法·行軍》篇“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只提及黃帝、“四帝”,而《黃帝伐赤帝》篇在黃帝戰(zhàn)勝“四帝”故事的基礎上,又新加入了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故事,較《行軍》篇發(fā)生了些許取向上的變化。《孫子兵法》中對于商、周二王記述并不多,只在《用間》篇說“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4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第300—301頁。講商周之興是因為用間。但是經過《黃帝伐赤帝》篇的編纂,商、周二王的故事被有意引入,并且“大滅有之”,實現(xiàn)了王朝更迭,體現(xiàn)出武力革命的色彩。這樣的增入可能并非偶然,“湯伐桀”“武王伐紂”的故事在戰(zhàn)國時期的兵學文獻中大量出現(xiàn),如《六韜》5目前大多數(shù)學者都將《六韜》判定為戰(zhàn)國時期的著作。徐勇先生指出《六韜》是戰(zhàn)國中晚期整理而成的作品,李零先生則認為在戰(zhàn)國晚期。參見徐勇:《<六韜>成書時代之我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3月24日,第010版;李零:《<孫子>十三篇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6頁。不過從目前《六韜》諸個相關版本(包括銀雀山漢簡、定州漢簡、敦煌寫卷、西夏刻本等)來看,今本《六韜》的編纂過程相當漫長,不同篇目的成書、編纂時間并不一致。此處所引《六韜》內容見于銀雀山漢簡、中古類書引文,應能判定成書時間較早。參見張帆:《<六韜>研究》,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2年。有豐富的武王伐紂的逸聞故事,還有許多夏桀亂政受到天罰的記載,《吳子·圖國》6對于今本《吳子·圖國》篇的成書時代,學者已經注意到其部分內容見于馬王堆帛書《經·本伐》和上博簡《曹沫之陳》,劉嬌先生由此認為此篇產生在戰(zhàn)國時期。參見劉嬌:《言公與剿說:從出土簡帛古籍看西漢以前古籍中相同或類似內容重復出現(xiàn)現(xiàn)象》,北京:線裝書局,2013年,第303、457—458頁。稱“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7陳曦:《吳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第32頁。《尉繚子·天官》8銀雀山漢簡中有與今本《尉繚子》相近的內容,但是篇名、文字均有出入。結合銀雀山漢簡、《群書治要》引《尉繚子》等資料,大致可以判斷《尉繚子》成書在戰(zhàn)國晚期,而今本《尉繚子》是經過后人修訂的刪改本。《天官》篇內容見于中古類書引文,文字與今本稍有出入,詳見許富宏:《尉繚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23年,第4—5頁。本文此處涉及的異文不影響文義,茲不贅言。也以武王伐紂之事論證天官不如人事。由于政治格局和社會背景的變化,戰(zhàn)國兵學文獻追溯古史時喜稱近世,頗具時代特色。此外,戰(zhàn)國時期大多數(shù)兵學文獻中看不到源出一脈的血緣帝系,更多的是擺脫了倫理限制的空間征服。《吳子》屢言“橫行天下”“威震天下”,《尉繚子》也說要“取天下”“戰(zhàn)勝天下”,這種變化在《孫子》的流傳中也有體現(xiàn)。“《孫子》十三篇”里軍事活動的主體多是“國”或“諸侯”,而《黃帝伐赤帝》篇以“一帝二王”為主體,戰(zhàn)略目標不再是十三篇所說的“安國全軍”,而是“大有天下”,空間視野上實現(xiàn)了從國家向天下的轉移。《黃帝伐赤帝》篇里最終黃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歸之”,將古史傳說中的圣王描述為以“滅”為主要占有方式的“天下之主”。這不僅反映了兵學文獻中古史敘事的增益現(xiàn)象,也透露出《黃帝伐赤帝》篇的完成時間更可能在戰(zhàn)國時期。
二、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設備》的兵器發(fā)明傳說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有“孫武既死,后百余歲有孫臏。臏生阿鄄之間,臏亦孫武之后世子孫也……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又言“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1司馬遷:《史記》卷65,《孫子吳起列傳第五》,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164—2165頁。明確提及有孫臏所作“兵法”。然而直到銀雀山漢簡發(fā)現(xiàn),《孫臏兵法》的面貌才真正顯現(xiàn)在大眾面前。檢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見威王》《設備》等篇都有援引古史來發(fā)揮己意的情況。其中,《設備》篇提供了與“蚩尤作兵”不同的兵器發(fā)明傳說故事,值得重視。
如果說在《黃帝伐赤帝》這篇文獻里,黃帝、商湯、武王還保持著君主、人王的形象,那么在《孫臏兵法·設備》2此篇篇題作“埶備”,整理小組原讀為“勢備”,后裘錫圭先生指出當讀“設備”。由此篇主旨是設立軍器,則讀為“設備”較好。今從裘錫圭先生意見對篇名作出修正。參見裘錫圭:《再談古文獻以“埶”表“設”》,載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4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487—488頁。中,3人已經被設定成為兵家先祖的角色。《設備》篇言:“故無天兵者自為備,圣人之事也。黃帝作劍,以陣象之。羿作弓弩,以勢象之。禹作舟車,以變象之。湯、武作長兵,以權象之。凡此四者,兵之用也。”3山東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銀雀山漢墓簡牘集成(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28頁。可以發(fā)現(xiàn),《孫臏兵法》選取的傳說史料與后世廣為流傳的“蚩尤作兵”不同,是黃帝、禹、湯、武等圣人發(fā)明了兵器。“蚩尤作兵”之說見于《山海經》《呂氏春秋》以及清華簡《五紀》等文獻,《孫臏兵法》的記述,展示出與“蚩尤作兵”不同的“作五兵”系統(tǒng),對豐富、補充戰(zhàn)國古史系統(tǒng)來說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湯淺邦弘先生曾總結《呂氏春秋》《通典》《黃帝內傳》等文獻中的說法,指出武器制造的傳說有蚩尤和黃帝兩系統(tǒng)。4湯淺邦弘:《戦いの神:中國古代兵學の展開》,東京:研文出版,2007年,第52—53頁。但其所引的文獻時代普遍較晚,其實在《孫臏兵法》中,已能找到這種不同記述。5《墨子·節(jié)用上》有“是故圣人作為甲盾五兵”之說,或與此有關。目前先秦典籍中,只能看到零星的黃帝作兵類敘事,如《越絕書》說“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之時,以玉為兵……禹穴之時,以銅為兵”,6李步嘉:《越絕書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03頁。圣王所發(fā)明兵器只是材質不同。則《孫臏兵法·設備》篇的圣人作兵故事,不僅與“蚩尤作兵”傳說相異,也與其他“圣人作兵”類故事不同。更重要的是,在發(fā)明傳說的基礎上,《設備》篇的作者或編纂者又將古史傳說與兵學的“陣、勢、變、權”相結合,其后文言“凡兵之道四:曰陣,曰勢,曰變,曰權。察此四者,所以破強敵,取猛將也”,7山東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銀雀山漢墓簡牘集成(貳)》,第29頁。依照這樣的敘事結構,四種“兵之道”都能追溯至黃帝、羿、禹、湯、武,這幾位傳說人物不僅是先圣,也是兵道之祖,兵道與圣人建立起了緊密的聯(lián)系。這不僅僅是簡單地取擇資料,更可能是作者或編纂者有目的、有意識地二次加工而成。
《孫臏兵法》不同的古史構建背后是編纂者的深層考量。雖然先秦時期軍事是“國之大事”,但是社會上“寢兵”的聲音幾乎從未消失過,《墨子》非攻,《莊子·天下》篇說宋钘、尹文也有“禁攻寢兵,救世之戰(zhàn)”之舉。儒家學者則是希冀以仁義替代戰(zhàn)爭,通過修德化民而天下和服。面對寢戰(zhàn)和廢兵的思潮,兵學文獻積極宣揚兵學和軍事的重要性,始終堅持兵不可廢。不同的立場在古史敘事中也有映射。
在兵學文獻的視角下,黃帝、堯、舜等成為天下之主與戰(zhàn)爭有直接關系,但在其他諸子尤其是儒家學派看來,卻并非如此。如《易·系辭下》言“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1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卷8,《系辭下》,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80頁。認為圣王“垂衣裳而天下治”。《荀子·議兵》說“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2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83—284頁。堯似乎只“殺一人,刑二人”,通過非常克制的方式,就能“天下治”,不需要戰(zhàn)爭和武器,也能收服和治理天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孫臏兵法·見威王》篇則是列舉了從神農、黃帝、堯、舜一直到周公等數(shù)位先圣的征伐之事,繼而說“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將欲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此堯舜非弗欲也,不可得,故舉兵□之”,3山東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銀雀山漢墓簡牘集成(貳)》,第8頁。用相當強的諷刺語氣指出五帝、三王、周公尚且不可廢兵,直接對“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說法進行了攻擊與批評。在古史構建時,儒家與兵家采取著不同策略,人物形象因此大相徑庭。
再如新出佚書清華簡《五紀》篇,選取了“蚩尤作兵”的傳說。其言:
蚩尤既長成,乃作為五兵。五兵既成,既礳、既礪,既銳,乃為長兵短兵,乃為左睘右睘。變詣進退,乃為號班:設錐為合,號曰武散;設方為常,號曰武壯;設圓為謹,號曰陽先,將以征黃帝。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拾壹)》,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此處采取寬式釋文。
《五紀》選取黃帝和蚩尤傳說史料后,也進行了非常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二次加工”。我們目前看到的大部分黃帝蚩尤故事,都是以黃帝為主角來展開敘述。《五紀》則別出心裁,這場戰(zhàn)爭的開端是以蚩尤的視角來講述的:蚩尤對戰(zhàn)爭做了精心準備,先制造和磨礪兵器,又進行了士卒訓練,練成了“三陣”。由此,蚩尤無論是武器還是士卒,都具有強大的戰(zhàn)斗力,然后前往征伐黃帝。如果處于兵學文獻的邏輯之下,蚩尤已經具備了戰(zhàn)勝的條件。但是《五紀》記載戰(zhàn)爭的結果并非蚩尤獲勝,而是黃帝在四荒、四冘、群祇等的輔佐下,恭敬地遵守“五紀”之法,5對于“五紀”的具體指代及與黃帝的關系,程浩先生指出:“《五紀》采用春秋戰(zhàn)國文獻常用的‘天見妖祥—圣賢救世’的敘事模式,謂后帝通過‘修歷五紀’等舉措平息了天下禍亂。在簡文的具體闡釋中,‘五紀’分別可與五時、五色、星宿、神明、干支等抽象概念,以及量具、五官、臟器、骨骼、尺度等具體事物相聯(lián)系,是時人的宇宙生成論、五行數(shù)術學說、天文歷法、自然科學知識的集中展示。為了論證作為‘天神’的后帝所設計的‘五紀’體系切實有效,簡文以最初的‘人王’黃帝為例,集中描述了人世間對這套理論體系的具體實踐。”則黃帝也只是“五紀”的執(zhí)行者,而非唯一的后帝。參見程浩:《清華簡<五紀>中的黃帝故事》,《文物》,2021年第9期。最終戰(zhàn)勝了蚩尤。蚩尤不僅被殺死,其身體還被黃帝分割、祭享,走向了帶有些許神話色彩的慘烈結局。也就是說,作者前文如此濃墨重彩地描述蚩尤的軍事能力和戰(zhàn)斗準備,只是為了反襯黃帝所行“五紀”的重要性而已。《五紀》的作者雖然并未旗幟鮮明地反對戰(zhàn)爭和兵學,但已經透露出他的態(tài)度:“兵”不是取天下最重要的因素,軍事能力也不是國家治理里最重要的能力。
雖然社會上蚩尤作兵的傳說廣為流行,“蚩尤”甚至被視為戰(zhàn)神,但蚩尤戰(zhàn)敗的結局始終是無法抹殺的。與《五紀》不同,《孫臏兵法》沒有選擇蚩尤的傳說,而是通過對圣人兵器發(fā)明傳說的構擬,搭建起“圣人—兵道—破敵取將”的敘事結構,彰顯著作者強烈的兵學呼吁。《孫臏兵法·設備》篇的“圣人作兵”傳說一方面顯示出先秦古史傳說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兵學文獻“以兵為利”的態(tài)度,通過古史構擬的途徑來對抗諸子“寢兵”說的沖擊。不過,以圣人作兵來宣揚兵不可廢,并不意味著對暴力和戰(zhàn)爭的推崇,《孫臏兵法·見威王》中明確說“兵者,非士恒勢也。此先王之傳道也”,又說“戰(zhàn)勝,則所以存亡國而繼絕世也。戰(zhàn)不勝,則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6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48頁。此處采取寬式釋文。兵事的存在只是為了保證和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樣的態(tài)度在《孫臏兵法》和眾多兵學文獻中都是一以貫之的,如《孫子兵法·見吳王》中有“兵,利也,非好也”,7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壹〕》,第34頁。《司馬法》也說“殺人安人”“以戰(zhàn)止戰(zhàn)”。1王震:《司馬法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2頁。兵學文獻頻繁地演說“圣人以興,亂人以廢”式的故事,目的只是為了證明“兵”的必要性。在軍事家的眼中,戰(zhàn)爭的終極目標不是殺人,戰(zhàn)爭只是消除戰(zhàn)爭的必要手段。
三、銀雀山漢簡《地典》與對黃帝兵學的批評
“百家言黃帝”,黃帝在諸子文獻中展現(xiàn)出不盡相同的形象。那么,在同一類型或者同一流派的文獻內,黃帝形象是否具有一致性呢?從兵學文獻中的材料來看,黃帝雖然是兵家共祖,但是對黃帝戰(zhàn)勝原因的總結,兵學文獻有所區(qū)別,甚至還出現(xiàn)了相抵牾的情況。銀雀山漢簡《地典》與《尉繚子》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例。
《漢書·藝文志》“兵書略”下有不少黃帝書,只是大多已經亡佚。2010年出版的《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公布了一篇記錄黃帝與地典對話的文獻,簡背有篇題“地典”,主旨是論兵,大多學者都認為這篇文獻很可能就是《漢志》“兵陰陽”下的《地典》,2整理者即言銀簡此篇就是《漢志》兵陰陽家的《地典》,《漢志》記有六篇,“殘簡數(shù)量不多,疑原本不足六篇之數(shù)”。裘錫圭先生則認為銀簡此篇是“單篇的抄本”。參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49頁;裘錫圭:《出土文獻與古典學重建》,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4輯),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第5頁。李零先生稱其有“填補空白的作用”。3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第396頁。雖然竹簡殘斷嚴重,但仍可以看到這樣一些內容:
……敗,高生為德,下死為刑,四兩順生,4“四兩順生”,馬王堆帛書《經·觀》篇有“今始判為兩,分為陰陽,離為四【時】”,《地典》篇“四”“兩”或即四時、陰陽之謂。參見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52頁。《經》,《集成》原作《十六經》,此書過去多稱《十大經》,學界對其命名始終有爭議,張政烺先生將“大”改釋為“六”,《集成》從之。但其實篇數(shù)既不是十也不是十六,李學勤先生指出“十大”是末篇篇題,“經”是總篇題。今從李學勤先生意見,暫以《經》稱之。參見李學勤:《論<經法·大分>及<經·十大>標題》,載氏著:《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7—296頁。此胃(謂)黃帝之勝經。黃帝召地典而問焉,曰:“吾將興師用兵,亂亓(其)紀【1107】剛(綱),請問其方。”地典對曰:“天有寒暑,地有兌(銳)方。天……天有十【1108】二時,地有六高六下。上帝以戰(zhàn)勝【1109】……
……者為陰地【1125】……者為陽,秋冬為陰,□……【1126】
……為生,然而大(太)陽者死,大(太)陰者死……【1129】
……□北。地典曰:“上帝審此,以戰(zhàn)必克,以攻必取【1138】……自降北,吾不頓(鈍)一兵,不殺一人,而破軍殺將。如此……【1139】……加之,四方皆服。【1140】5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147頁。
黃帝擔心興兵作戰(zhàn)會“亂其紀綱”,地典答以天時地形、陰陽向背,為黃帝制定了一部制勝寶典,也就是“黃帝之勝經”。寶典中的“紀綱”指的就是刑德,具體來說是按照陰陽系連的天時、地形來作戰(zhàn)的理論。按照這個理論,最終就能“不鈍一兵,不殺一人,而破軍殺將”,天下和服。諸家常以黃帝屢戰(zhàn)屢勝為說,如《鹖冠子·世兵》說“黃帝百戰(zhàn)”,6黃懷信:《鹖冠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62頁。《六韜》佚文有“黃帝七十戰(zhàn)而定天下”。7語見《孫子·行軍》篇張預注引《太公六韜》。參見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第189頁。但在《地典》的敘事鋪陳下,黃帝能夠戰(zhàn)必克、攻必取都是因為掌握了刑德,這自然是出于《地典》的“二次加工”。
李零先生認為《漢志》“兵陰陽”下都是依托黃帝君臣的兵法,屬于黃帝書。8李零:《蘭臺萬卷:讀<漢書·藝文志>》(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第159—160頁。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這類文獻與馬王堆帛書有思想上的相關性,并指出《地典》中的陰陽、刑德思想與馬王堆帛書的黃老文獻相近。9如葉山:《論銀雀山陰陽文獻的復原及其與道家黃老學派的關系》,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簡帛研究譯叢》(第2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2—94頁;田旭東:《“兵陰陽家”幾個問題的初步研究》,載西北大學文博學院編:《中國古代史論文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14頁。近來又有學者論證《地典》與北大漢簡《節(jié)》部分文字接近,是兵學與陰陽地理的結合。1洪德榮:《<銀雀山漢墓竹簡〔貳〕·地典>研究》,載《華學》編輯委員會編:《華學》(第12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17—226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陰陽、刑德等名詞外,上引《地典》篇的內容里還同時出現(xiàn)了“黃帝”和“上帝”,并很大程度上將他們等同起來。在馬王堆帛書《經·正亂》篇中,也同時出現(xiàn)了黃帝和上帝,其以黃帝征伐蚩尤之事強調“上帝以禁”,黃帝與上帝也是相對應的。2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第159頁。上帝在商周時期本是信仰神,文獻屢言“明明上帝”“皇皇上帝”,上帝是作為祭祀對象出現(xiàn)的,至高無上。而《地典》篇的黃帝作為“上帝”,卻沒有主宰的權力,反而強調要“順生”,尤其是要順應天時、地理,則在《地典》和馬王堆帛書的構建中,黃帝與上帝的形象處于交融期,黃帝還不是全能神,也不是后世流傳的能“剖判大宗,竅領天地”“大合鬼神”的至上神。3《淮南子·俶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窾,重九,提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于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黃帝似乎有創(chuàng)世之能。《韓非子·十過》又有“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并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黃帝具有極強的神性。晁福林先生指出這種能號令眾神的黃帝形象是出現(xiàn)較晚的。參見晁福林:《黃帝與畏獸——<山海經>研究的若干問題補釋》,載氏著:《夏商西周史叢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87—94頁。因此,《地典》作為融貫了黃帝刑德、兵法地理的著作,可以看作是“黃帝兵學”的一種早期類型。
非常有趣的是,在傳世兵書中可以找到對《地典》“黃帝刑德”說的回應與批評。今本《尉繚子·天官》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4許富宏:《尉繚子校注》,第4—5頁。“黃帝刑德”,《治要》引文作“黃帝有刑德”。過去有學者以為《尉繚子》此節(jié)所引“黃帝刑德”來源于《漢志》的“《黃帝》十六篇”,還有學者即以“刑德”為書名(即黃帝《刑德》或《黃帝刑德》),難以辨明。5徐勇主編:《先秦兵書通解》,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71頁。學者意見可參劉春生譯注:《尉繚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頁。今將《尉繚子》征引的內容和《地典》對照,很明顯可以看出,所謂的“黃帝刑德可以百勝”“天官時日陰陽向背”正是銀雀山漢簡《地典》的內容。大膽推測,《尉繚子》征引的黃帝書可能就是已經重見天日的銀雀山漢簡《地典》。不過,《尉繚子》又在《地典》基礎上做了新的加工,提出黃帝不是依靠刑德取勝的,而是憑借人事,與《地典》的黃帝兵學思想殊異。
從《尉繚子》和《地典》不同的思想傾向可以看出,兵學文獻之間也存在一些分歧。一類兵學文獻希望通過神秘化黃帝等傳說人物,將兵法與“道”貫通起來,典型代表如銀雀山漢簡《地典》、張家山漢簡《蓋廬》。傳世的《六韜》也有“黃帝曰:一者,階于道,幾于神”(《兵道》篇)、6王震:《六韜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22年,第113頁。“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五音》篇)7王震:《六韜集解》,第311頁。的內容,亦屬于神秘化的黃帝兵學流派。而另一類兵學文獻則是在盡力剔除黃帝兵學中的陰陽學說,如《尉繚子·天官》有“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8許富宏:《尉繚子校注》,第14頁。將黃帝兵學的重點置于“人事”之上。《孫子兵法·九地》也說要“禁祥去疑”,9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第249頁。對神秘難測的陰陽術數(shù)進行控制和祛除。這種分歧和沖突貫穿著兵學文獻的流傳史,極大地影響了黃帝形象的發(fā)展,直到中古時期仍有余音。10在《李衛(wèi)公問對》中,尚可看到對這種沖突的討論,太宗詢問“陰陽術數(shù),廢之可乎”,李靖雖然贊同《尉繚子》人事為重的觀點,但依然堅持“兵者,詭道也,托之以陰陽術數(shù),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唐律》雖將有陰陽方術色彩的兵學文獻(如《六韜》)列為禁書,但從現(xiàn)存目錄上看,李筌《太白陰經》等陰陽方術類兵學文獻數(shù)量眾多,大為流行。可見中古時期,兵學“禁祥”與“方術”兩條思想路徑皆在發(fā)揮影響,并行于世。
其實,由于早期古史傳說材料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即使是同一文獻內的古史系統(tǒng),也難以避免存在差異和矛盾。前文言兵學文獻后期強調“王天下”,圣王都是天下之主。《六韜》也是屢言圣王文武兼治、“天下和服”,但是《文啟》篇又有“古之圣人,聚人而為家,聚家而為國,聚國而為天下。分封賢人以為萬國,命之曰大紀”,1王震:《六韜集解》,第152頁。圣人并不親自治理天下,而是將“賢人”分封至萬國,各行其教。對于理想時代的刻畫,《六韜》的《盈虛》等篇都采取了圣王(如堯、周武王等)親自管理國家的方式,最終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2王震:《六韜集解》,第35頁。《文啟》篇則采取了“無為而成事”的方式,最終百姓實現(xiàn)“無與而自富”。雖然《六韜》多數(shù)篇目成書在戰(zhàn)國時期,但是《文啟》的古史敘事還保留著早期邦國、分封的痕跡,與戰(zhàn)國中后期開始發(fā)展起來的帶有統(tǒng)一意味的“天下型國家”有別。3本文所說的“天下型國家”概念來自渡邊信一郎先生,其說詳見[日]渡邊信一郎著,徐沖譯:《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增訂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93—95頁。
四、上博簡《曹沫之陳》所見歷史觀
人們樂此不疲地重復那些古代逸聞傳說,當然有黃金時代和圣賢具備吸引力的原因在,不過可能更多是出于古史對現(xiàn)實的關照性。無論何種主張、哪家學派,都不可回避地受著歷史的影響。“今之世”是要回歸“古之道”,還是要拋棄“古之道”?如何處理歷史留下的思想文化遺產,是諸子共同面對的課題。兵學文獻在使用古史材料時,彰顯出了頗具特色的古史觀。
2004年公布的上博簡《曹沫之陳》是戰(zhàn)國竹書寫本,不見于《漢書·藝文志》,可知很早就已亡佚。大多數(shù)學者都認為其反映著春秋中晚期至戰(zhàn)國前期的兵學觀念,是一篇重要的兵學文獻。4田旭東:《戰(zhàn)國寫本兵書——<曹沫之陳>》,《文博》,2006年第1期。王青先生則認為《曹沫之陳》是原始《國語·魯語》的一部分,與大多數(shù)學者意見不同,參見王青:《上博簡<曹沫之陳>疏證與研究》,臺北:臺灣書房,2009年,第175—222頁。這篇文獻在安徽大學收藏的戰(zhàn)國竹簡中再次出現(xiàn),內容基本相同,只是文詞稍異,證明其具有一定的流傳度。《曹沫之陳》以魯莊公和曹沫的對話為載體,論述了治國、治兵之道,文章中三次對古史的稱述引人注意。首段曹沫援引堯、舜“飯于土簋”的故事,“昔堯之享舜也,飯于土簋,啜于土铏,而撫有天下。此不貧于美而富于德歟”,5上博簡《曹沫之陳》簡文參見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45—285頁,本文采取寬式釋文。又,“啜于土铏”,上博簡原作“欲于土型(铏)”,整理者李零先生已指出“欲”是“歠”字之誤。安大簡《曹沫之陳》此字作“”,印證了上博簡“欲”確是“啜(歠)”的訛字,此句即當讀為“啜于土铏”。旨在勸諫莊公治國當儉,具有明顯的以古喻今色彩。中間在談及陣法時,曹沫話鋒一轉,說“臣聞之:有固謀而無固城,有克政而無克陣。三代之陣盡存,或以克,或以亡”。在陣法這個話題上,曹沫提出無須照搬古之道,三代的遺產不是萬能的、完美的,古今之間又失去了關照性。由于曹沫所說看似存在矛盾,所以在文章末尾,出現(xiàn)了對上述兩種立場的總結:
莊公曰:“沫,吾言寔不,而如惑諸小道歟?吾一欲聞三代之所。”
曹沫答曰:“臣聞之:昔之明王之起于天下者,各以其世,以及其身。6安大簡作“以沒其身”。參見安徽大學漢字發(fā)展與應用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二)》,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第56、76頁。今與古亦多不同矣,臣是故不敢以古答。然而古亦有大道焉,必恭儉以得之,驕大以失之。君其亦唯聞夫禹、湯、桀、受矣。”7此節(jié)綜合陳劍、李銳、高佑仁等學者意見寫出,參考高佑仁:《<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四)·曹沫之陳>研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372—385頁。
魯莊公想要深入地了解“道”,于是詢問曹沫三代圣王是如何做的。曹沫一方面說“今與古亦多不同”,這是呼應前文所說的無須模仿“三代之陣”;一方面又說“古亦有大道焉,必恭儉以得之”,這是呼應首段的要學習堯舜節(jié)儉之事。古、今之間有借鑒性,也有非因襲性:對于古史中圣王的恭儉故事,于今有益,那么就要效仿其節(jié)儉;對于古史中軍陣等技術層面的東西,用處寥寥,那么就要因時制宜,各行其是。《曹沫之陳》提出既不能拋棄圣王的治國法則,也不能盲目地迷信古代,其古史觀可以總結為:不片面非古,不全然復古。
這樣的思想主張在戰(zhàn)國時期具有獨特性。儒家的歷史觀非常強調對“古之道”的尊奉,如《荀子·議兵》篇記荀子之言曰:“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zhàn)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1王先謙:《荀子集解》,第266頁。依照荀子對古史的闡釋,古今具有一致性和連貫性,羿、造父、湯武的“道”對于現(xiàn)世也是一樣有效的,所以他又說“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再次以湯武為例,“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2王先謙:《荀子集解》,第290頁。這為湯武與現(xiàn)實中的君主建立起了聯(lián)系,將古之道與現(xiàn)實也建立起了聯(lián)結。《荀子·非相》篇稱那些認為古今相異的人為“妄人”,并說:“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3王先謙:《荀子集解》,第82頁。荀子屢言“古今一”的基礎在于他認為歷史和當下是可“度”的,存在不能磨滅的普遍規(guī)律。如果說看不到這種相關性,不是因為沒有規(guī)律,只是因為傳說時代史料匱乏而已。
與儒家針鋒相對,一些法家學者認為古今相異,不可法古,如《商君書·更法》言“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4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5頁。《韓非子·五蠹》言“世異則事異”,提出要因時變而事變的歷史觀。5宋洪兵先生將此概括為“應時史觀”,較進步史觀、變化史觀等說法更為準確。參見宋洪兵:《“應時”與“復古”之間——共識視閾中的儒法歷史觀初探》,《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08年第10期。《韓非子·五蠹》將歷史時期分為上古、中古、近古3個階段,各有與之適應的圣王和治道,古今已然不同,“今有構木鉆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于當今之世者,必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6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442頁。《韓非子》站在歷史遷移變化的立場上,強烈否定古之道的近世適用性。
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兵學文獻的態(tài)度與儒、法兩家皆不相同。兵學文獻雖然也認可先王之道,也在有意或無意地傳遞古今具有相關性,但是對于古代文化遺產,并不主張完全地尊奉和繼承。《曹沫之陳》一方面對“古之大道”中道德層面的“恭儉”進行贊譽,希望國君可以繼承和襲取;一方面又對工具層面的“軍陣”進行否定,認為謀勝于陣。對于堯、舜、禹、湯、桀、受時期的歷史經驗,《曹沫之陳》的取擇體現(xiàn)出基于實際的理性主義思考。
五、結 語
通過對上述出土兵學文獻中古史記載的考察,可以證明古史傳說在流傳過程中,會受到傳播者學術傾向的影響,呈現(xiàn)出一定的學派或流別特色。楊寬先生曾言:“諸子意在立說求用,其引據古史傳說,無非欲以發(fā)攄己意,以申其說,其取舍有不同,亦誠有之。”7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頁。這提醒我們,諸子對古史的構建并非疑古者主張的“托古改制”“古史出于諸子臆說”,而是在取擇社會流傳的古史資料時,有所偏重,有所發(fā)揮,也可能有“再加工”與“再創(chuàng)造”的行為。對于這些材料,真?zhèn)尾粦撌桥袛嗥鋬r值的唯一標準。在中華歷史文明記憶的塑造過程中,諸子對古史的闡釋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兵學文獻是戰(zhàn)國諸子多樣化古史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huán)。正是在兵學文獻對古史的構建下,歷史記憶中歷代圣王的軍事政策才沒有流于表面的道德判斷,而是展現(xiàn)出強大的實用價值和現(xiàn)世關懷。時至今日,“兵不可廢”的主張依然具有生命力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