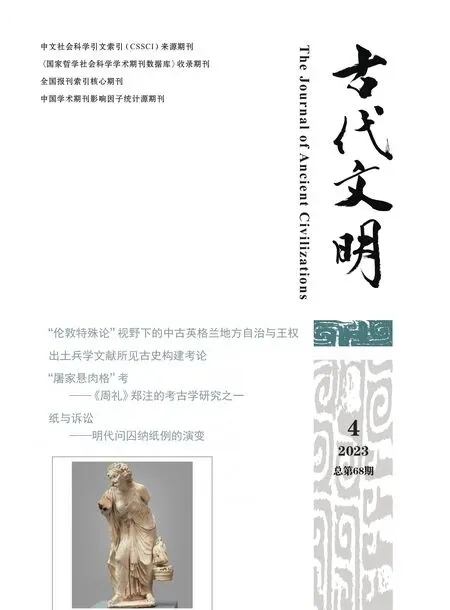紙與訴訟
——明代問囚納紙例的演變
劉正剛
提 要:明初中央各部院用紙多用刑部“贓罰鈔”購買,洪武末,允準刑部問囚納紙以補紙張不足。正統時,巡按監察御史、分巡按察使、布政司理問所及府州縣衛所也在聽訟中獲得納紙權。納紙對象由起初的有罪者逐漸擴大到原被告及案件牽連者,并在成化時合法化。從天順時起,訴訟納紙由本色互折轉向折納銀、米,后在實踐中形成二成本色、八成折色的模式,且折色逐漸成為地方財政的構成部分。納紙與訴訟密切相關,紙價卻被衙役和紙鋪商操控,因此,地方官府出于公私利益而維持訴訟規模。
明代社會公私領域處理各項事務均離不開紙。就公領域用紙來說,其來源大約有四:一是國家設廠“抄造紙札”;二是從市場購買;三是向地方征派;1參看佚名:《國朝典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6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41頁;佚名:《新官軌范·民情第四》,《官箴書集成》第1冊,合肥:黃山書社,1997年,第744頁。四是問囚納紙。所謂問囚納紙則與訴訟有密切關聯,文獻對此記載較豐富。明代重視法律的制定與實踐,洪武元年(1368)頒布的《大明令》就規定了標準化的詞狀格式,要求官府對訴訟進行文簿登錄,2李善長等:《大明令》,載楊一凡點校:《皇明制書》第1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7頁。國家在公私訴訟領域“徹底實行著書面主義”。3[日]夫馬進:《明清時代的訟師與訴訟制度》,載[日]滋賀秀三等著,王亞新、梁治平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395頁。晚明某些地域因訴訟激增,導致訴狀用紙價格飛漲。4[日]夫馬進編,范愉、趙晶等譯:《中國訴訟社會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2頁。明代各級問刑衙門審理案件,一般先審原告,再拘喚被告,如被告不服,再審干證人。若干證人供詞與原告相同,再問被告,“如各執一詞,則喚原被告、干證人一同對問”。5佚名:《諸司職掌》,《刑部·問擬刑名》,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續編》第3冊,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8頁。所有案件的審結,均以書面簽字畫押為準。也因為如此,朝廷根據司法實踐,不斷頒布條例,從法律層面對各級衙門的問囚納紙進行引導規范。學術界對明代問囚納紙問題的研究,臺灣學者較早專門關注,認為明代囚紙就是訴訟當事人的訴訟費用,其目的一方面是防止濫訴,另一方面為政府提供日用紙張、資助官吏俸鈔、糴谷備賑等需求。1巨煥武:《明代的訴訟費用——囚紙》,(臺北)《大陸雜志》,1981年第4期。這一結論稍后被大陸學者在研究明代訴訟制度時所接受。2杜婉言:《明代訴訟制度》,《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2期。除囚紙為明代訴訟費用外,有學者認為明代文獻中的“紙贖”也是訴訟費的代稱。3趙紅梅、程志兵:《明清文獻中的“紙贖”和“紙贖銀”》,《貴州文史叢刊》,2010年第4期。囚紙去向也成為學者的研究對象,明代自洪武后期以降的公文用紙多來源于訴訟繳納的囚紙,并因折色而導致紙張流通頻繁、紙價變動不一。4郭敏:《明代公文紙的來源、流通與價格》,遼寧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2年。上述學者從不同視角的研究表明,明代囚紙就是當事人繳納的訴訟費,屬明代訴訟法的重要范圍。然而學者至今鮮見從法律史的視角對納紙來龍去脈以及納紙在司法實踐中的動態演變進行系統梳理。明代問囚納紙條例如何出臺并推行?在司法實踐中納紙的對象如何進一步擴大?納紙從本色轉為折色后的用途有無變化?官吏在執行納紙例時有無權力尋租現象?本文通過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分析納紙從原先為保障公務用紙到后來逐漸發展為地方財政來源之一的轉變歷程,揭示納紙例演變背后并非完全是防止濫訴,抑或隱藏著維持訴訟規模的玄機。
一、問囚納紙由刑部擴展至各問刑衙門
明代中央司法機構為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地方為按察司、布政司、府州縣。軍事系統內的司法事務,自上而下,由五軍都督府斷事官至衛所鎮撫負責。洪武末,五軍都督府斷事官歸入刑部,地方衛所則繼續保留司法權。5張金奎:《明代衛所司法簡論》,載李文儒主編:《故宮學刊》(2006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刑部主要負責重案要案的審訊,按察司和府州縣則為地方聽訟機構。洪武初,刑部問囚定罪后,多以“贓罰鈔”懲處,該法承自元代。6陳高華等點校:《元典章》,北京:中華書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冊,第1611—1614頁。洪武二十七年(1394)之前,刑部“贓罰鈔”有部分被用來購買公務用紙,刑部“紙札舊例,收買應用。后令囚人納紙,而各衙門紙札亦從本部關給,各有事例”。7陶尚德等:《南京刑部志》卷3,《祥刑篇·收買紙札》,《金陵全書》乙編史料類第18冊,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年,第452頁。所謂“舊例”應是洪武二十六年(1393)頒行的《諸司職掌》中的《刑部·收買紙札》條:
凡本衙門合用奏啟本、案驗行移簿籍、囚人寫招服辨一應紙札,山西部掌行。每季會計合用奏啟本等紙札若干,估計合用鈔若干,本部明立文案,開付湖廣部,于贓罰鈔內照數關支。差官前去街市及客商販賣去處,照依時價,兩平收買數足到部,堂上官用印封鈐,責付庫子收領在庫。聽候各部將各季用紙數目呈堂,判送湖廣部立案,照數關支。候至季終,銷用盡絕,各部開稱為某事用過某色紙若干,逐一開付本部,將各部花銷紙數查理明白,將來付附卷。其余季分,如前施行。8佚名:《諸司職掌》,《刑部·收買紙札》,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續編》第3冊,第281頁。
從中可知,明初刑部各衙門用紙,先上報給該部的山西部,然后以書面文案給湖廣部,由湖廣部關支贓罰鈔,“照依時價”,從市場購買,再鈐封入庫,各衙門再按季按需領取,所用紙張數量皆詳細登記在案。此外,刑部還需供應朝廷其他部屬用紙,如吏、兵部的紙札,“移咨刑部,于贓罰鈔內關支價鈔買用,明白立案開銷”。9佚名:《諸司職掌》,《吏部·紙札》《兵部·紙札》,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續編》第3冊,第103、274頁。當然,朝中各部還從工部領取由“地方分派造解”之紙使用。10佚名:《諸司職掌》,《工部·紙札》,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續編》第3冊,第309頁。
洪武時,百廢待興,紙張相當匱乏,時“國子監生課簿、仿書,按月送禮部。仿書發光祿寺包面,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費如此”。11陸容:《菽園雜記》卷12,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53頁。缺少紙張,影響了書籍的刊印,“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之,外郡縣疑未有”。12陸容:《菽園雜記》卷10,第128—129頁。洪武二十七年為緩解紙札不足問題,朝廷出臺了刑部“囚人納紙”事例:“奏準問過罪囚,除逃軍、逃囚全家抄札起發并劫贓外,其余官吏、軍民人等俱各辦納紙札一分。”1陶尚德等:《南京刑部志》卷3,《祥刑篇》,《金陵全書》乙編史料類第18冊,第453頁。所謂“奏準”是明代權宜之法的一種表達,“出朝廷所降則書曰詔曰敕;臣下所奏則書曰奏準、曰議準、曰奏定、曰議定”,統稱“事例”。2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凡例》,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明正德刻本,第1冊,第2—3頁。上述事例明確規定刑部對問斷有罪者,“俱各辦納紙札一分”,改變了之前的“贓罰鈔”字樣,但對逃軍、逃囚等僅查抄家產和贓物,并不罰紙。明代文獻有時也將納紙稱為罰紙。有學者依據正德《大明會典》中“凡本司紙札,正統五年奏準令囚人買用”說法,認為明代京審囚人納紙始于正統五年(1440)。3楊雪峰:《明代的審判制度》,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1年,第352頁。按該條見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卷180,《二十二衛·錦衣衛》,第64冊,第6頁。但此條原置于錦衣衛下。刑部問囚納紙其實早在洪武二十七年就已開始。
刑部問囚納紙僅供京師各部使用。那么,地方衙門如何解決日常公務用紙?明初都察院常派監察御史巡視各地,他們到達地方之后的用紙則是用官鈔購買,地方提刑按察司派往州縣辦案的按察分司也如此。兩者“巡歷去處,合用紙筆、朱墨、燈油、柴炭,行移所在有司并支給官鈔收買應用,[具]實銷算”。4佚名:《憲綱事類》,載楊一凡點校:《皇明制書》第4冊,第1458頁。監察御史和按察分司派出辦案人員在巡歷中涉及問刑事宜時,可能也嘗試過問囚納紙,但被朝廷否決,“通行各處巡按等項監察御史及各處分巡按察司官,凡問罪囚,俱不許罰紙”。5佚名:《皇明弘治條例》,(弘治元年八月)《在外問刑衙門及巡按等官囚犯紙札俱照刑部則例及止據土產不許故索淹禁并非專問刑官不許罰紙》,邱仲麟主編:《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22冊,臺北:三民書局等,2022年,第196頁。
正統二年(1437),江西按察司副使焦宏奏,6據《明英宗實錄》記載,正統三年升江西按察司副使焦宏為江西右布政使。《明英宗實錄》卷49,正統三年十二月丁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942頁。下文所引明代各朝實錄均為此版,不再贅述。“所轄府州、衛所軍民詞訟數多,合用紙札本司措辦罰買用度不敷,要照在京法司罪囚納紙事例,減半追收紙札應用”。得到皇帝允準,經各部計議,由刑部、都察院“通行各處知會,照依所言事理,減半納紙應用。若有余積之數,類解順天府廣備庫交收,以備在京各衙門支用”。7佚名:《皇明成化八年條例》,《在外罪囚罰紙俱[照在京則]例減等不許多收濫罰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3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第194頁。焦宏所言在正統九年(1444)又被朝廷重申:“命各按察司[照]在京法司問囚納紙事例,減半追紙,送布政司收貯支用。余者,冬終類解順天府。從江西按察司副使焦宏言也。”8《明英宗實錄》卷121,正統九年九月丙子,第2433頁。從“各處”“各”等字樣看,江西納紙例已通行各地。除了江西按察司機構采取問囚納紙減半事例外,刑部也應福建布政司的咨呈,將在福建按察司推行的減半納紙例擴大到布政司、都指揮司,時布政司“理問所并府州、衛所囚人合無一體減半納紙”尚未獲準,刑部為此“已經通行福建等都、布二司行屬一體遵守”。9佚名:《皇明成化八年條例》,《在外罪囚罰紙俱[照在京則]例減等不許多收濫罰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3 冊,第193—194頁。可見,福建都、布、按三司以及府州、衛所都享有問囚納紙權。為防止州縣、衛所擴大納紙對象的范圍,條例規定:“今后司府州縣、衛所,止將立案問有罪名歸結原被告人,照依京例減半追收紙札應用。多余之數,照原擬解京。其余一概追被告人及發屬剖理軍民原告,并不許一概追納。”10佚名:《皇明成化八年條例》,《在外罪囚罰紙俱[照在京則]例減等不許多收濫罰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3 冊,第195頁。強調州縣、衛所只能在審斷后對有罪者納紙。
納紙例在實際執行中,并不是所有的按察司問囚均對犯人罰紙,但罰紙處置機構顯然趨于增加。景泰元年(1450),四川按察司僉事劉福“分巡出外問囚,亦不罰紙”,而四川按察使茅惟揚則“照依前例減半罰紙”。天順年間,“各處巡按清(事)[軍]等項御史、各處分巡按察官問囚俱罰紙札”。11佚名:《皇明成化八年條例》,《在外罪囚罰紙俱[照在京則]例減等不許多收濫罰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3 冊,第196頁。隨著問囚罰紙衙門的增多,成化八年(1472)朝廷又出新例加以規范:“各處巡按御史與各處分巡按察司官所問囚人,一體減半罰紙應用,清軍、巡鹽、巡河、巡關等項監察御史不專問囚,合用紙札,仍遵《憲綱》內事理支給官錢買用。今后囚人罰紙,俱照在京則例減半,不許多收濫罰紙張。”1佚名:《皇明成化八年條例》,《在外罪囚罰紙俱[照在京則]例減等不許多收濫罰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3 冊,第200—201頁。強調只有問刑衙門才有權對罪囚罰紙,不是專門問囚的官員,則仍用官錢購買紙札使用。
上述按察司、布政司審囚納紙主要供本衙門自用。若有多余紙札,則解京儲庫以供部院用紙之需。如明英宗“初即位,敕省諸冗費,于是禮部尚書胡濙等議,欽天監歷日五十萬九千七百余本,省為十一萬九千五百余本”。2余繼登:《典故紀聞》卷11,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87頁。弘治五年(1492),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丘濬要求內閣“將考校見有書籍,備細開具目錄,付禮部抄謄”,分送各地官員。3丘濬:《訪求遺書疏》,載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76,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651頁。如此大規模的用紙,可能包括地方“類解”都察院的紙札。而且,中央的多個部門都使用過在京儲備的紙張,此在弘治十年(1497)奏準事例中有所反映:“吏、戶、禮、兵、工五部及大理寺歲用紙札,刑部關支不敷,于都察院見收類解紙札內關用。如又不敷,并刑部題奏本紙俱于兩法司支贓罰銀買辦,有余作次年之用。”4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卷137,《刑部十二·收買紙札》,第50冊,第4頁。顯然,中央各衙門的用紙主要從刑部和都察院“類解紙札”中關支。據統計,弘治十七年(1504)在京大小衙門有近50個,“每年春秋二季俱赴刑部,夏冬二季俱赴都察院,各照數關用”。5申時行等:(萬歷)《大明會典》卷179,《刑部二十一·收買紙札》,《續修四庫全書》第79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2頁。而都察院的“見收類解紙札”,應是從各分巡按察使處押解而來。與此同時,地方用紙數量也頗為巨大。正德十年(1515)四月,河南都司所屬衛所“每年合用文冊一十五項,每項多者一樣十本,少者不下六七本,多者每本數百張,少者亦不下六七十張”。6趙堂:《軍政備例》,《續修四庫全書》第8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15頁。
可見,明代罪囚納紙從洪武末年的刑部開始,正統時,因巡按監察御史以及按察分司在地方巡歷中出現問囚納紙,并由此延伸到布政司、都指揮司及其下屬的府州縣、衛所等衙門也開始納紙。納紙例幾乎覆蓋了明代所有的聽訟衙門。成弘時期,隨著社會經濟轉型,納紙例在地方發生了新變化。
二、訴訟納紙對象的擴大化
從洪武末到正統年間,不同層級問刑衙門的納紙對象都是有罪者。正統二年(1437)出臺《在京法司問囚納紙事例》,根據涉案者身份的不同,納紙數量也不同:“官吏、總小旗、舍人、糧長,榜紙一十五張、中夾紙二十張;原告勘合紙一十張、中夾紙一十五張;軍民中夾紙二十七張、奏本紙五張、手本紙三張。”7佚名:《皇明成化八年條例》,《在外罪囚罰紙俱[照在京則]例減等不許多收濫罰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3 冊,第195—196頁。這里首次出現“原告”納紙。之所以強調原告納紙,應與朝廷提倡“息訟”理念有關。此規定的計量單位是“張”,與洪武二十七年規定罪囚納“紙札一分”不同。弘治元年(1488),“問囚納紙則例”將刑部與各問刑衙門之前納紙的“一分”具體化,刑部“官紙一分,納榜紙三十八張;告紙一分,納勘合二十張、中夾紙三十張;軍民紙一分,納中夾紙五十五張、[奏]本紙十張、手本紙五張。在外衙門亦合定與則例,該納官紙、吿紙者,每分中夾紙五十張;該納民紙者,每分納行移紙三十張”。8佚名:《皇明弘治條例》,(弘治元年八月)《在外問刑衙門及巡按等官囚犯紙札俱照刑部則例及止據土產不許故索淹禁并非專問刑官不許罰紙》,邱仲麟主編:《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22冊,第199頁。所謂的在外衙門,是指在京師之外包括監察御史、按察分司以及府州縣、衛所等問刑衙門。
景泰時,納紙對象進一步擴大到所有涉案者。景泰五年(1454),大理寺官員王恕說:“照得法司見行事例,除真犯死罪、竊盜并逃軍、逃匠、逃囚不納紙札外,其余一應罪囚,各納紙一分入官……及有一家同居人口被牽告,三兩口在官者有之,五七口者亦有之。發落之時,每人各納紙一分,且民紙一分直銀三、四錢,官吏紙一分直銀一兩。”被牽告家庭同居人口,“每人各納紙一分”,顯然不合理。王恕建議將“一家同居人口有犯,不分人數多少,只令納紙一分”。景泰帝批示“三法司計議停當行”。1王恕:《申明律例奏狀》,王恕著,張建輝等點校整理:《王恕集·王端毅公奏議》卷1,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48—250頁。這一指示較含糊,后續也未見具體說法。按當時情形論,除了原被告要納紙外,“被人牽告”者也都要納紙,這將之前僅對有罪者納紙擴大到所有涉案者皆需納紙。天順年間,在之前按“分”納紙基礎上,又出現按張數納紙的現象,時各處分巡按察官問囚“俱罰紙札,有罰軍民囚犯及原告中夾紙一百二十張,官吏有職役人等榜紙一百二十張者,有罰官吏紙加倍中夾紙二百四十張”。2佚名:《皇明成化八年條例》,《在外罪囚罰紙俱[照在京則]例減等不許多收濫罰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3 冊,第196頁。
罪囚納紙的種類,也隨著在京各衙門使用多寡不同而進行相應調整。成化二年(1466)四月,刑部浙江司“日逐囚人送納紙札,中夾紙數多,奏本紙、手本紙、榜紙數少。今內府各照局匠京府部等衙門,每季除關中夾紙一十九萬七千二百余張足夠放支外,奏本、手本、榜紙計七萬三千九百余張,放支不敷。見在庫中夾紙陳積可夠一年支用,各衙門領紙人員等候日久,亦有告要折支中夾紙張”。刑部為此不得不臨時對領紙人所需紙張變通折支,“依時價估計,榜紙一張該折中夾紙五張、奏本紙二張”,強調“不為常例”。同時對罪囚納紙也按紙折納,“今后囚人,審其有力者,該折中夾紙張,照依時估,兩平折納奏本、手本紙、榜紙收受入庫,候各衙門關支足用”。3佚名:《皇明條法事類纂》卷1,《五刑類·有力囚人折納紙札例》,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4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年,第17—18頁。明代按經濟條件將罪犯分為有力者、稍有力者、無力者等層次。4張光輝:《明代贖刑的運作》,《四川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無力者”可能因無法按時納紙而被長期監禁。成化十年(1474)四月,刑部尚書王概描述衛所貧窘的操官、總小旗等犯罪后,“及至送問,追納紙札,監禁日久,無從辦納,只得送發該衛或兵馬司禁迫有無,候半年、一年之上不得完納,又行原籍官司追理,甚是擾害”,他為此建議對這一部分人仍按景泰五年例免除納紙。5佚名:《皇明成化十年條例》,《處置條例十件》,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3 冊,第670頁。但免納紙又可能影響官府的公務用紙。據刑部河南司統計,成化十一年(1475),內府各監局在京各衙門關支榜紙15萬張,中夾紙55.08萬張,勘合紙6.87萬張,奏本紙11萬張,手本紙16.12萬張,各種紙累計達百萬張以上。而成化十二年(1476)正月刑部山西司收到浙江司囚犯劉升等榜紙4,712張、中夾紙25,855張、勘合紙2,580張,累計不足3.5萬張。以此推算,刑部各司納紙數難以應對支出,“內外衙門關用紙札數多,見收囚人紙札十不及一,委的支用不敷”,于是又規定:“今后將在逃操官、總小旗、將軍、校尉、力士、廚役,仍照舊例著納紙一分以備支用。”6佚名:《皇明條法事類纂》卷5,《名例類·在逃操官總小旗將軍校尉力士廚役照舊納紙例》,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4冊,第192—193頁。
自成化十一年開始,州縣多收回之前由里老在申明亭調處的裁判權,里老由“理判老人”變為偏重勸解的“勸諭老人”。由此加大了州縣聽訟的數量,州縣聽訟對原被告和解或供明無罪都要求繳納訴訟費,稱為“過堂紙贖”。7何朝暉:《明代縣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1—122、130—131頁。此時在地方社會活躍著一批職業告狀人,也使得州縣訴訟案增多,被牽連者也越來越多,是年十一月,刑部尚書董方說:“各處近年以來,有等刁潑之徒,不務本等營運,惟以告狀為生……牽告男婦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者。及至提人到官勘問,有監三五月者,有一二年者。”8佚名:《皇明成化條例》,(成化十一年)《通行在外大小衙門不許勸借出粟賑濟及指以修造為由科罰民財并申明誣告及內外守備官員人等不許濫受軍民詞訟例》,邱仲麟主編:《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17冊,第456頁。從“各處”看,專業告狀者較普遍。而一旦涉訟,“原告及訴人”、證人以及“供明”無罪者,均要納紙。成化十三年(1477)規定:
凡問過囚人,發審有名者,各納紙一分。文武職官正妻、監生、生員、吏典、總小旗、知印、承差、僧道、僧道官、醫生、天文生、應襲舍人、里老,俱官紙;軍校、灶匠、廚役、勇士、力士及各余丁、陰陽人、民人、婦女,俱民紙。原告及訴人該納官紙者仍納官紙,該納民紙者俱納告紙,供明亦照例納紙。1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卷137,《刑部十二·收買紙扎》,第50冊,第3頁。
可見,所有被案件牽連的人都須納紙,不同身份納紙的名目有別,嘉靖十年(1531)傅漢臣輯錄了各種納紙的規定。其中《納告紙人犯》規定“原告及訴狀人,但有狀者俱追告紙;若告、訴人系官仍納官紙,其余俱納勘合、中夾紙”。《納官紙人犯》涉及“文武官、監生、生員、吏典、知印、承差、天文生、僧道、醫士、里長、糧長、老人。總旗、小旗、職官正妻、應襲舍人”。《納民紙人犯》涉及“陰陽生、校尉、力士、勇士、軍民、匠灶、廚子、余丁、婦女”。又有《在京囚犯納紙則例》《在外囚犯納紙則例》《在外折紙則例》規定官紙、民紙、告紙不同紙張繳納時的折納情形,在京有具體“官價”數,在外則無。2傅漢臣:《風紀輯覽》卷4,《發落類·納告紙人犯》,《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第450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394—395頁。
成化十四年(1478),多省發生水災,都察院在回復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億奏疏時稱:“今天下如順天、保定、河間、淮安、鳳陽、徐州、山東、河南、湖廣、江西亦皆被災,宜通行寬免。自后除官吏并害民里老、群長、攬頭、刁頭、旗校納紙如故,其余軍民人等不分有罪無罪,原被告俱暫免納。俟秋成之后,依例施行。”3《明憲宗實錄》卷182,成化十四年九月己卯,第3291頁。也獲允準。從“不分有罪無罪,原被告俱暫免納”看,成化十三年原被告均納紙已得到執行。當然,成化朝也一直在執行之前的免納紙例,“凡強竊盜死罪、逃軍、民匠,囚犯充軍,遇革釋放者,并免紙”,“若監追紙札三個月以上,不能完納者,放免”。4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卷137,《刑部十二·收買紙扎》,第50冊,第3頁。此條在嘉靖《重修問刑條例》仍未改。5見《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2冊,第451頁。
可見,正統以后,聽訟納紙的對象主要是罪囚,但已出現原、被告罰紙的現象。成化時期,隨著官衙公務用紙的增加,且類型有別,一方面通過例調整不同紙札的折納,另一方面中央對地方納紙違規情形又不得不認可,納紙的對象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原被告乃至受牽連者均須納紙在地方聽訟中得以合法化。
三、納紙折色在實踐中的變化
聽訟問囚罰紙的改折,在上述景泰五年王恕奏疏中已有披露,但有無落實,不詳。天順八年(1464)湖廣按察司羅箎因湖廣納紙貯存量大,明確提出納紙折色,本司“并分司等衙門,每軍民納中夾紙一分,官吏、生員、舍人等在官之人俱納二分,每分俱一百二十張……收在庫大小紙張七十余萬,每歲本司用紙不過六萬之上”。6佚名:《皇明條法事類纂》卷5,《名例類·在外囚人紙札有余處準納鈔》,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4冊,第182頁。他請求將納紙改納鈔,以支付地方官吏俸祿:“本司所積罪囚紙札足備十年之用,而各衙門官吏俸鈔不給數月之需,竊恐天下皆然。宜令法司每歲正月至六月令其囚納紙,余月皆納鈔。”朝廷允準了他的請求,“命天下法司,凡囚納有余之處,皆令納鈔”。7《明憲宗實錄》卷7,天順八年七月乙丑,第167頁。所謂“天下”意味著廣泛行用,即上半年納紙,下半年納鈔。羅箎建議將之前審斷后“追收紙札”改為罪人到官即納,“內外法司聽理詞訟,罪人到官,不問輕重,悉令輸納紙張入官公用”。對繳納來的紙、鈔,“俱送所在有司收貯,就于官吏、官軍俸給支銷。年終通將收過數目呈報合干上司知會”。他甚至建議“暫將納紙事例停止。今后遇有問理罪囚,每紙一分改該時使八成銀三錢,就令改納張片(人)[完]全好鈔三十貫。官吏、舍人等加納一倍”。8佚名:《皇明條法事類纂》卷5,《名例類·在外囚人紙札有余處準納鈔》,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4冊,第183頁。盡管說是納鈔,實際又以白銀作為兌換標準,這與此時白銀貨幣化有關。1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2期。
自此之后,問囚納紙折色漸漸普及,且折色后又被逐漸納入地方財政系統。納紙比重越來越少,絕大部分均被折成銀或米。成化十五年(1479),巡撫湖廣左副都御史劉敷出于積糧賑災的用心,請求將納紙的八成改為折米,“各衙門囚犯紙札,量留二分公用,其余準令折米賑濟”,2《明憲宗實錄》卷196,成化十五年閏十月乙卯,第3452頁。獲準。湖廣自成化十二年以來,不時發生自然災害。成化十三年四月,劉敷上奏說:“去歲夏秋亢旱,田禾損傷,人染疫癘,死者甚眾。今春大雨、冰雹,牛死什八九。乞暫免上年拖欠稅糧,以蘇民困。”3《明憲宗實錄》卷165,成化十三年四月甲子,第2994頁。憲宗從之。湖廣問囚納紙八成改為折米,成為地方應對救濟事務的手段之一,而“二分公用”的紙似乎也留在地方。
劉敷所言湖廣情形應屬特殊。事實上,地方問囚納紙后只能留下二成,其余的八成都要押解赴京,以供中央各衙門使用。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戶部尚書陳鉞奏請將山東、河南、山西問刑衙門的紙札“量存二分”,其余差人解送禮部印造歷日書:
今山東、河南、山西、浙江等處布、按二司并分巡及布政司理問所俱系問刑衙門,每一囚犯納紙一分,每按察司連各道分巡官處一年之間所得紙札豈下數百萬張……合無將附近京師山東、河南、山西三按察司并分巡官、理問所問刑衙門,今后問過囚犯紙張以十分為率,量存二分本衙公用,其余罰納入官紙張免納連七等紙,俱收開花綿紙或中夾紙,每一按察司一年管解五十萬張,布政司理問所一年管解一十六萬,共一百九十八萬……俱限本年四月終差人解送禮部,轉送印造歷日。4佚名:《皇明成化條例》,(成化十六年)《各處鈔關收鈔及山東山西北直隸紙札要行解京》,邱仲麟主編:《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19冊,第359—360頁。
山東、河南、山西問刑衙門一年納紙198萬張,八成解禮部印造歷日,僅有二成留在各省作公務用紙。弘治以后,地方問刑衙門的納紙不再解送禮部,而是交付本省布政司,作為各省印造歷日使用。弘治元年八月,山東布政司印造歷日紙張由“各衙門罰過囚數紙札,除十存其一公用外,其余盡數交付布政司印造歷日……其不敷印造之數,支官錢收買”。這里的“十存其一公用”,應該是留在府州縣衙門。這一現象并非山東獨有,“各布政司印造歷日每歲不下數十萬本,多者或至百萬余本,盡將囚人紙札印造亦恐不敷”。5佚名:《皇明弘治條例》,(弘治元年八月)《在外問刑衙門及巡按等官囚犯紙札俱照刑部則例及止據土產不許故索淹禁并非專問刑官不許罰紙》,邱仲麟主編:《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22冊,第193—194、198頁。
正德以后,地方問刑納紙無論是本色還是折色,均不再上繳朝廷,留作地方官府支配。但朝廷對納紙折銀并不鼓勵。正德七年(1512),“令在外問刑衙門,凡問擬囚犯,該納紙札者,二分納紙,八分折米谷上倉,不許折收銀兩”。6申時行等:(萬歷)《大明會典》卷22,《戶部九·預備倉》,《續修四庫全書》第789冊,第385頁。正德十三年(1518),戶部核“兩廣問刑衙門公罰紙,以十分為率,二分存留本衙門公用,八分發該府州縣倉上納谷稻備賑”。7《明武宗實錄》卷164,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第3170頁。即二分紙,八分稻米。嘉靖三年(1524),問囚納紙一度全部折米繳納:
各處撫按官督各該司府州縣官于歲收之時,多方處置預備倉糧,其一應問完罪犯納贖納紙,俱令折收谷米,每季具數開報撫按衙門,以積糧多少為考績殿最,如各官任內三年、六年全無蓄積者,考滿到京,戶部參送法司問罪。8申時行等:(萬歷)《大明會典》卷22,《戶部九·預備倉》,《續修四庫全書》第789冊,第385頁。
納米存儲地方,成為地方用于社會救濟物資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王朝將問囚納紙與預備倉儲米掛鉤,作為地方官政績考成內容之一,似有暗示地方官府保持聽訟規模的意蘊。
地方衙門在辦理納紙過程中不時侵吞本色,嘉靖時出現將本色用于買谷儲存的呼聲。嘉靖七年(1528)刑部尚書胡世寧說:“舊例詞訟罰紙,本色公用,后之論事者謂所司多侵匿也,于是有八分糴谷之說……有盡數糴谷之說。”因為本色多被侵匿,故出現折色買谷的要求。但朝廷卻仍規定收納本色,“今后司府州縣問刑罰紙,仍聽收納本色,貯庫公用。禁其濫罰,似為得體”。1佚名:《復囚紙舊例》,《六部纂修條例》,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第460頁。地方官府鑒于納紙折色能給財政帶來好處,自然不愿回歸收納本色,嘉靖二十年(1541)王朝又規定維持二八比例,“今后問擬一應輕重罪名照舊例,除二分本色紙張外,其余八分并贖罪俱要米谷上倉,不許折收,以便侵欺花費”。2佚名:《嘉靖新例》,《名例例·五刑》,楊一凡、曲英杰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2冊,第371頁。可見,訴訟納紙仍維持在二八比例分別繳納。此處“贖罪”是明代自洪武以來采取的以贖代刑方式,適用于除真犯死罪外的所有罪犯。贖刑主要是以錢物繳納,地方官多以罰代贖,以此補充地方財政,原因是贓、贖須登記上報,而罰則不入冊籍。3何朝暉:《明代縣政研究》,第135、159頁。但納贖僅對罪囚贖刑而言,納紙則包括訴訟雙方及其受牽連者。明代贖刑以罰役、納鈔、納米、納銀等為主。4龍文彬:《明會要》卷67,《刑四·贖罪》,《續修四庫全書》第793冊,第588頁。嘉靖朝的“紙贖”包括了訴訟費。檢索《明實錄》電子庫,“納紙”“罰紙”共有45次,僅有13次在嘉靖以后,而“紙贖”50次全在嘉靖以后。有學者直言,“紙贖”是明代向訴訟雙方及證人收取的訴訟費,又稱紙費。5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通史》第7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544 —545頁。也有人說,“紙贖”不屬贖罪制度,屬訴訟范圍。6劉科進:《明代贖刑制度的司法特點及其局限性》,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第16頁。
實際上,嘉靖以后的“紙贖”,已將贖罪、訴訟費混用,區分兩者的關系則要依具體的語境判斷。嘉靖十五年(1535)至十七年(1537)間,廬州知府項喬說,時人陳紹“初理刑于廬,與予同官……凡任中所自問紙贖銀不下數千,皆入庫簿,不歸私橐”。7項喬:《項喬集》卷8,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下冊,第547頁。這些紙贖銀應是理刑官問刑納紙的折銀。項喬說:“本府先奉巡撫都察院明文,凡奉本院批發,乃本府徑理詞訟,每官紙一分,二分本色紙四十張,八分折稻八斗;告紙每分本色三十張,稻六斗;民紙每分本色二十張,稻四斗。贖罪米石一并折稻上倉。”所謂“贖罪米石”應主要指贖罪費,但似包括前三者的訴訟折稻。他接著說:“本府自問詞狀,除徒罪以上一定申請外,杖罪以下紙米贓銀罰,又欲糴谷備賑,開報循環,于各上司倒換間,或因公留用,亦不敢過十之二三。”8項喬:《項喬集》卷9,下冊,第601—602、606頁。這里的“十之二三”存留公用,與前述問刑納紙一致,即二分留存公用,稍后的淳安知縣海瑞在《興革條例·吏屬》中也說:“近日文移繁,用紙甚多。本縣于自理詞訟內,取兼二分紙價給用,不派里甲。”9海瑞:《海瑞集》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頁。
納紙和紙贖有時區別較為明顯,嘉靖三十一年(1552)七月,西安左衛胡仲金因對倒死官馬處罰分攤不均而到官府訴訟,最終官府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三月判決涉案人戴來、李智“俱民紙折銀各一錢二分五厘,并戴來贖罪米八石,折銀四兩……追完,與紙、贖銀俱發本府常濟庫收貯,接補祿銀支用”。10佚名:《嘉靖中案卷》,不分卷,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漢籍目錄編號B384500,第269—272頁。所謂“民紙折銀”應是訴訟費,與“贖罪米”有別。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徽州祁門縣謝順狀告謝祖昌搶奪莊稼,縣衙判定“謝祖昌、謝順各告紙一分,照例折銀五錢”;又“謝祖昌問擬不應罪名,照例追完紙贖貯庫”。11《為謝順狀告謝祖昌盜票事狀帖》,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1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42—144頁。可見,“各告紙一分”屬訴訟費,謝祖昌“不應罪名”的紙贖屬贖罪費。嘉靖時,四川綦江縣民張表狀告同族張朝宗、張鴻侵占自家分地,張朝宗在張表父親去世后,唆使張鴻誣告,并暗中央求同族璧山縣戶房役吏張恩“替伊稅印”,占奪張表土地。官府審斷后,張恩杖八十并罰官紙銀二錢,張表告紙銀一錢五分,張朝宗、張鴻各民紙銀一錢。12佚名輯:《四川地方司法檔案》,楊一凡、徐立志主編:《歷代判例判牘》第3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90頁。這里的各種紙銀應是訴訟費。隆慶、萬歷之際,江西新建縣民聶寅等先后奉例納充布政司吏役,在征收賦稅時做手腳而被告發。官府問斷后判罰紙銀如下:
照出樊鏡等俱供明免紙,聶寅、熊世英、陳希武各官紙銀二錢,邰化民紙銀一錢;與各贖罪米工價銀,聶寅、熊世英、陳希武各三兩,邰化一兩二錢,俱發南昌府追收貯庫,照例紙價買奏本紙轉解,米工價銀八分類解濟邊,二分存留備賑。1潘季馴:《潘司空奏疏》卷5,《巡撫江西奏疏·勘過原任張布政復職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10頁。
可見,吏役在訴訟中或因供明免紙,或因涉訟納紙,有罪者則紙贖,且均折銀。所謂“濟邊”,應與沿邊的軍事防御有關。萬歷年間,遼陽鳳凰城中所余丁陳得、流丁王保,均與軍人李佐妾高氏有染。李佐被陳得、王保打死,李佐妻劉氏上訴,陳得被斬,高氏杖八十,徒一年半。劉氏納告紙銀二錢,高氏等各納民紙銀一錢。2《整飭寧前兵備山東按察司僉事楊時譽遵巡按周批處理殺人奸淫案書冊》,載遼寧省檔案館、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遼東檔案匯編》,沈陽:遼沈書社,1985年,下冊,第996頁。劉、高兩人所繳納的應是訴訟費。萬歷四十八年(1620),四川成都生員楊柱接管其父佃耕的王田,因欠租被生員楊鐘、楊鐸、楊敬、楊铚、楊嶠、楊岑、楊試和軍伴唐仕登、楊友爵等敲詐。官府判決:“楊柱、楊鐘、楊鐸、楊敬、楊铚、楊岑、楊嶠、楊試官紙銀各二錢,唐仕登、楊友爵民紙銀各一錢,又贖罪銀……俱追貯成都府官庫。”3朱燮元:《督蜀疏草》卷7,《覆生員楊柱等招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65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234頁。可見,訴訟雙方均納訴訟紙銀,而贖罪銀則另計。
四、納紙例在行用中弊竇叢生
明代問刑衙門裁決訴訟后,多由衙役代納紙者從紙鋪行購買上交,于是衙役利用權力與鋪商暗中勾結,不時有意抬高紙價。成化元年(1465)八月,京城有軍民“不務本等生理,好曰‘打光棍’,專在通政使寺并兵部門首接攬告狀人,并送問囚犯前來賣紙人尤昱等家,指以買紙札,用強勒要財物”。尤昱又與“在官一般買紙人高智、孫杰、孫榮、馮四,各亦不合將自己紙貨用強多取價利,每官紙一分,時價銀五錢,勒要銀一兩或七八錢;民紙一分,時價銀二錢,勒要四五錢;原告[紙]一分,時價銀三錢,勒要銀五六錢。囚人被勒不過,只得依數出價買納。除還紙價外,余銀各人分用”。紙鋪商尤昱與衙役勾結,將紙價抬高一倍以上。這一現象引起了刑部的關注,遂下令規定:“今后本部按季行令順天府取撥鋪戶前來,將紙札照依時值,兩平估計,曉示各人遵守。”4佚名:《皇明條法事類纂》卷5,《名例類·按季估計囚人納[官]紙價及禁約打攬囚人納紙例》,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4冊,第184—185頁。但一紙規定根本改變不了社會現實,成化二十一年(1485)七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鄒魯在上奏中說:
犯罪納紙,例有常規。奈何有等不才司府州縣官員貪利壞法,每每通同賣紙鋪行移居衙門路口,一遇有罪人犯到彼,設法誆賺入門,或收其行李,或取其財物,卻乃與之通探消息,說事過錢。又將各官發出舊紙增價賣納。未幾,又行赴官領出在鋪,為官司者略不知愧,遂使賣紙鋪行往往置成財富。
州縣官員和紙鋪行商相勾結,以打探提供案情為借口,從紙鋪商處獲利;有的官吏將手中的舊紙交給紙鋪商加價售賣。而紙鋪商遂抬高紙價,從中獲利,以取悅官吏。刑部為此不得不再次下發禁約令:
通行在外司府州縣大小衙門……取本處鋪戶,照依彼中紙札時價,兩平估計允當,出給告示于各衙門并巡治地方,曉諭各人遵守,嚴加禁約,敢有故違,似前恣縱奸徒轉展增價賣紙,以致蠢政害民,及有等問發之后,仍前恃頑再犯者,許被害之人赴官陳告,或巡撫、巡按等官體訪得出,俱彼一體從重問斷,照例發落。5佚名:《皇明條法事類纂》卷20,《戶部類·內外人入官紙札不許增價賣納》,楊一凡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4冊,第895—897頁。
訴訟者因納紙被勒要高于市場的價格現象,在京城之外同樣存在。成化八年(1472),浙江左布政使劉福奏:“官吏、軍民人等犯罪輕重不同,中間貧富不一,有問罪已完,速日押出罰紙罰鈔,貧窮無錢買納,受責淹滯者;有剝脫衣襖質當,回鄉辦錢加倍取贖者;托人賒買后,將田園典當,加利償還者……況兼紙鈔之數,比之減半舊例,加兩倍有余。”1佚名:《皇明弘治條例》,(弘治元年八月)《在外問刑衙門及巡按等官囚犯紙札俱照刑部則例及止據土產不許故索淹禁并非專問刑官不許罰紙》,邱仲麟主編:《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22冊,第195—196頁。可見,問刑罰紙原本規定照舊例減半,現在反而多出兩倍有余。這與紙價被紙鋪商“增價”售賣不無關聯,其背后又有官吏的權力尋租。
弘治以后,紙鋪行與衙役串通抬高紙價,將正常價格之外的溢出部分據為己有。弘治六年(1493)大理寺左少卿屠勛在“平紙價以便囚犯”中說:
兩法司日逐問理囚犯,不分官吏、軍民人等,除死罪、竊盜、逃軍等項不納外,其余不論罪之輕重,與夫供明,俱納紙一分,以待各衙門支用。先年奏準事例,定有常價,官紙一分該銀三錢五分;告紙一分該銀一錢八分;民紙一分該銀一錢五分。奈何有等射利之徒,通同店家欺凌囚犯,百般強攬,承送吏典,巧立直柜,看驗名色,多方索取,遂至官紙一分使銀八九錢,告紙、民紙一分不下五六錢,官府止得常數。2屠勛:《為應制陳言疏》,載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89,第800—801頁。
官紙、告紙和民紙的價格都比國家規定的標準增加數倍。屠勛請求讓犯人家屬親自購買,或押著犯人親自購買,以防止吏典從中漁利,“官紙一分,時估價銀四錢,告紙[一分,價]銀一錢八分,民紙一分,價銀一錢五分。今后囚犯發大理寺審錄之日,令各家屬將紙照例收買送官,驗無破壞,即與收受;委無家屬者,方許該司差吏押發本囚自去買納……其紙價時有貴賤,亦要據實估計開示”。3佚名:《皇明弘治六年條例》,《在京法司囚犯納紙許家屬自買送納無籍之徒及承送吏典誆要錢物事發問罪枷號職官有犯奏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4 冊,第377—378頁。此條之后被弘治《問刑條例》吸收,“囚犯紙札,照依時估,聽其自行買納。若無籍之徒及管押吏典人等,通同作弊,分外增騙財物者,問罪,枷號一個月發落”。4白昂等:(弘治)《問刑條例》,載楊一凡點校:《皇明制書》第4冊,第1532頁;李東陽等:(正德)《大明會典》卷137,《刑部十二·收買紙扎》,第50冊,第3頁。嘉靖《重修問刑條例》仍保留此條。這足以說明朝廷始終將打擊衙役與紙鋪商哄抬紙價作為重要的目標。
隨著州縣訴訟案件的不斷增多,涉案納紙人數也不斷攀升,由此增加了對紙的需求量,地方衙役借機盤剝納紙人更是有恃無恐。成化十三年八月,京畿道監察御史王億奉差在京五府六部刷卷,發現刑部浙江司刷卷官員長期侵盜囚人上交的紙札,且支銷記錄相當模糊:
刷得浙江等道監察御史送刷成化元年至十一年卷內,每年囚人紙札一宗,俱各全備出入之數,易于查刷。及看刑部浙江等司刷得每司問過囚犯文卷,一年有五七百宗者,有八九百宗者,有一千以上者。每宗囚數又有一百余名,有八九十名者,少有一二十名,或五七名者,合納官民紙札,俱照例追收在官發落。案內明開付紙札卷作數支銷,實與各道事體相合,片紙不行送刷,無憑查考。及至行文吊取,卻稱自來不曾開立付文,粘有文卷。再查各司俱設有令史一名,不管(開)[問]刑,專以收掌紙札,蓋以紙札數多故也……乞敕本部行令各司,今后問追囚人紙札,俱照十三道事例開立卷宗,明白收放,以備照刷,不許仍前虛立文案。5佚名:《皇明成化十三年條例》,《贓罰不堪衣服給散孤老[并]囚人器物變賣[與追完]銀兩煎銷成錠類納紙札明立文卷查考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4冊,第146—148頁。
應納紙數一清二楚,支銷卻是糊涂賬。究其緣由,不排除被經手官吏侵欺入己。所謂“十三道事例”是指天順二年(1458)規定各道“每日一次”登錄收放情況,“各司囚人紙札俱要各立文卷一宗,就令收紙令史承行,凡收過并送庫數目,明立文案在卷,每五日一次,各具印信手本,仍送管庫主事處交收,(守)取印信實收,附卷備照”。即由每日改為五日一次。違法者將受到懲罰,成化十六年廣西按察司僉事陳琳因“多收罪囚紙價”,被下錦衣衛獄,“例贖為民”。6《明憲宗實錄》卷202,成化十六年四月己未,第3543頁。但地方官侵欺紙張并未得到改善,弘治元年八月,濟南府儒學署訓導倪詰說:“在外大小衙門問結囚人,每名罰紙一百張,以一歲計之,其數豈止千萬!而問刑衙門尤為倍蓰……貪墨不職則入從私家,或易換日用飲食,或饋送過往鄉里。”1佚名:《皇明弘治條例》,(弘治元年八月)《在外問刑衙門及巡按等官囚犯紙札俱照刑部則例及止據土產不許故索淹禁并非專問刑官不許罰紙》,邱仲麟主編:《傅斯年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22冊,第192—193頁。
隨著問囚納紙折色的推進,原本規定州縣官追繳紙價銀要類解布政司,再轉發缺糧州縣糴糧賑濟,弘治元年十一月,兵備陜西司副使王玹在奏疏中說:“訪得有等問刑官,將追究完囚人紙價銀兩,以十分為率,有侵欺三二分者,或五六分者,甚至五七年不解,全侵欺者。”他請求都察院“轉行在外問刑官員,將追完囚人紙價銀兩,每年終,盡數類解各布政司……俱發缺糧州縣糴糧賑濟”。2佚名:《六部事例》,《戶律·訪察問刑并掌錢榖官罰紙等項賢否例》,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抄本,無頁碼。可見,囚紙折銀后多被問刑官員侵欺入己。也因為有利可圖,故地方官多將問囚視為利藪,以滿足一己貪欲。弘治時大臣倪岳指出:“先年官司問囚,有罪之人方追紙札以備公用。今則不分有罪無罪,或狀批老人亭,亦照名數追征,且不收本色,俱追價銀。一狀有十名則追紙價十分,有百名則追紙價百分。以一月一歲千人萬人計之,不知通追紙價銀該幾百千兩。”3倪岳:《青溪漫稿》卷14,《奏疏·會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1冊,第187頁。
按照明代法律規定,聽訟只能是府州縣正官及專理刑名的推官,佐貳官不能聽訟,也無權罰紙。但至少在弘治之后,佐貳等官也涉足聽訟,并任意罰紙。弘治七年(1494)都察院《奏準禁約榜文》中規定:
各處知府、知州、知縣兼理刑名推官,專理刑名,例許罰紙。其佐貳首領并合屬衙門官,例不罰紙。今佐貳以下等官,或清軍,或清匠,或催糧勘事等項一應人犯到案,不分有無罪名,俱罰紙一分,各交通紙鋪,日逐發賣,收價入己,不顧名節,不畏法度……合無今后知府、知州、知縣、推官,凡問斷囚人,俱照例減半罰紙。4佚名:《皇明弘治七年條例》,《奏準禁約榜文》,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5冊,第218頁。
可見,佐貳以下官濫罰紙札已較多見。即使正官聽訟納紙,往往也多乘機侵貪入已,賬簿管理混亂已是常態。萬歷時,應天巡撫海瑞在《督撫條約》中規定:“今后凡詞訟,口告者登口告印簿,狀告者登狀告印簿……其有登簿不盡,一狀不存,一案毀滅,紙贖雖多,刻而且貪人也。雖己離任,必行追究。”5海瑞:《海瑞集》上編,第251頁。即不管口告還是狀告,都要登錄印簿,顯然是防止官員亂收包括訴訟費在內的紙贖。他在《考語冊式》中將紙贖列在“操守”首條以察官員賢否。6海瑞:《海瑞集》上編,第259頁。崇禎年間,廣州府頒布《禁收紙贖勒索》規定:“紙贖勒索之弊端,本廳屢示嚴禁……又示諭:完納紙贖到庫,照常平收,不許分毫加重,已經本廳給示。再行曉諭:今后如有差役通同庫吏需索勒加,許即纏稟,重責五十板,問罪革役不恕。”7顏俊彥:《盟水齋存牘》,《公移·禁收紙贖勒索》,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670頁。可見,盡管中央和地方均有禁令,但地方官吏向狀告人勒索紙張依然如故。
五、結 語
明初,中央部院用紙多從刑部的“贓罰鈔”中開支購買。洪武二十七年后,由于部院用紙緊缺,朝廷允準刑部問刑納紙,以滿足京師各衙門公務用紙。自正統年間開始,都察院巡歷地方的官員為解決公務用紙問題,撕開了地方衙門問囚納紙權的口子,并將罰紙對象由罪囚擴大到原被告及證人,國家還以條例的形式承認地方問刑納紙的合法化。自天順開始,湖廣按察司正式推行納紙折色,并在司法行用中逐步推廣到其他區域。一般情況下是本色二成、折色八成,納紙由開始的中央和地方分成,逐漸轉變為地方財政留用。折色多以鈔、銀、米上繳,發展為地方財政的來源之一。嘉靖時,用以贖刑的“紙贖”在行用中與納紙混用,情形較復雜,黃仁宇認為明代官府自16世紀向罪犯、原告、被告征收的紙筆費并沒有完全停止,這項收入被稱為“紙贖”。1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324頁。這一說法顯然將訴訟納紙和紙贖混為一談。其實,納紙至少從洪武末年已開始,紙贖則開始于16世紀。
例在明代法律中屬權宜之法,變通性較強,即便某些條例進入國家“常法”,甚至“大法”,但在行用中仍難被嚴格遵守。2劉正剛、高揚:《明代法律演變的動態性——以“僉妻”例為中心》,《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明代納紙例在司法實踐中,無論本色還是折納,都在執行中逐漸走樣,國家只能修正條例以彌補法律的漏洞。但法律是一把雙刃劍,明太祖時期重視普法教育,規定官吏須通曉律令條文,不曉律意者甚至降級敘用;又要求各級學校將律令列入必讀課。同時鼓勵軍民收藏《大誥》作為減刑的依據。3李琳琦:《朱元璋立法普法行法述論》,《學術界》,1991年第3期。當官民知法后,既可以用法維護自身的權益,又可刻意規避法律漏洞。明代納紙例的演變顯示,中央因應公務用紙的實際需求,允準各級問刑衙門問囚納紙,并在實踐中因應地方財政之需,允準納紙折為銀、米,使納紙與地方財政的結合越來越緊密。
明代納紙例的演變,反映了國家從法律層面一直在不斷調整訴訟費用,意味著國家對訴訟普遍化的現象已相當知曉。國家不斷出臺納紙例,顯然承認了訴訟普遍的現實。而地方官府為了解決地方財政不足以及滿足個人私欲需求,其實并不真正希望減少社會訴訟。如果說,納紙例起初是為解決公務用紙而兼有防止濫訴目的的話,那么后來在地方司法實踐中卻漸漸朝著維持訴訟規模的方向演變,明顯背離了條例出臺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