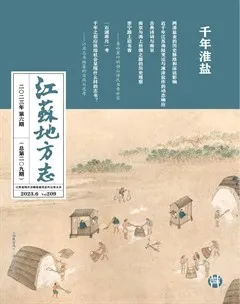南京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觀察
◎賀云翱 干有成
(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江蘇南京 210033)
南京作為江蘇的省會,在國家的區域發展戰略布局中,是長三角輻射帶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重要門戶,也是面向全球的“一帶一路”交匯城市。回看歷史,在中國四大古都(西安、洛陽、南京、北京)中,南京是唯一具有海洋文化因子的城市。南京得天獨厚地擁有世界第三大河和“通江達海”的地理優勢,這為她成為航海城市奠定了堅實的自然基礎,正如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中所說,南京擁有“橫貫大陸直達海濱之干線”的優勢地位。
歷史上,南京借助于長江與海洋走向世界。3世紀初葉的魏、蜀、吳“三國鼎立”時代,南京首次成為長江中下游及中國南方沿海區域的政治中心城市,后歷東晉及南朝的宋、齊、梁、陳四代,共300 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南京真正開辟了中國的海洋時代,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城市。明朝早期,“鄭和七下西洋”更是書寫了南京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城市繁榮的一頁。
一、東吳時海上絲綢之路的開拓
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割據江東的孫權將治所移到秣陵(今南京),在金陵邑舊地筑石頭城要塞,次年改秣陵為建業。吳國在南京建都達51 年,對造船業和航海交通十分重視,又訓練水師,以水軍立國,并派遣航海使者開發疆土,與外通好。據史料載,孫吳武裝船隊出海時可達百余艘,隨行將士萬余人,北上遼東、高句麗(今朝鮮),南下夷洲(今臺灣)和東南亞今越南、柬埔寨等國,至吳國滅亡時,還有戰船、商船等5000 多艘。學者朱健文在《東吳的造船業與泛海遠航》中考證,當時孫吳造船業已經達到當時世界領先水準。
(一)東海航線開辟
今南京作為當時吳國的都城,成為中國海外開拓與交往的始發點與中心地。吳黃龍二年(230),吳大帝孫權因聽說秦代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數千人出海求仙,留居在亶洲和夷洲,“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1]。結果亶洲未尋得,只到了夷洲。學界認為,夷洲就是今天的臺灣,而亶洲一說即今天的沖繩島。
日本各地古墳中出土的吳鏡,可能是這一時期貿易交流的物證。如日本山梨縣鳥居原古墳出土的赤烏元年(238)對置式神獸鏡、兵庫縣安倉古墳出土的赤烏七年(244)對置式神獸鏡等。據學者考證,這些可能是當時亶洲人渡海到吳地進行貿易的結果。同時吳地也有人流移到日本,如當時有大量工匠從會稽郡東冶縣(今福建福州一帶)入海,經臺灣(夷洲)、琉球,抵九州島南部的種子島(一說為亶洲)到達日本。[2]此外,在日本古書《日本書記》和《古事記》中稱東晉、南朝為“吳國”,稱其人民為“吳人”,來自南朝的絲織品、服裝等也都被冠以“吳服”。可見,東吳和日本在經濟上已經是往來較多。
據《三國志·公孫度傳》及裴松之注《三國志》等記載,吳國曾多次派遣船隊前往遼東,和割據該地的公孫氏聯絡。吳嘉禾元年(232),孫吳政權為與遼東公孫氏政權聯合,開辟由長江口直抵遼東半島與朝鮮半島的航路,派出船只多至100 艘,并進行了通商活動;次年又派使者到遼東賞賜公孫淵,并封公孫淵為燕王,不料,公孫淵將東吳到達遼東的士兵殺害關押,并吞并了東吳使者帶去的金銀財寶,其中4 人幸免得脫,到達高句麗,“因宣詔于句驪王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宮(按:當時高句麗國王名“宮”)等大喜,即受詔。”高句麗國王宮派遣使臣護送東吳使臣返回南京,并向吳王孫權贈送貂皮、鹖雞等禮物。自此,東吳與高句麗建立了聯系。次年,孫權派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到達高句麗,封高句麗王為單于,加賜衣物珍寶。[3]在與高句麗建立聯系后,孫權又于吳赤烏二年(239)派遣羊衜、鄭胄為督軍使者與將軍孫怡等率領艦隊前往遼東“擄人”。東吳艦隊到達遼東后,攻旅順口海防城堡牧羊城,與魏守將張持、高慮等發生爭戰。東吳的三次入遼東及與高句麗建立聯系,證明東吳開辟了由今南京經東海至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的航線。
(二)南海航線發展
南海航線促進了都城建業(今南京)與南海諸國的海上交通及經濟文化交流。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海諸國”,是指交州(包括今中國廣東、廣西,越南北部和中部)以南及西南大海諸島上的國家。[4]吳黃武五年(226),交趾太守士燮卒,其子士徽作亂,為吳廣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滅,自此交州之地為吳所據。后呂岱派遣從事前往南海諸國,宣揚吳國聲威,促使扶南(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方)、堂明(在今泰國境內)諸王,各遣使奉貢。吳赤烏六年(243),扶南國王范旃派使者送來一個樂隊,吳王專門在王宮附近建“扶南樂署”,請他們把扶南優美的歌舞傳授給吳國宮女。孫權還派朱應、康泰等前往東南亞地區出訪,他們在扶南國期間,將親自到過及聽聞的國家詳情記錄下來,分別著成《扶南異物志》(朱應著)、《吳時外國傳》(康泰著,亦稱《吳時外國志》,包括《扶南記》《扶南傳》《扶南土俗》諸篇)等著作。東吳丹陽太守(時丹陽郡治在南京)萬震寫成《南州異物志》。這些都是中國最早系統記錄東南亞乃至南亞地區各國歷史風物的重要著作,也成為當今研究海上絲路及海洋文明的重要文獻遺產。其中《扶南異物志》是世界上首部介紹海上絲綢之路重要國家柬埔寨(時稱“扶南”)的著作,也是我國古代記述南海諸國最早的一部專著,可惜內容已大都佚失;《吳時外國傳》在《水經注》《藝文類聚》《通典》《太平御覽》等書中還零星地保留了若干條,成為研究南洋各地古代歷史地理最可貴的史料。[5]有學者認為,孫權委派朱應、康泰出訪南海諸國,其意義不亞于兩漢時期張騫、班超之通西域。在孫吳人韋昭的《吳鼓吹曲·章洪德》中就有對當時東吳和南海諸國來往的描述:“章洪德,邁威神。感殊風,懷遠鄰。平南裔,齊海濱。越裳貢,扶南臣。珍貨充庭,所見日新。”東吳時期,南海諸國與東吳的海上貿易絡繹不絕,各國商船往返兩地,促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交往和友誼。
南海交通發達,佛教遂從海上絲綢之路經由林邑(也稱占城、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傳到交州和廣州。自華北南下佛教和交州、廣州北上的佛教在東吳建業匯合,促使佛教在這里得到發展和傳播。其中南下代表人物為支謙,北上代表人物則是康僧會。赤烏十年(247),天竺僧人康僧會經廣州來到建業,雖晚于支謙數十年,但他對吳地佛教的影響甚大。據《高僧傳》載,“康僧會至建鄴,權初不信佛,試打舍利,具顯神異,遂大嗟服,并為建塔,號建初寺。”孫權為康僧會造建初寺,為江南有寺院之始。
(三)與波斯、天竺、大秦往來
據康泰《吳時外國傳》所記:“從加那調州乘大海船,張七帆,時風一月余,乃入秦,大秦國也。”又據《梁書·海南諸國傳》所載,黃武五年(226),大秦即羅馬的商人秦論從南海來到交趾(位于今越南北部紅河流域),后從交趾到達吳都建業。史載他在東吳居住長達七八年,直到嘉禾三年(234)至六年左右才返回本國。這表明東吳已有航海能力到達大秦。又據萬震《南州異物志》記載,當時在南海上還有波斯、天竺等國的大海船遠來貿易。
二、東晉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一)東海航線的開拓
東晉時期,北方的航海事業,其主要區域仍在渤海的四周及山東半島一帶。東晉建武元年(317),東晉元帝司馬睿初即王位時,控制今渤海遼東灣北部一帶的慕容廆,曾派長史王濟航海到建康(今南京)上表擁戴[6]。此后慕容廆經常經海道通使建康。咸和八年(333),東晉政權為與東北地區的慕容氏政權溝通,派遣王齊、徐孟等率船隊,從建康出長江入海,沿黃、渤海航行到達遼東半島,為拓展和加強中國與東亞國家之間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據《晉書》卷七《成帝紀》《康帝紀》記,咸康二年(336)高句麗“遣使于晉”;建元元年(343)高句麗遣使朝獻。[7]《南史》卷七十九《夷貊傳下》記有高句麗王高璉在晉安帝時奉表進獻,受晉朝的冊封。
東晉時,海上絲綢之路東延促成佛教初傳朝鮮半島。東晉武帝時,建康與朝鮮半島的遣使往返和文化交流在東亞文化交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寧康二年(374,一說寧康元年),印度僧人阿道從東晉到達高句麗,并入丸都城,主持高句麗小獸林王創建的寺廟。又有太元之末(396),東晉僧人釋曇“賚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為戒,蓋高句麗聞道之始也。”[3]晉太元九年(384),胡僧摩羅難陀自東晉至高句麗鄰國百濟。佛教在東亞的這種影響、傳布正是通過以建康為樞紐和出發點的海上絲綢之路來完成的。據《北史·百濟傳》載,百濟國內“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8]。與此同時,百濟學者王仁到日本教授《論語》,這表明百濟不僅廣受漢文化影響,還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橋梁。這一時期,東晉與百濟、與日本的關系都比較密切,據《南史·夷貊傳下》載:“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余映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同時,日本派使者到東晉建康,也往往取道百濟。此外,新羅(在今韓國境內)佛教的初傳,更是完全依靠由建康出發的海上絲綢之路。東晉孝武帝(373—396)曾親自向新羅王贈送焚香。到新羅納抵王(417—458)時,還向僧人阿道請教孝武帝所贈之香的使用方法。這些均顯示出新羅與以建康為中心的江南佛教的源流關聯,深受海上絲綢之路東延通達的影響。
第二,如果所學內容涉及到運算律,而且授課的時間在學運算律之后,例如“小數乘法”本質上是乘法分配律,老師們應充分利用運算律的知識,使學生不僅能夠理解新知識,而且也加深了對運算律的認識.
(二)南海航線的推進
東晉時期,南方航路進一步推進,與南海諸國的交往和貿易更見繁盛,交州以南諸國和天竺、康居(今中亞阿姆河以北、咸海與巴爾喀什湖之間)等國的使節、商人不斷由海上絲綢之路前來建康及南部海港,出現了“四海流通,萬國交會”“舟舶繼路,商使交屬”的活躍景象。當時的進出口商品中,出口的多為絲織品、陶瓷、金銀器、漆器等;進口的有香料、異果、珍珠、琉璃、珊瑚、琥珀、水晶、珠璣、金剛石、郁金、蘇臺、象牙、犀角、吉貝、斑布、兜鍪等。南京出土的東晉墓葬中常見有胡人形象,說明當時有外國人居住在建康城內。南京象山7 號墓出土了一件嵌金剛石的金指環[9],很可能是當時南亞國家的舶來品。南京象山1 號墓中出土的一件鸚鵡螺杯[10],當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珍貴酒器。此外南京地區大型墓葬中還經常發現一些珊瑚、琥珀、綠松石等裝飾品,以及各種來自羅馬、波斯的玻璃器,來自波斯的薩珊銀幣等,反映了建康與各國貿易往來的興盛。

《佛國記》
這一時期,高僧法顯西行求法,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法顯從中國經陸路到達印度后由海上回國,至建康著書立說,寫出我國第一部記述當時中亞、印度和南海諸國山川地貌和風土人情的游記——《佛國記》。
三、南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繼續推進
(一)東海航線繼續擴展
南朝同日本繼續保持著航海交通。當時的航線主要是從日本通向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百濟,橫渡黃海,而入長江口,到達南朝都城建康。宋、齊時,日本多次奉表獻方物,求除授。據《宋書》卷九十七《倭國記》等記,劉宋六十年間,倭國(日本)遣使入貢者,先后有十多次。南朝也分別于南齊高帝建元元年、梁武帝天監元年遣使倭國,對倭國王進行冊封。
南朝梁時,中日通過海路的交流更是日益頻繁,中國的學術、文化、手工業技術等相繼傳入日本。當時日本與南朝交往的主要通道,為經由朝鮮半島上當時的國家百濟,而后沿大陸海岸南下江南地區。這一時期,佛教也傳入日本,梁武帝普通三年(522),來自梁朝的司馬達在日本建造精舍崇佛,這是佛教進入日本的最早記錄。
繼東吳、東晉與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互派使臣后,南朝與高句麗、百濟往來更為密切,且于梁時與新羅互通使節。劉宋時,高句麗貢使往來頻繁。梁、陳時,雙方官方通使頻繁,一再授給高句麗王“征東大將軍”之稱。同時,《昭明文選》《字林》《字統》《玉篇》等典籍也傳入高句麗,促進了高句麗的文化發展。與百濟的往來是在宋武帝即位后,時百濟王余映進號鎮東大將軍,元嘉二年(425),宋文帝派人前往百濟國宣旨慰勞,后百濟國每年遣使奉獻方物,并上表索要《易林》《式占》、腰弩。南齊時,百濟王多次遣使上書,請求除授官職。梁時,百濟遣使來朝通貢,并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11]可見,百濟與南朝往來甚為密切。新羅地處高句麗東南,與梁、陳同樣保持使節往來。新羅派出大量僧人前來梁朝求法,因佛教經籍和教義大量傳入,新羅佛教獲得極大發展。
正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不斷推進,南朝與朝鮮半島的文化交流頻繁而順暢,在朝鮮和韓國的高句麗、百濟、新羅故都出土的文物中,南朝藝術風格十分顯著。1971 年,在朝鮮半島忠清南道公州郡宋山里發掘出的百濟王余隆墓,其形制、結構完全仿造中國南朝都城的墓葬制度,墓內出土的青瓷器等遺物多見中國南朝的制品。可知這一時期的南京成為先進文化的輸出國。南朝都城所擁有的城市規劃、建筑技藝、儒學思想、禮儀制度、書寫文字、佛教藝術等各方面都對朝鮮半島(百濟、新羅、高句麗等國)和日本列島(倭國等)國家產生了重要影響。正如日本學者吉村憐說:“從文化上來說,6 世紀的南朝就如君臨東亞世界的太陽,圍繞著它的北朝、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周圍各國,都不過是大大小小的行星,像接受陽光似的吸取從南朝放射出來的卓越的文化。”
(二)南海航線發展興盛
南朝時在南海方面,對國外的海上交通已取得顯著發展。劉宋建立初,通過海上與南海諸國建立起密切的關系,南亞的天竺(今印度)、獅子國(今斯里蘭卡)頻繁遣使奉獻。到劉宋后期,隨著劉宋與林邑關系的改善,與南海諸國的關系也活躍起來。與扶南、盤盤國、訶羅單、媻皇、媻達等國往來交通一時興盛。尤其是與扶南、林邑兩國往來密切。南朝時,扶南多次遣使建康,貢獻方物。梁武帝在大同五年(539)派沙門釋寶云隨使臣去扶南迎佛法,還聘請不少扶南名僧,在都城建康建立譯經道場——扶南館。扶南高僧伽婆羅、真諦等到建康講經論法,伽婆羅譯經數十部,真諦在梁、陳二代共譯出經、論40 多部。扶南還向梁朝贈送大量的佛教藝術品,深受梁武帝喜愛。[12]
林邑,又稱臨邑,即今天越南中南部地區。該國有金山,其中含有生金,又盛產玳瑁、貝齒、吉貝、沉香木。繼東吳時與通使后,南朝時往來更為密切并互贈禮物。梁、陳時,林邑先后九次遣使貢獻方物。
除扶南、林邑外,南朝與南海其他很多國家有著友好往來。如訶羅陁國、訶羅單國(治阇婆洲,即今爪哇島)、婆皇國、婆達國、阇婆達國、盤盤國于劉宋時期都曾來朝奉表或進獻方物。還有天竺迦毗黎國、蘇摩黎國、干陀利國、婆利國等曾向宋、齊兩朝遣使貢獻。此外,南海諸國中的歌營國(今馬來半島南端)、奴調國(又名姑奴國,據稱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上)、諸薄國(位于今印度尼西亞諸島上)、丹丹(今馬來西亞半島南部的吉蘭舟)、狼牙修(今泰國南部,一說在馬來西亞境內)等國,也均與南朝有著較為密切的文化交流。據《梁書》記載,狼牙修國曾多次遣使到建康訪問并貢獻方物。梁代蕭繹所繪《職貢圖》,真實地記述了當時波斯、倭國、百濟、狼牙修國等使臣來南朝都城建康訪問的情況。南朝陳時,與扶南、林邑、狼牙修、丹丹等國仍有往來。
四、明代早期南京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
南京海上絲綢之路是以國家力量組織,實施與國外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為主要特色。在整個隋唐宋元時期,除南唐這一割據政權外,南京喪失了都城和重要國際港口地位,對外官方貿易開展較少,海絲文化的發展處于低潮期。
(一)明朝是南京海上絲綢之路歷史最輝煌的一頁
明代早期,南京第一次成為全國性統一政權的都城。明初實行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朝貢貿易”,推動了海上絲綢之路的進一步延伸。明初將一些亞洲鄰國如朝鮮、日本、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臘、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齊、浡尼等列為不征國。[13]同時明王朝還主動與海外各國建立關系,如曾先后于洪武元年(1368)、洪武二年派遣使臣前往安南、日本、朝鮮、占城諸國及爪哇、波尼、暹羅等。洪武三年,朱元璋派萊州府同知趙秩去日本,日本也隨即派出使者來到明首都南京,開展兩國正常的雙邊關系,重新建起了兩國中斷了一百多年的政府邦交。兩國一度展開了經貿文化交流,日本向華輸入銅、硫磺、刀、扇、蘇木、劍、漆器等,明則向其輸出銅錢、書籍、金銀、綢緞、布帛、陶瓷等。再有就是朝鮮在幾經政變后,仍一直與明朝保持友好關系。洪武五年,朝鮮派150 多人前往南京太學留學,學習明朝先進的典章制度和科學技術。明朝政府向其贈送《四書》《通鑒》等典籍,以及輸出絹、布、藥材、硝黃、火藥、牛角等物品。
明朝政府沿襲宋、元的市舶司制度,在沿海口岸設立市舶提舉司作為專門主管對外貿易的機構。起初在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三地開設對外口岸,期間因沿海動亂,三處對外口岸被一度關閉,直到永樂初年才被重置,為浙、閩、粵三市舶司。隨后在永樂三年(1405),前來明都城朝貢的國家日漸增多,三市舶司為此還分別設置了專門的館驛接待外國商使,為海上頻繁的往來提供便利。
正是在明朝友好和平外交政策和“朝貢貿易”的影響下,海外使團不斷來到南京朝貢。據《明太祖實錄》卷四十七載:“洪武初,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據專家統計,明洪武年間,明王朝外派使臣57次,各國來南京的使臣達183次;永樂年間,出使61 次,各國來使318次。不僅來使次數之多,而且來使人員之眾,為以往各朝所罕見。如永樂九年滿刺加國王率其妻子、陪臣多達540 人來華。[14]據史載,朱棣還在皇宮奉天門朝賀群臣,當時海外來使千余人群集闕下。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南京成為留都,但是仍然設中央“六部”等機構,一些中外使臣來往的活動還在南京開展,如中日貿易往來尤以南京的船和貨物為甚,為此,日本曾一度將南京當成中國的代名詞,涌現了一批以“南京”命名的貨物名稱,如“南京物”“南京袋”“南京豆”“南京燒”“南京刨”“南京操”“南京鼠”“南京軍雞”“南京鳩”“南京錠”“南京町”等。這表明當時的南京在海外頗具聲譽,也表明明朝通過海路與海外諸多國家有著頻繁友好的往來。
(二)鄭和下西洋將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拓至頂峰
明朝政府為宣揚國威和發展朝貢貿易,多次派遣使臣遠航海外各國,而將這一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推向高潮的則是“鄭和下西洋”這一壯舉。明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航海家鄭和受明成祖朱棣之命,率領船隊從南京出發,歷時28年,七次下西洋,遠航東南亞、印度、波斯灣、非洲等地,代表明朝政府遍訪近40個國家和地區,航程10萬多海里。其航行規模之大、人員之多、技術之先進、航線之長、交流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及之前的歷史跨度內,均無可比擬者。梁啟超稱贊鄭和是與哥倫布、達伽馬“并時而興”的海上巨人,是“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15]鄭和這一壯舉,不僅為中國和世界航海史寫下光輝的一頁,也標志著古代海上絲路已經發展到了頂峰。
鄭和下西洋在前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基礎上,把航路不斷延伸,開辟了東起中國長江下游內河第一大港(南京港),中經東南亞和南亞,然后橫越印度洋直抵非洲東岸的中非航線,結束了此前中國與非洲之間的聯系通過阿拉伯人中轉的歷史。它的遠航,比西方哥倫布和達伽馬的航行還要早半個多世紀。

南京市考古機構發掘寶船廠作塘遺址現場(干有成 提供)
鄭和七下西洋不僅拓展了航線,還建立了之前海上絲綢之路從未有過的多點交叉的遠洋航路網絡。船隊從中國長江及東海之濱,經南海入印度洋,遠伸至西亞、東非的廣大海區,其西北方向的航路直通波斯灣、阿拉伯海和紅海,這一海區的主要海港忽魯謨斯、祖法兒、阿丹是鄭和船隊常往的海上基地;西南方向的航路,沿東非沿岸已經超過赤道,到達南半球海域的麻林(亦作麻林地,今坦桑尼亞的基爾瓦、基西尼瓦)。鄭和在第四次下西洋時,到達莫桑比亞克境內的兩個港口比剌和孫剌。[16]
鄭和船隊每到達一地,還將隨船所帶的中國特產絲綢、瓷器、茶葉、金、銀、銅錢、鐵器、農具等物品在當地交易,各國也用本國的特產與他們交易。各類進口物品有布類、香類、珍寶類、藥品類、動物類、五金類、用品類、顏料類、食品類、木料類等。此外,中國的銅錢也流通到了爪哇,而蘇門答臘在這一時期開始采用中國的度量衡,[17]甚至東南亞一些地區建造廟宇和寶塔使用的磚瓦、琉璃也都是鄭和下西洋時所帶去。馬來西亞學者趙洪澤說:“在發展南海經濟貿易、改善生活方面,鄭和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使南洋各國各地都信任的錢幣、中國的度量衡制度和政府組織等等,都是鄭和下西洋期間從中國帶出來而在南洋流通、通行的。”
鄭和下西洋是從南京定淮門外的寶船廠開船、在龍江關(今南京下關)出水前往南洋、西洋各國,這條線路也正是六朝時以今南京為中心使用了千余年的傳統海上絲綢之路。時南京成為鄭和下西洋的造船基地、始發港和人員物資匯聚地,見證了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最后的輝煌。永樂皇帝為下西洋興建的大型官辦造船基地寶船廠以及為表彰鄭和平安出使西洋而修建的天妃宮、靜海寺等歷史遺存就是這一歷史的有力見證,反映了南京在世界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非凡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高度重視海外留學生的教育。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下詔建國學于南京雞籠山下,并于翌年五月落成,定名為“京師國子監”。國子監為海外留學生專辟學習及居住地,起名為“光哲堂王子書房”,配設有藏書樓、倉庫、菜園、射擊場等。國子監曾接納和安置許多國外前來學習的日本、高麗、琉球、暹羅等國留學生。據《南雍志》記載,明代來南京的外國留學生開始于高麗國所派遣金濤等4 人。洪武二十三年,日本曾派遣官生入南京國子監學習。當時來南京學習的留學生數量最多的國家為琉球。洪武二十五年,琉球中山王還派遣其子日孜每等入南京國子監讀書。明政府對海外留學生都極為關懷和重視,留學生的學習期限一般為六年,學成畢業時要舉行筵宴款待,有時皇帝還親自接見;按季節給他們發放衣物和生活補貼等。這種友好的對外教育方針,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友誼。
鄭和下西洋以后,隨著倭寇之患,明政府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加之受西方近代殖民主義浪潮的沖擊,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衰弱。明代后期,有些西方的傳教士從海路來到中國,除了帶來不同的宗教信仰外,還引入了西方科技,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三到南京,開啟了中歐文明相交往的新起點,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先進科學技術開始進入中國。在南京,利瑪竇結識了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朝野人士,與他們進行各方面的交流,還與南京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使雙方增進了了解,互相取長補短,被認為是當時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縮影之一。利瑪竇在南京及中國的活動,對明晚期的社會思想、學術、科學技術、音樂藝術等多方面皆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回顧南京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自古即秉持和平外交的思想,不斷推動國家之間的友好往來,從而為各國分享文明成就創造了條件,這些同樣成為今天踐行“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思想基礎和優秀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