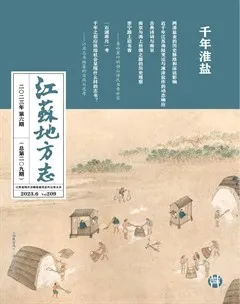溧河洼往事
◎莫 云
(江蘇宿遷 223800)
溧河洼,是一個村名叫“臺”的地方;溧河洼,又是一個見證人間苦辣酸甜的地方。
我的家鄉溧河洼在洪澤湖西岸的泗洪縣城頭鄉(今為臨淮鎮)。洪澤湖是我國第四大淡水湖,其西岸歷史上有三大洼,由北向南依次為:成子洼、安河洼與溧河洼。明代筑洪澤湖東岸大堤后,三大洼也逐漸成了湖區,遂使洪澤湖的面積增大。溧河洼東臨古汴水,即隋唐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通濟渠,1979 年版《辭海》“汴水”條載:“今僅存泗洪縣青陽鎮到臨淮鎮的60 華里一段,上承濉河,南注入洪澤湖。”溧河洼西靠古蘄水,今名溧河,也是上承濉河,下注入洪澤湖。
溧河洼歷史悠久,東有古吳城,西有古徐城。2016年,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同號文教授通過勘察、鑒定,認為泗洪縣石集鄉桂臺村西的溧河河床下面,為約5 萬年前淮河古菱齒象化石出土點。原城頭鄉徐莫村西面,為漢代臨淮郡與徐縣治所,東漢建武十五年(39),劉秀封其子劉衡為臨淮公,臨淮郡改臨淮國。南朝陳時,陳國大將吳明徹在此筑城,置兵防守,并以其姓命名“吳城”。直到明萬歷二十二年(1594)夏,黃河奪淮,地勢低洼的“吳城”被洪水淹沒,僅剩一個城頭浮在水面上。水患過后,人們就把這里稱為“城二頭”“城兒頭”,最后簡稱“城頭”。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占領過雙溝,卻因水淺地偏,沒有到過這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大部隊北撤蘇北、山東,留下的少部分地方武裝堅守洪澤湖上58天,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當時中共洪澤湖工作委員會與陶灘武工隊的臨時駐地,就在溧河洼里,即今臨淮鎮水域中的剪草溝與陶灘。
千百年來,沿老汴河西岸與溧河東岸的村名大都叫“臺”。這是因為,家鄉人世世代代深受洪澇之苦,所以祖先在建村定居時,先要墊起高高的臺子,然后再蓋房子,就不容易被洪水沖倒。于是,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村莊就以“臺”命名了。“臺子”詮釋了溧河洼人的智慧,也道出了溧河洼人的無奈。
溧河洼是水鄉,也是蘇北的魚米之鄉。新中國成立以后,當地政府在沿湖岸邊筑起了綿延百里的防洪大堤,還建了20多個電力排灌站,溧河洼的土地從此旱澇保收。
溧河洼無船難出行,故渡口密集。三里一個小渡口,十里一個大渡口,那一個個擺渡人就是家鄉的活菩薩。雖然昔日的渡口已經被今天的一座座橋梁取代,但在記憶中,其情其景總是歷歷在目,難以忘懷。細數一下,東面的老汴河上有石集、城頭、二河口、臨淮頭幾個大的渡口,還有十幾個小渡口;西面的溧河上,水域最寬處達十余里,最窄處也有三四里,從南往北有新集渡、蔣渡、李渡、三岔河渡與柳山渡幾個較大的渡口。

溧河洼濕地鳥群圖(莫云 提供)
兒時,我家居住在老汴河邊,見過多少船來帆往。船家的規律是,逆風拉纖,順風揚帆。順風時,船工就會把白帆高高揚起,利用風力推動船行,也只有在這個時候,纖夫們才能得到解放,從而躺在船板上那一份清閑之福。在兩個世紀的交接點,隨著科學技術的快步發展,美麗的白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的機器渡輪。白帆,是溧河洼人永遠難以忘卻的鄉愁。
溧河洼的土地與湖區的交接處,就是國家AAAAA級景區洪澤湖濕地公園。有好多回,外地的朋友前來游覽,我還驕傲地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兒時放牛、割草的地方。20 世紀60—70 年代,每到春天,洪澤湖大堤的內外就成了綠油油的大草甸,遠近上百里內的許多生產隊,都派專人將牛領到這里來放牧,那浩浩蕩蕩的牛群,夾雜著黑的、黃的、橙的、黑白的等各種顏色,讓人看得眼花繚亂。那時我在縣中讀初中,正趕上“文化大革命”,學校不上課,我年紀小,就到這地方陪著父親放牛。
剛到放牧場時,我連自己隊里的牛都不認識。生產隊長忽然讓人通知我,帶上兩頭水牛,到十來里外的大草地去盤草,就是在泥水地里讓牛用柝(一種生產工具)拉草。父親把兩頭牛交到我的手中,我騎上牛背就往目的地走去。途中遇上暴雨,我只好到一個護堤人的庵棚里躲雨,牛也跑進另外的牛群中去了。雨過天晴,我到牛群中去找牛,竟認不出哪頭是我們隊里的牛。忽然,一種天性的直覺使我如愿以償。我發現,在那黑壓壓的牛群里,有兩頭牛深情地望著我,于是,我親切地騎上牛背趕路。聽老一輩人說,大牲口通人性,這話果然不差。
溧河洼原有兩座山,一座叫柳山,一座叫毛山,山高約百米,這在地勢低洼的洪澤湖邊,說是鶴立雞群并不為過。初中畢業的第二年,年僅16 歲的我,作為回鄉知青回到溧河洼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當時生產隊的壯年男人是整勞力,每天拿滿工分10 分,婦女算半勞力,每天拿8分工,我因初出茅廬,每天只能拿6 分工。我接受再教育的人生第一站就是做纖夫。這是因為,莫臺小學要實行“草改瓦”,原有的土墻要改成磚墻,而且磚墻下面還要用石頭做地基。施工由沒有船的生產隊負責,我們幾個有船的生產隊負責到柳山去運石頭,就這樣我成了名副其實的纖夫。柳山的石頭質地好,連南京長江大橋的橋墩上,都砌有柳山的石頭。山陵空谷,滄海桑田,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開采,人類的斧鑿竟讓一座山慢慢變成了一片湖泊。
運石頭任務完成以后,我的纖夫生活大多是到洪澤湖中裝運牛草或燒草,夏天運牛草,冬天運燒草。運石頭與運草正好相反,一個沉重,一個輕飄,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讓纖夫流汗,因為拉石頭在水中而沉重,草類因為在風中阻力大而拉起來費勁。這就是一個體力勞動者要面對的生活。
菱藕蓮荷是溧河洼的特色,洪澤湖西岸淺水灘上的荷塘可以稱作萬畝荷塘,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能深知其境其妙。當年做纖夫時,我和幾個小伙伴經常在荷塘中聽漁家妹子唱歌,雖然歌詞在風中難以聽清,但那婉轉空靈的腔調,讓人閉上眼睛仿佛云間徜徉,荷間飄蕩,水中流淌,心曠神怡。
如今,一座溧河洼大橋連接東西兩岸,大大方便了家鄉人的出行。溧河洼的村莊也拆遷了,村民們都搬進了敞亮的社區樓房。記憶中的溧河洼仿佛很遙遠,但銘刻在一代代人心靈中的溧河洼卻很近、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