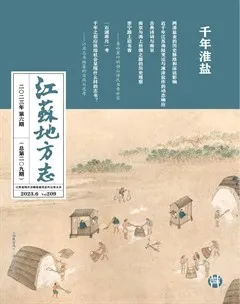鄉愁小記
◎凌 子
(江蘇蘇州 215200)
牽腸掛肚,鄉愁濃濃又淡淡。是時間沉淀成記憶,是鄉土氣息與鄉間土灶上的煙火氣縈繞心頭。腸胃有記憶,童年多野趣,鄉愁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回望與回味。炊煙裊裊,鄉愁系于味蕾。咀嚼蠶豆的快樂,夏日小橋下垂釣的閑適,農忙時節農家“飯菜一鍋熟”的緊湊情景,仿佛就在昨日,下筆已成記錄。
“吳江青”
翡翠青,立夏的蠶豆,活色生香。清炒嫩豆子,撒一把細桿香蔥,青蔥一片;剝開,一瓣瓣,溫潤如玉,加入腌莧菜,煮湯,鮮爽啊。
是“蠶時始熟”而名,還是“豆莢狀如老蠶”故名?脫不了活生生的蠶桑印記。記憶中,蠶寶寶食桑葉日長夜大;我們的童年,在咀嚼著蠶豆的快樂中逐漸長大。
蠶豆枯老了,豆粒呈現陶瓷般光澤,那是陽光把“天青色”投射在豆殼上?色彩學上由此多了一個專有名詞“豆青色”,令人遐想。
老蠶豆爆炒,噴香,咬得牙齒咯嘣作響。老婆婆望豆興嘆,小孩子們則歡天喜地。夏至的陽光特別慷慨,嚼一把端午的“炒現豆”(加入點鹽水則成“鹽津豆”)則格外過癮。
年少時就學于小鎮上,學校不遠處有座“梅蘭橋”。但吸引學生流連的,不是“梅蘭”,更非“站在橋上看風景”,而是那一小包“麻子豆”,用裁成小方塊的舊報紙包得有棱有角,恰似迷你的三角粽。報紙隱隱透著油墨香,而“麻子豆”粒粒精致,釋放出濃郁的甘草味。“麻子豆”亦茴香豆也,炒制者人稱“麻子”,和善而微胖,四五十歲光景,手藝是祖傳的。當在《孔乙己》中讀到“茴字有四種寫法”時,驚詫,經典不遠!小鎮另一處,也是在橋堍,有“老虎豆”,氣派大些,開始稱斤售賣。改革開放了,我們初中畢業了,也就極少光顧“麻子豆”“老虎豆”了。
一度為小鎮茴香豆的“小”而汗顏。看看人家大上海老城隍廟包裝講究的茴香豆,何其高大上——扁闊,栗黃色,且有奶油香味!后來明白了,人家的品種叫“牛踏扁”,而家鄉的蠶豆小而緊致,細膩而玲瓏,特謂“吳江青”。別有風致“吳江青”,是小家碧玉,可能也是“同桌的你”?
中年時進縣城,居住在東太湖畔,曾經陌生而遙遠的吳江“西橫頭”親近了。“西橫頭”就像浙江溫州,重商,敢闖。計劃經濟年代,搖著船,販賣農產品。印象極深的是大頭菜和大白菜。大頭菜腌制,暑天當粥菜,開胃。大白菜被當作“年菜”,買回來還要包裹好,懸掛于屋梁上。香大頭菜肉絲湯,鮮潔無比,今天還向往;大白菜不稀奇了,不過“青菜”一族而已。

吳江香青菜
青菜是菜中百姓,不稀奇,更不貴。此番引起我注意的是西橫頭的“香青菜”(現已打上地理標志,不免“名貴”)。香青菜特征鮮明,葉皺,葉緣鋸齒狀,葉脈細而白,密布葉面,猶如繡花筋。筋織成錦,因而又作“繡花錦”。當年,無所謂,看著偌大棵的香青菜,諧音,想當然呼作“瘦八斤”,可能是由魯迅筆下的“九斤老太”聯想出來。“肥美”為上,“瘦八斤”上不得臺面,不受待見。想不到風水輪流轉,今天是“素美”時代來了,香青菜一下子逆襲成了香餑餑。炒食,糯而香,香而鮮。尤其是經霜后,淀粉轉化為糖分,那個味,難以割舍。是好風水成就了好品種,東太湖西南岸,空氣、水分得天獨厚,而獨特的“小粉土”何處能尋覓!小粉土俗稱“夜潮泥”,有點浪漫吧。
“口音難改,口味亦然。”吳江人口中的費老(費孝通)念念不忘“鄉味”。他曾寫道:“我們家鄉特產一種小茄子和小黃瓜,普通燉來吃或炒來吃,都顯不出它們鮮嫩的特點,放在醬里泡幾天,滋味就脫穎而出,不同凡眾。”費老所言的家鄉特產小黃瓜,最著名的要數平望醬黃瓜,又稱醬乳瓜。黃瓜青色,也有乳黃色的,但作醬菜多用青乳瓜。而今列為“中華老字號”的平望醬黃瓜,有上百年歷史,工序繁多,產品需經“百日”涅槃,味至淳厚,色轉深黛方成。20 世紀50 年代,作為特殊軍需品,運送到前線慰勞志愿軍將士。
吳淞江,吳江的母親河,牽引湖海,繼本來,開未來,本色永葆。如果作一幅江南寫意畫,很可能是“小橋流水烏篷船,粉墻黛瓦青石巷”;如果用一個典故為“吳江青”作注,那一定是“莼鱸之思”,秋色滿東南,風流千古。
釣夏
真閑靜,夏日午間,水面上銀光閃爍,那是風與陽光在切磋。農人們珍惜這難得的一刻午休,小孩子卻不安寧,趁機溜出家門。
村頭水泥橋下,蔭涼。石塊砌就的橋墩坡,硬生生辟出一方獨立天地——坡陡峭,需攀爬,但一到橋底,就有大塊大塊的護坡石,突出水面,可立,可蹲,有的還可坐。小橋不遠處,有竹林,小屁孩們如小麻雀群集,喧囂納林間。

小溪穿石橋
橋下,通常只我一人世界。我的年紀有點尷尬,向上夠不著“半小子”,向下不屑與“小屁孩”為伍,就像魚漂漂浮在水面,既入不得水,又上不得天,只能獨自“釣夏”。
釣蝦最妙。用一根細竹篾,甚至可以用一根細線,系上一粒螺螄肉,放置在石隙口,輕輕晃動幾下,不必操心,很快蝦須探出來了,過不了多久,長長的蝦鉗也伸出來了。水面寧靜,時光如在打盹。只要有小小的耐心,蝦總會全身出洞。這時,輕輕牽引,小抄網悄悄一抄,晶瑩如玉的蝦就到手了。更多的時候,不講究,就用小竹匾甚至是淘米籮“抄”,基本十拿九穩。蝦一被抄起,如夢初醒,急急地跳,眼前便濺起一個個靈動的星星。河水清澈,流經橋墩時隱隱拉出婉轉的水紋,蝦能感知,它們在石隙中潛伏。
小蝦太單薄,也喜歡湊熱鬧,但鉗不住螺螄肉。就像鳑鲏魚鬧鉤,不受抬舉。我要釣的是大蝦,抱籽大蝦,品質好,但不是重點。引得釣興的是大雄蝦,背殼發亮,須長而有力,鉗寬大威武泛出金屬般的藍光,戲稱“老拇鉗”。“老拇鉗”城府深,輕易不上鉤。蝦須出沒,蝦身就是不出洞,可謂神出鬼沒。試探過幾回,終于伸出長長的鋼鉗,夾住螺螄肉,有時一用勁,直接夾劫去了。但狐貍再狡猾也斗不過好獵手。就著婉轉的水紋,來回逗引,引得“老拇鉗”暈暈然,一發狠,全身“沖”出洞,早早伺候的網抄起了。好多回,我與網中的“老拇鉗”對峙,大青蝦那油菜籽般光亮的小眼珠鼓凸還打著轉,仿佛昭示一百個不服氣。釣趣盡在其中。
稍長后,看過齊白石水墨畫《蝦》,有所觸動——蝦們才是真正把畫畫在水中的畫師。不過白石老人的蝦畫得密集了,我記憶中的釣蝦情景清朗而利索,畫面中央就一只大青蝦“老拇鉗”,至多陪襯兩三只白玉柔須的少年蝦。
不知何時起,龍蝦橫空出世。大多棲居水渠、水坑。龍蝦粗糙,一身堅硬的盔甲,頭盔碩大,雙螯如戟。炎炎午日,龍蝦藏在洞中,從那洞豁口,一眼就能看到露出的蝦須。一吞吐,水變濁,原形畢露。最初的一段時間,僅是好玩,用細竹棍捅一下,龍蝦便縮回去,縮得太猛,便彈出來,豎直眼球,憤憤然,一副呆霸王相。待盱眙龍蝦以各種口味閃亮登場,才省悟這玩意兒也不賴,大可大快朵頤。對付龍蝦,鄉間頑童多用“趕網”粗魯捕捉,偶起雅興,也釣。只是這回的釣直奔主題,餌料,更多時候是“空餌”送到龍蝦跟前,這呆霸王一困惑,一發昏,兩只大鉗連竿一并鉗住,真是狠角色!龍蝦煮熟,一襲大紅袍,氣派。
無鉤釣夏,釣田雞。田雞是青蛙屬的昵稱,言下之意,滋味妙如雞。當年的田野“野”,孩童也“野”,抓青蛙談不上破壞。蛙眼偌大,光亮,但對靜止的物體幾乎如盲,視而不見。看到眼前活動的小東西,舌尖如簧,飛速出擊,也不辨青紅皂白,想當然以為是飛蟲一類的美味。因而,只需用一根細長的稗草稈,就可直截了當地“釣”。稗草稈梢,掐留得一小穗,狀蠕蟲。發現田間草叢中的青蛙,悄悄探桿過去。一抖一抖,引得蛙兒躍起,一口咬住稈頭小穗,迅捷提入敞口籮頭中,獵物到手。特大個頭的青蛙,我們稱之為“戇雞”。釣到“戇雞”,別提多帶勁了。
也可如釣蝦一般,用一根細線系上餌料釣田雞。餌料有點殘忍,有時干脆就用一條剝了皮的小蛙腿,“戇雞”就好這口。多半時候,我們就著水渠、田埂草叢,胡亂釣,不愁沒上鉤的。上鉤的往往是灰不溜秋、小不點兒的小田雞,孩子們稱它為“麻姑田雞”。恰似小癩子,與“青蛙王子”根本不能相提并論。小麻雞特別多,饑不擇食,不多時間就能釣上一小兜。喂給雞鴨吃,雞鴨吃了,生的蛋特別大,尤其是鴨蛋,雙黃,腌制后油多,蛋黃呈朱砂色,好不誘人!
田雞無辜,雞鴨也無罪。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鄉野漸遠,童年的“釣夏”沉入夢底。間或一激靈,化作水花,化作白石老人筆下的墨蝦,一只只,躍然。
一鍋熟
炊煙裊裊,鄉間土灶。土灶上安大鐵鍋,俗稱鑊子,結結實實。
南方小年夜臘月二十四,家家蒸團子,用大劈柴,硬柴旺火,灶膛亮堂堂,灶面熱氣騰騰。團子出鍋,點上紅印記,那真叫喜氣洋洋。
煙火氣催生鑊子氣,當年農家,灶臺便是家的中心。難忘飯菜“一鍋熟”。
計劃經濟年代,油米金貴,柴也得節省。或許食材貧乏,或許勞作艱辛,善持家的農家主婦,總在勞作一天后來個“一鍋熟”,省料,快捷,但“鑊子氣”太重,火候不到位的話,就成了“整鍋悶”。記得母親有時把大青菜放在飯鍋里一起蒸,為了省那一把柴火,結果,大青菜像染了病,又蔫又黃,水酷酷,毫無菜味,但也是無奈。雙搶大忙時節,撈一把螺螄,隨鍋一燉,也能讓農家漢子就一口烈酒,吃得津津有味。

蘇州市吳江區七都鎮江村文化園內灶臺圖
“一鍋熟”都用竹制的蒸架,如“井”字,一格可置一碗盆,用來蒸團子、糕點最合適不過。再捏幾個小塌餅,貼在鍋沿上,乘機一鍋熟。
不得不提的是一道農家菜法寶——農家自制“大醬”。大醬多用大豆(蠶豆或黃豆)作原料。對于農家生活而言,釀制大醬(俗稱“合醬”)是件大事。清代蘇州風俗志《清嘉錄》有專門條目介紹:“謂造醬饀曰罨醬黃,饀成之后,擇上下火日合醬,俗忌雷鳴。”籍貫吳江的費孝通先生在回憶“鄉味”時,親切地稱“這醬缸是我家的味源”。潔白鮮嫩的茭白、光滑紫亮的茄子,上鍋一蒸,蘸點大醬,絕對的美味。也可以將食材裹上大醬直接“一鍋熟”,油汪汪,香噴噴,徹底征服你的味蕾。
秋收過后,臨近播種冬麥,這是小孩子們最快樂的時節。牛犁田的時候,孩子們就跟在鏵犁后,撿拾泥中翻出的野獲。有野荸薺、泥鰍,最驚喜莫過于撿到小黃鱔。黃鱔細長,陽光下泛出金屬一般光澤,昵稱“金絲黃鱔”。金絲黃鱔肉質特別緊致,醬燉的話,鮮美無出其右者。
記憶中,家鄉的一鍋熟總能把不同的食材燉出各種各樣的美味,蒸土雞蛋、燉絲瓜湯,道道爽口開胃,就連咸菜豆瓣湯也能燉出獨特的味道來,更不消說那些魚肉葷腥。如今,當年那些食材已不再那么難以取得,卻很難再找到那種對一鍋熟的期待感和鑊子氣熏蒸下的滿足感。
苦中作樂一鍋熟。回望炊煙,忽記得土灶蒸團子有一禁忌:不爭氣,蒸不透;回落水,塌臺面(團子塌餡)。把握火候,才能蒸蒸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