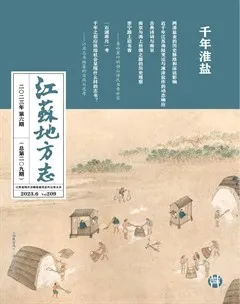兩淮鹽業(yè)的歷史脈絡和深遠影響
◎穆家良
(北京 100080)
我國海鹽生產歷史悠久,其中北起蘇魯交界的繡針河口,南至長江口,這一斜形狹長黃海沿岸、淮河故道入海口南北的兩淮地區(qū)是中國歷史上海鹽生產最發(fā)達地區(qū)之一。淮河以北的為淮北鹽場,淮河以南的為淮南鹽場,所產海鹽稱為淮鹽,以“色白、粒大、干”著稱,銷售范圍遍及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的大部以及河南部分地區(qū)等。從“東楚有海鹽之饒”到“兩淮鹽、天下咸”,千百年來兩淮鹽業(yè)在中國鹽業(yè)發(fā)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對地區(qū)乃至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起步與成長:淮鹽登上歷史舞臺
兩淮地區(qū)海鹽生產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時期。當時位于江淮地區(qū)的吳王闔閭、夫差父子,效法齊國海鹽生產,鼓勵沿海居民煮制海鹽。吳國因煮鹽國富,盛極一時。為運輸北上爭霸的軍隊和供給糧餉,夫差開鑿了邗溝,溝通了長江與淮河兩大流域,使揚州、淮安成為南北交通樞紐,奠定了兩淮鹽運的交通優(yōu)勢。在今連云港市贛榆區(qū),考古工作者發(fā)現了戰(zhàn)國時期修建的鹽倉城遺址,在贛榆青口鹽場發(fā)現了古代煮鹽遺跡,是為發(fā)源于齊魯的煮鹽技術遞次向江淮傳播的實物佐證。
西漢高祖十二年(前195),漢高祖侄子劉濞被封為吳王,建都廣陵(今揚州),擁有東陽、鄣、會稽等“三郡五十三城”。劉濞在封國內因地制宜發(fā)展經濟,“招致天下亡命者……煮海水為鹽”[1]。為打通淮鹽運銷通道,開挖了溝通兩淮鹽場的運鹽河,將所煮海鹽經海陵(今泰州)運至廣陵(今揚州)分銷,時稱吳王邗溝(老通揚運河的前身)。劉濞在此經營四十余年,吳國因“海鹽之饒”而富甲東南。
自此以后,兩淮鹽業(yè)受到歷代統治者所重視。這一時期,隨著鹽業(yè)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兩淮沿海地區(qū)開始出現以鹽為業(yè)的城鎮(zhèn)。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古射陽縣東靠黃海的一部分因遍地是煮鹽亭場和運鹽的鹽河,始設鹽瀆縣(今鹽城)。贛榆是江蘇沿海最早建立的縣之一,在贛榆鹽場到灌東鹽場一帶發(fā)現大量“四銖半兩”銅錢,是漢初吳楚銅鹽之利的實物佐證。連云港海州地區(qū)還發(fā)現了秦漢時期的“瑯琊鹽佐”官印,是最早的淮鹽官印。
漢代的制鹽技術已有改進,出現了鹽田生產法,在濱海地帶營造鹽田,利用鹽田制鹵,放在鐵鍋里煎煮[2]。漢武帝時,“募民煮鹽,官與牢盆”。魏晉南北朝時期,兩淮地區(qū)鹽業(yè)生產活躍,從鹽城到泰州的沿海地區(qū),鹽亭密集分布。阮升之《南兗州記》載曰:“上有南兗州鹽亭一百二十三所。縣人以魚鹽為業(yè),略不耕種,擅利巨海,用致饒沃。公私商運,充實四遠,舳艫往來,恒以千計。”[3]鹽城已成為淮南鹽業(yè)生產的中心,此時淮北鹽業(yè)發(fā)展規(guī)模遠不如淮南[4]。
二、發(fā)展與壯大:“吳鹽如花皎白雪”
隋煬帝楊廣在位期間,修治了南北大運河,兩淮地區(qū)的淮安、揚州成為水運樞紐所在地,淮鹽可轉運直達都城洛陽。唐代海鹽生產技術進步,產量開始超過池鹽,以江南道的“兩浙鹽”以及河南道的“兩淮鹽”最負盛名。為疏通淮北鹽運,唐武則天垂拱四年(688),從泗州漣水縣向北開鑿了一條通達海州的漕河,這就是北起海州、南達漣水入淮,后又西通淮陰的淮北鹽河的前身。
隋代至唐中期以前,不實行食鹽專賣,也不推行鹽稅。安史之亂以后,政府財政困難,先后擔任鹽鐵使的第五琦、劉晏,取法漢武帝食鹽專營制度,恢復國家對鹽業(yè)的統管,行“榷鹽法”。隨著政府對食鹽產銷運營的全面控制,形成了嚴格的食鹽管理體制,鹽利成為國家稅收的大宗。唐代宗時,劉晏在漣水設海口場,開始建立專場產鹽。唐代還創(chuàng)設亭戶和鹽商專業(yè)戶籍,亭戶由鹽亭管理,不承擔雜泛差役,專職產鹽,交場監(jiān)統購;商人專職銷鹽,繳納包括課稅在內的鹽價后,從場監(jiān)領取食鹽,自由運銷。全國設置十監(jiān)四場、十三巡院,其中兩淮地區(qū)有揚州海陵監(jiān)、楚州鹽城監(jiān)、泗州漣水場,場監(jiān)主管收鹽售商,巡院主管查緝私鹽。
唐永泰元年(765),山西池鹽由于鹽區(qū)頻遭暴雨,顆粒無收,長安市場鹽價飛漲,人心惶惶,朝廷降旨急調三萬斛淮鹽運至關中接濟。大歷年間(766—779),淮南節(jié)度判官李承筑捍海堰抵擋海潮,北起鹽城,南抵海陵,堤防屏障為鹽灶安全提供了保障。唐代制鹽技術有了較大發(fā)展,出現了淋鹵煎鹽法,東南沿海地區(qū)產鹽數量多,“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余石”[5],僅海陵縣鹽監(jiān)就“歲煮鹽六十萬石”[6]。而且質量好,所產的“吳鹽”享有盛譽,李白詩中有“吳鹽如花皎白雪”的描寫。揚州因淮鹽集散而成為超越益州(今成都)、富甲全國的大城市。當時的食鹽運輸采取船隊集群模式,編立字號,成批運送,名曰“綱運”。唐文宗時(826—840),西渡來華的日本國遣唐使團所撰寫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輯錄了沿途所見運輸淮鹽船隊的盛大場面,“雙結續(xù)編,不絕數十里”。五代時升海陵縣為泰州,以轄其監(jiān),淮東鹽業(yè)均歸管轄。南通南部“上多流人,煮鹽為業(yè)”。20 世紀70 年代出土《姚徐夫人墓志》有“司煮海積鹽,鹺峙山岳”“東海都場官”“永興場運鹽河”字樣,說明南通鹽業(yè)初具規(guī)模。當時還劃分了海鹽與池鹽行銷的地界,規(guī)定汴、滑、唐、蔡四州以東皆食海鹽。
宋元時期,兩淮鹽業(yè)進一步發(fā)展壯大。范公堤的興修有力地抵御了海潮侵襲,保障了鹽業(yè)生產的環(huán)境。宋代產鹽機構有三:大者為監(jiān),中者為場,小者為務。監(jiān)轄場,場轄務。北宋兩淮地區(qū)設泰州海陵監(jiān)、楚州鹽城監(jiān)、通州利豐監(jiān),領轄25 場。其中通州豐利監(jiān),轄鹽場7座;泰州海陵監(jiān),轄鹽場8座;楚州鹽城監(jiān),轄鹽場7座;海州設2 場,漣水設海口1 場。此時南通南部地區(qū)漲并大陸,生成北海灣,沿灣亭場密布。北方抗遼御夏,始行折中法,繼行鹽引法,以鹽利接濟邊餉。“引”既是納課支鹽憑據,又是運銷鹽斤執(zhí)照,鹽丁產鹽年有定額。亭戶產正鹽,交官收;鍋戶產浮鹽,售商販。淮鹽以淮南、江南、荊湖、兩浙、京東5 路49個府、州、軍為銷區(qū)。
宋代鹽業(yè)生產技術的進步集中表現在海鹽生產方面,當時取鹵、制鹵技術取得很大進步,東南沿海已出現海水曬鹽的嘗試。天圣年間(1023—1032)海鹽產量還比較少,“通、楚州場各七,泰州場八,海州場二,漣水軍場一,歲鬻視舊減六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余石”[7]。到北宋元豐(1078—1085)時年產銷156.2 萬石(每石50 斤),南宋紹興時(1131—1162)年產銷268.4 萬石。紹興末年,海陵監(jiān)年售鹽30 萬席。
元代,隨著新灘的不斷淤現,淮北鹽區(qū)先后擴建了板浦場,興建了臨洪場(今青口場),廢除了洛要、惠澤兩場,變成草灘,供板浦場煎鹽柴草。全國有鹽場125個,其中淮南有鹽場25 個,淮北有鹽場4 個,兩淮鹽場的產量仍居全國首位[4]。元代鹽業(yè)生產規(guī)模擴大,技術也有進步,政府對食鹽生產運銷的管理極為重視,建立了管理機構,制定了嚴格規(guī)定。當時兩淮地區(qū)設都轉運鹽使司,在真州(今儀征)置批驗鹽引所。元代沿用宋代引鹽法并加以完善,戶部印引,運司召商賣引,商人納錢買引,攜引赴鹽場支鹽,運往指定銷區(qū)售賣。元代罷唐宋以來鹽監(jiān),每場置司令、司丞、管勾,場下設團,灶戶分隸各團,每戶領盤鐵一角,平時分散曬灰淋鹵,至期載鹵攜盤鐵入團,拼合鐵盤,輪流煮鹽,是為“團煮制”。大德年間(1297—1307),于揚州、淮安地區(qū)分建6 倉,煮鹽于場,運積在倉,以備支發(fā)。淮鹽產銷年額65萬零75 引(每引400 斤),后追加余鹽30 萬引。元末至正年間紅巾軍大起義,淮南白駒場灶戶張士誠召集鹽民萬余人,先后攻取泰州、高郵、興化,后在蘇州建立政權,稱吳王。鹽民起義及后續(xù)戰(zhàn)亂,使江淮人口急劇減少,對鹽業(yè)生產造成巨大影響。

古代攤灰淋鹵圖(源自《江蘇省志·鹽業(yè)志》)
三、繁盛與衰落:兩淮歲課當天下之半
明代是淮鹽發(fā)展的繁盛期,其間因海岸線變化迅速,淮南鹽場的發(fā)展受到一定影響。元末明初的戰(zhàn)爭使兩淮地區(qū)的人口急劇減少,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將南方人口移民到鹽城、淮安、南通、泰州、海州等沿海地區(qū),從事產鹽勞役。移民為沿海鹽業(yè)開發(fā)帶來了大量勞動力,南宋時開挖的縱貫諸鹽場的串場河,被大量用于鹽運。朱元璋創(chuàng)行“開中法”,將食鹽運銷與鞏固邊防聯系起來,以鹽固邊、以鹽富商、以銷促產,一舉多得。弘治五年(1492),改開中法為折色納銀法,召商納銀,以賣鹽引。萬歷四十五年(1617),為疏銷積引,廢開中法,立“綱法”,凡綱冊有名者,始準運鹽,政府向鹽商課稅,是為專商之始。
明代制鹽仍以煎熬為主,不過試鹵技術有很大的進步。兩淮鹽業(yè)生產方式有所區(qū)別,淮南鹽場以“團煎”為主,盤鐵為主要器具,淮北鹽場開始采用曬鹽法,故《明史·食貨志》中有“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曬”的記載。不過就質量而言,淮南的煎鹽質量不如淮北的曬鹽,因此到明末時,淮南鹽的地位逐漸為淮北鹽所取代。明代鹽課收入僅次于田賦,戶部尚書李汝華疏曰:“國家財賦,所稱鹽法居半者,蓋歲計所入止四百萬;半屬民賦,其半則取給于鹽策。兩淮歲解六十八萬有奇。”[8]
明朝在兩淮、兩浙、長蘆、河東、山東、福建六個鹽區(qū)設立都轉運鹽使司,建成了完整的治理體系,加強了對各大產鹽區(qū)鹽政事務的統一控制。其中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設在揚州,下設分司,作為運司的派出機構,實施就近管理,地位有如唐宋的“監(jiān)”,負責督促各場大使收鹽或征銀。據記載,兩淮地區(qū)設有通州、泰州、淮安三個鹽運分司,通州分司駐石港場,泰州分司駐東臺場,淮安分司駐安東縣城(今漣水縣),從南向北依次稱上十場、中十場、下十場。通州分司有呂四、余東、余中、余西、金沙、西亭、石港、馬塘、掘港和豐利等十場;泰州分司有栟茶、角斜、富安、安豐、梁垛、東臺、何垛、丁溪、小海和草堰等十場;淮安分司有白駒、劉莊、伍祐、新興、廟灣、莞瀆、板浦、臨洪、徐瀆和興莊等十場。明代在兩淮鹽區(qū)還設巡鹽御史一職,大概始行于永樂十四年(1418),到英宗時成為定制,負責監(jiān)察鹽政事務。兩淮巡鹽御史統轄淮南、淮北兩個鹽引批驗所,駐地分別在揚州儀真和淮安安東,轄有30 個鹽場17個巡檢司。
清代海鹽生產技術較明代有很大發(fā)展,曬鹽法被推廣到更廣泛的區(qū)域,曬鹽技術也有很大的提高。不過淮南鹽場因“海勢東遷,鹵氣漸淡”,鹽場數量明顯減少,清初轄鹽場30 處,乾隆以后裁減為23處,其中通屬9場,泰屬11 場,海屬3場。
淮北鹽場在清代有進一步發(fā)展,而淮南鹽場每況愈下。雍正中期將兩淮鹽運使司淮安鹽運分司移駐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驗鹽引所也在山陽境內河北鎮(zhèn),乾隆年間移駐板浦場,改稱海州分司。乾隆時“兩淮歲課當天下之半,損益盈虛,動關國計”。道光十二年(1832)兩江總督陶澍議準將兩淮鹽務改歸兩江總督兼管,以統一事權。陶澍推行鹽政改革,廢除總商,改行票法,打破自明中葉以來鹽務管理和鹽課征收上實行的國家特許專商經營和引岸制度的“綱法”體制,兩淮鹽場由“商疲、丁困、引積、課懸”的危困局面,轉變?yōu)椤胞}銷、課裕、商利、民便”的興盛形勢。
清末民國時期,隨著灘涂東擴,鹽區(qū)不斷向海邊擴展,淮南鹽場數量由20 場減少為11 場,再加上張謇實施“廢灶興墾”,加速了淮南地區(qū)鹽業(yè)的衰落,使淮北鹽場的產量超過淮南鹽場。1931 年,國民政府開始實行新鹽法,以徽商等為代表的鹽商紛紛轉向上海、北京等地,數萬鹽工生活漸失依靠,紛紛外流四方謀求出路,隨鹽發(fā)展繁榮起來的商業(yè)和其他行業(yè)隨之衰落下來。日本侵華后,淮北鹽場遭受空前劫難,淮北鹽區(qū)年產量由抗戰(zhàn)前的60 萬噸,下降至15 萬噸。

清末淮南鹽運銷:支鹽筑裝(源自《蘇鹽印記》)
四、涅槃與新生:致力打造“淮鹽”為中國健康食鹽第一品牌
新中國成立以后,淮鹽作為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yè)而得到迅速發(fā)展。1950 年4 月,淮北鹽場生產管理分開,成立淮北制鹽公司負責鹽業(yè)生產,淮北鹽務局負責行政稅收和制鹽場管理工作。1950 年10 月,淮南鹽務管理局在如東縣栟茶鎮(zhèn)成立,管轄呂四、余中、北坎、苴鎮(zhèn)、豐利、栟茶、角斜、黑苴、三倉、川東、草廟、五港等14 個鹽場。1953年元旦恢復江蘇省建置后,淮北鹽務管理局及其鹽區(qū)并入新海連市管轄,淮南鹽務管理局撤銷,鹽區(qū)廢灶興墾。1958年12 月,淮北鹽務管理局所屬鹽場下放地方管理,按各場實屬區(qū)域重新劃分,埒子河以北的徐圩、臺南、臺北三場劃歸新海連市管轄,坪子河以南、灌河以北的灌西場劃歸灌云縣管轄,灌河以南的灌東、淮河、新灘三個鹽場,劃歸濱海縣管轄。這一時期從“一五”規(guī)劃起,鹽場開始向著“三化四集中”(即鹽田結構合理化、工藝科學化、生產機械化和納潮、制鹵、結晶、集坨四集中)的方向不斷進行技術改造,鹽業(yè)生產得到較大發(fā)展,鹽場落后面貌很快得到改變。1956年底,集中納潮、儲水工程已基本完成。從1958年開始,先后多次組織鹽田改造高潮,勞動模范楊再柏創(chuàng)造了“常年修灘,四季保養(yǎng)”的改灘經驗,得到國家的肯定和重視,后在全國推廣。[9]
1963 年12 月,江蘇省人民政府調整鹽業(yè)生產管理體制,成立江蘇省輕化工業(yè)廳鹽務局,性質確定為企業(yè)。1964 年7 月,江蘇省輕化工業(yè)廳鹽務局所屬的青口、臺北、臺南、徐圩、灌東、灌西、淮河、新灘8 個鹽場劃歸輕工業(yè)部直屬領導,以省輕化工業(yè)廳鹽務局為基礎,成立輕工業(yè)部淮北鹽務管理局。1965 年5 月,經國家經委批準,實行產銷合一的“托拉斯”模式的鹽務管理機構,成立中國鹽業(yè)公司江蘇省公司和第一輕工業(yè)部淮北鹽務管理局,為兩塊牌子、一套班子。除管理直屬的8 個國營鹽場及直屬單位外,還新設南京、蘇州、淮陰、鹽城、揚州、南通、徐州7 個二級批發(fā)站,各縣設立批發(fā)部。1965 年10 月,南通、如東、海門、啟東、射陽諸縣的地方國營場全部劃歸江蘇省公司統一領導。1970 年5 月,輕工業(yè)部淮北鹽務管理局下放到省,重歸江蘇省輕工業(yè)局領導。1971 年3 月,淮北鹽務管理局及其所屬單位劃歸江蘇省生產建設兵團領導,并易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qū)江蘇生產建設兵團淮北鹽務管理局,下設9 個鹽場和15 個直屬單位。這一時期,全省曾兩次掀起大辦縣鄉(xiāng)鹽場的高潮。1958—1962 年,政府投資和企業(yè)自籌資金4822 萬元,在沿海10 個縣新建鹽田7008 公頃,建成10 萬噸規(guī)模的射陽鹽場,后來成為江蘇八大省屬國營鹽場之一。1977 年,全省沿海各縣、鄉(xiāng)人民政府采取“國家投資,自己貸款,省鹽務局補助”的辦法,共投資2771萬元,在啟東、海門、南通、如東、大豐、東臺、濱海、射陽、響水、灌云、贛榆等11 個縣市及農墾系統部分農場新建鹽田1400 多份,使縣、鄉(xiāng)鹽場的鹽田達15000公頃,占全省灘地面積四分之一。[9]

20 世紀80 年代江蘇鹽場鹽田(源自《蘇鹽印記》)
改革開放以后,江蘇鹽業(yè)發(fā)展進入快車道。1983年4 月,江蘇省人民政府決定,改革全省鹽業(yè)管理體制,以淮北鹽務局為基礎,成立產、銷統管的江蘇鹽業(yè)公司,與省淮北鹽務管理局兩塊牌子,一套班子。1985年12 月,淮北鹽務管理局易名為江蘇省鹽務管理局,江蘇省鹽務管理局與江蘇省鹽業(yè)公司為兩塊牌子,一套班子,負責全省鹽政管理和省屬國營鹽場、批發(fā)銷售企業(yè)的生產經營。在全省11 個省轄市,設立7個批發(fā)銷售分公司、56 個支公司,負責各地方鹽的批發(fā)經營工作,在全國創(chuàng)造了獨具特色的鹽務管理體制。[9]20 世紀80 年代,在全省推行食用鹽精細化、多品種化和小包裝化,在全國率先結束了人民群眾食用原鹽的歷史。截至目前,江蘇省鹽業(yè)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已發(fā)展成為全國最大的鹽業(yè)企業(yè)集團之一,員工近7000 人,在省內各市縣及全國重點區(qū)域均設有銷售機構,“淮鹽”品牌實現創(chuàng)新突破,榮獲中國消費者最喜愛民族品牌、中國安全食品十大消費者滿意品牌等多項殊榮。
五、地位與影響:因鹽聚商興業(yè)傳文

淮北鹽集散地——河下古鎮(zhèn)(施德懷 攝)
淮鹽生產運銷歷史源遠流長,文化底蘊深厚。在兩千余年的發(fā)展歷程中,兩淮鹽業(yè)對國家的財政支持、區(qū)域城鎮(zhèn)空間的塑造以及精神文化的涵養(yǎng)等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兩淮鹽利居天下之半
中國古代的鹽稅僅次于田賦,素有“天下之賦,鹽利之半”的說法,而兩淮鹽的稅利在其中又占極其重要的位置。《史記·吳王劉濞列傳》載:“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唐乾元、寶應年間,第五琦、劉晏推動鹽制改革,在淮南設置鹽業(yè)生產和收購的專門管理機構,當時全國稅利1200 萬緡,鹽稅占了二分之一以上,其中兩淮地區(qū)鹽稅利占全國鹽稅利的12%,順宗時兩淮鹽稅利占全國鹽稅利比例升至32%。宋代,兩淮鹽課在財政收入中的比例顯著提升,北宋末年兩淮鹽利的最高額為1500 萬貫至2405 萬貫,而當時全國鹽利最高額為3113 萬貫,兩淮鹽利就占全利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明清是兩淮鹽業(yè)的鼎盛時期。淮鹽因質量好、銷區(qū)廣、產銷量大,向國家繳納食鹽課稅占比繼續(xù)獨重。萬歷中,兩淮歲行大引鹽70 萬5180 引(每引400 斤),年征余鹽銀60 萬兩,引價銀35 萬2590 兩,〔嘉靖〕《兩淮鹽法志》評價道“兩淮鹽賦實居天下諸司之半”。清代,兩淮鹽課分為商課、灶課。商課征于鹽商,按承銷鹽引數量計征;灶課征于灶戶,按所占草蕩面積計征。〔嘉慶〕《兩淮鹽法志》稱:“鹽課居賦稅之半,兩淮鹽課又居天下之半。”淮鹽生產和運銷的發(fā)達也催生了一批“富可敵國”的大鹽商,明萬歷時兩淮鹽商總資本銀達3000 萬兩,清乾隆嘉慶間達7800 萬兩,與同期國庫存銀相當。
(二)淮鹽產銷帶動城鎮(zhèn)興盛
兩淮鹽業(yè)的生產和運銷伴隨著江蘇沿海灘涂地區(qū)的開發(fā)和交通水運的成熟完善,促成了以鹽為業(yè)的城鎮(zhèn)和以鹽為商的都市繁榮發(fā)展,形成獨具特色的淮鹽城市群和文化圈。從春秋戰(zhàn)國時鹽阜平原沿海灘涂散落的“煮海為鹽”的亭灶蘆舍,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鹽瀆縣”的設立,到唐宋時期兩淮地區(qū)“監(jiān)、場、灶”三級城鎮(zhèn)格局的基本形成,再到明清時期揚州、淮安等淮鹽集散中心“繁華以鹽盛”,兩淮鹽業(yè)的發(fā)展塑造了區(qū)域城鎮(zhèn)空間。
如明初淮安鹽運分司設在安東(今漣水縣),淮北引鹽批驗所設在山陽縣(今淮安市淮安區(qū))淮安壩,正德中淮北引鹽批驗所移駐河下鎮(zhèn),地當淮河、運河、支家河交匯處。明中葉黃河奪淮,安東受洪水威脅,致河岸多次崩塌,于是鹽運分司移設山陽。淮北的產鹽地在海州等地,掣鹽場在山陽,河下遂成為淮北鹽引必經之地,于是淮北運商卜居河下,“淮北商人環(huán)居萃處,天下鹽利淮為大”,河下日漸繁盛,酒館歌樓、鱗次櫛比,有“小揚州”之號。道光年間淮鹽改綱為票,淮鹽掣驗所移駐西壩,鹽商各業(yè)隨遷。日月成市,繁華依舊,18 家鹽棧、72 家鹽局、32 家錢莊,儼然淮海名區(qū)。直到民國前期淮北食鹽改走海道與鐵路,西壩因鹽運發(fā)達100 年。
因鹽而興的兩淮鹽場一些村落和集鎮(zhèn)的興起大都與煮鹽、貯鹽、運鹽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業(yè)興而百業(yè)旺。眾多以鹽、亭、場、團、灶、鍋、垛、倉、總、甲等帶咸味的地名,它們是承載淮鹽歷史的活化石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古老鹽業(yè)遺存下的歷史印記。時至今日,一些與鹽業(yè)生產有關的機構早已消失,但還有部分鹽業(yè)生產的機構及所屬場、團、灶等名稱轉化為歷史地名保存并延續(xù)下來,并成為鹽城、南通等鄉(xiāng)鎮(zhèn)建置和行政村及自然村的名稱。

鹽城、南通地區(qū)淮鹽遺留地名表
(三)淮鹽文化蔚為大觀
淮揚地區(qū)是魚米之鄉(xiāng)、交通要沖,官商匯聚,兩淮鹽商家資雄厚、禮賢好客、飲食考究。鹽官童濂“治庖甲于邗上”,鹽商吳楷首創(chuàng)蛼螯糊涂餅,鹽商童岳薦用心記錄淮揚菜品,著成《調鼎集》。流風所及,逐漸形成帶有兩淮鹽商飲食文化烙印的淮揚菜系。
兩淮鹽商園林數量多、構造精。錢泳《履園叢話》載“雖數間小筑,必使門窗軒豁,曲折得宜。”揚州園林集中在城北至平山堂,乾嘉間有24 景觀,李斗《揚州畫舫錄》紀其勝;淮安園林集中在河下鎮(zhèn),有33景觀,李元庚《河下園林記》錄其跡。時人有“車馬少于船,園林多似宅”之嘆。淮揚園林著名的有瘦西湖、個園、汪氏小苑、何園、清晏園等。
兩淮鹽業(yè)給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的源泉。鹽民詩人吳嘉紀,貧而好詩,著《陋軒詩》400 首,其名篇《絕句》感動乾隆帝,發(fā)帑恤灶。《紅樓夢》《水滸傳》《西游記》等都與淮鹽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曹雪芹生在鹽官家,其祖父曹寅和舅爺李煦,從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五年(1704—1716),輪流任職兩淮巡鹽御史,掌管兩淮鹽業(yè)的生產和運銷,權重利厚,家道昌盛。施耐庵與鹽民起義首領張士誠在海陵白駒鹽場,就學于同一位老師,后施耐庵為張士誠軍師。張士誠失敗后,施耐庵隱居于白駒鹽場,著述《水滸傳》。吳承恩,自小在淮鹽鹽區(qū)成長,鹽民的生活給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西游記》第一回所寫“只見海邊有人捕魚,打雁,挖蛤,淘鹽”就是淮北鹽民的生產生活場景再現。
明清時期淮鹽產區(qū)揚州、泰州誕生了兩大學派,豐富壯大了淮鹽文化,影響深遠。泰州學派創(chuàng)始于明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它發(fā)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學派創(chuàng)始人王艮,泰州安豐場(今江蘇東臺安豐)人,出身灶戶,做過鹽工,深知草根的需求。他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把哲學從殿堂移植民間。揚州學派形成于清代乾嘉時期,注重經世致用,為晚清經世派之先驅,其研究將乾嘉漢學推向巔峰,并在歷史轉折時期開啟了近代學術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