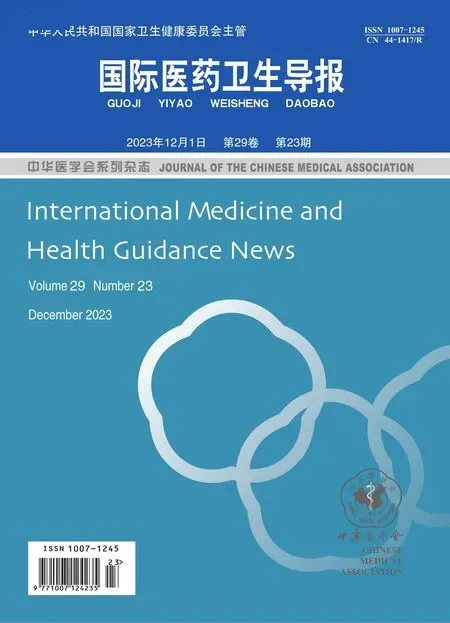維生素C在呼吸道感染中應用的研究進展
肖曦 石斗飛
濱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濱州 256603
呼吸道感染是主要由細菌、病毒、非典型病原體以及真菌等引起的呼吸系統疾病,又包括上、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其中上呼吸道感染是指環狀軟骨下緣以上呼吸道,鼻、咽或喉部感染的統稱;下呼吸道感染為環狀軟骨以下部位,氣管、支氣管和肺部感染。呼吸道感染是人群中極為常見的疾病,患病率高、變異性大,發病率和病死率相當高。尤其是在抗菌藥物耐藥性惡化的情況下,對此類感染的新治療方法的需求日益增長。維生素C(vitamin C)又稱L-抗壞血酸,20 世紀70 年代諾貝爾獎得主Linus Pauling 大力倡導將維生素C用于感冒以及流感的治療[1],其預防及治療疾病的效果一直飽受質疑,現如今被廣泛應用于臨床呼吸系統疾病的治療,其療效在爭議中不斷被研究證實。研究顯示,口服和靜脈注射維生素C 可以減少普通感冒、肺炎、敗血癥和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的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2],有利于降低病死率、ICU 停留時間和住院時間,以及減少嚴重呼吸道感染機械通氣時間,加快病情的好轉。
呼吸道感染與維生素C
1.呼吸道感染
眾所周知,呼吸道感染的發病率極高,尤其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健康青年平均每年也會感染數次,絕大多數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由病毒引起的,病毒感染還會損害呼吸道,同時損傷先天和獲得性免疫反應,為細菌的生長、黏附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而下呼吸道感染嚴重時可發展為ARDS 甚至是死亡。全球估計每年有29.1~64.5 萬人死于呼吸道感染[3],此類疾病給家庭和社會帶來不小的負擔。
呼吸道感染的結果取決于微生物的毒力和感染部位的炎性反應。當少量的低毒性微生物入侵呼吸道時,固有免疫防御系統可以建立有效的防御,比如纖毛的活動、氣道表面的抗菌蛋白、肺泡巨噬細胞等。氣道上皮是第一道肺部屏障,包括能夠釋放大量趨化因子和細胞因子的細胞[4],并被富含抗菌肽的黏液層覆蓋,負責病原體清除。黏膜下抗原提呈細胞和中性粒細胞也參與了肺部感染的防御機制和反調控,可以直接影響肺屏障功能。氣-血屏障(air-blood barrier)是保障在空氣和血液之間進行有效的氣體交換的保護傘,除了防止含有蛋白質的液體流入肺泡空間,還能保護身體免受病原微生物和環境污染物的侵害。當致病因子觸發由免疫細胞介導的局部或全身的促炎反應,就會激發促炎介質的釋放。炎癥細胞如巨噬細胞、淋巴細胞、中性粒細胞[5-6]和嗜酸性粒細胞的活化和招募是各種炎癥介質的來源,如組胺、腫瘤壞死因子(TNF)-α、白細胞介素(IL-1β、IL-4、IL-5、IL-6)、前列腺素、白三烯等炎癥介質。這些炎癥介質與肺功能喪失、氣道高反應性以及梗阻、水腫、黏液高分泌和肺重構等肺部疾病特征相關[7]。活性氧(ROS)生成增加和宿主抗氧化反應減少之間的失衡,導致氧化還原應激增加。如冠狀病毒,引發氧化還原應激的增加導致抗病毒宿主反應的減少和病毒誘導的炎癥和凋亡的增加,最終導致細胞和組織損傷和最終器官疾病[8]。氧化應激和過度炎癥是導致呼吸道屏障破壞的主要原因,而屏障破壞在ARDS等肺部疾病的發病機制中起著關鍵作用[9]。
2.維生素C
維生素C 是動、植物生存不可或缺的一種水溶性維生素,主要以抗壞血酸和脫氫抗壞血酸兩種主要形式存在。大多數動植物都可以合成L-抗壞血酸,而人類、其他靈長類動物、硬骨魚、蝙蝠、雀形目鳥類和豚鼠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對這些生物來說,維生素C 仍是必不可少的飲食成分[10]。L-古洛糖酸內酯氧化酶(L-gulonolactone oxidase,GLO)存在于合成抗壞血酸的動物的肝臟或腎臟中,該酶負責催化合成L-抗壞血酸的最后一步,在人類中,合成維生素C 的能力由于GLO 基因的發生突變而喪失[11]。因此,需要通過鈉依賴性維生素C 轉運體(SVCT1 和SVCT2),從腸道吸收和血液循環中獲取維生素C[12]。
維生素C 除了作為抗氧化劑能夠保護重要的生物分子免受代謝和炎癥過程中內源性產生的氧化劑以及環境產生的氧化劑的破壞作用外,還作為輔助因子參與眾多重要的生物合成及調控的過程,包括膠原和肉堿生物合成、激素產生、基因轉錄和表觀遺傳調控等[13]。維生素C 通過減弱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κB,NF-κB)通路的激活來減少ROS 和炎癥反應,有證據表明,在感染、創傷和手術等生理應激條件下,人血漿維生素C 水平迅速下降[2],在感染期間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增強,對維生素的需求增加,可導致維生素C 的顯著耗竭[13]。維生素C 可能通過增強各種免疫細胞功能和組織愈合能力支持各種感染的恢復[14],該維生素還顯示出直接的殺病毒活性[15],并被報道維生素C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臨床治療中有一定作用[16-17]。
維生素C在呼吸道感染治療中的作用機制
1.減弱氧化應激反應
維生素C 可通過以下途徑實現抗氧化功能:直接清除自由基和活性氧/氮(ROS/RNS)、下調ROS/RNS 生成酶、促進其他細胞抗氧化劑的作用以及激活Nrf2信號等。許多感染會導致吞噬細胞激活,釋放ROS,激活氧化還原敏感轉錄因子,在病毒失活和細菌被殺滅的過程中發揮作用[18]。然而,氧化還原平衡失調,許多ROS 似乎對宿主細胞有害,它們在感染的發病機制中發揮作用。炎癥及其后遺癥導致粒細胞積累,導致更多ROS 的產生,引發炎癥反應,最終導致器官損傷和功能障礙[19]。維生素C 不僅能夠直接猝滅自由基和ROS/RNS,通過抑制NADPH 氧化酶(NOX)途徑阻止新的自由基的產生[20],并協助其他抗氧化劑的循環,激活體內其他抗氧化劑,如谷胱甘肽和維生素E,來增強細胞抗氧化能力[21]。氧化應激和炎癥反應相關基因,包括TNF-α、IL-1、IL-8和細胞間黏附分子(ICAM)-1的誘導之間的相互作用早已被證明是通過激活NF-κB 介導的[22],維生素C 通過衰減NF-κB通路活性來減少ROS的生成。Nrf2正向調控抗氧化基因表達,增強細胞抗氧化防御能力[23],維生素C 上調Nrf2 蛋白表達,并使其活化啟動下游抗氧化途徑[24]。有研究顯示,維生素C顯著提高ARDS大鼠模型的超氧化物歧化酶、過氧化氫酶和谷胱甘肽水平,即上調抗氧化蛋白來降低氧化應激[25]。
2.減輕炎癥反應
在腎上腺中,維生素C 的濃度是其他器官的3~10 倍,在生理應激[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刺激]以及病毒等暴露條件下,從腎上腺皮質釋放出來使血漿維生素C 水平提高5倍。維生素C可促皮質醇的產生,增強糖皮質激素的抗炎和內皮細胞保護作用[2]。同時細胞對維生素C 的攝取是由SVCT2介導的,在炎癥狀態下SVCT2被下調,使用糖皮質激素可以增加轉運蛋白的表達[20]。Nrf2是調節細胞防御機制對抗關鍵應激反應的關鍵轉錄因子。維生素C 通過調節氧化還原敏感的轉錄因子Nrf2 和NF-κB 表現出抗炎活性。感染刺激氧化劑出現并誘導NF-κB觸發信號級聯反應導致ROS 和其他炎癥介質的增加,最終導致炎癥。大量實驗表明,感染時應用維生素C 可顯著降低促炎性細胞因子水平,增加抗炎性細胞因子IL-10 的產生[26-27]。維生素C 具有抗組胺作用[14,28],顯著降低過敏性和非過敏性疾病患者的組胺水平。
3.對肺的保護作用
肺固有免疫系統由氣道上皮屏障、肺泡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中性粒細胞和自然殺傷細胞(NK 細胞)組成。1992年,Buffinton 等[29]發現,小鼠感染甲型流感病毒導致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維生素C 濃度降低,同時伴隨脫氫抗壞血酸增加。2006 年,Li 等[30]研究發現,流感病毒感染后,需要維生素C 來維持足夠的免疫反應,以限制肺部病理變化。2013 年,Kim 等[31]的小鼠模型研究表明,維生素C 可調節抗病毒細胞因子干擾素(IFN)-α 的產生,保護小鼠免受病毒所致的肺損傷。Hemil?[32-33]經過研究發現,體力活動等生理應激導致氧化應激升高,維生素C 參與組胺、前列腺素和半胱氨酸白三烯等誘導支氣管收縮發病機制中的介質的代謝,維生素C 將呼吸道癥狀的發生率降低了52%(95%CI:36%~65%)。維生素C 不僅能促進皮質醇的產生[2],2017 年,Barabutis 等[34]的一項研究發現,氫化可的松(HC)與維生素C 聯用能顯著逆轉脂多糖(LPS)誘導的屏障功能障礙。2021 年,Teafatiller 等[12]研究發現,維生素C 處理BEAS-2B 細胞后,多種代謝通路和干擾素刺激基因(ISGs)顯著上調,肺損傷和炎癥相關通路下調。維生素C 也上調了上皮細胞中的醛固酮信號轉導,醛固酮合成和表達的減少也與肺損傷相關[35]。維生素C 通過多種途徑發揮肺部保護作用。
4.調節免疫作用
維生素C 可以調節先天性免疫和獲得性免疫,影響細胞免疫和體液免疫[36],對感染的益處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增強免疫反應[37]。血漿、白細胞和尿維生素C 水平在普通感冒和其他感染中下降,Hume 和Weyers(1973)報道說,當受試者感冒時,白細胞中的維生素C 水平減半,在康復1 周后恢復到原來的水平[38]。在豚鼠腹腔注射維生素C 后,發現維生素C 能提高離體血淋巴細胞的有絲分裂活性和免疫過程中體液抗體水平[14]。
先天免疫的第一道防線是中性粒細胞通過表達30 多種趨化因子被募集、浸潤到感染組織,以及對宿主來源的炎癥信號和病原體的反應。白細胞中的維生素C 水平是血漿中的幾十倍,維生素C 在中性粒細胞等吞噬細胞中積累,可增強趨化作用、吞噬作用、ROS 的生成,最終對微生物產生殺傷作用;維生素C 在淋巴細胞中,可促進分化和增殖[37]。淋巴細胞主要有3 種亞群,即T 細胞、B 細胞和NK 細胞。T細胞參與細胞毒性適應性免疫,B 細胞負責適應性、體液性免疫,NK 細胞是先天、抗原非依賴性免疫的一部分。研究發現,體外培養的經維生素C 處理的淋巴細胞增殖能力增強,還有助于未成熟T 細胞和未成熟NK 細胞的發育。維生素C 通過促進葡萄糖轉運體1(Glut1)保護線粒體免受氧化損傷,而Glut1 又是CD4 T 細胞激活和發揮效應不可或缺的[14]。有研究顯示,健康個體補充維生素C 可能會提高B細胞的功能和活性,增強體液免疫,增加血清免疫球蛋白A(IgA)、IgM、IgG 水平[39]。還能刺激機體IFN 的產生,導致IFN 應答通路以及IFN 信號通路下游的JAK/STAT 通路均上調[12]。
5.改善循環
維生素C 通過降低內皮細胞通透性,減少內皮細胞損傷,改善微血管和大血管功能發揮循環改善作用。已知有多種途徑發揮血管內皮保護,包括抑制四氫生物蝶呤(tetrahydrobiopterin,BH4)氧化。BH4 是多種酶的必需輔因子,BH4與血管內皮功能的關系已在高血壓、糖尿病和動脈粥樣硬化等多種疾病中報道。BH4易氧化為二氫生物蝶呤(BH2),BH4 與eNOS 結合產生一氧化氮(NO),而當BH2 與eNOS 結合時產生超氧化物。Madokoro 等[40]發現病程早期給予維生素C 可以抑制BH2/BH4 比值的升高,可以幫助擴張血管,延緩血管內皮功能障礙與其他疾病的惡化。在膿毒血癥動物模型中,注射維生素C 提高了存活率以及改善微血管功能,具有抑制小動脈功能障礙和毛細血管堵塞的能力。動脈功能障礙包括血管收縮/舒張功能受損和血管收縮/舒張信號沿小動脈傳導功能受損。在膿毒癥小鼠中注射抗壞血酸通過抑制神經元型一氧化氮合酶衍生的NO,通過包含連接蛋白37 的縫隙連接恢復內皮細胞間電偶聯,從而防止受損的血管功能障礙。注射抗壞血酸通過抑制血小板-內皮黏附和內皮表面P-選擇素的表達,防止毛細血管堵塞。抗壞血酸還可以防止凝血酶誘導的血小板聚集和血小板表面P-選擇素表達,從而防止微血栓形成[41]。有研究報道,血管緊張素轉換酶II(ACE2)在血小板中表達,促進COVID-19 患者血栓形成,而維生素C 對ACE2 的表達有中度但持續的降低作用[42]。
6.抗病毒及抗菌作用
大量實驗及臨床研究數據表明,維生素C 被發現對包括細菌、病毒、白假絲酵母菌和原蟲在內的各種感染性病原體有益。除了呼吸道感染,如支氣管炎和扁桃體炎,以及肺炎和膿毒性休克,維生素C 在保護人類免受各種感染方面可能都具有一定的臨床效果,通過攝入維生素C 可以避免或減輕多種類型的病毒和細菌等病原感染[43]。
在體外維生素C 在補充劑量時即可利用自身氧化產生的自由基直接降解病毒核酸,在體內通過調節免疫和抗氧化發揮額外的抗病毒作用[44],其中包括EIF2 信號轉導、自噬、干擾素反應和JAK/STAT 通路,上調與IFN 信號、凋亡信號和病毒識別、防御相關的基因,表現出抗病毒以及降低病毒效價的效果[45-46]。不僅對呼吸系統病毒感染有效,在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中補充維生素C 減輕肝損傷達到抗病毒治療效果[47]。維生素C 抑制細菌群體感應(quorum sensing,QS)和胞外多糖(exopolysaccharide,EPS)的產生,并通過ROS 的產生誘導細菌細胞內糖和蛋白的泄漏,對多重耐藥、生物膜形成的大腸桿菌和其他革蘭陰性菌發揮抗菌作用[48]。
維生素C在呼吸道感染治療中的應用概況及效果分析
1.動物實驗及臨床研究
動物實驗模型證實,給予維生素C 對呼吸道感染有諸多益處。Lankadeva 等[49]靜脈注射大劑量維生素C(150 g·40 kg-1·7 h-1),顯著改善輸注活大腸桿菌引起的綿羊高動力敗血癥臨床癥狀,從乏力、嗜睡改善為警覺、有反應和活動狀態。
在膿毒癥小鼠中,早期給予維生素C 通過抑制BH4 氧化保護血管內皮細胞,從而減少器官功能障礙,提高存活率[40]。維生素C顯著提高ARDS模型大鼠超氧化物歧化酶、過氧化氫酶和谷胱甘肽水平,降低血清TNF-α 和IL-1β 水平[25]。GULO-KO 小鼠模型等研究顯示,使用維生素C 改善肺功能和防止肺損傷,而且還能增強氣道上皮細胞對病毒核酸和Ⅰ型IFN的反應[12]。
在膿毒癥動物模型中,靜脈注射維生素C 恢復小動脈傳導和毛細血管床灌注有助于提高膿毒癥的生存率。通過含連接蛋白37 的縫隙連接恢復內皮間電耦聯,從而防止受損的血管收縮;膿毒癥中的缺氧/復氧通過蛋白激酶A(PKA)依賴的連接蛋白40 去磷酸化破壞電偶聯,而維生素C 可以恢復偶聯所需的PKA 激活;早期注射抗壞血酸可通過抑制血小板-內皮細胞的黏附和內皮細胞表面p-選擇素的表達來防止毛細血管堵塞[41]。
一項2013 年納入29 項臨床試驗涉及11 306 名參與者的meta分析顯示[50],每天口服≥0.2 g維生素C對普通人降低感冒發病率無明顯效果,但在減少癥狀、持續時間方面有一定的效果,在體力消耗極大的人群總共598 名馬拉松運動員、滑雪者和參加亞北極訓練的士兵參加的5 項試驗中,維生素C將感冒的發病率降低了52%(P<0.000 1)。
近年,一項納入了5 項實驗共涉及2 655 名參與者的研究[51],有2 項實驗評估了補充維生素C 對預防肺炎的效果;還有3 項實驗評估了補充維生素C 作為肺炎治療的輔助治療的效果。為了預防肺炎,提供了補充劑量:每天1 g,連續14 周;每天2 g,連續8 周;每天2 g,連續14 周。對于肺炎治療,以每日125 mg 和每日200 mg 的劑量直到癥狀消失或出院,作為肺炎治療的輔助治療。而結果是不確定補充維生素C對預防和治療肺炎有效果。
有報道稱,維生素C 抗病毒活性可能通過產生NO 來預防COVID-19 感染[52]。上表皮細胞產生的NO 有助于滅活空氣或氣溶膠中含有的病毒和細菌。食用維生素C 可以減少唾液中的亞硝酸鹽,使咀嚼食物時口腔產生NO。在胃中,亞硝酸鹽也可被胃表皮細胞分泌的維生素C 還原為NO,胃液的強酸性有利于亞硝酸鹽的還原,從而產生NO。
一項就維生素C 對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肺部感染和肺癌等呼吸系統疾病影響的研究[53],分析發現維生素C 通過多種機制對氣管平滑肌產生舒張作用,在不同呼吸系統疾病的實驗動物模型中,通過抗氧化、免疫調節和抗炎發揮預防或治療作用,甚至對肺癌有一定影響。
2.給藥方式與劑量
有研究表明,補充維生素C 對呼吸道感染及重癥患者獲益具有不確定性[51,54]。但維生素C 的需要量不僅與維生素C 給藥途徑和劑量有關,還與最初的膳食攝入水平、其他營養狀況、病原體暴露水平、運動水平和溫度應激等相關。由于維生素C 是水溶性的,可以在數小時內排出,在活動性感染期間頻繁給藥以保持足夠的血藥濃度非常重要。腸道吸收維生素C 存在閾值,而靜脈注射能產生較高的血漿維生素C 水平[55],同樣劑量靜脈注射可使血漿維生素C 水平提高約10 倍。危重患者在維生素C 快速消耗的條件下,靜脈給藥比單獨口服給藥能更有效地達到最佳降低氧化應激和發揮抗炎作用所需的治療血漿水平[56]。此外年齡、性別、體質量、吸煙、孕期和哺乳期等影響維生素C 需要量,推薦劑量也存在差異[57]。
維生素C的平均需要量男性90 mg/d、女性80 mg/d可維持50 μmol/L的正常血漿水平。但在感染、創傷、手術等生理應激條件下迅速下降,出現明顯的維生素C缺乏,即血漿維生素C水平≤11 μmol/L。在感染期間和生理壓力下可能需要更高的維生素C攝入量,2~3 g/d才能維持60~80 μmol/L的正常血漿水平,以糾正疾病引起的缺乏,減少炎癥,增強IFN的產生,支持糖皮質激素的抗炎作用[2,19]。已有研究證明,口服維生素C(2~8 g/d)可減少呼吸道感染的發生率和持續時間,靜脈注射維生素C(6~24 g/d)可以降低病死率、減少ICU和住院時間以及嚴重呼吸道感染的機械通氣時間[2]。
3.不良反應
維生素C 作為藥物似乎是相對安全的,有著較大的用藥范圍,不良反應的報道相對較少。雖然維生素C 有著較高的安全性,但也有大劑量應用出現不良反應的證據,比如惡心、嘔吐、嗜睡、疲勞以及靜脈炎等,以及增加金屬離子鐵、錳、鈣在尿液中的排泄,提高形成腎結石風險[58]。單次口服5~10 g 維生素C 可引起腹痛或一過性滲出性腹瀉[53]。腎功能不全的患者高劑量使用維生素C 后可能會增加草酸鹽腎病的風險[2,59],但也有個別腎功能正常使用高劑量維生素C 而導致嚴重草酸鹽腎病的病例[60]。一項靜脈注射抗壞血酸劑量在0.2~1.5 g/kg 的研究[61],檢測了輸注期間及6 h后尿草酸排泄量,證實在腎功能正常的人群中靜脈注射大劑量抗壞血酸后,不到0.5%的抗壞血酸可恢復為尿草酸。除非必須條件下否則將有腎結石或腎功能不全病史的人排除在口服或靜脈注射大劑量維生素C 之外。短期使用高劑量的維生素C,在2~8 g/d 的范圍內不太可能對腎功能正常的人產生重大影響。一些影響維生素C 利用的遺傳代謝性疾病,如葡萄糖-6-磷酸缺乏癥(G6PD)、因維生素C 增強鐵吸收而引起的血色素沉著癥和地中海貧血[2,60],需謹慎使用大劑量維生素C。
總結與展望
維生素C 在呼吸道感染治療中通過多種途徑發揮作用,其重要的抗炎、免疫調節、抗氧化、抗血栓和抗病毒特性已廣為人知,是一種我們的身體無法產生的物質。維生素C 是一種水溶性的有機酸、分子式為C6H8O6的己糖醛酸,溶于水時會得到緩和的酸性溶液,抗壞血酸鹽為帶負電的陰離子[43]。其具有還原性,通過提供電子保護機體免受氧化損傷,在人類及動植物生存中發揮不可小覷的作用。鑒于維生素C 在呼吸道及其他感染性疾病中的有效性,若將維生素C 與抗生素等抗感染性藥物制成復合制劑,患者獲益程度是否會比單獨服用二者高?尤其是對于記憶力較差易漏服藥物的老年患者。其他還原劑,如H2、Fe2+等,是否可以應用于臨床感染性疾病的治療中,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作者貢獻聲明 肖曦、石斗飛負責文章設計與構思;肖曦負責資料收集、文章撰寫;石斗飛負責論文修訂、質量控制與校審、監督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