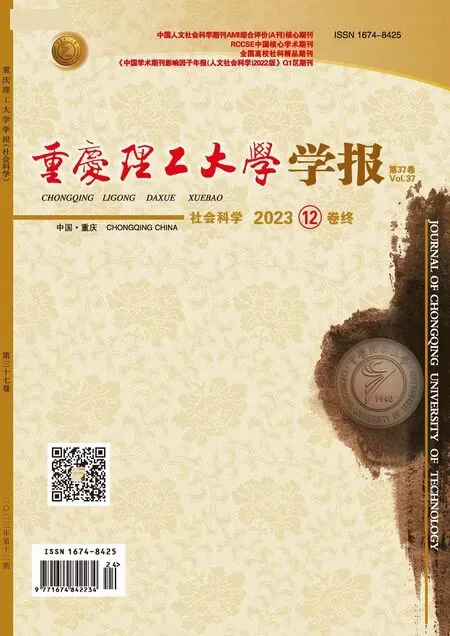文化如何影響邏輯?
——基于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的機制分析
黃 彧,翟錦程
(南開大學 哲學院, 天津 300350)
邏輯推理和論證是人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社會交流活動,不少研究表明,邏輯推理和論證受到文化的制約。那么,文化是如何影響邏輯的?這一問題得到了邏輯學、腦科學、心理學和生物學等多個領域學者的關注。根據抽象層次的不同,學者們給出的回答可分為兩類,一類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和邏輯出發,闡釋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如邏輯學;一類從神經元層面出發,將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闡釋為文化對神經元或腦區活動的影響,如腦科學、心理學和生物學。但是,就日常生活中的邏輯推理和論證活動來說,前一類的闡釋較為抽象,未能深入文化和邏輯的概念空間內部,分析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后一類的闡釋過于具體,人們的推理和論證活動受文化影響時,人們并不會意識到腦神經的活動情況。因此,文化如何影響邏輯,目前并沒有令人滿意的解釋。不了解文化影響邏輯的具體機制,會讓我們在推理和論證的理解、規則選取、構建及評估等活動中面臨丟失關鍵信息和缺乏系統性的風險。認知科學中的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Tri-Process Theory),將人的認知活動分為情感進程、效率進程和公平進程,可為這一問題提供合適的分析框架,闡明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所以,本文從邏輯學和腦科學對文化影響邏輯機制的分析切入,引入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的分析框架,并結合不同文化中的案例,嘗試分析文化影響邏輯背后的認知機制。
一、文化和邏輯的界定
“文化”和“邏輯”的含義經歷過長期的發展變化,學者們有不同的界定,為明確討論的范圍有必要先對它們的定義進行簡要考察。
(一)文化的界定
文化一詞的不同定義反映出文化的主要特征,文化是由人類創造的;文化的范圍廣泛,是所有文明成果的總和;文化可以在人和代際間傳遞,可塑性強,以語言為主要傳播媒介;文化塑造人類的思維方式,文化改變人類的生活;文化具有相對穩定性,但也會發生文化變遷;文化塑造人的認知,人的認知也會影響文化。文化的主要類型和范疇,著名腦科學家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概括為:“藝術、哲學探詢、道德能力、司法、政治治理、經濟制度(市場和銀行等)、技術以及科學是‘文化’一詞所指的主要類型。區分不同社群的各種觀念、態度、習俗、方式、實踐以及制度都屬于文化的范疇,同樣地,文化是通過語言以及文化最初創造的物體和儀式本身在人和代際之間傳遞的。”[1]10文化的定義不下幾百種,這里不做定義辨析,而是采用便于展開本文論述的定義,如,汪丁丁從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三維度對文化的界定——“在物質生活這一維度表現為‘器物’(或廣義的技術),在社會生活這一維度表現為‘制度’(或與制度共生的行為模式),在精神生活這一維度表現為‘宗教’(或信仰及共享的意義)”[2]82。所有和人的物質、社會、精神生活相關的事物集合,都屬于本文討論的文化范圍。
(二)邏輯的界定
日常生活中,人們常說“這是什么邏輯?”“把握市場運行的邏輯”,本文的“邏輯”一詞與此不同,特用來指邏輯學中的邏輯,但邏輯是什么尚未形成統一定義。邏輯學的建立源于亞里士多德的古典形式邏輯,后來歸納邏輯、思辨邏輯以及源于弗雷格和羅素的現代邏輯等發展起來,到20世紀50年代,圖爾敏、佩雷爾曼等學者對形式化方法的局限進行反思,關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推理和論證實踐,于是非形式邏輯興起。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文化對邏輯的影響,如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對阿贊得(Azande)人的論證方式的實證研究[3],漢普爾(Dale Hample)對不同國家被試論證實踐的研究,以及廷代爾(Christopher Tindale)采用人類學方法對不同文化中的論證產生方式的研究[4]。鞠實兒從說理活動出發,對邏輯的概念進行了拓展,認為“邏輯學是一個家族類似概念”[5],論證邏輯具有文化相對性,提出廣義論證理論,從內涵和外延兩方面定義了論證。廣義論證的內涵為“某一社會文化群體的成員,在語境下依據合乎其所屬社會文化群體規范的規則生成的語篇行動序列;其目標是形成具有約束力的一致結論”[6];外延為采用在課堂教授和生活中已使用的規則作為論證規則的論證,以及采用論證主體從論證實踐中獲得但未被表述的論證規則的說服活動。本文采用這一拓展的廣義論證邏輯概念。在此條件下,邏輯同推理和論證的用法是相同的。
二、影響機制探索:邏輯學和腦科學的闡釋
文化如何影響邏輯,本文將著重從認知科學的視角,闡釋文化影響邏輯背后的機制。在這之前有必要先概述從邏輯學和腦科學視角對該問題的闡釋,因為該問題起源于邏輯學,且研究成果最多;而腦科學的成果可為文化影響邏輯這一主張提供證據支持。
(一)邏輯學的闡釋
文化如何影響邏輯?從邏輯學的角度,現有研究給我們呈現了3種思路:一是通過文化的需求來影響,即文化的需求塑造了邏輯的形態,文化的需求不同則邏輯形態不同。張東蓀認為文化塑造邏輯。他說:“可見邏輯乃是應乎文化的需要而起的。文化上需要若有不同,則邏輯的樣子便亦跟著有變化了。”[7]69此外,阿贊得人的推理和論證特征可以說明這一點,埃文斯-普里查德[3]對阿贊得人關于巫術的推理和論證進行了描述,結合鞠實兒在《論邏輯的文化相對性——從民族志和歷史學的觀點看》一文中的論述,概括如下:
1.巫師會帶來不幸和傷害;
2.通過請教神諭或占卜師可知,某男性是否是巫師或具有巫術物質;
3.巫術、巫師、巫術物質同性遺傳;
4.阿贊得氏族通過父系血緣關系確立群體;
因此,依據西方邏輯,埃文斯-普里查德認為,由1~4,可得如下結論:
5.如果一個人被證實為巫師,那么他的整個氏族男性就都是事實上的巫師[3]3。
但實際情況是,阿贊得人明白這個推理的意義,但不接受該結論,并認為:
5’.如果一個人被證實為巫師,只有惡名遠揚的巫師的父系近親男性才是巫師。
在我們看來,由前提1~4應得出結論5,如果接受結論5’是矛盾的。但阿贊得人明白由前提1~4推出結論5的推理,卻接受結論5’。說明阿贊得人擁有自己的邏輯。
埃文斯-普里查德進一步給出了阿贊得人如此推理的理由。鞠實兒將其概括為社會因素、文化因素、目的與語境因素、規則制約因素,并認為,正是阿贊得人的社會文化背景因素“既塑造了阿贊得人邏輯的獨特形式,也為他們的合理性提供了基礎”[8]。
三是通過文化中的語言使用及規則的使用。20世紀50年代興起的非形式邏輯以論證性言語活動為對象,重視論證的語用要素分析(語用功能、言語行為、言語互動等),文化因素因此滲透到推理和論證的實踐中,影響推理和論證。例如,萊考夫(George Lakoff)概括的文化中關于時間的隱喻——“時間是金錢和資源”,通過該隱喻,時間可以預算、有效益、節省、浪費等,我們可依此推斷該如何運用時間,如何設計制度。而在普韋布洛人(Pueblos)的文化里,時間沒有被概念化為金錢和資源,所以普韋布洛人不會依此安排時間,設計相關制度。鞠實兒提出的廣義論證理論,引入社會文化解釋途徑,通過廣義論證研究程序的田野調查、數據分析、候選規則辯護或解釋、驗證規則的階段,揭示出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論證方式,文化因素如語言、習俗、規范等影響論證的產生和發展。
邏輯學從三方面對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進行了闡釋,首先論證了文化對邏輯的影響,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邏輯;其次提供了文化影響邏輯的3種途徑,特別是廣義論證研究程序可直接用于分析文化群體的論證方式。但是,目前這方面的探索還著眼于較宏觀的層面,而文化因素如何影響推理和論證?論證主體在選取推理和論證規則、構建論證結構和評估論證合理性時,所依據的是什么?為什么要這樣依據?這些問題還需深入探索。
(二)腦科學的闡釋
達馬西奧在《萬物的古怪秩序》一書中從生物基礎的角度探討了文化的起源和建構,認為“文化活動始于感受,并且深嵌于感受”[1]3。感受(Feelings)即有機體對自身或環境的體驗,一端為快樂,另一端為痛苦。感受最重要的一個特質是可以做出正向(快樂)和負向(痛苦)的區分,這使得感受可以為我們提供關于有機體和社會境況的信息,一方面幫助我們預測有益的結果,另一方面提醒我們需要避免的風險。
那么,感受和邏輯有什么關系?文化如何影響邏輯?從腦科學的角度來看,文化影響邏輯主要有3種途徑:通過感受、塑造道德系統、建立層級分類框架。
感受以兩種方式作用于邏輯推理:首先,感受通過正向和負向的區分影響邏輯推理活動的意愿和結果。感受為我們提供推理的動力,“哲學和科學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由范圍廣泛的感受促成的。……尤其是那些試圖解答宇宙奧秘所帶來的愉快感受,以及對解答將帶來的獎賞的期待”[1]154。感受直接參與推理活動并影響推理結果。在心情好的時候,人們可能更傾向于支持某個方案;當受到鼓舞時,人們做事的效率會大大提高。其次,感受還可以作為一種監督工具,對邏輯推理進行調節。在實際推理活動中,理性思考并不總是能夠解決問題,此時感受能通過當下的體驗來決定如何推理,或是否采用新思路來進行推理。
日常的邏輯推理和論證活動,大部分是圍繞道德推理進行的。世界腦科學泰斗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的研究認為文化可通過塑造道德系統影響道德推理,人類有運行特定道德程序的硬件,這些硬件受我們的社會文化世界塑造,其中的一部分變成只在特定文化中被接納的美德[10]115。也就是說,我們所處的環境和文化,會引導我們走向一個特定的道德系統,我們依此進行推理和論證,做出行為。例如,幾乎所有文化都認同亂倫禁忌,人們依此自覺規范行為。進化心理學家利伯曼(Debra Lieberman)的研究揭示出亂倫有一套內在機制,對亂倫的整體道德態度,不因后天習得的社會或父母教誨而增強,也不因與兄弟姐妹的血緣關系親密而增強[10]116-117。
建立層級分類框架。大腦的功能之一是對信息進行分類,“人類是天生的分類學家”[10]249,通過分類,我們得到一個關于事物的層級分類框架,并可依此進行推斷。推斷有些是天生的,有些是后天習得的,后天習得的部分受到文化的影響。文化因此可以影響推理和論證。如,在所有關于牛的文化中,從牛的概念開始,可推斷牛是一種哺乳動物,有4條腿等;但如果推斷牛是可食用的,不同文化得出的結論會有差異,在崇拜牛的文化中是不恰當的。
腦科學為文化影響邏輯提供了證據支持,但腦科學視角的闡釋面臨一個顯著質疑,就是人們在推理和論證的過程中,幾乎不會意識到大腦內部是如何工作的。所以,它雖然為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提供了解釋,但應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推理和論證,似乎不是最佳選擇。
三、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TPT
邏輯學和腦科學從多方面闡釋了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但為什么人們進行推理和論證會選擇這部分論證規則而不是另一些,為什么會如此建構論證結構,其背后的機制還需深入探索。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TPT)是對認知科學發展成果的最新總結,可為我們提供分析文化制約邏輯機制的分析框架。本節先介紹TPT,然后說明采用該理論作為分析框架的理由。
式中,Bi為多時相近紅外最小值合成圖像上第i個像元的灰度值;Bmax和Bmin分別表示在多時相全色圖像上提取的積雪范圍內,通過近紅外波段多時相最小值合成后圖像上的最大像元值和最小像元值.當上式成立時,像元值賦為1,表示為積雪,否則為0,表示為非積雪區.
(一)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
大腦是如何工作的?從大腦認知進程的角度出發,探索和區分大腦信息處理的不同方式,是當代認知科學的重點。不少研究(1)關于大腦認知雙進程理論的發展歷史,可參見JONATHAN ST.B.T.EVANS的History of The Dual Process Theory of Reasoning一文,見于MANKTELOW K,CHEUNG CHUNG M.Psychology of Reasoning: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G].New York:Psychology Press,2004:241-266。大腦認知雙進程理論的最新研究進展,可參見WIM DE NEYS.Dual Process Theory 2.0[M].London: Routledge, 2018。認為大腦存在兩個認知進程,即大腦認知的雙進程理論(Dual-Process Theory),其中一個進程偏重直覺和情感,自動運行,運行速度較快,另一進程偏重理性計算,需要有意識地控制,運行速度較慢。如斯坦諾維奇(Keith Stanovich)和韋斯特(Richard West)提出的“系統1”(System 1)和“系統2”(System 2)[11]658-660,以及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對“系統1”和“系統2”的論述[12]。在這兩個進程之外,大腦是否還有其他認知進程?
公平感是人們常體驗到的感受,也是日常生活中人們行為的依據,如:別人打碎了你的杯子你覺得他應該照價賠償,客觀條件相同的條件下競爭對手得獎而你落選你會覺得不公平。近半個世紀以來,對公平的研究得到了認知科學、博弈論、演化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等學科的共同關注。在此基礎上,成凡認為公平認知可單獨作為一個認知進程,在大腦認知雙進程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大腦認知的三進程理論,將大腦認知進程劃分為效率進程、情感進程和公平感進程[13],神經科學中分別對應效率腦、情感腦和公平腦。大腦認知三進程,我們還可從中西文化中找到很多類似的說法,如倫理學中結果論、美德論、道義論的分法,傳統文化中法家、墨家、儒家的思想。
效率進程偏重結果計算(Calculation),即根據行為選項的后果來進行推理和決策。“如果行為人做X能夠給他帶來更好的后果或者更能夠實現他所欲求的目的,那么他就應該做X。在邏輯學上,這種思維模式所對應的正是假言命令。”[13]效率進程啟動后,人們總是會選擇那些結果好的,利大于弊的選項,如:根據兩家初創企業的未來收益決定是否投資,比較兩款機器人的價格決定買哪一個,“識時務者為俊杰”。在神經科學上,效率進程的關鍵腦區是大腦外部的新皮層(Neocortex),該腦區主要負責處理語言邏輯和數學符號。
情感進程偏重直覺(Intuition)和情感,并依此行動,“可以不借助推理就能夠直接得出結論的直覺。就此而言,它在邏輯學上對應的是‘定言命令’,也可以用康德的術語即‘絕對命令’來定義它”[13]。情感進程啟動后,人們會依據不假思索的直覺得出結論,如:看到小貓心生喜愛,看到蛇后被嚇出一身冷汗,“愛不釋手”。它對應的關鍵腦區是大腦內側的杏仁核(Amygdala)和基底核(Basal Ganglia)。
公平進程偏重直覺推斷(Heuristics),它不同于情感進程和效率進程。從反應速度上來說,公平進程的啟動速度介于情感進程和效率進程之間,比情感認知慢,比效率推理快;從啟動條件上來說,公平認知的啟動有條件、有原因;從是否包含計算過程來說,公平進程涉及計算,計算的是事件的前因。“公平推理僅僅基于損害事實,而這個前因將直接得出應當向他主張賠償的結論,此處不存在更多計算的空間與機會。”[13]在邏輯學上,公平推理也是一種假言推理,但和效率推理的方向相反,如果X有某個前因,那么就應該X,如:購買車票的時候按先來后到排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公平進程在神經科學上的重要依據是海馬、內側顳葉、嗅皮質等大腦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
需注意的是,雖然可從功能的角度將大腦認知分為3個進程,但它們之間并非沒有聯系,例如,效率計算有時也需要控制,過度強調效率可能會導致人們過度計算而無法做出決策。大腦認知是一個整體,但大腦對信息的處理體現出3種不同的進程,由此可為我們理解大腦運行機制并以此為背景框架分析其他問題提供便利。
(二)何以是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
邏輯推理和論證是人們社會交往的重要活動,受到文化的制約。為何要引入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的分析框架?在文化與邏輯中間,為何突出大腦認知三進程的環節?理由有三:一是大腦認知進程理論是對大腦運行的一般機制的總結,是一切認知的基礎,因此可用來分析推理和論證實踐;二是文化影響邏輯需要通過文化對認知進程的塑造和選擇來實現;三是采用大腦認知三進程的分析框架可為推理和論證活動的展開帶來良好效果。
理解和分析不同文化中的推理和論證方式。每一文化中的論證主體有其相應的推理和論證方式,從大腦認知三進程的角度看,人們的推理和論證實踐是依據大腦認知做出的,而文化塑造認知進程,所以對同一事件,不同文化群體中的人有不同的推理和論證方式。如:同樣是治理天下,墨家強調利他兼愛,因而從情感認知的角度論述,“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14];法家強調集體效率,因而從效率認知的角度論述,“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15]。
基于不同的文化構建推理和論證。推理和論證實踐的重要環節是構建論證,如何構建論證涉及論證規則的選取,以及論證結構的構建。借助大腦認知進程三進程的分析框架,我們可獲知不同文化中人們論證規則的選取方式,因而可依該文化中的論證規則做出更好的論證。例如,在鼓勵孩子努力拼搏的文化中,假設我們要構建一個論證說服孩子熱愛學習,從效率認知的角度說明學習的效用,可能達到較好的論證效果;而如果從情感認知的角度說明學習可以使人成為一個高尚的人,成功說服的幾率可能大打折扣。
評估推理和論證。現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中,形式邏輯用有效性來評估論證的合理性,語用分析進路用一系列批判性問題來評估論證。前一種方法很難適用日常生活中論證的評估,后一種方法缺乏系統性,實際運用過程繁瑣。此外,廣義論證理論采用論證所發生的文化中的局部合理性標準,可以更好地評價不同文化中的論證活動,但一個論證如何相對其所在文化具有合理性,還需進一步分析。大腦認知三進程的分析框架可以提供一個具體的操作指南,從認知進程的角度出發,如果某個文化群體重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接,那么,以結果為導向,唯利是圖,不擇手段的論證策略,大概率不是一個好論證,雙方達成一致結論,成功說服對方的可能性較小。如果推理和論證規則的選取,論證策略的構建與該文化群體一致,則有較大幾率成為一個好論證。
四、基于TPT的文化影響邏輯機制分析
討論文化如何影響邏輯,需要回答兩個問題:
(1)文化是否影響邏輯,影響是否是決定性的?
(2)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是什么?
對第一個問題,學者們已經做了精彩的論述和證明,邏輯具有文化相對性,邏輯受文化制約。因此,我們可以說文化制約邏輯且具有決定性作用。對第二個問題,本文的回答是:TPT可為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提供合適的分析框架,文化通過塑造和選擇大腦認知進程來決定人們的推理和論證方式。具體來說,大腦認知進程直接決定邏輯推理和論證活動,而文化塑造大腦認知進程,并在認知進程博弈的過程中選擇合適的認知進程,從而幫助人們做出推理和論證。
為清晰闡述TPT分析框架下,文化影響邏輯推理和論證的機制,我們先分析最簡的理想化模型,然后在該模型上進行拓展。即:先分析大腦認知三進程如何直接作用于邏輯推理和論證,然后加入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如何通過認知進程影響邏輯推理和論證。需說明的是,這只是為了闡述方便的操作方法,文化通過認知進程影響邏輯是一個整體。
(一)大腦認知三進程如何影響邏輯
人們的推理和論證是如何隨著大腦認知進程的變化而變化的?我們以“電車難題”(The Trolley Problem)的不同版本為例來說明。電車難題由富特(Philippe Foot)于1967年提出,此后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正義》公開課中將該難題帶入大眾視野。不同的電車難題版本可概括為3類,這里參考成凡在《法律認知和法律原則:情感、效率與公平》[13]一文中的總結。
一輛有軌電車在前行中失控。軌道正前方有5個鐵路工人正在施工。電車繼續直行將撞上這5個工人,他們將全部被撞死。司機無法剎車,因為剎車已經失靈。在相同的背景前提下,有3種可能情形:
效率版——電車難題原型。司機可以扳動方向盤,讓電車駛入另一條軌道。那條軌道上只有一個工人。如果司機扳動方向盤,可以救下5個人,但要犧牲1個人。如果你是司機,你會怎么做?扳動方向盤,或者不扳。
公平版——天橋版本。此時,有一個人正在軌道上方的天橋上看風景。你可以推下這個人,攔住電車。犧牲1個人,救5個人的生命。你會不會把這個人推下去?推,或者不推。
情感版——殘忍版本。此時,有一個人正在司機旁邊。如果把這個人吊在火車前,它的腿會被完全磨損,但他臨死摩擦地的慘叫肯定會驚醒那5個人,挽救5個人的生命。如果你是司機,你會怎樣做?推,或者不推。
心理學家豪瑟(Marc Hauser)對此做的在線匿名調查,超過30萬人作答,在效率版電車難題中,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司機應該扳動方向盤,犧牲1人救5人,在公平版電車難題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愿意將橋上的人推下去[16]。成凡對華中科技大學85名學生做的測試,結果類似,此外在情感版的電車難題中,沒有人會選擇犧牲1人救5人[13]。
同樣是犧牲1人救5人,為何在不同的情形下人們的選擇會如此不同?因為它們激活的認知進程不同,在電車難題原型中,場景激活的是效率認知進程,以扳動方向盤的方式犧牲1人救5人,合算。在天橋版本中,大多數人覺得看風景的人是無辜的,推他下去不公平,場景激活的是公平認知進程,否定效率選項。在殘忍版本中,讓一個人面目全非地死去直接引起人們的惡心或恐懼,場景激活的是情感認知進程,否定效率選項。電車難題不同版本中人們的決策,揭示出人們根據大腦被激活的認知進程進行推理。認知進程發生改變,相應的推理也會發生變化;認知進程不變,推理不變。
(二)文化如何影響大腦認知三進程
接下來,我們在大腦認知三進程影響邏輯推理的模型上,加入文化因素,分析文化如何作用于認知進程,從而影響邏輯推理和論證。根據邏輯推理和論證發生的過程,文化影響邏輯推理和論證的具體機制可分為3個階段:
首先,在推理和論證活動發生前,文化塑造認知進程。大腦認知進程具有可塑性,文化作為人生存其中的環境無時無刻不在塑造認知進程。本文的文化內涵包含物質生活、社會生活、精神生活3個維度。物質生活維度以效率為特征,包括各種文化成果,如技術發明、知識成果;社會生活維度以公平為特征,包括社會規范,風俗習慣等;精神生活以情感為特征,包括群體和個體的精神氣度,品格等。相應地,文化也可從效率、公平、情感三方面塑造人的認知進程,每個人的認知進程深深烙有其所在文化的特點。例如:在效率認知方面,集體利益優先的文化環境中,個體可能會為了集體利益犧牲自己,舍身為國;但在個體價值優先的文化環境中,個人權利神圣不可侵犯,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其次,在推理和論證活動的過程中,文化選擇認知進程。事件在進入推理和論證過程之前,需要先激活認知進程,線索是推理和論證的場景。被激活的認知進程的數量、種類、強度會影響邏輯推理。如果同時被激活的認知進程不止一種,便會出現認知進程的沖突,邏輯推理的糾結。認知進程被激活后,文化通過選擇認知進程決定邏輯推理。這里有兩種情形:
(1)如果激活的是單一認知進程,那么根據該認知進程進行邏輯推理,如:決定買戴爾電腦還是蘋果電腦,通常我們會比較價格和參數,選擇性價比高的一款,這里激活的是效率進程,根據結果計算來選擇即可。
(2)如果事件同時激活的認知進程不止一個,那么認知進程之間會進行博弈,文化選擇最終勝出的認知進程。認知進程博弈的一般原則是,情感進程優先于公平進程,公平進程優先于效率進程,效率進程優先于情感進程。如:刑法中的“緊急避險”,是指為保護一個法益不得已而損害另一個較小或者同等法益的避險行為,如果為保護財產而犧牲生命,可能是“避險過當”,因為生命權高于財產權;如果保護某些生命而犧牲某個生命,也是“避險過當”,直覺告訴我們,這不公平;如果不侵害生命權,也不損害公平,經權衡利益后犧牲較小利益,“緊急避險”一般成立[17]。大多數文化環境中可以發現上面的原則,但也有特例,體現出不同文化對認知進程的塑造,如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親親相隱”和“大義滅親”原則,它們分別激活情感進程和公平進程,中間有一個博弈,偏向情感進程會支持“親親相隱”,偏向公平進程會支持“大義滅親”,在“大義滅親”的情形下公平進程優先于情感進程,但也被一定的社會成員接受。
最后,在推理和論證活動完成后,文化會動態調整認知進程的選擇策略,鞏固為社會群體所接受的認知進程選擇策略,弱化相對不受歡迎的認知進程策略,進一步塑造認知進程。
基于TPT,我們再來看阿贊得人接受我們看來覺得錯誤的論證,原因何在?一個阿贊得人如果接受結論5,那么他需要承擔的代價太大,因為“這個推理會使整個有關巫術的觀點陷于矛盾之中”[3],這激活了他的效率認知進程,且是負向效率認知進程,所以他為了維護整個巫術的信念而選擇忽略單個推理中的不一致。埃文斯-普里查德還解釋,阿贊得人對不一致問題沒有理論興趣,只和自身利益相關的條件下才對巫術感興趣,也就是說,關注不一致的結論不會給阿贊得人帶來任何利益,所以阿贊得人不會去關注這個問題。從TPT的角度,分析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不僅能揭示出推理和論證規則選取,論證構建的過程,還能揭示出背后的理由。這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分析和做出更好的推理和論證。
五、結語
文化如何影響邏輯?本文基于大腦認知三進程理論的分析框架,得到以下結論:文化塑造大腦認知進程,并在認知進程博弈的過程中選擇合適的認知進程,認知進程決定規則的選取及推理和論證的方式,文化通過認知進程影響邏輯。具體來說,在推理和論證活動中,偏重結果計算的效率進程,偏重直覺和情感的情感進程,偏重直覺推斷的公平進程,以單獨或聯合的方式,決定我們如何選取推理規則,決定我們采用何種方式進行推理和論證。而認知進程又由文化塑造。對文化影響邏輯的這一根本機制的把握,有助于我們做出更好的推理和論證。這在當下社會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邏輯可以作為一種文化工具應對社會危機。如:邏輯中蘊含的秩序、理性和公平的價值取向,有利于預防社會情感失調,維護社會穩定;邏輯的理性思考精神有助于認識并化解文化沖突。此外,對文化影響邏輯的根本機制的理解,有助于我們分析不同文化中的邏輯,以此為基礎更好地開展跨文化交流。
人類智能是當代最重要的話題之一,人類認知受文化塑造,我們不僅作為當下的個體存在,也承載著所在社會的文化。文化是我們的一種存在方式,也是我們的思維方式,從這個角度看,文化對邏輯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但由于文化和邏輯的內涵和外延都十分豐富,論述文化影響邏輯的機制是困難的。可能有人會反駁,文化為什么要通過認知進程影響邏輯,而不是直接影響邏輯?認知進程在這里是必要的,因為認知進程是大腦工作的一種方式,邏輯是大腦工作的類型之一,所以文化對邏輯的影響實際要通過認知進程才能實現;且文化塑造認知進程,它們是一個整體。文化如何塑造認知進程,認知進程之間如何博弈,優勝的博弈策略如何進一步推動文化對認知進程的塑造,文化如何繼承傳統,如何結合當下環境煥發力量,推動個體和社會發展等,文化、認知、邏輯和智能,為我們拉開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