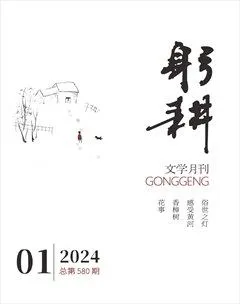清月巷拙耕園拾趣
譚瀅
天下所有與美相關的事情,也大都與藝術密切相關。現實生活中盆景是個高雅的玩意兒,玩盆景多是有錢有閑的主。既然是“玩”,就沒有什么門檻,可要想玩出境界,就不是那么簡單的事了。獲個獎,還是金獎,那就是“出圈兒”的大事了,肯定得有兩把刷子!紙上種字的人,和盆里種景的人,看似八竿子打不著,卻因藝術的相通相融,在不同的層面悄悄滋生著“觸角”,并在一個冬日的雨天“觸角與觸角”搭在了一起,進行了促膝長談。
農歷小雪節氣過后,氣溫一下子從二十度降至四度,還下起了雨,冬天的雨怎一個冷字了得。這樣的天氣適宜待在暖氣房里,喝喝茶,看看書最愜意。然,急欲探尋“美”的世界,超拔境界的人,氣候再惡劣也阻止不了他們急吼吼的心,和迫不及待的腳步。
進入清風巷拙耕園盆景基地,一雙眼睛顯然是不夠的,平時在酒樓大堂或格調高雅的人家里看到一兩盆盆景總會前后左右360度無死角地觀賞。從驚訝繼而驚嘆:簡直“鬼斧神工”!常常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怎么就如此詭異奇崛呢?今天終于深入“虎穴”一探究竟。進園入眼的是一盆雀梅,“清風明月”的主人麻世軍說,玩盆景80%是從雀梅入手的。園里北側有幾間平房在藤蔓和盆景中坐落,頗有幾分雅氣。這里的桌上面擺著一方黑玉石,很是顯眼。麻世軍說是朋友從欒川送過來的。早就聽說過,玩盆景的和賞石的,以及玩根雕的私下里都是好朋友,他們中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我立馬就想到兩個成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今天“聊閑”的可是大師級的人物,一個是河南省盆景藝術大師楚紅旗、另一個是在第14屆中國(合肥)國際園林博覽會盆景展覽暨全國盆景精品邀請展中獲金獎的“清風明月”主人麻世軍。麻世軍說,藝術師和藝術大師差著一個級別,楚老師雖然比我小些,也是我老師。他不說也沒人知道這中間的道行,隔行如隔山呢。
楚師傅說,盆景是“立體的畫,無言的詩”。大家深以為然!他說,盆景和石頭、根雕雖然都謂藝術品,卻是有著本質的區別,盆景是活著的藝術,令人百看不厭。石頭,根雕看個三年五年可能會產生視覺疲勞,盆景則四季常新,給人不同的觀感。美是美,可活物難伺候!它們“春天抽嫩綠,夏天賞百花,秋天掛碩果,冬天看枝丫”哪一季的美都不是白來的。每一棵植物和每一個人是一樣的,各有各的性情。作為主人的職責就是不停地琢磨每一棵樹的習性,特征,從而對癥施法。玩盆景的工作室里盆景自然是標配,洛陽人有句俗語叫:有啥,耍啥。對于琳瑯滿目的盆景,我等門外漢飽了眼福,美了心境,卻叫不出它們的名字。
麻世軍是一個頗為白凈的中年男人,這和印象中黑不溜秋玩盆景的人截然不同。玩盆景的多年在野外踅摸,“黑不溜秋”是常態,只要聽說哪兒有好苗了,箭一般“嗖”就跑去了。只怕慢一步會失之交臂。麻世軍感慨地說:“一入盆景深似海”,入行十多年了,投入很多,人力物力財力。僅一個盆景大盆需要三四千,雖然知道不便宜,但聽到具體數目我等還是驚得瞪大了眼睛。園子里有一棵柏樹,有二三百年的樹齡,是鎮園之寶。麻世軍笑著說,楚師傅給它加了兩百歲。我們一臉懵,這樹齡還能隨意添加?原來是楚師傅為盆景加持了老樹“舍利”。老樹,經過雷擊、風霜雪雨、落石和病害的摧殘,傷及部分就會枯萎,樹皮剝落,木質部會呈現白骨化。這種山野中自然形成、樹干或枝條先端樹皮剝落的,木質白骨化的稱為“舍利”。楚師傅不愧為大師,講起來頭頭是道。把老樹“舍利”進行打磨,并涂刷石硫合劑,和盆景合為一體增強了盆景的觀賞價值。大家很是驚奇。楚師傅說,經過特殊處理的樹舍利可幾百年不腐,與盆景樹共生。
談到初入盆景行,麻世軍說最初只是小小的喜歡,在平房頂上養了兩盆自個玩,誰知道這一玩就玩野了,收不住了。只要聽說哪里有原始株,就想方設法“攫為己有”。他說,哪怕顛倒下井,也要把它弄回來。簡直就是樹癡,景瘋子。一個人如果失去理智地去愛一個事物,就預示著離成功不遠了。他從南陽荊子山里運回了一棵近兩米高的樹樁,這棵樹樁上面分叉,像一對夫妻,背后看像丈夫摟著妻子的腰。樹上長著長長的嫩枝,他指著“妻子”的那一側說,等她長壯實了上面的枝條就全部剪掉,只留一個側枝,往粗壯里憋著長。正如楚師傅說的:達到一定境界后,就是“樁在手,景在心”,如何“謀篇布局”都在主家心里了。楚師傅看起來像個沉默寡言的人,一旦說到盆景話匣子一下就打開了。他說,盆景里也有學問,有“四大家,七賢,十八學士”“四大家” 分別是金雀、黃楊、迎春、絨針柏;“七賢”是黃山松、瓔珞柏、榆、楓、冬青、銀杏、雀梅; “十八學士”是梅、桃、虎刺、吉慶果、枸杞、杜鵑、翠柏、木瓜、蠟梅、南天竺、山茶花、羅漢松、西府海棠、鳳尾竹、紫薇、石榴、六月雪、梔子花。這里面許多是南方的盆景樹,在北方是養不活的。使人不由想到了“南橘北枳”。
一棵出塵的盆景怎么都得十多年培育。原始株移盆里需要“挨三刀”輪廓、形狀才能出來,才成“型”,再在上面接小枝做文章,才可以去參展。第一刀需要長四年左右才能做;等長出新芽兩三年再切第二刀;再憋出新芽長到一兩年再切,挨三刀切,樹才有功力,枝干由粗到細,再拉絲造型。麻世軍說,養盆景比養孩子可操心多了。養個孩子四五歲都可以打醬油了,養盆景得十來年才能出手。這中間付出的艱辛一點兒不比養孩子少。澆水、打藥、施肥、打枝抹杈,一不小心就死給你看。養了兩棵棠梨,眼看掛果長得可養眼了,不知怎么到秋天突然提前落葉,萎靡不振。趕緊翻盆換土,天天跟前伺候著,還是病懨懨的,不見好轉,養了十多年的心血打水漂了!心里真的是五味雜陳。說到養盆景的艱辛,麻世軍說,一個伙計玩了十幾年盆景,連一棵也沒有出手。也就是只有投入,沒有產出。有人說,是不是養十多年的盆景,都養出感情了,像自家女兒一樣,出再多彩禮也不愿意她“出嫁”?麻世軍說,盆景也分很多檔次的,有的幾百年樹齡就當鎮園之寶了,如果不是急需錢,幾十萬也不舍得賣。有的是作為商品出售,為它們找下家,以苗養苗。畢竟養盆景是一個高投入的行業。對于去參展獲金獎的那棵盆景“吉慶人間”,麻世軍又打開了獲獎作品的話題。金獎有很多參數的,一是看盆是否與樹相匹配,株型,高矮等等,樹本身占60%,其他條件占40%。那時真的就像嫁閨女,吹吹打打盛裝把她送上花轎,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眾人的品頭論足。她獲得了鮮花和掌聲,這當爹的自然臉上有光!大家哈哈大笑。一邊說笑,一邊流連于盆景基地。棵棵都是寶貝呀!每一棵都有一個故事,每一個故事里都有栽培者的影子。
說起盆景的歷史,還是咱老祖宗的玩意兒,得從乾陵發掘的唐代章懷太子墓甬道說起,在甬道東壁上繪有侍女手托盆景的壁畫,這便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盆景實錄。事實上,喜歡盆景的多為文人雅士。宋代著名文士都有對盆景的描述和贊美。其中陸游的《懷舊》云:翠崖紅棧郁參差,小盆初程景最奇,誰向豪端收拾得,李將軍畫少陵詩? 原來楚師傅說的“立體的畫,無言的詩”是有出處的!宋代戴復古的詩則更細膩,更接地氣兒,他在《滸以秋蘭一盆為供》寫道:“吾兒來侍側,供我一秋蘭。蕭然出塵姿,能禁風露寒。 移根自巖壑,歸我幾案間。養之以水石,副之以小山。 儼如對益友,朝夕共盤桓。清香可呼吸,薰我老肺肝。不過十數根,當作九畹看。”把一棵盆景的來由以及發自內心的喜愛描摹得淋漓盡致。
元代的高僧韞上人則善作小盆景,取法自然,稱之為“些子景”。明確有“盆景”一詞,出自明代屠隆的《考盤余事》。而盛行于日本的“盆栽”也是由我國傳入的。流傳至今,歐美流行的“bonsai”則是盆景的別名。一路走下來邊欣賞邊聽解,大家的自豪感便抑制不住,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