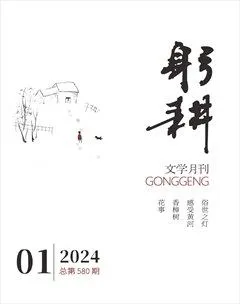閩南的三重夢
曾龍
古城
從沒有一塊土地像漳州那樣易于擄獲人心。
近年來,行走的城市多了,越發疲于城市間的大同小異,反而開始鐘情于一座城市的特質。
城市的特質并非那些外在的繁華和景觀,它源于歲月的沉積與傳襲,用堅實的地基承載了一座城市的血脈和根系,從而使其生發出不朽魅力。
漳州的特質幽藏在古城里,那些街巷、牌匾、雕花永遠帶著新鮮而瑰麗的氣息召喚著游人來探秘。
尋味漳州,最好的方式是行走。行入古城,應先讓身心褪去都市的氣息,再放慢步子,像一個信徒尋找心靈的指引。歲月在這里洗掉了一切喧雜,等待腳步在流連間偶遇意外之喜。
少有一座城市像漳州這樣,留存了大量近代建筑。作為記憶的載體與血肉,建筑承載了一座城市的歲月之美,像一部凝固的史書,耐人尋味。漳州古城不像我近年在許多城市見到的古鎮,這些古鎮要么在模仿中走向爛俗,要么充斥滿商鋪,少有真正的煙火氣息。唯有漳州古城真正兼具了韻味與生命力。這些古城里的老建筑非但沒有成為充滿隔閡感的文物,當地人反而生活其中,延續著每座建筑的血脈與承襲。
在古城漫步,每一眼的交匯都會打開一口時空的深井,讓心緒隨悸動懸停。我最喜在街上端詳那些老鋪子,有時沉醉其中久久挪不開步子。牌匾上,那些過往的店鋪早已易主,或換成了別的行當,或隱去了姓名。每當看到這些充滿戲劇性的變遷,我就會好奇它們曾有過怎樣的經歷。漸漸地,歷史在我眼中不再是一個個抽象的符號,反而深埋著引人入勝的謎底。
除了歷史,美食是古城最值得的尋覓。各種小吃店在古城應接不暇,許多小店不僅有多年歷史,還形成了品牌,牢牢俘獲著漳州人的味蕾。有的光聽名字就讓人饞涎四起,一眼望去滿是煙火氣息。
在漳州琳瑯的美食中,最惹人饞涎的要數蚵仔煎。那帶有大海咸香的牡蠣肉和雞蛋液碰撞在一起,瞬間就在味蕾上激起無窮風味。干脆爽口的蚵仔煎,蘊含的不僅是舌尖滋味,更是大海對漳州人千百年來的哺育之情。
除了各種小吃,古城街頭最為顯眼的莫過于鮮榨果汁。在古城,鮮榨果汁店隨處可見,且價廉味美。榨上一瓶甘蔗汁,隨飲于古城街巷,滿是人間風味。
在古城漫步,最大的感觸就是多情。或許,旅行就是要讓一個人忘卻過去,融入新的身份,去做當地人所做,食當地人所食,甚至要在艱苦與不便中體味那份人間真味。
云水謠
云水謠,最先讓我動心的是它的名字。
初知云水謠,瞬間就被這詩意的名字所吸引。腦海中不禁浮現一幅醉心的煙火畫卷,不過忙于生計一直未能成行。
前些日子辭了職,了卻諸多瑣事,瞬間閑了下來。云水謠又浮上心頭,于是立即買票行往漳州。
漳州的交通四通八達,有的公交車站點甚至多達百站。從漳州市區先乘車到南靖縣,再換乘另一班公交就可直抵云水謠古鎮。
抵達云水謠時已是傍晚,一片褐色的民居漸次映入眼簾,其間不斷穿插著各式土樓。到云水謠后,我才知土樓之眾遠不止知名的那幾座。事實上,在來往云水謠的沿途隨處可見土樓的身影。一座土樓,隱匿了太多人世悲歡。
水,給了云水瑤靈動與生命。有著數百年歷史的榕樹在溪流邊四處可見,撐著繁盛的枝葉,為這靜好的歲月遮風避雨。水車、果樹、古橋在夜色中變得柔軟而多情,似乎在云水謠,生活僅余下了繾綣的詩篇。
夜游云水謠是最好的。我常在古宅與土樓間漫步至凌晨,夜游既能避開白日的喧囂,又能在寂寥中安享寧靜,觸摸到土樓最為隱秘的體溫與紋理。似乎所有的心緒都會在夜行中,被打磨成一面時空之鏡。
除了能在寂寥中體味歷史的曠遠,土樓的美也只有在夜晚才會盛放得最為酣暢淋漓。每當夜幕降臨,土樓的美會陡然變得嫵媚起來。在光暈的渲染下,顯得尤為神秘動人。除了光感所帶來的視效,夜幕時分,一座土樓的市井氣也便真正開始蘇醒。行入其間,你會感到縈繞周身的人煙,像層層熱浪在耳畔翻滾。仿佛霎時間,所有的人間況味都已融入了這窄窄的方寸之地。
懷遠樓和云貴樓在云水謠最負盛名,它們一方一圓,不僅外觀不同,就連建造也有迥異的來源。云貴樓據說建于沼澤之上,踩在其上甚至會有輕微的起伏感。我還付了十塊錢門票,專程上樓看了趟。上樓的俯瞰,又與在土樓間的仰視不一,視野會瞬間變得清朗開來。層層土樓,層層的煙火之氣,包裹著瑣碎的日常與世道人心,又像一條條觸角,連接著千百年來的血脈承系。
河坑
知曉河坑,還是從云水謠結識的一友所聞。他說河坑土樓要比云水謠更為原汁原味,瞬間就讓我動了心。不過,從云水謠到河坑無車直抵,為了方便,我還專程去書洋鎮上租了一輛電動車。
河坑的布局形似北斗七星陣,因而被稱為土樓界的北斗七星。它是世界上最為密集的土樓群,不大的面積內集聚著14座土樓。
初入河坑,瞬間就被一股濃郁的煙火氣所吸引。一切維系著百年前的原貌,在時間的激蕩間安享著生活的閑靜。在河坑,不僅尋不見任何商業場所,甚至找不到賣土特產之地。漫步其間,絲毫感受不到旅行所帶來的疏遠與隔離,似乎河坑生來就是為了迎接歲月的綿長與愜意。
土樓里的老人或在長椅上閑聊,或在日光中享受著生活的恬靜。歲月,在他們的臉上留下了磨痕與皺紋,同時也饋贈了更多的甘與蜜。許多老人見我進入土樓,紛紛邀請我去他們的房間參觀。其中有位大叔尤為熱情,大叔裝扮時髦,梳著油頭,西裝革履,乍看與這土樓有些不搭。他有三個兒女,如今都定居在縣城。幾年前,女兒接他去城里享福,他待了一段時間卻又回到了土樓,他說這里有煙火氣。
大叔的房間不大,里面設有一張茶桌和長椅,桌上擺放著一臺老式電視機。電視機上貼著大叔年輕時的照片,五官俊朗,眉目秀氣,嘴角掛著一絲笑意,頗有港星風范。然而,一切的美好卻終究敵不過歲月的摧殘,或許大叔光鮮的外表不過是一種對消逝的不甘與反叛。
我問大叔,為什么河坑里的人不像云水謠那樣賣點東西,也能謀點收入。大叔聽后笑了笑,反問我是否覺得河坑和我去過的其他土樓不一樣,我點了點頭,說更有生活氣息。大叔接著說,幾年前,村里把水泥樓全部拆除,僅留下了老房子,就是為了恢復最原汁原味的河坑——這樣的土樓才是最有煙火氣息的土樓,這樣源遠流長的經營才能留住最為久遠的人心。
如今,土樓里的住戶大多外出務工,年輕人也都選擇去市區或縣城定居,許多房間空置了下來,紛紛租給了外來的游客。
河坑的十四座土樓各有特色,其中讓我印象最深的要數兩座連體土樓,高低有致。
登上山頂的觀景臺,再觀河坑又別有風韻。登高望去,十四座土樓隱現于山嵐之間,聚散合離。四周群山環繞,夕陽在蒼翠間鍍著金色的斑點。
我來時,許多土樓前立著一長串金色拱門。在我老家,凡紅白喜事,親戚們都會送上拱門,彰顯家族昌盛。但在土樓所見的拱門不同,上面一致寫著某某答謝,答謝者還多為同一姓氏。問過當地人才知這叫做作大福,三年一次。在一座土樓中,還意外見到了皮影戲。
觀者不多,都是些花甲老人,唱詞為漳州方言。臺前有兩個男人在對演皮影,一人五十歲上下,另一人年輕,估摸是師徒關系。中年男人邊撥弄手中的細繩邊誦著唱詞,另有一個中年女人,拿著話筒坐在幕后對唱。雖不懂大意,但聽著有韻的唱詞,賞著活潑的皮影也頗覺趣味。后來,跟土樓的人聊起,才知這皮影戲是流動演出。昨晚在云水謠已演過一場,不過云水謠的那場冷清許多,無一人駐足。我望著臺上竭力演出的師徒,又瞅了眼四周,土樓里的老人也似乎未全心聽戲。不禁令我悲涼了起來。
順裕樓離河坑不遠,整座土樓有368間房間,依山傍水,因其規模宏大而享有“土樓王”的美譽。前往順裕樓時已是傍晚,山路暗了下來,加之電動車電量不足。在去之前,我還有些許猶豫,不過最終還是冒險騎了過去。
至順裕樓,天完全暗了下來,加之無燈,視野分外模糊,并不能很好地感觸到順裕樓的恢宏。不過壯闊的氣勢在夜色中依稀可見。土樓中間是一大片空地,雜亂生著各種野草,層層房間像筍節般盤立于夜色。在粲然的星空下,織成了一張浩瀚的棋盤。
樓前有條小溪,響著銀鈴般的唱詞向前奔去。溪面兩座石樁橋,隨波光閃動著蛇形的腰肢。夜晚的石橋村頗寂,在山路間漫步,仿佛能滌除心中一切的塊壘。或許,所有的村莊都是一場隱秘的邀約,只為了等待心靈的鳴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