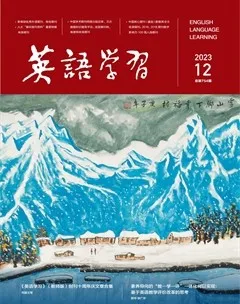后人類主義世界中的“科技病”
——評石黑一雄小說《克拉拉與太陽》*
馬坤豪 南京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張俊萍 江南大學外國語學院
引言
石黑一雄是當代日裔英國作家,曾獲得1989 年布克獎、2017 年諾貝爾文學獎、大英帝國勛章、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勛章、首屆大益文學雙年獎等多個獎項,代表作有《長日將盡》《上海孤兒》《莫失莫忘》等。《克拉拉與太陽》(KlaraandtheSun)是他的最新作品。在科技發達的時代,小說主人公AF 克拉拉(陪伴機器人)邂逅了身染“科技病”的主人喬西,并設法拯救她。正當喬西的母親克里西選擇放棄救治喬西而用機器人替代她時,克拉拉仔細觀察,不斷思考,發現可以借助太陽使喬西獲救。于是,她摧毀了庫廷斯機器,解放了太陽的力量,最終拯救了喬西。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體現了后人類主義的思想。早在20 世紀80 年代和90 年代,人們就圍繞著電子人的話題熱火朝天地討論起來,并形成了一種理解——身體是一種商品,可以通過現代技術塑化,對生物進行改造將會是未來的一種趨勢,這種態度通常是由“對人類狀況本身的厭倦”引發的(Baillie &Casey,2005)。而這種思想就像一種病一樣,企圖顛覆“肉體的人”的意義。針對這種聲音,正如哈桑(1975)所提到的,人類形態——包括人類的愿望及其各種外部表現——可能正在發生劇變,因此必須被重新審視。當人類主義進行自我轉化,并尋求與機器建立合理的聯系時,后人類主義的進程也就開始了。就理性的話題,海德格爾對曾經理性比感性高級的論調提出質疑,他認為理性(rationale)是動物也擁有的一種比較低級的精神物質(Heidegger,1977);對于“具身化”的話題,后人類的建構觀念并不要求他的主體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的電子人(cyborg),無論身體是否受到干預,認知科學和人工生命等領域出現新的模式,都必然包含著一個被稱為后人類主義生物學上依舊如故的“萬物之靈”(海勒,2017);關于人類的地位,他們主張把人當作世界中的普通一員,人類不是自然界的例外,限制人類對于世界的過分探索,去人類中心才是真正保護人類的手段(Kumm et al.,2019)。
喬西病情的溯因:理性至上的荼毒
喬西的疾病是貫穿《克拉拉與太陽》始末的重要線索,她的病是人為的“基因提升”而造成的,而它的產生正是由于人們陷入了理性主義的泥沼之中,漸漸地忽視了人的感性價值。隨著理性運動不斷帶來科學技術上的突破,有人開始認為人是一種高于動物的、有高度概括能力和推理能力的理性生物。后人類主義者們卻發出不同的聲音:人具有動物的一面,但是理性本來就存在于動物身上,所以其實理性也只能反映人的動物性,而非人性(Heidegger,1979)。文中喬西的母親克里西和喬西也為理性至上所困擾。
首先,對于克里西而言,她作為喬西的監護人,在喬西是否進行基因提升的選擇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她卻未能處理好理性與感性統一的問題。在做決定的時候,克里西為理性所裹挾,堅定地選擇了基因改造,而非從喬西的身體出發進行考量,展現母親應有的關愛。在喬西病危的時候,克里西對里克(喬西的男朋友)說,“我剛才在想啊,此時此刻你會不會感覺自己是贏家,感覺自己或許笑到了最后”(353),“她下了大注……結果輸了”(354)。即便到了喬西病入膏肓的時候,母親居然依舊把“基因提升”和“賭博”進行類比,忽視了人的生命和未來比賭桌上的籌碼重得多得多。事關女兒的性命,母愛這種崇高的感情竟不知去向,令人黯然神傷。克里西經歷過薩爾(喬西的姐姐)殞命之后,為什么沒有為了喬西的健康而停止基因提升?如果說大女兒的去世是無可避免的悲劇,有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在小女兒喬西面對基因提升的選擇之時,喪女之痛為什么沒有警示克里西?由此可見,她沒有處理好感性與理性的統一。
其次,面對全社會瘋狂吹捧的基因提升,喬西也無力做好理性與感性的統一。喬西說了自己做決定的話,她也依舊會選擇基因提升這條道路。飽受病痛摧殘之際,她的理性戰勝了名為自愛的感情。喬西借里克之口說“關于這個接受基因提升的問題……她說她會和你做出一樣的選擇”(356)。讓人吃驚的是,原本是基因提升受害者的喬西即便已經飽受病痛煎熬也依舊愿意接受基因提升,可見喬西對于自己的生命的珍愛已經完全被命名為“基因提升”的理性浪潮所打敗。人與機器最明顯的區別之一就在于人是有感情的。而如果基因提升只是打著提升人類的幌子,專注所謂的身體和腦力提升而忽略了人類最基礎的情感關懷,那么提升后的人真的會獲得幸福嗎?喬西和薩爾就是血淋淋的真相。
再次,人們忽視了理性并不具有絕對性。小說中人們堅信基因提升代表著進入一流大學和有一個更加光明的未來,并奉其為顛撲不破的真理。這不免讓人懷疑,這份理性是絕對正確的嗎?基因提升者的死亡這一鑿鑿鐵證無疑給了不少人一記耳光。基因提升者的身體健康必然是要放在考慮范圍之內的,然后結合各方面的要素(如成績提升、思想道德培育等),才能對基因提升是良方還是毒藥作出一個客觀公正的判斷。可見理性本身不具有絕對性,任何所謂理性的觀點都需要不斷的勘驗。而小說中最令人感到恐懼的是薩爾的死亡,它并沒有給基因提升問題帶來多么大的反響,即便是痛失愛女的克里西,也依舊對基因提升情有獨鐘,最終造成了喬西得病的悲劇。
總而言之,這種理性至上其實反映了以下兩個問題:其一,忽略了感性的價值,未處理好感性和理性的統一;其二,忽視了理性不具有絕對性這一事實。文中克里西和喬西本人都沒有處理好以上兩個問題,他們對于喬西的基因提升都負有責任。若“理性至上”思想的頑疾無法根除,喬西的悲劇會在任何人的身上發生。
喬西病情的應對:科技建構中“具身化”的思考
喬西之病源于基因提升技術,因而治病也必然離不開科技。在科技高度發達的后人類主義世界里,人的身體結構可以為機器所改造,人的主體性也隨之產生動搖。對于人的身體能否被技術改造,小說中的人們認為可以利用它來重塑人類的狀況,克服人類的生理限制,使那些想成為“后人類”的人成為可能。至于工具是自然的還是非自然的則完全無關緊要。小說中,人們就是否采用機器替代喬西的肉身展開了激烈討論,最終喬西身邊出現了三種聲音。
首先出場的是人文主義的守衛者,他們人數眾多,主張守衛“具身化”,反對將精神置于肉體之上,承認并贊揚“肉體的有限性是人類存在的一種狀態”,認為人的生命深植于極為復雜的物質世界,絕對不能用機器取代肉體的存在。其代表是梅拉尼婭管家、里克以及里克的母親海倫。這些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肉體的喬西為中心,對最新的技術持排斥的態度。他們最初都對克拉拉懷有明顯的敵意,謹慎地提防克里西會用機器人取代喬西。
當梅拉尼婭剛出場的時候,她會沖著身邊的克拉拉吼叫:“AF,別再跟著我了,走開!”(61)最初,讀者可能對于她這種沒來由的火氣感到困惑,漸漸便會發現她的所有行為都是想保護那個正在逝去的千金小姐,并提防著克拉拉取代喬西,她是喬西的守護者。當克里西想帶喬西去見卡帕爾迪的時候,梅拉尼婭害怕克里西會用機器人來取代喬西,所以著急地對克拉拉說道:“AF,你看緊了……不然喬西小姐會出大事。”(221)由于陪同喬西去見卡帕爾迪的請求遭拒絕,她擔憂地喊道:“我想和喬西小姐一起去,太太說沒門。她要帶AF。真搞不懂……你盡全力,AF。我倆一伙的。”(221)她守衛著的是有血有肉的喬西,是“具身化”的喬西,而非擁有喬西容貌的某種物件。
里克是喬西的童年玩伴和戀愛對象,他十分害怕克拉拉會取代喬西,因為那將不再是那個與他相伴至今的女朋友了,所以他說:“可惜(克拉拉的)許多事情都會妨礙(喬西與里克的)友誼。”(77)他清楚地認識到友誼或者他與喬西的愛情是具體的,是肉身的愛情,他所愛的絕非一個冰冷的空殼。
海倫并沒有直接說要守護喬西的“具身化”,但是當談及薩爾的機器人替代品時,她形容機器人是“看上去像薩爾”;而當里克說海倫把機器人認作薩爾的時候,她則會正色反駁:“薩爾去世了,那是一場巨大的悲劇,我們不會拿愚蠢的玩笑玷污她留給我們的記憶。”(186)通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相信,對于用機器人取代喬西一事,海倫肯定也會采取反對態度。值得一提的是,海倫和兒子里克都被人視為“英國人”,一方面是由于口音的特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是“精神上的共同體”(周麗秋,2021),即都具備保守的性格特點,象征著他們是傳統的人權捍衛者。
喬西身邊傳統的人文主義守衛者強烈地反對用機器人取代活人的反“具身化”思潮,但,也只能止步于此。對于機器人和科學技術的抗拒,使得他們在喬西身邊扮演的更像是一個守護者而并非解救者的角色。
對待技術的第二種態度來自技術狂熱者的堅實擁躉。克里西和卡帕爾迪先生是反對“具身化”的代表人物。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發現科技能代替人完成很多事情。因此有人認為只要能維持人類的行為和活動,機器人也可以代替人類存在。“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這種行為是對于人性(human nature)的踐踏,‘人不再為人’(cease to be human )”(法蘭多,2019:14)。克里西產生用機器人替代喬西的念頭至少有三次表現。第一次,喬西要購買克拉拉作為自己的AF 時,克里西要求克拉拉回憶喬西的長相和動作,最后的測試則是要求克拉拉模仿喬西的走路方式(20)。初讀時,人們可能會誤以為是主人在測試自己家機器的性能,而隨著小說的推進,一個用機器人替代喬西的伏筆就此埋下。第二次,喬西病勢加重,但是克里西沒有選擇陪伴在喬西的身邊,而是讓克拉拉陪她一起去看瀑布。在這場旅行中,克里西甚至要求與克拉拉進行親子間的互動,要求克拉拉模仿喬西陪伴著自己(131—133)。第三次,則是克里西帶著克拉拉去見卡帕爾迪,去實行把克拉拉“變成”喬西的計劃。她的用意通過卡帕爾迪之口和盤托出:“我們不僅僅是要求你(克拉拉)模仿喬西的外在行為。我們還請你延續她,為了克里西,為了所有愛喬西的人。”“這真的就會是喬西。是喬西的延續。”(261)
卡帕爾迪先生是堅定的反“具身化”的人。作為一個科學狂人,他企圖通過克拉拉對于喬西的模仿和認知,把這些記憶凝聚在一個芯片之中,再植入一個和喬西相似的機器人的體內,使得喬西獲得“重生”。卡帕爾迪并不是喬西的親人,所以他更多地會從科學技術層面而非親情層面思考問題。卡帕爾迪幫助克里西更多是出于實驗的需求,他已經徹底分不清現在有血有肉的喬西和那個軀體冰冷的機器人有什么區別了。通過克里西和海倫,我們得知薩爾的機器人取代計劃失敗了。薩爾的機器人瘋狂地想逃跑,而克里西只能抱著那個冰冷的被她認為是女兒的機械生物。可見反“具身化”從技術層面上本身就是不可行的,更何況不管是克里西還是卡帕爾迪都忽視了喬西本人的意志,這是對倫理道德的蔑視。
卡帕爾迪和克里西都是反“具身化”的主要人員,他們相信只要意識和行為長存,肉體就可以被機械所取代。因此,他們才會說未完成的機器人是喬西的延續。他們針對喬西病癥的方法只有一條,就是用機器人的軀殼取代喬西的肉體,讓她以機器人的形式生活著。但是,如果深入剖析的話就會發現,這與其說是治療,倒不如說是放棄,是逃避喬西病情惡化的事實,是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放棄了重病中的喬西。他們的行為不僅僅踐踏了人權和倫理,而且具有非常惡劣的社會影響。
最后一類人,便是喬西真正的救星——克拉拉與保羅(喬西的父親)。他們都是后人類主義的信奉者。后人類主義指的是將人文主義的價值與其各種非人文的“他者”(機器)相結合。在西方的思想路線中,后人文主義標志著人文主義和反人文主義(反“具身化”)對立的結束,追溯了一個不同的話語框架,更肯定地尋求新的選擇。即,后人類主義是對于人文主義的繼承,如果人類可以無所顧忌地用機器的軀殼代替肉體,那是觸犯了人文主義的底線,是在打著以人為本的幌子褻瀆人類的尊嚴與身份。
克拉拉知道后人類主義是對人文主義的繼承而非背叛。克拉拉多次嘗試救助喬西,而這里的喬西是肉體的喬西。“我不介意損失了寶貴的液體。我情愿獻出更多,獻出全部,只要那意味著您會給喬西提供特殊的幫助”(345—346)。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克拉拉為了救助主人愿意奉獻上自己的生命。救助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為了喬西的徹底康復,而非用機器人替代喬西這種反人類的方式。
此外,克拉拉也意識到高科技世界中人類與自然環境的不平衡問題。小說巧妙地設計了克拉拉驚人的觀察能力。剛開始,她就敏銳地發現了陽光是機器人能量的來源這個設定(4)。緊接著她就觀察到一個流浪漢和一條狗在晚上奄奄一息,卻又在陽光沐浴下重獲新生,由此開始揣測是否太陽對人類也具有療愈作用。而在喬西病情不見好轉的時候,她去了太陽落下的谷倉,在那里祈求太陽來救治喬西,并通過分析得出陽光的明亮度可能與庫廷斯機器的污染有關的結論(300)。于是,為了拯救喬西,克拉拉設法與太陽達成契約,以摧毀庫廷斯機器為代價來拯救喬西。在喬西危在旦夕之際,太陽照射到喬西的床前,喬西獲救了。科技發展到極致的誤區就是人類以為憑借科技可以為所欲為,什么問題都能解決,但是卻從未反思過,在生產力條件低下的從前曾經多少次受到大自然的庇護。而陽光正是最具代表性的自然之物。克拉拉去向太陽求助也反映了去人類中心化的含義,即人類首先處于一個存在的環境中,只有回歸于存在,傾聽存在,人的本質才會本質性的發生(肖建華,2019)。
克拉拉意識到污染的機器才是萬惡之源。庫廷斯“先是發出一聲尖利的嗚鳴”,緊接著“三根短煙囪從它的頂篷里伸了出來,濃煙開始從那里面滾滾而出”。按照這種情況,人們應該采取一些措施。然而,“第二天,還有第三天,庫廷斯機器依舊沒完沒了,白晝幾乎變成了黑夜。”(37)這段文字象征著人們已經迷失在機器提供的便捷之中,卻忘記了它會給自然環境和人類自身帶來多少潛在危險。這也反映出喬西和薩爾因為基因提升得病,而克里西等人從未把問題反思到人類自身之上。
保羅的設定非常有趣。首先,他曾經是王牌科學家,對機器的運行甚至是破壞都有著極為準確的把控。在破壞庫廷斯機器的時候,保羅提供了技術支持,準確地提出用機油來破壞這一方法。
其次,保羅更是個堅定的人文主義者。當保羅還在從事科研工作的時候,他并沒有足夠的時間顧全自己的家庭,以致最后離婚。而失業在使他失去光鮮工作的同時,又使得他的人性逐漸回歸,他開始關注自己的女兒。所以他會說:“被替代使我得以用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世界,我真心相信這幫助我分清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241)。他也懷疑可能女兒可以被取代,但是他絕對不會允許這種事發生。也許就是從他失業的那一刻開始,他就堅定地站在維護“具身化”的喬西這邊。當克里西試圖把喬西留在實驗室以獲取更多數據的時候,保羅說:“喬西,我們現在就走。相信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257)這反映了保羅對于克拉拉變成喬西的實驗毫無興趣,堅定地守衛著“具身化”的喬西,因而保羅會成為幫助克拉拉破壞庫廷斯機器的重要幫手。
最后,保羅可以與克拉拉共情,他會思考并執行克拉拉的建議。當克拉拉口頭上說“對機器搞破壞”可以拯救喬西的生命,而又沒有辦法給出解釋的時候,保羅沉穩地回答道:“那我們至少就試一回吧。”(278)通過這一細節,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開明的保羅,他沒有擺出一個專業工程師和人類的傲慢,而是試著與克拉拉合作,最后利用P-E-G 9 溶液的成分摧毀了庫廷斯機器,并且也間接拯救了喬西。
總而言之,只有克拉拉和保羅真正地把握住了后人類主義的精髓。人們既需要認識和運用機器,同時也需要守住人類身份的底線,守住“具身化”。顯然克拉拉與保羅是對的。首先他們堅定了救治病重的喬西這個目標,而不是放棄她。其次,克拉拉借助陽光的力量,與保羅合力摧毀了萬惡之源庫廷斯機器,拯救了喬西。
通過以上三類人的三種選擇,我們發現救助喬西,其實就是人們面對技術建構困局所作出的三種選擇。有的人是頑固派,他們選擇守衛傳統的人文主義,排斥新技術。盡管他們能夠守住為人的底線,但在面對科技瘋狂的威脅時卻茫然無措。第二類人是反“具身化”的狂熱分子。這類人相信“人不是獨一無二的東西”,因此肉身可以被任意替代,其結果自然是倫理遭踐踏,人類的一切價值也被解構,機器人替代人類。而第三種就是后人類主義思想的探索者,他們學習、了解機器,并且本著以人為本的初心,更好地應對各種各樣的挑戰,適合在科技發達的后人類主義世界生存。
喬西治愈后的余波:后人類主義世界的隱憂
在小說結尾,喬西恢復了正常人的生活,看似皆大歡喜,其實危機重重。在喬西重獲健康之時,三重隱憂也被悄悄地埋在了這個后人類主義世界。
第一,“科技病”一旦出現,便極難治愈。喬西的治療離不開機器人克拉拉——一個熱愛自己的主人而且具有出眾觀察能力的機器人,以及保羅——一個精通機器的父親。只有二者通力合作才能成功治愈喬西。因此,喬西只是幸運的特例而已,更多的基因提升病者只能像薩爾一樣等待死亡。
第二,喬西的治愈并未改變AF 機器人和基因提升加劇社會貧富差距的事實。小說中,當一個小男孩(羨慕想要機器人)可憐兮兮地看著克拉拉時,經理說道:“如果有時候一個孩子用奇怪的眼神看著你,帶著怨恨或悲傷……一個那樣的孩子,沒有AF,一定會非常孤獨的。”(13)AF 機器人作為陪伴孩子成長的最新產品,無法面向所有的孩子,只有少數家境優越的人才能獲得。小說中有的貴婦還在饒有興致地糾結選擇B2 還是B3,而窮人的孩子卻連擁有一臺AF 的資格都沒有。這在無形之中給予富人優越感的同時,也給窮人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然而,技術不僅給窮人帶來精神上的痛苦,也堵塞了他們通過奮斗致富的道路。里克作為喬西的戀人正是這個時代的受害者。他既沒有接受基因提升,也沒擁有自己的AF,他的求學之路注定坎坷崎嶇。首先,進入阿特拉斯·布魯金斯大學,參加TWE(升學培訓班)是必經之路,而成為TWE 的學員必須至少滿足兩個條件之一:要么接受過基因提升,要么付一大筆錢。但是,這簡直是一個“第22 條軍規”,基因提升歷來就是被富人壟斷的特權。因此,基因提升直接封鎖了窮人通往頂級學府的道路。而里克如果想要進一步學習,就只能和其他未提升的學生爭取百分之二的名額,不然就得成為一輩子的“下等人”。
里克的母親海倫為他購買了(來自上一個時代的)“最好的教科書”,但這些書全都默認孩子的身邊蹲守著一個導師之類的角色。這又間接導致“當他(里克)遇到一些他不理解的東西,而身邊又沒人跟他解釋的時候,他就會灰心”(190)。因此,海倫才會請求克拉拉指點里克的學習。
里克的結局也非常現實,他沒有選擇進入阿特拉斯·布魯金斯大學,而是嘗試尋找一條新的道路。無疑,里克是不幸的,在一個機器主導的社會,他很難通過大學爬到社會頂端,實現階級躍遷;而他又是幸運的,他在物理、工程類的領域很有潛力。可是,更多的基因未提升者資質平平,沒有天賦。沒有基因提升,也沒有AF 機器人,他們比里克更加絕望。
第三,喬西的治愈并未引起人們對機器人的足夠反思。隨著機器人走入千家萬戶,“人與機器的反交流—交流”必然是人工智能時代中很長時間內的交流模式(陳昕,2020)。在喬西得救之后,克拉拉被克里西捧成了英雄,而沉浸在女兒康復喜悅中的克里西竟然說克拉拉理應(像人一樣)得享善終,慢慢凋零,她終究是把克拉拉當成人了。而卡帕爾迪也并未因此放棄他的機器人替身計劃。他在喬西康復后,表示想尋求克拉拉作為志愿者繼續他的實驗。可見,喬西是活了,但反“具身化”思潮并沒有消亡,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關于如何對待機器人,恰恰是生病的喬西給了我們一些啟示。在喬西與里克拌嘴時,克拉拉提議讓自己代替里克玩“泡泡游戲”(填字游戲),但是喬西卻回道:“我說,這行不通的。我不介意你旁聽。可你說什么也替代不了里克的。門也沒有。”(165)言下之意,這是只屬于里克和喬西的游戲,即便克拉拉比里克更加能體察喬西的心意也不行。
在喬西晚上做到自己死亡的噩夢時,喬西也想要母親的擁抱,而非克拉拉的擁抱。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喬西清楚“泡泡游戲”代表著情侶間的調情,想得到母親的擁抱更是她對母愛的渴望,而這些絕非機器人能夠替代。喬西在病重時讓里克轉述了她的話:“無論發生了什么,她都愛你(克里西),永遠愛你,她非常感謝你能做她的母親,她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換一個母親,一次都沒有。”(225)喬西理解后人類主義世界的意識(精神)包括感覺,情感,記憶和其他精神狀態,而這一切都需要借助具體的身體傳達出來(Pepperell,2003)。喬西認為肉體是邊界,對待機器人可以友善,但是友情、愛情是人類的特權,絕不容機器人染指。
總之,喬西的“科技病”順利治愈,讓我們看到了三重隱憂。其一,“科技病”的治療將難如登山;其二,科技的發展將會加劇貧富階層之間的撕裂;其三,對待機器人的態度將會成為一個需要長期探究的命題。
結語
無論是理性主義的瘋狂,或是反具身化的巨浪,又或是后人類主義世界的隱憂,都是過度的人類中心主義在背后操縱著一切。即,人類可以主宰世間萬物的一切。然而,我們不是在克服現代性的局限適應力,而只是擴大了現代主義控制的幻想,因為它忽視了社會和生態的運轉自有它獨特的規律(Wakefield et al.2022)。“科技病”恰恰就是過度人類中心主義造就的惡果。
首先,理性至上反映了人類企圖主宰情欲,是人類對自古以來所積累的知識和經驗的一種執念。其次,“反具身化” 反映了人類主宰身體,堅信可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改變自己的身體,反抗大自然的約束。最后,人類嘗試左右后人類主義世界的方方面面:在主宰世界并利用機器創造科技產品的同時,也創造了更棘手的病毒;利用機器主宰人的上升通道,加劇貧富差距;創造機器人并自發地用它來取代人類自身,而不考慮這一舉動將會對人類種族造成怎樣的惡果。因此,去除過度的人類中心化是當今世界不可回避的問題。
小說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科學技術發展的同時,應該防微杜漸,時刻警惕過度的人類中心主義,只有這樣,在步入后人類主義時代時才能做到心中有一道防線。“個體要立足當下,選擇性‘遺忘’(過去的成就),從而進入建構新的身份”(劉杰,2020)。筆者認為,人們要防止過度的理性主義,認識到反具身化絕非是拯救人類苦痛的良藥,后人類主義世界也有其自身的運轉規律,而絕非人類自己可以隨意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