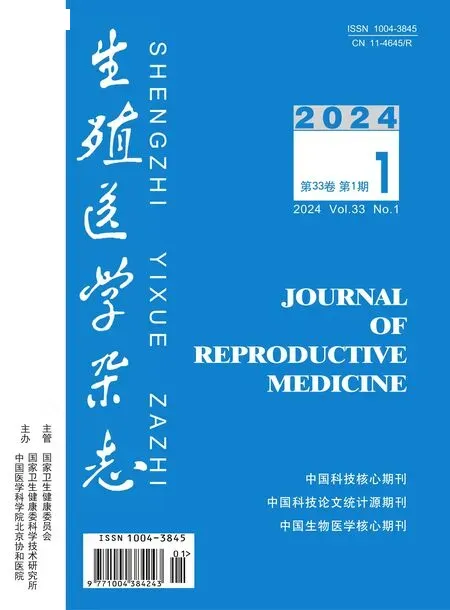子宮巨大未分化多形性肉瘤1例報道并文獻復習
王黎,姚志強,楊永秀*
(1.蘭州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蘭州 730000;2.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蘭州 730000)
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ndifferentiated polymorphic sarcoma,UPS)是一種來源于間葉細胞的高級別肉瘤,好發于中老年人的四肢等部位,無特征性臨床表現,臨床上易誤診誤治。近期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婦科收治了1例子宮巨大UPS患者,腫物位于子宮左側宮角處,大小約30 cm×25 cm×10 cm,極其罕見,術前未能充分利用影像學檢查及穿刺病理組織活檢來明確腫瘤性質,手術完整切除腫塊、子宮、雙側附件及大網膜,術后病理組織學檢查診斷為UPS。本文整理該病例的診斷、治療和預后資料并復習相關文獻,以加強臨床上對該腫瘤的認知,減少誤診,改善預后。
一、病例資料
患者,53歲,女,已婚,自然絕經6年,因“下腹部增大伴腹痛、腹脹4月余”于2021年12月16日收入我院。
患者自訴于入院4月前發現下腹部增大,伴腹痛、腹脹。于入院3 d前就診于隴南市宕昌縣中醫院,行腹部計算機斷層掃描(CT)提示:(1)腹水;(2)盆腔積液;(3)盆腔巨大腫塊影。行婦科超聲提示:(1)腹腔內巨大混合回聲包塊;(2)腹水(大量)。我院婦科以“(1)盆腔腫物(性質待查);(2)腹水;(3)盆腔積液”收住院。
發病以來體重減輕7.5 kg。入院后完善相關檢查,檢測腫瘤標志物提示:糖類抗原125(CA125)64.6 U/ml、甲胎蛋白(AFP)3.6 U/ml、癌胚抗原(CEA)0.7 ng/ml、糖類抗原199(CA199)14.3 U/ml、人附睪蛋白4(HE4)63.5 pmol/L。婦科超聲檢查提示:(1)盆腹腔巨大囊實性占位(上界達劍突下,下界至盆腔,左側至腋后線,右側至腋中線,內見無回聲及低回聲區,其內部可見血流信號);(2)盆腔積液(約27 mm)。婦科檢查示:外陰發育正常,已婚已產型,陰道暢;宮頸光滑,無舉痛及搖擺痛;子宮前位,正常大小,形態規則;腹部膨隆,如孕5月,有壓痛。
患者于2021年12月17日行經腹左側宮角巨大腫瘤切除術+大網膜切除術+全子宮切除術+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術。術中探查可見腫物呈實性,表面凹凸不平,質脆活動度差,與腹膜粘連;鈍性分離腹膜后探查腫塊上界至肝緣下,且與肝臟有粘連帶,胃部、脾區整個被腫塊占據,兩側至側腹壁髂血管水平以下,下界至盆底道格拉斯窩。取部分腫塊送術中冰凍病理檢查。延長切口,鈍性分離腫塊,見巨大腫物在左側宮角處有約3 cm的蒂部與子宮相連,鉗夾、切斷蒂部,縫扎宮角部。腫塊大小約30 cm×25 cm×10 cm(圖1)。術中冰凍病理結果回報:腹腔腫物形態學支持惡性病變。后行全子宮切除術+雙側卵巢輸卵管切除術。
術后病理檢查診斷報告:(1)肉眼所見:①腹腔腫物(術中冰凍):灰白灰紅色不規則組織2塊,大小6 cm×5 cm×1.5 cm,切面呈灰黃灰紅色,呈魚肉狀;②灰黃間灰紅色不規則腫物2塊,總體積24 cm×22 cm×8 cm,切面呈灰白灰黃灰紅色,部分區域囊性變,部分區域呈膠凍樣,質韌。(2)鏡下所見:瘤細胞圓形或卵圓形,胞漿豐富,嗜酸,核淡染,可見核仁,其間可見巨核、多核瘤巨細胞,核分裂像常見,呈彌漫片狀排列,部分區域瘤組織出血、壞死(圖2)。免疫組化染色示:HMB-45(個別細胞+)、CD117(局灶+)、CD34(血管+)、CD99(-)、CDK4(局灶+)、CK(Pan)(個別細胞+)、CR(-)、Desmin(局灶+)、DOGI(局灶+)、ER(-)、Inhibin α(-)、Ki-67(70%)、MDM2(-)、Melan A(-)、MyoD1(-)、Myogenin(-)、p53(70%)、PR(-)、S100(-)、SMA(局灶+)、SOX-10(-)、STAT6(-)、TLE1(局灶+)、Vimentin(+)、WT-1(-)。(3)病理診斷:間葉源性惡性腫瘤,結合形態學及免疫組化結果,考慮UPS。
術后轉入重癥醫學科治療,生命體征平穩后轉入婦科給予對癥支持治療,一般情況好轉后出院。

圖1 子宮巨大UPS大體標本

A:圖中可見瘤細胞呈圓形或卵圓形;B:圖中還可見部分區域瘤組織出血、壞死。圖2 巨大UPS鏡下特點(HE染色 ×100)
患者及家屬拒絕術后放療,后給予多柔比星脂質體60 mg靜脈化療6次,化療過程順利。2022年5月25日行盆腔磁共振成像(MRI)檢查提示:右下腹多房囊性腫物(圖3A)。5月27日復查腹部CT提示:右側腹、盆腔多房囊性腫物(約6.2 cm×5.0 cm),惡性病變不除外(圖4A)。6月19日復查婦科超聲提示:(1)盆腔囊性占位;(2)腹水。穿刺抽液后盆腔包塊明顯變小,行腹水脫落細胞學檢查提示未找到異性細胞,胸部CT未見明顯異常,遂出院隨訪。2022年9月19日再次復查腹部CT提示:(1)新增右側腹腔及腹膜多發條片及結節狀異常強化灶,考慮轉移;(2)右側腹、盆腔多房囊性腫物較前增大(圖4B)。9月26日再次復查盆腔MRI提示:腹、盆腔多房囊性占位,病灶較前略增大,其內新增少量出血(圖3B)。綜上考慮腫瘤復發,與患者及家屬充分溝通病情后患者及其家屬決定行靶向治療,方案為每日口服1粒鹽酸安羅替尼膠囊,連服兩周,停藥1周,周期進行。隨訪至今,患者訴下腹痛逐漸加重,與患者及家屬再次溝通病情后患者及家屬選擇繼續口服靶向藥物。
二、討論
UPS過去被稱之為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Malignant fibrous histiocytoma,MFH),是一種來源于間葉細胞的高級別肉瘤。最早于1963年由Ozzello等[1]提出。1978年,Weiss等[2]通過分析200例MFH患者的病理資料,將MFH分為4種組織學亞型:巨細胞型、黏液樣型、梭形細胞型和炎癥型。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MFH與UPS相似,并將其分為3個亞型(巨細胞型、多形性型和炎癥型),后續在此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更新[3]。2013年,第4版WHO骨與軟組織腫瘤分類中將MFH刪除,并將其命名為UPS,歸類于未分化/未分類軟組織肉瘤,這是一類沒有明確分化方向的異質性腫瘤,在病理學上是一個排他性的診斷[4]。目前尚未明確UPS的發病誘因,其發病率占軟組織腫瘤的30%以上,常見于中老年人,主要集中在50~60歲,且男性發病率是女性的2~3倍。UPS最常見的發病部位是下肢,約占49%;其次是上肢,約占19%;腹膜和腹腔約占16%;其他部位較罕見[5]。其病變組織主要位于深部的肌肉和筋膜,少數位于皮下組織[6]。

A:術后5個月盆腔MRI(T2W1)圖像,箭頭示右下腹多房囊性腫物;B:術后9個月盆腔MRI(T2W1)圖像,箭頭示腹、盆腔多房囊性占位,病灶較前增大。圖3 術后盆腔MRI圖像

A:術后5個月腹部CT檢查圖像,箭頭示右側腹、盆腔多房囊性腫物;B:術后9個月腹部CT檢查圖像,箭頭示右側腹、盆腔多房囊性腫物,病灶較前增大。圖4 術后腹部CT檢查圖像
UPS的診斷需參考臨床表現及影像學檢查,術前穿刺活檢在明確診斷方面也具有一定意義,但其診斷的“金標準”仍是術后病理組織學檢查。UPS的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大多數患者因體表腫塊、疼痛及壓迫癥狀而就診[7]。實驗室檢查缺乏特異性,通常腫瘤標志物無明顯異常,但有文獻報道炎癥型UPS可能出現白細胞升高或類白血病反應[8]。影像學檢查對UPS的診斷具有輔助作用。超聲檢查下,大部分UPS呈不規則形狀,內部多為低回聲,腫瘤內部和周邊可見數量不等的彩色血流信號[9];盡管超聲表現缺乏特征性,但可以初步確定腫瘤的大小、形態及與周圍組織的關系。UPS在CT檢查中的表現因腫瘤部位而異,但大多形態上呈卵圓形、不規則形或分葉形,平掃呈低密度,鈣化很少見,邊界不清;增強后呈多樣性強化,可能與腫瘤內血管成分、纖維成分及壞死程度有關[10]。總的來說,CT檢查對于UPS具有良好的定位效果。相較于CT,MRI具有更高的軟組織分辨率,且可以進行多方位成像,因此在顯示UPS病變范圍、腫瘤成分、有無周圍組織浸潤方面更具優勢[11],還可以更好地為手術方案的制定及術后復發情況的評估提供依據。UPS在T1W1上多呈等信號,如病灶合并壞死則表現為低信號,合并出血則表現為高信號;在T2W1上表現為低、等、高混雜信號[12]。
UPS的大體組織多表現為孤立或分葉狀的魚肉樣腫物,切面多為灰色或白色。顯微鏡下,常觀察到由呈束狀或席紋狀排列的梭形細胞和多形性細胞混合而成的瘤組織,其特征表現為多形性區域出現大量染色質豐富、核不規則的多核巨細胞[13],瘤細胞中常見病理性核分裂象;間質中富含血管和膠原纖維,可有炎癥細胞浸潤。UPS的免疫組化標記物沒有特異性,但在多數病例中可見Vimentin、CK、CD68、EMA表達。Al-Agha等[14]認為UPS僅對Vimentin表現出彌散且較強的免疫反應,Vimentin(+)對診斷UPS具有重要意義。
UPS的鑒別診斷包括多形性脂肪肉瘤、多形性平滑肌肉瘤、多形性橫紋肌肉瘤、黏液纖維肉瘤和惡性黑色素瘤等其他間葉源性腫瘤[13]。本例患者腫瘤發病部位為子宮宮角處,且腫塊巨大,約30 cm×25 cm×10 cm大小,臨床上極其罕見,容易誤診誤治,術前需與卵巢良惡性腫瘤、輸卵管惡性腫瘤、消化道腫瘤等鑒別。其臨床表現、影像學檢查、病理特征與文獻中的描述大致符合,但術前未進一步行MRI及穿刺病理組織活檢來明確腫瘤性質,導致術前并未制定合適的治療方案,這是在以后的臨床診療工作中需要改正的地方。
UPS患者的主要治療目標是提高生存率、降低復發率,并最大限度地保留功能,提高生活質量。目前,UPS的首選治療方式是手術治療,手術原則是完整切除腫瘤及腫瘤周圍1 cm的正常組織,并確保切緣為陰性[15]。此外,UPS淋巴轉移的風險并不高,術中是否需要清掃淋巴結因個體而異。大部分學者認為放療可以減少UPS的復發及轉移[16]。然而,放療的時機目前仍存在爭議,一些學者發現,在術后進行放療的UPS患者,10年無復發生存率為62%,總體生存率為80%[17]。其他學者則提出相較于術后放療,術前放療者復發率更低、總生存率更高[18]。而Peiper等[19]認為術前放療+手術+術后放療在UPS這類高級別肉瘤中具有顯著效果,可縮小腫瘤范圍并降低術后復發率。化療是否能作為治療UPS的一種重要方式,目前也存在爭議。常用的術后化療藥物包括多柔比星和異環磷酰胺[20],一些研究發現,多柔比星和異環磷酰胺的聯合應用可顯著提高患者的總生存率[21],但也有研究指出化療可能增加患者的病死率[22]。隨著靶向藥物及免疫檢查點抑制劑(PD-1、PDL-1抑制劑)的快速發展,它們也逐漸被應用于軟組織肉瘤的治療中。目前尚無指南推薦用于治療UPS的靶向藥物,但臨床上已有一些靶向藥物投入使用,如派母單抗、貝伐單抗、安羅替尼等。一項研究通過對86例UPS患者進行二期臨床試驗,得出派母單抗對UPS有效的結論[23]。因此,靶向治療與免疫治療有望成為晚期UPS患者的最佳治療方案。本例患者以手術治療為主,術前及術后均未行放療,手術完整切除了腫塊、子宮、雙側附件和大網膜,但未切除腫瘤周圍其它正常組織,也未清掃淋巴結。術后未行基因檢測,給予多柔比星化療6次,未采用多柔比星聯合異環磷酰胺的化療方案。術后9個月考慮復發,口服安羅替尼行靶向治療至今。
總體來說,UPS惡性程度高,術后易復發,預后較差。影響預后的因素包括腫瘤部位、大小、浸潤深度、分化程度、腫瘤切除是否徹底以及是否發生遠處轉移等[24]。其遠處轉移最常見的部位是肺,其次是骨、肝等,所以建議UPS患者術后定期行胸部CT檢查,以評估是否發生肺部轉移。國外一項研究顯示UPS患者復發率高達50%,5年生存率僅有14%[25]。有學者提出UPS患者腫瘤越大(直徑>5 cm)、位置越深,預后越差[26]。另外有研究表明不同部位的UPS,患者的總生存率也有所差異,例如軀干和四肢UPS患者的5年總生存率約為77%,而頭頸部患者的5年總生存率僅為48%[24]。本例患者術后9個月考慮腫瘤復發,隨訪至今,患者訴下腹痛逐漸加重,選擇繼續口服靶向藥物,后續仍會定期隨訪。
綜上,UPS好發于中老年人的四肢等部位,因其無特征性臨床癥狀,臨床上容易誤診誤治,需要與其它疾病仔細鑒別。超聲、CT、MRI等影像學檢查在術前診斷中具有重要意義,但術后病理組織學檢查仍是診斷UPS的“金標準”。其治療方式以手術治療為主,放療、化療等其他治療為輔,但術后易復發,預后較差,需嚴密隨訪。本例患者術后僅9個月復發的可能原因包括:(1)術前腫瘤巨大,約30 cm×25 cm×10 cm;(2)術前未能完善相關輔助檢查;(3)術中未切除腫瘤周圍其它正常組織,也未清掃淋巴結;(4)術前及術后均未行放療;(5)術后未行基因檢測來指導后續治療;(6)術后未采用多柔比星聯合異環磷酰胺的化療方案,僅給予多比柔星單藥治療。本文通過報告本例患者的診治及預后情況,為加強臨床上對該腫瘤的認知、吸取經驗教訓、減少誤診及制定最佳的治療方案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和參考,以期改善此類患者的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