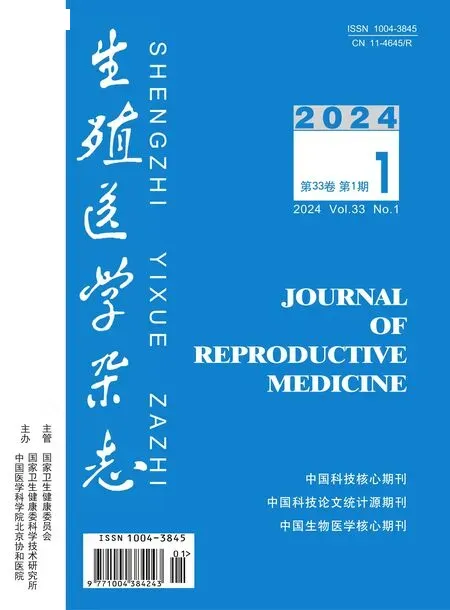子宮內膜癌逆轉伴難治性薄型子宮內膜患者IVF成功妊娠1例
熊巍,王含必,鄧成艷,郁琦
(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北京協和醫院婦科內分泌與生殖中心,國家婦產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一、病例資料
患者女性,32歲,G1P0,初潮起月經不規律,7 d/1~6個月,量中,痛經(-),未規范診治。患者于2012年結婚,由于存在排卵障礙,婚后未避孕未孕6年,于2018年就診于北京協和醫院生殖中心。
2014年因“異常子宮出血”于當地醫院行宮腔鏡檢查+診刮術,術后病理提示子宮內膜非典型增生,予以高效孕激素及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治療2年。2016年9月復查宮腔鏡,病理提示高分化子宮內膜樣腺癌,此后予以口服甲羥孕酮、GnRH-a、曼月樂環治療。2017年8月于北京協和醫院查進行宮腔鏡檢查+更換曼月樂環治療,病理提示“部分子宮內膜退縮不全伴中度子宮內膜非典型增生”。
為保存腫瘤患者生育力,盡快完成妊娠,建議輔助生育治療。患者于2018年5月就診于北京協和醫院生殖中心,男方精液檢查無異常,患者子宮輸卵管造影未見異常,擬行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由于患者治療后子宮內膜仍存在非典型增生,故采用放置曼月樂環同時行控制性卵巢刺激(COS)方案,共凍存囊胚5枚。
2018年8月于我院行宮腔鏡診刮+取環,病理提示子宮內膜組織大部分退縮成管狀、間質蛻膜樣變。考慮內膜病變逆轉。遂行凍融胚胎移植(FET),先后人工周期準備內膜4次,其中因內膜薄(內膜厚度5.1~5.9 mm)取消移植2次,移植失敗1次(內膜厚度6.7 mm),HCG陽性1次(內膜厚度7.1 mm)。2019年8月再次COS治療后新鮮胚胎移植(內膜厚度10.2 mm)1次成功持續妊娠,但孕26周時,發生重度子癇前期于外院急診剖宮產,新生兒33 d夭折。2021年4月再次行FET,因既往內膜薄,嘗試大劑量雌激素,如口服戊酸雌二醇片(補佳樂,拜耳醫藥,德國)5 mg/次,3次/d,以及雌二醇/雌二醇地屈孕酮(芬嗎通2/10,蘇威制藥,荷蘭)紅片 1片,2次/d陰道上藥,刺激內膜生長,用藥20 d超聲監測內膜厚度僅6.1 mm,取消周期。
2021年9月行宮腔鏡檢查提示輕至中度宮腔粘連,行宮腔粘連分離術。術后給予大劑量雌激素治療后,監測內膜依然菲薄。2021年12月再次復查宮腔鏡,術中見子宮下段兩側壁內聚,可見纖維束樣粘連,子宮內膜薄。放置COOK球囊支撐宮腔,術后1個月取出COOK球囊,同時行自體血小板灌注治療1次。
2022年3月再次行FET,按之前的大劑量雌激素方案刺激內膜,兩個移植周期內膜最厚處6.6 mm,因內膜薄取消周期。2022年9月至2022年10月,患者使用盆底仿生電刺激治療兩個周期,內膜下血流阻力改善,盆底電刺激期間內膜厚度增至8 mm,行人工周期FET(人工周期胚胎移植前內膜厚度8.3 mm),但移植后未孕。
2023年5月采用注射用高純度人尿促性素(HMG;賀美奇,輝凌制藥,德國)75 U促排卵周期準備內膜,注射重組人絨促性素(HCG;艾澤,默克雪蘭諾,德國)250 μg進行扳機后,周期第15天順利排卵,扳機日內膜厚度5.6 mm,排卵日內膜厚度為4.9 mm,內膜厚度仍不符合移植條件,臨床醫生曾一度想放棄本周期。但考慮到患者為子宮內膜癌逆轉,應盡快完成生育,加之既往多次因薄型子宮內膜取消周期使治療周期延長,本次患者治療后盡管排卵當日內膜仍薄,但是超聲提示內膜血流改善,內膜形態B型,與患者充分溝通,繼續觀察至排卵后第5天,內膜增至7.7 mm,遂行胚胎移植。移植7 d查血清HCG 32.06 U/L,繼續黃體支持治療至9周停藥。現患者孕20+3周,胎兒發育良好,產科定期隨診中。
二、討論
在輔助生殖技術中,薄型子宮內膜是生殖醫學領域最棘手的難題之一。子宮內膜的厚度與子宮內膜的容受性密切相關。薄型子宮內膜周期取消率高,胚胎種植率和臨床妊娠率明顯降低,流產率增加,被認為是妊娠失敗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1]。本病例是一個子宮內膜癌逆轉后發生宮腔粘連及難治性薄型子宮內膜的患者,即使在采取了大劑量雌激素刺激、富血小板血漿灌注等多項干預措施后,仍不能達到滿意的子宮內膜厚度,反復取消移植周期,加之合并子宮內膜癌,給臨床決策帶來很多難題。幸運的是,在治療過程中小心求證和不斷嘗試中,該患者最終獲得了臨床持續妊娠至今。分析本病例的診治經過,有幾點值得我們思考。
目前,隨著肥胖、多囊卵巢綜合征、不孕不育等因素發生率增加,年輕女性子宮內膜癌發病率日益增加。研究顯示目前子宮內膜癌患者中≤40歲的比例為4%~4.5%[2-3],且越來越多的年輕患者采取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療方案,但這種治療多采用大劑量孕激素制劑會使內膜萎縮,加之反復通過診刮手術對藥物療效進行評估,使大量子宮內膜癌患者存在繼發性薄型子宮內膜、宮腔粘連的問題,給胚胎著床帶來很大的阻礙[4]。分析其原因可能有兩點:第一,治療子宮內膜癌或子宮內膜不典型增生的藥物如大劑量醋酸甲羥孕酮會引起子宮內膜的組織學改變,包括腺基質比降低、腺細胞數量減少、基質蛻膜化和有絲分裂減少[5]。這些可能導致子宮內膜萎縮和變薄,并且在治療終止后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恢復內膜組織的功能[6]。 第二,子宮內膜癌治療過程中的多次刮宮手術容易造成子宮內膜基底層損傷。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細胞因子是重要的子宮內膜間質纖維化調節因子[7]。有研究顯示,子宮內膜損傷后,內膜組織中VEGF下調,宮腔內組織表面在愈合時可能發生融合,形成組織橋,輕者表現為子宮黏膜組織形成的膜性粘連,重者表現為完全由結締組織構成的致密粘連,產生的子宮壁粘連可能造成宮腔部分或完全消失。另外,子宮內膜損傷和瘢痕形成可能影響血管形成[8]。這些改變是造成子宮內膜癌患者薄型子宮內膜的主要因素。
近年來,子宮內膜癌合并薄型子宮內膜的治療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幾種:(1)雌激素刺激子宮內膜:大多情況下對于薄型子宮內膜患者首選雌激素治療促進子宮內膜再生。超生理劑量的雌二醇能使子宮內膜生長時間延長,有利于增加內膜厚度[9-10]。但長時間大劑量使用雌激素可能增加子宮內膜癌復發和血栓發生的風險。故對本例子宮內膜癌逆轉患者采取了在嚴密監測下使用宮腔鏡下宮腔粘連松解術,術后結合雌激素治療的方案。同時,在內膜愈合過程中,宮腔內放置COOK導管進行物理隔離。(2)富血小板血漿(PRP)宮腔灌注治療:PRP是一種具有高濃度血小板的自體血漿制劑,其治療機制在于其可以提供生理量的必需的生長因子和細胞因子,如轉化生長因子-β、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和2、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和表皮生長因子等,從而促進組織再生、血管生成、細胞遷移、分化和增殖,有利于低愈合潛力組織的修復[11]。2019年加拿大生育和男科學會發布的輔助生殖中薄型子宮內膜臨床管理指南中提到,對于Asherman綜合征引起的薄型子宮內膜患者可以使用PRP[12],但由于臨床案例較少,缺乏高質量的隨機對照研究支持,其療效尚不明確。在本例中,采用PRP灌注治療后內膜增長并不滿意,可能與陳舊性宮腔瘢痕相關。(3)盆底仿生物電刺激治療:盆底仿生電刺激是指放置于會陰部的電極通過不同頻率的電流,無創地刺激子宮血管平滑肌收縮和松弛,能夠增加盆底、陰道、子宮內膜和子宮肌肉的血液循環,增加組織營養,促進子宮內膜新生血管形成,從而促進內膜生長,改善子宮內膜容受性[13]。考慮到難治性薄型子宮內膜患者存在內膜血流灌注不良。子宮動脈的高血流阻抗可能導致內膜腺上皮生長受損,子宮內膜血管VEGF水平降低,從而導致血管發育不良,這可能會進一步減少子宮內膜血流量,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子宮內膜變薄[14-15]。本例患者在嘗試多種治療效果不佳的情況下,采用了盆底仿生物電刺激治療,通過兩個周期的盆底電刺激治療,內膜厚度和內膜下血流均有明顯改善。(4)促排卵周期替代人工周期進行FET的子宮內膜準備:本例患者多次大劑量雌激素替代周期準備內膜效果不佳,加之既往合并子宮內膜癌的病史使我們對反復大劑量雌激素治療有所顧慮。回顧患者既往COS周期的內源性雌激素作用可使子宮內膜厚度達10.2 mm,我們嘗試采用促排卵周期進行內膜準備。有研究認為人絕經期促性腺激素(HMG)可用于改善卵巢功能正常但既往使用大劑量、長時間雌激素刺激內膜仍未達到理想厚度而取消周期的患者結局。劉景瑜等[16]比較薄型子宮內膜患者內膜準備方案,發現與使用17β雌二醇組相比,HMG組臨床妊娠率、種植率更高,早期流產率及宮外孕率更低。薄型子宮內膜中雌激素受體的缺乏、雌激素受體基因多態性改變,可能導致對外源性雌激素和內源性雌激素的反應不一樣。促排卵周期中,使用HMG來促進卵泡發育,從而刺激內源性雌激素的釋放,加速了子宮內膜生長,且HMG能促進內膜細胞胞飲突的形成,增加內膜的容受性。
值得注意的是,臨床對胚胎移植時期的確定,需個體化評估子宮內膜厚度。目前學術界對薄型子宮內膜厚度標準不統一。近期一項大型研究納入了超過40 000個IVF-ET周期,其結果顯示在新鮮周期中,子宮內膜厚低于8 mm時,臨床妊娠和活產率降低、妊娠丟失率增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FET周期中,子宮內膜厚度小于7 mm,臨床妊娠和活產率顯著下降(P<0.05)[17]。雖然妊娠率和活產率隨著子宮內膜厚度的降低而降低,但子宮內膜較薄時也有獲得妊娠的可能性。一項針對1 294個周期的研究發現,若選用優質胚胎,子宮內膜厚為6 mm時臨床妊娠率也可達到66.7%、活產率可達50.0%[18]。Check等[19]報道了1例子宮內膜厚度小于4 mm的患者胚胎移植后獲得活產。另有報道1名接受放化療治療后卵巢衰竭,子宮內膜厚度僅有3 mm的女性,實現了健康的足月活產[20]。本例患者既往多次在內膜6 mm時放棄了移植,本次排卵前扳機日雖然內膜厚度僅5.6 mm,仍堅持觀察至移植前日內膜厚度達7.7 mm,在移植后獲得持續妊娠至今。本病例提示,對于難治性薄型子宮內膜患者,臨床醫生應謹慎評估并與患者充分溝通,在得到患者理解與配合前提下,對薄型子宮內膜的患者進行胚胎移植也有成功妊娠的可能。
另外,還需注意的是,本例患者既往在孕26周時曾發生重度子癇前期,考慮可能與內膜環境差導致的螺旋動脈重鑄不良等相關。這也提示臨床醫生對子宮內膜病變患者妊娠期間需要重點關注子宮動脈血流、血壓等臨床指標,警惕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的發生。
綜上所述,子宮內膜在胚胎植入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子宮內膜厚度是臨床中最常用的評估子宮內膜容受性的指標之一。對薄型子宮內膜的治療仍然是臨床醫生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子宮內膜癌或子宮內膜不典型增生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是薄型子宮內膜的高危人群,其原發疾病及治療手段容易導致內膜損傷。對于這類患者需結合年齡、是否合并宮腔粘連等全面綜合考慮,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多方案聯合改善子宮局部微循環,優化臨床決策。我們仍需要探索治療薄型子宮內膜的新方法,更好的解決這一臨床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