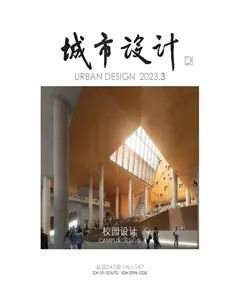大學校園與城市:一場設計變革的解析
邁克爾·赫伯特



摘 要這篇關于設計史的文章思考了城市大學的建筑和景觀最近在設計方法上的轉變。基于二次文獻和已發表的校園總體規劃,本文將20世紀中期對城市與校園分離的關注和當代對城市與校園融合的探索進行了對比研究。雖然主要借鑒的是歐洲和美國的例子,但這一話題是普適的。文章從3個尺度對校園設計革命進行了探討和解釋,首先是大學的城市環境尺度,其次是校園布局和景觀尺度,最后是建筑及其功能尺度。每一個尺度都為追求知識的目標找到了一個設計要素。
關鍵詞:大學校園;大學校園與城市;大學規劃;大學校園設計革命;大學校園設計史
0 引 言
大學及其校園的歷史揭示了兩件事:一方面是機構的個體多樣性,每所大學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文脈和精神內核;另一方面是共同的模式和類型,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們在大學的物理結構中留下痕跡,使其成為文化變遷的底色。本文論述了近年來高等教育校園建筑和景觀設計思維的一個顯著轉變。城市設計師對這一轉變特別感興趣,因為它與城鎮和鄉村、大學和城市之間的關系有關[1-3]。
從歷史上看,大學與城市密切相關。大多數大學的名字來源于其所在的母城。在歐洲古城的基礎上,學院和系所散布在城鎮的街道中。在啟蒙時代,他們向公眾展示了巨大的柱廊式立面和門廊。19 世紀后期,當美國大學在他們稱之為校園田園風光的郊區或農村嘗試建立新校園環境時[4],歐洲的公立大學和技術高中則留在市中心有軌電車線路交叉口的紀念性公共建筑中。
過去 100 年的歷史可以被解讀為一個長期的脫鉤實驗。反城市主義是現代主義思潮的一種普適體現。藝術和建筑力圖擺脫人行道和立面的礦物屬性,解放被建筑門窗限定的視野,緩和城市生活的雜亂和密度。20 世紀的交通和通訊技術為人們提供了通往理想化自然景觀的逃離路線。所有大學建設項目都以獲得大量綠地為前提,如納爾遜·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為紐約州立大學建造的63 個校區。資助戰后英國建立“烏托邦式校園”的大學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Commission, UGC)認為,寬敞的公園環境比城市街區更有利于創造性思維,這是不言而喻的[5-6]。大學資助委員會致力于將高等教育校園打造成一個廣闊的景觀園區,拒絕了市政當局要求在市中心附近進行投資的請求,“他們認為,寬敞的空間本身和一個不受工業發展影響的場地對一所大學來說具有內在優勢[7]”。考文垂市(Coventry)的一所新大學項目被“發配”到了鄉村地區,并被重新命名為華威大學(Universityof Warwick)[8]。盡管一項備受矚目的保護研究[9]表明,新建一所大學是重新利用和修復市中心許多廢棄中世紀建筑的理想方式,但在歷史名城諾里奇(Norwich)和約克(York),大學校園被安置到鄉村區域的橋段再次上演。
1968 年多特蒙德工業大學(DortmundsTechnical University)成立時,魯爾工業區的中心地帶明顯存在著對自然的崇拜。這所大學的方案來源于一場建筑設計競賽,在競賽中一些參賽者主張選擇一個城市地點,以促進城鎮和鄉村、大學與城市的融合。然而,在傾向于選址鄉村地區的官方政策下,這一方案思路被明確拒絕[10]。因此,這所偉大的現代學習中心被建造于城外三公里處的綠色草地上,周圍是放羊的牧場(圖1),從 1984 年開始,有一條現代主義的單軌鐵路從中穿過,校園被分成兩半,位于森林保護區的兩側。同時期的法國科技園區沒有那么過度地反城市,但用韋克曼(Wakeman)的話說,他們 “將城市化降低到花園式郊區的理想類型——工程師和科學家工作和娛樂的天堂”[11]。
大量既有機構從城市中心撤離同樣揭示了過去的設計精神,這些城市如奧爾堡(Aalborg)、布魯塞爾(Brussels)、波爾圖(Porto)、魁北克(拉瓦爾大學)(Québec (Université Laval))和斯德哥爾摩(Stockholm)。梅林(Merlin)[12]記錄了法國當局如何通過將校園分散到郊區的方案以應對 1968 年的學生騷亂。英國的大學也在被疏散,盡管教職員工的停車需求可能是比擔憂學生激進主義更強烈的動機。倫敦大都市發展計劃的研究報告在當時是這樣的假設的:在即將到來的全面機動化和個人移動的時代,有能力遷出城外的大學都希望搬遷校園[7,13]。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曾經探討將其密集的中心建筑群搬遷到倫敦南部克羅伊登(Croydon)以外的一塊 45 英畝綠地上的可行性——由于學術民主,這一提議在1965年5 月被員工以壓倒性投票所否決[14]。維也納技術大學(TU Wien)的教職員工也同樣拒絕從其位于環城大道(Ringstrasse)的歷史校區搬到50 公里外的圖爾恩(Tulln)校區。
被鎖定在城市中心區域規模較大、歷史較長的城市大學的處境,大家普遍認為是不利的。一些大學利用城市更新計劃來擴大校園場地。當街道、商店、企業和低收入家庭被清除后,擴大的校園邊界被柵欄、空白墻或灌木和樹木的緩沖綠化帶所標記(圖2)。現代主義校園與古老的回廊和圈地的學術范式之間存在著一種矛盾的親和力:兩者都將學術界與無序的公眾領域區隔開來。正如關道文(Tom Kvan)所言,對知識的追求被定義為一種“內在的使命”[15]。
大學就是這樣,他們很快就仔細研究了自己在世外桃源(Arcadia)的生活體驗。彼得·馬里斯(Peter Marris)的研究《高等教育的體驗》(The Experi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中接受采訪的學生抱怨周邊地區的不便和孤立,以及他們“與外部世界隔絕”的感覺[7]。人們曾希望物理隔離會鼓勵合作制、跨學科和對知識更全面的追求[16]。但事與愿違。學術專業化的強大作用在獨立學科的建筑群中充分體現。學院院長們對校園領地施加了一種男爵式的強有力控制。低密度校園空間阻礙了互動,在朝九晚五的環境中更強化了學科的概念性隔離。在實踐中,在田園式的理想建筑自由點綴在開放的景觀中,“形成了適合駕車穿越、無序蔓延、支離破碎和孤立的校園”[17]。
本文寫作的出發點是,自千禧年以來,一場激進的設計轉變已經顛覆了大學和城市之間的以往關系[18-20]。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Zu?rich) 的 Kerstin Hoeger 和Kees Christiaanse在他們的《知識社會的城市設計》(UrbanDesign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 一書中,通過廣泛的案例研究發現這一全新的都市主義精神,這些案例包括企業園區、技術中心以及位于市中心和郊外的大學。正如他們的標題所暗示的,他們將設計創新的認識論基礎歸因于:一種新的開明思想文化(譯者注釋)或知識文化[21]。結合類似案例,本文重點討論校園總體規劃的設計策略。阿米爾·哈吉拉索利哈[17] 近期發表的寶貴清單和分析使這項任務變得更加簡單。哈吉拉索利哈對美國大學設計策略的隨機樣本進行了精細粒度分類,總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特色校園總體規劃行動的清單。為了辨別趨勢而簡化細節,當代校園規劃設計實踐可以在街區、街道和建筑的尺度上進行[22]。下文的3 個篇章首先考慮校園的外部環境,其次是內部布局,最后是其校園建筑。每個篇章都將試圖勾勒出創新的主要路線并解釋其緣由。
1 城市環境中的校園
首先, 我們從1:10,000 左右的尺度范圍開始討論,在這一比例下,可以觀察到大學的周邊環境。這揭示了一個項目的城市意象五要素——分界、邊緣、焦點、地標和聯系——是城市設計專業人員的核心議題。無論建筑的標志性如何,這一領域最成功的設計實踐者不是單體建筑的設計師,而是經驗豐富的實踐中的城市規劃專家,如佐佐木建筑師事務所(SasakiAssociates)(馬薩諸塞州劍橋市)、都市策略(Urban Strategies)(多倫多)、文丘里與斯科特·布朗事務所(Venturi Scott Brown)(費城)、倫敦法雷爾建筑設計事務所(Farrels)或英國都市主義環境與設計事務所(URBED)(曼徹斯特)。將大學校園嵌入到城市中涉及高層次的城市設計技巧。
關鍵的創新與校園園區邊界的作用有關。哈吉拉索利哈[17] 通過他所謂的“開放友好的邊緣”來描述校園環境設計的特點。關道文[15] 在他對英國皇家建筑師協會(RIBA)關于大學設計的專業實踐指南的介紹中,強調了設計的邊界從不可滲透到鼓勵連接的轉變。他列舉了校園在費城(Philadelphia)內城環境中的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例子。半個世紀前,當這所大學威脅要搬遷到城外的切斯特縣(Chester County)時,市政當局慷慨地利用城市更新權力,將鄰近的非裔美國人社區夷為平地,將校園改造成一個由隔離墻圍成的超級街區[23]。幾十年來,推平的場地一直被用作大學教職員工通勤停車場。《費城詢問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的建筑評論家評論到:隨著賓夕法尼亞大學校園日益輝煌發展,它成為了貧困之海中的一座特權之島。賓夕法尼亞大學通過建造面向內部的建筑有效地封鎖了校園,甚至將范佩爾特圖書館(Van PeltLibrary)的裝卸區安置在了曾經風光無限的核桃街(Walnut Street)一側[24]。
非法侵入和搶劫最終導致了兩起備受關注的謀殺案,促使政策發生轉變。校長朱迪思·羅丹(Judith Rodin)開始根據近鄰的需求重新調整大學校園,特別是通過建造和贊助一所公立學校。賓大鏈接(Penn Connects)戰略[25] 通過各種可能的手段緩解了校園與城市的分隔——重新向街道開放,重新調整建筑物正面和背面的方向,服務于校園和社區的大型和小型零售商業開發。2011 年更新修訂的“賓大鏈接 2.0”擴展了這一戰略,創造了通往斯庫爾基爾河(Schuylkill River)的 “連接之橋”,同時擴大了大學園區,并通過公園和開放空間擴大了城市的公共空間。校方制定了建筑指南,以確保新建筑在公共大道上呈現出積極的臨街面,并使設計同時滿足校園內外的觀賞性。佐佐木事務所的設計團隊與大學校園建筑師大衛·霍倫伯格(David Hollenberg)持續合作,成功實施賓大鏈接戰略(圖 3)。
哈吉拉索利哈的調查發現,許多其他美國大學中也有類似的設計方案和表達:城鎮契約、社區合作、沿校園邊緣的街道走廊,以及把大學打造成為目的地的大眾傾向[17]。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采用“將校園融入現有結構”的戰略——打通街道以改善交通,在教學樓之間安置新的住房單元,并將行人、汽車和輕軌在街道層面重新整合[26]。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2000 年的校園規劃框架,其前提是“耶魯大學應通過減少阻礙耶魯大學和紐黑文市(New Haven)融合的物理和心理障礙,努力將大學校園的邊界與周圍的社區相融合”——例如百老匯零售區的低層、外向建筑[27]。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總體規劃由校長李·卡羅爾·布林格(Lee CarrollBollinger)委托進行,“將我們的校園作為一個整體進行構思,并考慮其在更大的安娜堡社區(Ann Arbor community)中的地位”[28];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對其東道主城市漢密爾頓安大略省(Hamilton Ontario)采用重新定位戰略,通過門廊、立面、步行道和“大學——社區合作伙伴關系”,為校園帶來新面貌[29]。麻省理工學院(MIT)正在對其校園東端的前停車場進行重建,使其成為具有綜合用途和雙重功能的建筑,為校園和鄰近的肯德爾格林區(Kendall Green)服務[30]。在墨西哥邊境以南,佐佐木建筑師事務所因其蒙特雷理工學院(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城市再生計劃而獲獎(圖 4)。盡管拉丁美洲城市的背景明顯不同,但在從一個防御型的、安全驅動型的飛地轉變為一個通過空間連接和實際協作來重塑城市環境的開放的合作伙伴上具有明顯的相似之處[31]。
將迄今為止分散的土地使用單元與城市環境重新整合的嘗試在零售業、交通規劃和住宅區中有許多相似的做法,但高等教育對連通性的話題有特別的共鳴。全球市場爭奪投資和就業機會的城市已經開始意識到,在當地建立大學可以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和競爭力[32]。就學術界而言,學者們越來越意識到,追求知識的目的不在于學術出版,而在于閱讀、引用、轉化為技術和其他類型的影響:與東道主城市的緊密聯系有助于知識轉移[33]。信息經濟的流動性加強了大學與地理環境相聯系的動力,以及吸引和留住人才的“粘性”[20]。知識轉移被描述為一項接觸式運動:信息在全球范圍內的網絡化程度越高,對在創新場所面對面接觸的需求就越大。地區和校園之間這種創造性的共生關系取決于日常交往和共享的生活方式,而這只有在嵌入式大學中才可能實現[34]。
總而言之,知識經濟的作用是打破了校園和城市之間的傳統界限。在最新的發展中,這兩者可能像在最古老的城市大學中一樣混雜。因此,劍橋市目前的西北郊區大學擴建項目占地150 公頃,將私人住宅開發(1,500 套)、研究生宿舍(2,000 套)、大學員工宿舍(1,500 套)混合在一起,將教學樓與研發空間、初創企業和商業混合在一起。總體規劃師 AECOM 的目標是在 21 世紀的環境中復制歷史上劍橋的土地混合使用模式[18]。
2 校園布局
傳統低密度校園的一個優勢是為一代又一代的資產管理者留下了充足的土地供應。大學享有根據不斷變化的需求進行發展的余地,建筑物以一種特殊方式安置在開放的公園景觀中。然而,近年來的總體規劃對場所營造的品質采取了更堅定的觀點,實施了設計原則,以維護校園空間作為大學機構身份最重要的集體表意的作用[35]。單個建筑被要求與它們的毗鄰建筑在共享的臨界建筑線和朝向上協同以組成適宜的校園環境。用 2000 年法國大學計劃的話來說,“密集化邏輯”已經取代了以前的 “擴張邏輯”[36]。城市設計技術已被應用于以前的開放式校園,將建筑物連接在一起以形成圍墻[37]。大學已經學會了街道、廣場和場所這些視覺詞匯;用布萊恩·愛德華茲(Brian Edwards)的標準文本來說,“圍墻、路線、大門、長廊和景觀是校園場所營造的基本特性”[38-39]。
通過分析過程和結果, 波利佐伊迪斯(Polyzoides)[40] 將成功的校園設計定義為“虛空的具象化”。它意味著使校園的室外空間和定義它的建筑一樣清晰易讀;在格式塔(Gestalt)術語中,實體和虛空應該形成一個可逆的格局[41]。可讀性與可行性、可居住性、安全性、認同感和社區意識有關,這些價值在最近的校園規劃中反復出現[17]。這種場所營造的精神可以在圣地亞哥大學(University of SanDiego)的戰略中看到,該大學在地面停車場的基礎上進行建設,取而代之的是建筑設計的三維停車結構,構成了校園山頂庭院的框架[42](圖5),這也可以在佐佐木建筑師事務所對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Austen)的填充方法中看到[43]。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巨大產業的長期整合和場所營造戰略中,前大學校園建筑師大衛·紐曼(David Neumann)說:“我們正在建設一個校園,但每個建筑都是校園建設,建筑是一個動詞[44]。”在康涅狄格大學(Universityof Connecticut),針對學生申請人數不斷下降的一種應對方式是建設斯托爾斯中心(StorrsCenter),這是一個位于校園旁的新城市主義風格的街區,由五層樓高的建筑組成,為以前的無人區帶來城市氣息[35]。英國的一個例子是曼徹斯特大學的設計歷程。20 世紀60 年代,該大學的規劃顧問休·威爾遜(Hugh Wilson)和劉易斯·沃默斯利(Lewis Womersley)將野蠻主義的巨型建筑與郊外校園的環境結合起來,四面都是多車道的高速公路,并以綠植為緩沖屏障。在這一規劃下,45% 的區域被停車場占據,其余區域則鋪設草地、灌木和樹木組成的非正式景觀[45]。40 年后,由特里·法瑞爾(TerryFarrell)及其合作伙伴制定的“超級互聯”計劃試圖消除校園邊緣所有的障礙感,并將大學與它的公共環境重新連接起來(圖6)。地面停車場和非正式的草皮被重新定位為集約開發的場地,這將恢復實體和空間之間的連貫性。新的公共領域將由有適宜名稱的種植行道樹且沿街面積極的街道和廣場組成[46],而不是非正式景觀無邊際的“失落空間”[47]。
同樣的范式轉變也可以在郊外的場地觀察到。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在霍格伯格(H?nggerberg)的瑞士,其最負盛名的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它建于20 世紀60 年代,是城外一個寬敞的科技園區。“與這一時期建造的許多衛星科學園區一樣,它因其地理位置偏僻、開放空間不受歡迎和建筑缺乏吸引力而受到影響。這是一個從朝九晚五的通勤園區,被空間分裂和地域偏遠的陰影所籠罩[48]。”解決霍格伯格校區問題的辦法是密集化(圖 7)。這所大學聘請了荷蘭設計師吉斯·克里斯蒂安(Kees Christiaanse)在其空曠的空間上進行建設,引入住房和商店,并將這座龐大而單調的城外校園改造成一個準市郊。這一過程在《校園與城市:知識社會的城市設計》(Campusand the City: Urban Design for the KnowledgeSociety)一書中得到記錄。
這種內部整合過程有著明顯的經濟基礎。在公共補貼減少,針對師生和研究基金的全球競爭加劇的情況下,大學必須善用他們的資產。學者佩里(Perry)、大衛(David)和威姆·魏威爾(Wim Wiewel)[49] 對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商業理念做了充分的記錄。建設在草地或戶外停車場上的房產,因延長假期而空著的教室,以及每周幾乎無人問津的員工辦公室,都是責任管理的明顯目標。新的建筑和高質量的景觀設計顯示了活力,吸引了學生,同時吸引了投資[50]。
還有兩個因素加強了對場所營造的關注。一個是氣候變化。正如布萊恩·愛德華茲(BrianEdwards)所建議的那樣[38],理想情況下,大學校園應該讓社會看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將減少碳排放納入大學的績效衡量標準,為緊湊、便捷和節能的布局提供了新的動力。在哈吉拉索利哈對 50 個校園總體規劃的內容分析中,可步行性是被引用最多的一個目標[17]。
最后,正如大學歷史中經常出現的那樣,物理趨勢往往有一個抽象的認識論基礎。今天,科學和創造力的前沿跨越了學科之間的界限。最肥沃的知識環境不再是專業化的細胞,而是不同專業匯聚在一起的間隙空間。這也為塑造一個有形的公共空間提供了新的推動力。跨國制藥企業競爭激烈的研究環境中的一個例子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當汽巴- 嘉基(Ciba-Geigy)和山德士(Sandoz) 合并為諾華(Novartis)公司時,他們在巴塞爾的 51 英畝的圣約翰(StJohann)工廠被重新開發為一個研究場所。與所有科技園區的設計規則相反,該地塊被高密度地配置為一組城市街區,以深而窄的街道網格為基礎,網格尺度與城市的歷史核心區相似。2001 年由維多里奧·馬尼亞戈·蘭普尼亞尼(Vittorio Magnago Lumpagnani) 設計的總體規劃對巴塞爾的街道網格進行了延伸,配備了行道樹、標準的鋪裝和照明細節,并通過設置咖啡館以鼓勵來自不同部門的工人進行日常交流(圖 8)。建筑的設計師是在保護街道完整性的前提下,從眾多頂級建筑師中挑選出來的。整個項目希望盡可能地與低密度的園區環境不同,因為低密度的園區環境會給人以無家可歸的印象。諾華城不是一個科技園區,而是一個新生的城市,在這里,創造力將由“日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來維持[51]。事實上,這個所謂的小鎮根本就不是什么小鎮,而是一個位于堅固圍墻內的高度保密的公司研究部門,但它的準城市規劃充分呼應了當代的實踐,從而在克斯汀·霍格 (Kerstin Hoeger) 的《知識社會的城市設計》(Urban Design for the KnowledgeSociety)[21] 一書中獲得了一席之地。
3 建筑的混合使用
最后放大到建筑規模,新校園城市化的建筑含義是什么?答案可以在傳統城市的特色建筑類型中找到:建在地塊的邊緣,面向公共道路、庭院或花園;垂直分層,沿街面活躍;最重要的是,建筑的上方和下方都混合使用。上個世紀功能離散的建筑類型正在被混合型建筑所取代,混合型建筑旨在實現隨著時間推移具有功能復合性和多樣性。在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無處不在的時代,單功能的圖書館正在與咖啡館、走廊、公共休息室、研討會、計算機集群合并成“學習公共空間”。類型的模糊化反映了現實世界中工作模式和學習行為的變化。營銷戰略家已經追蹤了 “Y”時代(1977 年后)、千禧年和后千禧年一代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轉變:厭惡日常通勤并愿意住在現場;傾向于步行或騎車而不是開車;消除了日常生活中生活和工作之間的傳統界限;一種社會地理學,將咖啡館帶回18 世紀的起源,作為思想交流和做生意的地方。
對大學建筑的影響可以通過麻省理工學院在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3 個后千禧年的新增項目來說明。新的混合性的一個開創性例子是為計算機、信息化和智能科學而建的雷與瑪利亞史塔特科技中心(Ray and Maria Stata Center)[52]。該建筑由弗蘭克·蓋里(Frank Gehry)設計,于2005 年啟用,顛覆了傳統的隔間辦公室和走廊之間的關系。流動空間占主導地位,每一個角落都有非正式的長椅和黑板,以鼓勵偶遇和靈感的記錄。麻省理工學院大學園區的重建在外觀上更為傳統,但在功能上同樣激進,該校園位于馬薩諸塞大道,占地 27 英畝,以前由新英格蘭糖果工廠低密度占用,2005 年被重新開發為生物技術和其他高科技產業的孵化區。Koetter Kim 建筑設計事務所的設計創造了 250 萬平方英尺的混合開發,這些城市街區與鄰近的街道網格相一致。這些建筑將研發實驗室與辦公室、公寓、會議中心和酒店結合在一起,并在第二階段擴展到馬薩諸塞州大道上的零售業。第三個例子已在上文中提及,來自麻省理工學院校園的東部,緊鄰肯德爾綠地,在那里,該大學正在將以前的停車場重新開發成一個混合功能區,包括實驗室、辦公室、住宅、零售、文化和學術空間,以及一個兩英畝的景觀廣場。該項目啟動時宣布 One Broadway建筑將納入一個雜貨店和食品市場,為當地社區和學術界服務[53]。
4 結 語
對校園設計的趨勢一概而論是輕率的做法。傳統的郊區景觀校園仍在大量建造,尤其是在中國,那里的高等教育正在最大限度地擴張。正如布萊恩·愛德華所指出的[38],大學總體規劃中的圖紙并不能保證什么:這些飽含期望的文件在實施中可能被忽視,或者被大學校長的更換或新校園管理者的任命所推翻。但是,這個歸納是符合條件的,歷史趨勢是明確的。知識不再是一種需要與大眾隔絕的精英活動。它必須通過勞動人口盡可能廣泛地傳播。城市與校園的二分法已經被顛覆。佐佐木事務所的簡·科尼爾(Janne Corneil)和菲利普·帕森斯(Philip Parsons)建議,我們應該致力于使大學和城市之間的界限至少是多孔隙的,最好是不存在的,“在一個健康的知識社會中,大學成為城市,城市成為大學”[48]。
在20 世紀,大學紛紛遷往城外,在開放的環境中尋求更好的未來。最后,思考一下最近在另一個方向上的兩個簡例。一個是美國贈地大學(US Land Grant campus)的縮影——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它在鳳凰城外的鹽河邊發展起來,如今坐落在大都會的環郊區地帶。大學當局試圖擴展到生物科學和信息學這些活躍領域,但他們意識到如果轉基因研究所這樣的跨學科的前沿機構被安置在郊區,招生工作將受到影響。喬恩·杰德(Jon Jerde)被委托在鳳凰城中央商務區以北的混合區設計一個新校區:一個擁有15,000 名學生和3,800 名員工的“新興知識中心”。其建筑以街道為基礎,混合使用,為商戶提供可供出租的 B 級辦公空間以創造“鳳凰城中心的協同力量”[54]。在2004 年10 月的啟動儀式上,最近當選的市長菲爾·戈登(Phil Gordon)談到一所大學選址于鳳凰城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高薪工作、積極的移民趨勢、對城市經濟的顯著倍增效益。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孩子,他愛上了教育[55]。十幾年后,戈登市長對城市校園經濟影響的樂觀預判得到了證實。
讓法國人的案例作為收尾。20 世紀60 年代,他們的大學引領了歐洲的離心式轉變。30年后,他們正引領著“回歸”,常常為廢棄的建筑帶來新的生命力和活動[36]。許多城市都有這樣的例子,包括里爾(Lille,)、格勒諾布爾(Grenoble)或里昂(Lyon),但最引人注目的是狄德羅大學(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éDiderot (Paris VII))從其城外校園搬遷到塞納河左岸,奧斯特里茨火車站(Gare Austerlitz)后面的前工業運輸區。由克里斯蒂安·德·波特桑帕克(Christian de Portzamparc)規劃的馬塞納區(Quartier Masséna)是一個新區,部分建在廢棄的鐵路用地上,部分建在運行的軌道上。以街道為基礎的建筑分散在該區的住宅、商店和商業中(圖 9)。狄德羅大學的核心是宣稱自己是“沉浸在城市中,沉浸在生活中的校園”。在這所城市大學里,城市化和對知識的追求是一枚硬幣的兩面[56]。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1] THOMAS B.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 GENESTIER P. Luniversité et la cité[J]. Espaces et
sociétés, 1991 (80): 1-45.
[3] HALL P.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J]. Geojournal,
1997, 41(4): 301-309.
[4] TURNER P V. Campus: An American planning
tradition[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5] BIRKS T. Building the new universities[M]. Newton
Abbott: David & Charles, 1972.
[6] MUTHESIUS S. The postwar university utopianist
campus and colleg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7] ABERCROMBIE N, COWAN P. The university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A study of activity patterns
from a planning viewpoint sponsored by the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M]. London: Heinemann, 1974.
[8] THOMPSON E P. Warwick University Ltd: Industry,
management and the universities[M]. London: Penguin,
1970.
[9] ESHER L B, VISCOUNT. York - A study in conserva
tion report of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 local government
and York city council[EB/OL].[2018-02-21].https://www.
bcin.ca/Interface/openbcin.cgi?submit=submit&Chink
ey=118106.
[10] HNILICA S, JAGER M, J?chner C. Die Universit?ten
im Ruhrgebiet. Hochschulbau zwischen Reform-und
Massenuniversit?t C. Ruhr-Universit?t Bochum. Berlin:
Gebr. Mann, 2015: 99-110.
[11] WAKEMAN R. Dreaming the new Atlantis: Science
and the planning of technopolis, 1955-1985[J]. Osiris,
2003, 18(1): 255-270.
[12] MERLIN P. Lurbanisme universitaire à létranger
et en France[M]. Paris: Presses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 1995.
[13] GLC. Greater London development plan report of
studies[R]. London: Greater London Council, 1970.
[14] DAHRENDORF R. LSE: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1895-1995[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5] KVAN T. Context[M]//TAYLOR I. Future campus:
Design quality in university buildings. London: RIBA
Publishing, 2016: 4-5.
[16] OSSA-RICHARDSON A.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and its concrete form[M]//TEMPLE P. The Physical
University: Contours of Space and Place in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159-181.
[17] HAJRASOULIHA A H. Master-planning the
American campus: Goals, actions, and design strategies [J].
URBAN DESIGN International, 2017, 22(4): 363-381.
[18] COULSON J, ROBERTS P, TAYLOR I. University
trends: Contemporary campus design[M]. London:
Routledge, 2014.
[19] COULSON J, ROBERTS P, TAYLOR I. University
planning and architecture: The search for perfection[M].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5.
[20] TAYLOR I. Future campus: Design quality in
university buildings[M]. London: RIBA Publishing, 2016.
[21] HOEGER K, CHRISTIAANSE K. Campus and the
city: Urban design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M]. Zurich:
Gta Verlag, 2007.
[22] TALEN E. 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M]. 2nd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Education, 2013.
[23] PUCKETT J L, LLOYD M F. Becoming Penn:
The pragmatic American university 1950-2000[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24] SAFFRON I. Changing skyline: The ugly story
behind penns bucolic urban campus[EB/OL].[2018-02-
21].https://www.inquirer.com/philly/living/20151127_
Changing_Skyline__The_ugly_story_behind_Penn_s_
bucolic_urban_campus.html.
[25] Sasaki Associat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enn
connects[EB/OL]. [2018-06-17]. http://www.sasaki.com/
project/116/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enn-connects/.
[26] UrbanStrategies. 1994.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aster Plan.” Accessed February 21, 2018[EB/OL].
[2018-02-21].https://www.urbanstrategies.com/project/
university-of-minnesota-master-plan/.
[27] Yale university: A framework for campus planning
[EB/OL].[2018-02-21]. https://facilities.yale.edu/sites/
default/files/files/Design%20Standards/YALEFRMW.
pdf.
[28] VSB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aster plan.
Venturi, Scott Brown & Associates Inc f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EB/OL].[2018-02-21].https://www.vsba.com/
projects/university-of-michigan-campus-master-plan/.
[29] MCMASTER. McMaster university campus master
plan[EB/OL]. [2018-02-21]. https://secretariat.mcmaster.
ca/app/uploads/2019/06/Campus_Master_-Plan.pdf.
[30] MIT. MIT2030: The framework massachus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facilities[EB/OL].
[2018-02-21]. https:// http://mit.edu/mit2030/.
[31] Sasaki Associates. Tecnológico de Monterrey urban
regeneration plan[EB/OL]. [2018-02-22]. http://www.
sasaki.com/project/345/tecnolgico-de-monterrey-urbanregeneration-
plan/.
[32] BENNEWORTH P, HOSPERS G J. Urban
competitivenes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Universities
as new planning animateurs[J]. Progress in Planning,
2007, 67(2): 105-197.
[33] GODDARD J, VALLANCE P.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M]. London: Routledge, 2013.
[34] FLORIDA R. Regions and universities together
can foster a creative economy[J].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06(9): 77-100.
[35] COULSON J, ROBERTS P, TAYLOR I. The future
of the campus: architecture and master planning trends[J].
Perspectives: Policy and Practice in Higher Education,
2018, 19(4): 116-121.
[36]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facilities for
tertiary education[M].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8.
[37] CARMONA M, TIESDELL S, HEATH T, et al.
Public places urban spaces: The dimensions of urban
design[M]. 2nd ed. Boston: Elsevier, 2010.
[38] EDWARDS B. University architecture[M]. London:
Spon Press, 2000.
[39] DOBER R P. Campus design[M]. New York: Wiley, 1992.
[40] Polyzoides, S.“Success and Failure in Campus
Design in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In Designing
the Campus of Tomorrow: The Legacy of the Hearst
Architectural Plan, Present and Future[EB/OL]. [2018-
02-20].https://newsarchive.berkeley.edu/news/media/
releases/2000/01/01-25-2000a.html .
[41] HEBBERT M. Figure-ground: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a planning technique[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16,
87(6): 705-728.
[42] USD.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master plan update.
[EB/OL]. [2018-04-11]. https://catcher.sandiego.edu/
items/usd/USD%20MasterPlan.pdf.
[43] Sasaki Associates.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Master Plan[EB/OL]. [2018-02-22].https://www.sasaki.
com/projects/university-of-texas-at-austin-master-plan/.
[44] BLUM A. David neuman: Planning utopias where
campus is king[J]. Architectural Record, 2004, 192(1): 208.
[45] WILSON H, WOMERSLEY L. Manchester education
precinct: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planning consultants[M].
Manchester: Corporation of Manchester, 1967.
[46] FARRELLS. Manchester university masterplan[EB/
OL]. [2018-04-11]. https://farrells.com/project/
manchester-university-masterplan.
[47] TRANCIK R. Finding lost space - theories of urban
design[M].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Company,
1986.
[48] CORNEIL J, PARSONS P. The contribution of
campus design to the knowledge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CHRISTIAANSE K, HOEGER K.
Campus and the City - Urban Design for the Knowledge
Society. Zurich: GTA Verlag, 2007: 114-127.
[49] PERRY D C, WIEWEL W. The university as urban
developer: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50] MARMOT A. TEMPLE P. Managing the Campus[J].
The physical university: Contours of space and place in
higher education, 2014(1): 58-71.
[51] INGERSOLL R. From the confinement of heterotopia
to the urbanity of novartis ville[M]//BOUTELLIER R.
Novartis International AG Novartis Campus. Ostfildern:
Hatje Cantz Verlag, 2009: 257-265.
[52] A&U. Special Issue: New University Environments[M].
Tokyo: A&U, 2005: 7-119.
[53] MIT. MITs one Broadway building to be the
future home of brothers marketplace: announcement
delivers on a key commitment by the institute to the
Cambridge community[EB/OL].[2018-02-21]. https://
news.mit.edu/2017/mit-one-broadway-building-brothersmarketplace-
1214.
[54] PHOENIX. Downtown phoenix, a strategic vision
and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EB/OL]. [2018-05-21].
https://www.phoenix.gov/villagessite/Documents/pdd_
pz_pdf_00419.pdf.
[55] FRIEDMAN D. An extraordinary partnership
betwee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of
phoenix[J].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Outreach and
Engagement, 2009, 13(3): 89-100.
[56] Diderot. Luniversité Au Coeur De La Société[EB/
OL].[2018-08-22]. https://irem.u-paris.fr/luniversite-aucoeur-
de-la-soci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