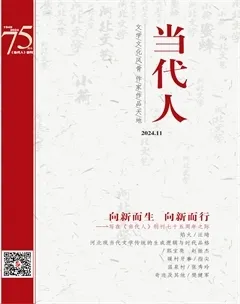河北現(xiàn)當代文學傳統(tǒng)的生成邏輯與時代品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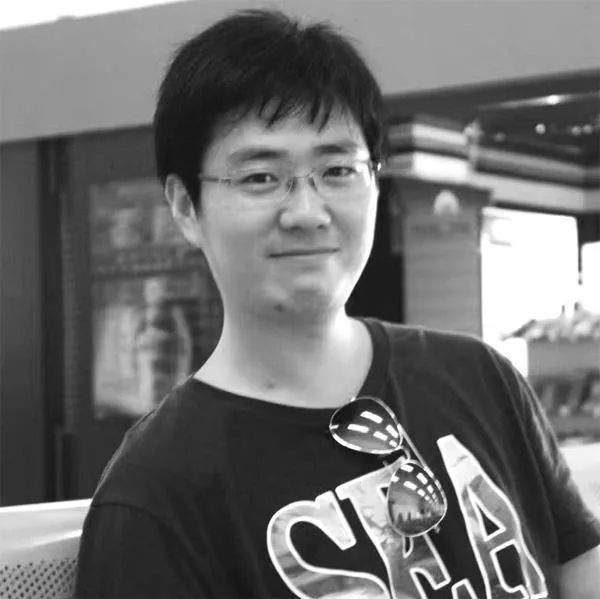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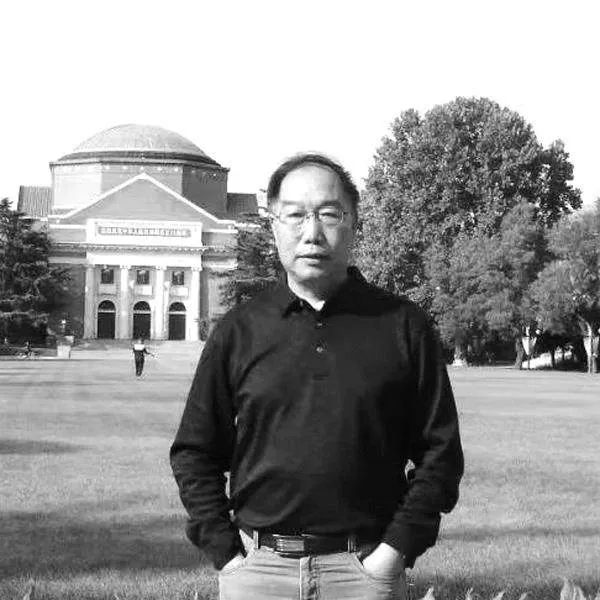
郭寶亮,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州華商學院特聘教授,河北省政府特貼專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小說學會常務理事,首屆河北省百名優(yōu)秀創(chuàng)新人才支持計劃入選者。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評委。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發(fā)表評論文章190余篇,出版《王蒙小說文體研究》等專著7部。
趙振杰,文學博士,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評論見于《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當代作家評論》《當代文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等。曾獲《人民文學》“近作短評”金獎,第十三屆河北省文藝振興獎,第十、十一、十二屆河北省文藝評論獎。著有文學評論集《螢火微光:文學的散點與聚焦》。
一
趙振杰:郭老師您好,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周年,從文學史的角度回顧和重溫河北現(xiàn)當代文學的發(fā)展歷程,厘清和考察紅色文脈與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的內涵與外延,對于當前的文學實踐、理論創(chuàng)新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與借鑒價值。在此向您請教幾個關于河北現(xiàn)當代文學與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的問題。在展開討論之前,我想首先我們需要明確一下何為“河北文學”,何為“現(xiàn)當代河北”。也就是說,當我們談論“河北現(xiàn)當代文學”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么?在您看來,“現(xiàn)當代河北”的具體研究范疇和研究對象應該如何界定?
郭寶亮:“河北”這一省名是1928年6月間根據(jù)南京國民政府的訓令改稱的。此前,無論是清朝末期還是北洋軍閥統(tǒng)治的民國時期,今河北省所屬區(qū)域均稱“直隸”。在清末,今河北省與北京市、天津市基本上同屬一個省。天津在當時不僅一直受直隸省管轄,而且自同治朝以后更逐漸成為直隸省事實上的省會。即便是北京,在當時也兼屬直隸省,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受朝廷“直轄”。民國建立之初,地方行政區(qū)劃一開始仍沿襲清制,河北省仍稱直隸,轄清末之12府、7直隸州、3直隸廳。1913年1月北洋政府頒布命令,決定廢除府一級建制,同時所有直隸州、直隸廳及散州、散廳均統(tǒng)一名稱為縣。順天府因系首都北京所在地,特予以保留并直接隸屬中央,這是北京與直隸省完全脫離隸屬關系之始。1928年6月北伐戰(zhàn)爭基本結束時,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布訓令決定直隸省改名河北省,同時決定撤銷京兆區(qū),將其所屬20縣全部并入河北省,將北京易名為北平,特置為受國民政府直轄的特別市。1930年6月國民政府曾決定將北平市改為河北省轄市,但至當年11月又恢復其為特別市。這樣,在整個民國時期,一方面是1928年以后原京兆區(qū)所轄各縣都劃歸河北省,另一方面則是曾經作為北洋政府統(tǒng)治時期的民國首都的北京市和后來的北平市,除去1930年的短短幾個月外都一直由中央政府直轄,與環(huán)繞著它的直隸/河北省不再存在兼屬關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河北省的行政區(qū)劃又陸續(xù)發(fā)生過一些較為重大的變更。一是察哈爾省、熱河省相繼撤銷,部分縣重新劃歸河北省。二是天津與河北的幾度分分合合。新中國成立后天津一開始為中央直轄市,到1958年被變更為河北省直轄市,河北省省會也相應地由保定遷至天津。但到了1967年天津再度升格為直轄市,河北省省會只得再度遷出,先是在保定,后來在石家莊扎下根來。三是部分縣重新劃歸北京和天津。1928年北平、天津兩市被確立為特別市時,原京兆特別區(qū)域所屬20縣已全部劃歸河北,天津特別市在當時亦未下轄縣。所以現(xiàn)在北京、天津兩市所轄各縣(區(qū)),基本上都是新中國成立后由河北省劃撥過去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河北省行政區(qū)劃幾度變更,概而言之,由于察哈爾、熱河兩省的撤銷和今張家口、承德兩地區(qū)的回歸,河北省的版圖就其外緣來看,較之民國時期無疑更接近清末時期的直隸省版圖。但北京、天津兩座大城市的直轄,特別是天津與河北之間的分分合合,無疑給當代河北政治、經濟、文化、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提出了新的問題和挑戰(zhàn)。
因此,我們基本可以確定現(xiàn)當代河北文學的研究范疇。首先是籍貫意義上的河北作家,即那些生長在河北,又長期工作在河北的作家。其次是雖然不是河北籍的作家,但長期或者一段時間在河北工作,有的甚至還擔任過河北文藝界領導職務,比如康濯、丁玲、劉真、袁靜、孔厥、邵子南、湯吉夫等。再次是后來定居京津的作家,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如孫犁、梁斌,雖然他們后來都到了天津工作生活,但他們的籍貫在河北,部分重要作品在河北完成,而且取材和生活基礎也在河北故鄉(xiāng)。另外一種如王蒙、浩然、蔣子龍等作家,他們的籍貫或祖籍雖然都是河北,但他們的主要創(chuàng)作卻是在京津時期完成的,故而不能算河北作家。當然,由于河北行政區(qū)劃的頻繁變更,這個研究對象范圍只是相對而言的,進入研究視野的作家,我們關注的是其創(chuàng)作與河北的關聯(lián),而沒有納入研究視野的作家,我們看到的是其創(chuàng)作與整個河北文化特征的疏離。因此,在研究對象取舍的問題上,雖然頗費思量,但仍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
趙振杰:眾所周知,自五四以降,河北新文學伴隨著中國社會百年的現(xiàn)代化進程,完成了文學的現(xiàn)代化過渡。李大釗先生無疑是河北新文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他在《什么是新文學》一文中明確指出,新文學要有“宏深的思想,堅信的主義,博愛的精神”,應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并在一系列政論文章中斷言“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其作品均有很強的啟蒙性和革命性,從而為河北新文學的發(fā)展奠定了現(xiàn)實主義總基調。那么河北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中潛在的紅色基因和政治品格又是如何沉淀在作家的潛意識中,支配和影響作家創(chuàng)作的?
郭寶亮:當然,政治與文學本來就不可分。文學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tài),所謂的“純”文學是不存在的。不過,文學是一種審美意識形態(tài),它是以審美的方式來顯示意識形態(tài)的,較之于一般的意識形態(tài)而言,文學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tǒng)》中,提出文學活動的四要素:作品、世界、作家、讀者。在這四要素中,作品是作家對生活世界的體驗凝結而成的認識的反映,讀者通過閱讀作品激活了自己對生活世界的認識,并反饋到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因此,作品是核心,而世界是一切創(chuàng)作的出發(fā)點。從這一意義上說,河北文學中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是河北這塊大地上人民生活斗爭的自然產物。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fā)源于北平,而北平與河北在地緣上血肉相連。新文化運動史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黨史的前史,作為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的李大釗就是河北人。隨后的“一二·九”運動、“盧溝橋事變”等,河北大地經歷了中華民族最嚴峻的血與火的淬煉,政治成為生活中的第一現(xiàn)實,也成為文學表現(xiàn)的第一生活素材,天然的紅色基因和政治品格,又怎能不支配和影響著作家的創(chuàng)作?
趙振杰:是的。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標志著中國全面進入到艱苦卓絕的抗日戰(zhàn)爭階段。中國共產黨在河北先后建立了晉察冀、晉冀魯豫等抗日根據(jù)地,河北文學的發(fā)展也隨之呈現(xiàn)出新的氣象與風貌。為配合抗戰(zhàn),根據(jù)地和解放區(qū)各條文藝戰(zhàn)線紛紛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文藝浪潮,“冀中一日”群眾寫作運動、戰(zhàn)地劇社運動、街頭詩運動、歌詠運動等層出不窮。河北作家陣容也空前壯大,集結了全國的文學精英。丁玲、康濯、阮章競、賀敬之、郭小川、周而復、邵子南、孫犁、田間、王林等一大批文藝工作者和知名作家云集于此,相繼創(chuàng)作出具有“中國氣派”“民族風格”且“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優(yōu)秀文藝作品。為何當時晉察冀根據(jù)地和解放區(qū)會吸引來如此之多的知名作家和文藝工作者?《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新兒女英雄傳》《我的兩家房東》《地雷陣》《雨來沒有死》《白求恩大夫》等重要作品均集中產生于河北,其背后原因有哪些?
郭寶亮: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抗戰(zhàn)如火如荼,自然會吸引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投入到救亡圖存的行列中。丁玲是第一個到達陜北延安的知名作家。后來她又來到晉察冀根據(jù)地,創(chuàng)作了大量優(yōu)秀的作品。還有其他作家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描寫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土地改革的優(yōu)秀作品出現(xiàn)在河北,首先是毛澤東抗戰(zhàn)文藝思想的指導,為晉察冀根據(jù)地文藝繁榮的出現(xiàn),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南;其次是這塊大地上廣大民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艱苦卓絕和豐富多彩的斗爭生活使然。
趙振杰:正如您所說,毛澤東抗戰(zhàn)文藝思想的指導,為晉察冀根據(jù)地文藝繁榮的出現(xiàn)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南。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科學系統(tǒng)地解決了文藝“為誰服務”和“怎樣服務”的根本性問題,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無疑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然而,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以“告別革命”“反思歷史”為核心訴求的“重寫文學史”思潮中,我們剛才提到的這些革命作家及其作品都曾一度遭到不同程度的輕視和貶低,您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對于這一現(xiàn)象作何評價?
郭寶亮: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確出現(xiàn)了一些輕視貶低革命文藝的不和諧聲音。當時情況下,大家對“四人幫”極左路線的憤怒導致了情緒上的不冷靜,有些人把“啟蒙”與“革命”對立起來,認為我們前進道路上的挫折和失誤都是由于“革命”壓倒了“啟蒙”的緣故。近些年來情況變得好起來,大家能夠冷靜客觀地看待革命文藝,開始重視革命文藝,是一種好的現(xiàn)象。
二
趙振杰: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集結在河北的作家群體中有人離開河北赴京、津和軍區(qū)部隊,河北創(chuàng)作隊伍銳減,不過從戰(zhàn)火硝煙中走來的新銳作家們,自覺秉承起解放區(qū)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在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生活題材兩個創(chuàng)作領域走向全國文壇的最前列。徐光耀、李英儒、劉流、雪克、李曉明、邢野、劉真等革命作家把真摯的情感化在紙上,將革命激情和文學才情熔鑄成了恢宏篇章,不僅形成了河北“紅色經典”創(chuàng)作高潮,同時也為中國當代文壇提供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在您看來,河北“紅色經典”創(chuàng)作高潮的出現(xiàn),其背后的歷史動因是什么?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與根據(jù)地、解放區(qū)時期的文學,在美學風格上存在哪些異同點?
郭寶亮:新中國成立以后,河北文學中的“紅色經典”創(chuàng)作迎來了高潮,出現(xiàn)了《紅旗譜》《風云初記》《鐵木前傳》《小兵張嘎》《野火春風斗古城》《烈火金鋼》《新兒女英雄傳》《戰(zhàn)斗的青春》等優(yōu)秀作品。我認為其背后的歷史動因就是許多作家轉入較為安定的生活,他們有時間和精力坐下來好好把戰(zhàn)爭年代經歷的革命斗爭生活細致地深入地回憶梳理,把這些紅色歲月寫下來,沉淀在作品中。因此,這一時期的創(chuàng)作比起解放區(qū)時期的文學明顯見出從容和深刻。比如梁斌的《紅旗譜》,1934年作者在“左聯(lián)”刊物《伶仃》上發(fā)表了以“高蠡暴動”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夜之交流》,1942年又根據(jù)同一題材創(chuàng)作了短篇小說《三個布爾什維克的爸爸》,后又將其擴展為五六萬字的中篇《父親》,即《紅旗譜》中朱老忠一家故事的雛形。《紅旗譜》全書,1942年開始構思,經過長期醞釀,于1953年至1956年間完成了三部曲的初稿。經過反復修改,1957年底出版了第一部《紅旗譜》,1963年出版第二部《播火記》。第三部《烽煙圖》初稿“文革”中丟失,“文革”后幾經周折而復得,精心修改后,于1983年出版。第一部《紅旗譜》,成為新中國成立十七年時期最為重要的“紅色經典”之一,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說的“三紅一創(chuàng)”“青山保林”中的“三紅”的第一“紅”就是指的《紅旗譜》。《紅旗譜》史詩性地再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河北大地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殊死斗爭,描繪了中國現(xiàn)代大革命時期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且小說在藝術上也有了很大的長進,梁斌將西方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融會貫通,將民族性與世界性結合起來,特別在人物心理描寫上做到了“比中國古代文學細一些,比西洋文學粗一些”的藝術效果。從美學風格上,這一時期的“紅色經典”呈現(xiàn)出更加崇高壯美的風格。
趙振杰: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河北文學又迎來了一個歷史發(fā)展的新階段。從賈大山的“高山仰止”,鐵凝的“獨樹一幟”,到陳沖、陳超的“雙峰并峙”,再到“三駕馬車”“河北四俠”“燕趙詩群”的迅速崛起,河北文學朝著繁榮創(chuàng)新和兼容并蓄的方向闊步前行。作家們扎根燕趙沃土,緊跟時代步伐,助力改革開放,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學作品,不斷豐富和拓展了河北文學傳統(tǒng)的內涵和外延,為人民群眾提供了豐富精神食糧,向世人展示了燕趙文化的獨特魅力。就整體而言,新時期以來的河北當代文學呈現(xiàn)出怎樣的一種發(fā)展態(tài)勢?與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文壇層出不窮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潮(諸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派、先鋒派、新歷史主義、新寫實主義、實驗小說、女性小說、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等)相比,這一時期河北文學存在哪些優(yōu)勢與不足呢?
郭寶亮:新時期以來的河北當代文學,從總體上呈現(xiàn)出堅守與發(fā)展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的態(tài)勢。現(xiàn)實主義是河北文學的堅實底色,一代代的河北作家一直堅守在現(xiàn)實主義的旗幟下,為中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貢獻智慧和力量。我們單以小說為例來說明這一問題。新時期以來以鐵凝為旗幟的河北文學與時代共呼吸,既繼承堅守著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又不斷地創(chuàng)新發(fā)展,成為河北文學繼往開來、走向全國乃至世界的一種風向標。“香雪”時期的鐵凝以“香雪般善良的眼睛”在細微處尋找真善美,在日常生活中謳歌理想。善良、美好、溫馨構成鐵凝早期創(chuàng)作的基調,細膩、恬靜、雅致構成了她的基本風格。而“玫瑰門”時期的鐵凝一改那種單純地在生活中尋找真善美的沖動,而是深入生活的細部,深入人物復雜的內心,試圖全方位、復雜地表現(xiàn)生活,加強了對生活復雜性的展示。小說中塑造的司猗紋是中國當代文學人物畫廊中不可多得的形象之一。到2000年,長篇小說《大浴女》實現(xiàn)了鐵凝所追求的“復雜的單純”的藝術境界。2006年,長篇小說《笨花》,則是鐵凝走向藝術綜合階段的集大成之作。對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堅守,是這部作品的基本主題之一。
賈大山的《取經》率先獲得全國大獎,之后的“夢莊系列”“古城系列”在現(xiàn)實主義的底色里,融入中國古代筆記小說傳統(tǒng),豐富了現(xiàn)實主義的文化底蘊。陳沖的小說一直把城市工業(yè)企業(yè)的改革作為重點,直面現(xiàn)實,在正面謳歌改革生活的同時,又不回避現(xiàn)實中的矛盾,常從一個側面來反映時代前進的步伐,敏銳地捕捉到改革過程中各種人物的精神世界及其嬗變,并由此形成了他小說藝術的特色。被稱為“三駕馬車”的何申、談歌、關仁山成名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他們的小說關注國有企業(yè)與鄉(xiāng)鎮(zhèn)的困境,表現(xiàn)改革進程中出現(xiàn)的種種矛盾,在當代文壇掀起了一場“現(xiàn)實主義的沖擊波”。胡學文、劉建東、李浩、張楚被稱為“河北四俠”,這主要是從他們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上來考量的。正是“河北四俠”將先鋒小說的寫作因素與河北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傳統(tǒng)結合起來,使得這一傳統(tǒng)具有了新的質素。另外,何玉茹、阿寧、賈興安、劉榮書、曹明霞以及后來的年輕寫作者們,都在為豐富現(xiàn)實主義的內涵作著自己的貢獻。
新時期河北文學的優(yōu)勢就是現(xiàn)實主義。但其不足也在于有些作家固守多,創(chuàng)新少,以至于缺少了向世界文學學習的環(huán)節(jié),阻礙了現(xiàn)實主義的更新和良性發(fā)展。
三
趙振杰: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fā)展新的歷史方位。在這樣的歷史和時代背景下,隨著傳播介質和傳播形式的新變,學界適時提出了“新時代文學”的概念。河北作家迅即做出響應,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積極參與到“新時代文學”構建進程之中。關仁山繼“農民三部曲”之后先后推出《金谷銀山》《大地長歌》《白洋淀上》等長篇,在全國文壇產生巨大反響,《多瑙河的春天》《最美的青春》《太行沃土》《金銀灘》《綠色奇跡塞罕壩》《大山教授》《風中的旗幟》等一大批優(yōu)秀的現(xiàn)實題材作品不斷涌現(xiàn)。從“新時期文學”到“新時代文學”,其內涵上發(fā)生了哪些本質性的變化?如果讓您來定義“新時代文學”,您會給出哪幾個關鍵詞?為什么是這幾個關鍵詞?
郭寶亮:事物的發(fā)展總是要經歷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的辯證發(fā)展過程。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時期”的文學屬于“正”,新時期文學則屬于“反”,那么,新時代文學是“合”,即否定之否定。這種“合”是對前兩個時期文學的整合與繼承性的揚棄。如果要用幾個關鍵詞來表述的話,我覺得是不是可以用這樣幾個詞語,即人民性、當代性、綜合性、開放性。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把人民利益放在最核心位置,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文學也不例外,人民性是文學的核心。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文學表現(xiàn)生活,就是要表現(xiàn)人民的生活。當代性有兩個涵義,一是指當下性,二是指變動性。新時代文學的當下性首先要表現(xiàn)人民當下的火熱生活以及喜怒哀樂,其次是要寫出人民群眾生活的可能性,這種瞬息萬變的可能性既植根于歷史,又生長于未來。綜合性則是兼收并蓄,把所有有利于文學發(fā)展的因素都加以綜合,形成新的美學范式。開放性則指新時代文學應該立足民族,面向世界,以博大的胸懷、強烈的民族自信向世界開放。
趙振杰:近年中央高度重視哲學社會科學工作,2016年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了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新要求。那么在立足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河北篇章的理論與實踐探索中,“重寫”百年河北文學史,進而完成對經典作家作品的再解讀、再闡釋和價值重估,日益成為河北人文社科領域普遍關注的熱點議題。據(jù)我所知,目前您正在開展的一個國家級社科項目是關于王蒙文學批評與新時期文學變革研究的。該項目進展情況如何?您研究過程中面臨的最大挑戰(zhàn)是什么?
郭寶亮:重構“人民文藝”的總體性視野,建立科學、完整的文學評價體系和正確的價值取向,是目前迫切的任務。我的項目目前已經結項,明年可望出版。目下王蒙研究已成為熱點,但大部分研究還是從作為作家的王蒙入手,關于批評家王蒙,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我認為王蒙不僅僅是著名作家,還是頗具眼光的批評家。從2020年出版的50卷本《王蒙文集》看,幾乎有一半的文字可以看作是批評文字。王蒙寫過大量的對當代作家作品以及文學思潮現(xiàn)象的批評,也有對《紅樓夢》、李商隱的研究專著,還有對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國學的研究專著問世,這些研究實際上可看作是批評。有人把王蒙的批評看作印象感悟式的批評,我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王蒙的文學批評表面上看是印象感悟式的,但實質上是體驗式的,王蒙的批評是以生命體驗和作家創(chuàng)作體驗進入批評對象的。這些體驗式的批評,雖然是在場的批評,但始終以對體驗的歷史經驗作為內在參照,我稱其為“內面歷史化”。內面歷史化是說王蒙以歷史親歷者的身份觀照批評對象,這就使得王蒙的批評既是主觀的有溫度的,又是客觀的理智的。這對于當下文學批評生態(tài)日益歷史化、史料化、外向化的現(xiàn)狀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趙振杰:好,感謝郭老師的交流分享,這次向您請教關于河北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淵源與流變,受益頗豐,也期待您的研究成果盡早出版,早日惠及學界和文壇。
編輯: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