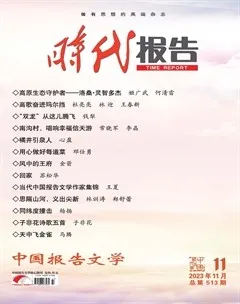布谷鳥(外一篇)
王山根

每到暮春和初夏,布谷鳥就準時從南方遷徙到豫北平原,一天到晚在村莊和田野上空鳴叫不已,即使人們進入夢鄉,也還在時不時地啼叫幾聲,給寂靜的夜晚增加幾分深沉。那聲音渾厚悠長、韻律十足,或由遠及近,或由近及遠,如天籟之音,似琴弦和鳴,給人一種酣暢淋漓、親切自然的感覺。
布谷鳥是杜鵑科鳥類的一種,也叫大杜鵑。在我們老家最常見的是兩聲布谷鳥和四聲布谷鳥,兩聲布谷鳥的叫聲好似“布谷、布谷”,一次有兩個音節;四聲布谷鳥的叫聲好像是“布谷布谷”“割麥種谷”,一次有四個音樂節。老家人根據布谷鳥的叫聲,特別是四聲音符,對比眼前的農事,又給它的叫聲賦予了新的涵義:“光棍好苦,光棍好苦。麥子該割,高粱該鋤。”仔細聽聽,還真是這么一回事。于是,便按照布谷鳥的溫情提示,抓緊安排農事活動,以防錯過了節氣,耽誤了農時。
實際上,人們在與大自然的朝夕相處中,常常把草木枯榮、候鳥遷移、昆蟲出沒、物候變化等自然現象與農事活動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生生不息的農耕文化,在推動和延續我國農耕文明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布谷鳥是農耕文化的代表,是名副其實的時令預報員和鄉村歌唱家。
關于布谷鳥,還有一個美麗的神話故事。相傳周朝末期,蜀王杜宇稱帝,號望帝。當時楚國荊州有個叫鱉靈的人,死后尸體逆江而上,至蜀復活,并被望帝立為宰相。望帝在位期間玉壘山暴發了兇猛洪水,于是他派鱉靈鑿山疏洪,造福黎民百姓。望帝自感功德不如鱉靈,就讓位于他,自己到西山隱居修道。望帝是一個非常勤勉清明的君王,當他看到有人整天沉湎于樂,心急如焚。為了不誤農時,每到春播時節,他就四處奔走呼號,催促人們趕快播種。后來望帝積勞成疾,不幸去世,他的靈魂化成一只小鳥(即杜鵑鳥),每到春天,都要呼喚人們“布谷、布谷”“快快種谷”。古人因見布谷鳥嘴上有一塊紅斑,認為它是苦啼流出的鮮血,而此時正是杜鵑花盛開的季節,杜鵑花的紅色乃布谷鳥鮮血所染。《全唐詩》就有“杜鵑花與鳥,怨艷兩何賒。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之說,李商隱“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的詩句,也引用了“杜鵑啼血”的故事。傳說固然不是歷史,但有歷史的影子,人們對布谷鳥的喜愛,蘊含著樸素的歷史情感。
布谷鳥上體灰色,嘴呈紅色,尾偏黑色,腹部近白而具黑色橫斑,比鴿子瘦長,與斑鳩相仿,常以昆蟲為食,是有名的森林益鳥,像松毛蟲、毒蛾等其它鳥類都不敢吃的昆蟲,對布谷鳥來說卻是口中美餐。李時珍曾曰:“杜鵑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狀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啼,夜啼達旦,鳴必向北,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其聲哀切。田家候之,以興農事。惟食蟲蠹,不能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則藏蟄。” 2000年8月,布谷鳥被列入《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
布谷鳥以其獨特的魅力,攪動了不少詩人的情懷。如杜牧“繁艷歸何處,滿山啼杜鵑”,借布谷以傷春。杜甫“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寫盡春之凋零。秦觀“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里斜陽暮”,用布谷抒發謫居凄怨。讀到這些優美的詩句,仿佛穿越千年時空,看到了布谷鳥在樹枝上跳躍。
五月的田野,絢麗多姿。一望無際的麥田,如同鍍上了一層黃金。堅實飽滿的麥穗,昂首挺胸,在麥浪中搖曳,仿佛是一群群急待出征的勇土。漫步在田間小路,聆聽著布谷鳥悠揚曠遠的啼鳴,享受著五月風柔和多情的吹拂,呼吸著泥土里散發出的悠悠芳香,別有一番風味。
煦誠是我們村里的老光棍,因家中弟兄多、負擔重,40多歲還沒有娶上媳婦。生產隊長看他老實能干,責任心強,便讓他擔任生產隊的飼養員。為便于生產和防火,當時的生產隊都在離村較遠的地里建有各自的打麥場,而且都是將飼養棚建在打麥場旁邊,煦誠幾乎都是一年到頭吃住在場院。農忙時,場院里干活的人多,非常熱鬧,但到了夜晚,干活的人回家了,只剩下他和看場的人,就顯得無聊了。特別是在農閑時,場院里來的人更少,他和看場的人晚上都是天南地北侃大山,直到說得兩眼打架,困得不行才睡覺。那時農村沒有電視機,收音機也沒有幾臺,煦誠躺在床上,也只能瞪著眼睛看房頂,與飼養的牛、馬、驢、騾為伴。布谷鳥也不解人情,常常站在場院的鉆天楊上,一聲聲叫著“光棍好苦、光棍好苦”,直叫得他心煩意亂。
有一天村里的張媒婆找到他娘,說鄰村的一個腿腳不靈,但長得耐看的閨女想找戶人家,看看家里有沒有這種意向。煦誠娘感覺好歹煦誠能有個伴,比打光棍強,于是便應承了這門親事。剛開始,煦誠也是不愿意,但拗不過他娘,只好聽從母親的安排。我們那里有一個風俗,新人結婚當天晚上是要喝圓房酒的,同輩份或低一輩的年輕人還要聽房。如果沒人聽房,就意味著這家人氣不旺。煦誠結婚當天晚上,新媳婦不但不喝圓房酒,而且也不脫衣睡覺,鬧出了一場笑話,讓村里人至今成為閑談的笑料。幾個月后,煦誠感到和她在一塊兒別別扭扭,就離了婚,一直到老沒有再婚。后來,有幾位愛開玩笑的人都說是布谷鳥啼叫讓煦誠打了光棍,慫恿他把打麥場樹上的布谷鳥轟走,以圖吉利,但煦誠卻說,布谷鳥就是一只小鳥,沒有罪,它愛咋叫就咋叫吧。
進入21世紀信息化時代,老家人已不再局限于用老黃歷、老經驗來安排農事,而是更多地依靠科技力量發展農業生產,但對布谷鳥的如約而至,還是非常喜歡和稱贊的。每年,它依然是那么的執著,那么的忙碌,那么的急切,以大地為舞臺,呼喚著一座座村莊在晨曦中蘇醒,導調著一幕幕農耕大戲在田野里上演。
鵪鶉
鵪鶉是一種雉科動物,形似雞雛,頭小尾禿,身呈褐色,并帶有明顯的草黃色矛狀條紋及不規則斑紋。我國是鵪鶉的主要產地之一,也是飼養野鵪鶉最早的國家。早在春秋時期的《詩經》中就有“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的詩句。戰國時代,鵪鶉被列為“六禽”之一,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珍味佳肴。清朝貢生陳面麟所著《鵪鶉譜》,分別敘述了44個鵪鶉品種的特征特性,詳細介紹了飼養方法及37種宜忌事項,對我國養殖鵪鶉起到了顯著的推動作用。
鵪鶉性甘、平、無毒,營養豐富。我國醫學認為,鵪鶉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膽固醇食物,非常適合中老年人及營養不良、體虛乏力、貧血頭暈、腎炎浮腫、瀉痢、高血壓、肥胖癥、動脈硬化癥等患者食用。鵪鶉蛋所含蛋白質,維生素B1、B2,卵磷脂、鐵等均高于雞蛋,有補益氣血之作用。《本草綱目》曰:“肉能補五臟,益中續氣,實筋骨,耐寒暑,消結熱”,“肉和小豆、生姜煮食,止泄痢、酥煮食,令人下焦肥。”
在我的記憶里,小時候老家農村養殖鵪鶉的人家不多,但玩鵪鶉的人不少。這些人年齡大都在50多歲,而且玩的鵪鶉都是清一色的野生雄性鵪鶉,主要用途是為了讓鵪鶉打斗,以分勝負,借此打發時光,換取娛樂。老家人將這種比斗叫做“斗鵪鶉”。斗鵪鶉,是豫北地區農村常見的一種娛樂活動。這種活動始于唐宋,盛于明清,但什么時候興于我們那里就無從考證了。據老輩子人講,他們記事的時候就有這種活動,屬于輩輩相傳。
斗鵪鶉一般安排在春節期間進行,這時候的鵪鶉經過喂養、馴化,斗性和體質達到最佳狀態,加上村里人除了走親戚,比較閑暇,觀看的人多,氛圍濃厚,能為節日增添不少樂趣。
你別看鵪鶉這個小家伙其貌不揚,但個性極強。雄性鵪鶉善斗,給人一種酣暢淋漓的感覺和強勁的沖擊力;雌性鵪鶉溫順,像一團可愛的繡球,可當作誘餌捕逮雄性鵪鶉,這也是人們喜歡鵪鶉的重要原因。
鵪鶉按照其年齡和身上的羽毛,區分為處子、早秋、探花、白堂四種。在這四種鵪鶉中,只有白堂會格斗。斗鵪鶉都是選在早上,在一間空房子里舉行,一來可以防止鵪鶉飛跑,二來空間較大便于人們觀戰。此時的鵪鶉餓了一晚上,食欲很強。比賽時,雙方主人把鵪鶉放在事前準備好的一張簸籮里,簸籮底部鋪上一層被單,被單上面放上一點鵪鶉喜歡吃的谷子,然后各自手持鵪鶉,相互挑釁,讓鵪鶉因搶食而爭斗。俗話說:“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鵪鶉為了爭奪谷子,不惜一戰。但見兩只鵪鶉你撲我,我撲你,你咬我一口,我啄你一下,無影腳、滾地龍、回馬槍、鎖喉……招招致敵,殺氣騰騰,驚心動魄。嘴巴、下巴、脖子、眼睛,都是攻擊的對象。脾氣暴猛的鵪鶉,有時還會咬住對方猛然起身,嘶下一撮羽毛,引得觀眾連聲叫好,手舞足蹈。如果其中一只鵪鶉不斗了,在簸籮中被對方追得亂跑,就證明戰敗了。鵪鶉身段較小,體力不大,多是一場決斗,一兩分鐘就結束了,但決斗后的鵪鶉大都是羽毛受損,血跡斑斑。這時獲勝者的主人情緒激昂,興奮異常,臉上露出止不住的喜悅,小心翼翼地將“戰將”拿到手中仔細撫摸。村里人再見到他時,常會說:“某某鵪鶉真厲害!”說得他心花怒放,得意洋洋。而敗下陣的一方主人,卻情緒低落,無精打采,索性將斗敗的鵪鶉送給我們小孩子玩。咬敗的鵪鶉斗敗的雞,鵪鶉一旦被咬敗后,一生都不敢和其它鵪鶉斗架,再飼養也沒有多大意義了。他們會捕逮新的雄性野生鵪鶉,馴化完后再把它送上戰場。
捕逮雄性野生鵪鶉是有技巧的,長庚哥是我們村有名的捕逮高手,在四鄉八村也很出名。我們村西有一大片離村莊較遠的土地,平時除了干農活,很少有人涉足。因比較偏僻,生活在這里的飛鳥走禽較多。每年秋收過后,玉米、谷子、高粱等農作物收割進場,只剩下一塊塊沒有開完桃的棉花孤苦零丁地長在地里。鵪鶉、野兔等無處可藏,棉花地成了它們的棲息地。長庚哥經常帶著他的幾個好友踏霜冒寒,半夜就趕到了棉花地,在地北頭支起一張十幾米長的大網。他和其中的一個人留下看守大網,“哧喳哧哧喳”模仿著雌性鵪鶉求愛聲吸引雄性鵪鶉,其他人從棉花地的南頭扔著細碎的坷垃塊轟攆熟睡的鵪鶉。鵪鶉被驚醒后,會飛向雌性鵪鶉鳴叫的方向,一頭碰撞在沾網上。長庚哥麻利地抓住鵪鶉,將它放進鵪鶉袋里。這樣,一個晚上能逮上幾只。當然也會有撲空的時候,按照他們的說法,就只當是一次演練罷了。
逮來的鵪鶉,主人并不會立即讓其參戰,而是挑選最好的雄性鵪鶉,放到特制的籠子里,進行一段時間的飼養和馴教。黑嘴白胡須的鵪鶉品相最好,善于格斗,是首選;其次,才是黑嘴紅胡須的鵪鶉。
喂養鵪鶉的籠子是用荊條編織的,圓木托底,籠上無蓋,以布繩束口,里面襯以柔軟的布料,防止鵪鶉性躁撞頭,并經常掛在腰間,時不時取出鵪鶉玩上幾下。
所謂玩,其實就是對鵪鶉耐心調教。他們會把鵪鶉握在手中,將它的兩腿夾在小指和無名指之間,使其兩爪懸空,拇指和食指夾住頸部,使得鵪鶉既舒服又不至于跑掉,并帶它到各種場合,以適應決斗環境,改變其怕人的習性。鵪鶉餓了或渴了,就拿點隨身攜帶的谷物,或倒點涼水置于掌心,讓其啄、喝。有的為培養鵪鶉的暴躁性格,有時還會采用讓其聞臭襪等辦法,加以訓教。等到鵪鶉完全聽從了主人的把控,才開始考慮什么時候讓其參加決斗。
現在,野鵪鶉已被列為國家保護動物,加之老家農村物質生活條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各種文化娛樂活動豐富多彩,斗鵪鶉這種民間娛樂活動已經消失,但曾經的記憶還是非常清晰的。小小鵪鶉給人帶來很多歡樂,稀釋了過去的貧困、寂寥和單調,使人的心靈得到一絲慰藉。
責任編輯/石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