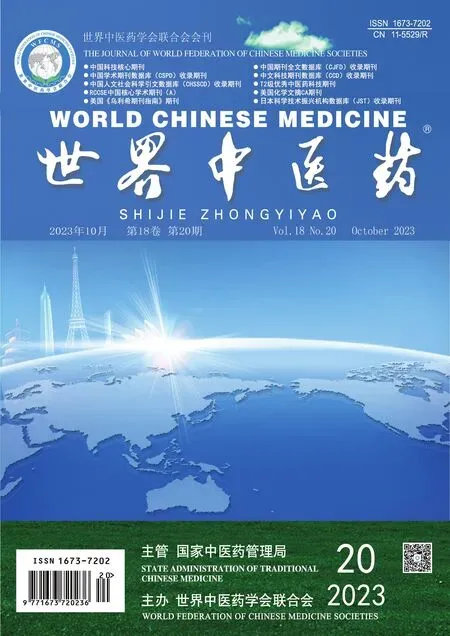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中醫病機及其診療進展
陳茉芬 崔 松 賈美君 阮小芬 楊 瑩 李 欣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心內科,上海,201203)
據流行病學調查顯示,我國高血壓呈現出“三高三低”的特點,即患病率高、病死率高、致殘率高,以及知曉率低、控制率低、治療率低,分別為51.6%、16.8%、45.8%[1]。《中國心血管病報告2018》推算中國成人高血壓患病人數為2.45億,且人數仍在呈逐年升高的趨勢[2],其中焦慮情緒是一項主要危險因素[1],高血壓合并焦慮的發生率為11.6%~38.5%[3-4]。
現代醫學模式正由“生物學”轉變為“生物-心理-社會學”[5],高血壓屬于心身疾病范疇,國內外研究發現焦慮與高血壓密切相關,焦慮障礙會增加高血壓的患病風險,高血壓患者更容易產生焦慮情緒,情緒障礙會引發患者自主神經功能的改變,[5-6]包括副交感神經的抑制、交感神經的激活,使心率增快,交感神經興奮性增高,可促進釋放兒茶酚胺類激素,導致心率增快,外周血管阻力增加和血壓升高[7]。焦慮障礙既是高血壓的促發因素,又是影響其預后的不良因素[7-8]。二者常常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引起惡性循環,預后較差。治療方面,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患者其血壓波動范圍往往較大,臨床上許多醫生因未足夠重視焦慮對高血壓的影響,單純使用常規的降壓藥物進行治療,故患者的降壓效果通常難以達到預期療效[9]。
中醫藥自古重視情志因素對疾病的影響,對高血壓伴焦慮狀態患者用安神定制、調暢情志等治療方法常可起到良好的降壓效果,現嘗試對高血壓伴焦慮狀態患者的中醫病機進行分析,總結其中醫藥診療進展,以期對高血壓伴焦慮狀態患者的臨床治療有所裨益。
1 中醫對高血壓及焦慮的認識
在中醫古籍中并沒有關于高血壓、焦慮、高血壓伴焦慮的病名,根據其臨床癥狀,高血壓歸屬于“眩暈”“頭風”“肝風”范疇。“焦慮癥”屬于情志病范疇,可歸于中醫“郁證”“臟躁”“梅核氣”等,其基本病因為情志不舒導致氣機郁滯[10],與五臟六腑關系密切。高血壓伴焦慮可歸屬于“郁證性眩暈”,表現為眩暈、精神緊張、心神不寧、胸悶、心悸、失眠、多汗等,常具有易怒、急躁、愛生悶氣、孤僻等性格特點[11],其伴隨癥狀具有廣泛性、怪異性、多樣性等特點,大多數屬于軀體化癥狀,或屬于自主神經功能紊亂[12]。
高血壓屬于雙心疾病,高血壓伴焦慮的患病率也呈逐年升高趨勢。《雙心疾病中西醫結合診治專家共識》[13]中提出雙心疾病病位在心,與肝、脾、腎密切相關。中醫學理論中的“心”不僅是西醫解剖、生理意義的心臟,還包括心理情志,其實質就是“雙心”。劉倩[14]研究發現,高血壓伴焦慮患者中大多數為肝郁痰阻型,占47%,其次是占23%的陰虛陽亢型,再是分別占13%、10%、7%的肝火亢盛型、陰陽兩虛型、心脾兩虛型。
2 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中醫病因病機
中醫認為,眩暈的主要病因是體質、年老、情志、飲食和過勞[15],其主要發病機制是肝火亢盛,主要病理因素是痰濁[16],多與心、肝、脾、腎相關。古代醫家認為“無痰不作眩”“無虛不作眩”,故眩暈常見于痰濕質、陰虛質、陽虛質人群[17-18]。痰濕質的人群先天稟賦不足,加之后天飲食不節,脾失健運而致氣血津液運化失司,濕聚成痰,壅阻脈道,營血壅盛,氣機失暢而致血脈壅滯,血壓則出現波動[19]。陰虛質人群多數是因臟腑功能失調,體內陰液不足,出現陰虛生內熱的證候,陰虛不能制陽,虛陽上越,故見血壓升高[20]。陽虛質患者多因臟腑功能失調,陽氣不足而生里寒,寒凝血瘀或脈絡絀急,引起血壓上升[21]。
郁證主要病因是七情、體質和外界因素刺激,郁證日久常導致心、肝、腎等臟腑出現虧損的癥狀,不止是單一的臟腑功能異常,其病因病機主要在心-肝-腎軸上,《王孟英醫案》中提到“肝主一身之氣,七情之病必由肝起”,情志病多與肝臟相關,肝失條達,疏泄不暢,氣機郁滯,郁而化火。肝郁化火是其病機關鍵,氣血不足、陰虛火旺是病理轉歸[22-23],“氣”“火”“痰”是主要的致病因素。
由此可見,眩暈和郁證的病機都有痰與虛,皆與肝密切相關。高血壓伴焦慮患者多為久病或年老體虧者,其腎精虧虛,水不涵木而致肝氣郁結。眩暈與郁證二者又相互影響、促進,現代醫家周世章、蔣健提出“無郁不作眩”的觀點[24-25]。部分痰、虛皆因郁而成,“痰”“虛”為標,七情郁結為本,肝、脾、心、肺等臟氣受損可致情志郁結,氣血虧虛,進而發展為眩暈。而惱怒傷肝、郁結傷脾、焦思勞心、悲號傷肺等情志因素也可導致眩暈的發生,而眩暈日久,病情遷延不愈,患者身心俱勞,情志不舒,也會加重氣機郁滯而致郁證。《丹溪心法·六郁》云:“人身諸病,多生于郁。”六郁包括氣、血、痰、濕、火、食,其中以氣郁為本,氣郁又以肝郁為本,“一有怫郁,諸病生焉”。
3 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中醫治療
3.1 藥物治療
中醫藥具有一定的調節血壓、改善焦慮情緒的作用,且能有效改善高血壓伴焦慮患者的各種臨床癥狀[26]。中醫臨床上治療高血壓伴焦慮有古方治療、單方治療、經驗方治療或中成藥治療等不同方式,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臨床研究數據也表明,不管是單獨應用中藥還是與降壓藥、抗焦慮藥聯用,中醫藥均能表達出良好的臨床效果,同時安全性較高。
有醫者認為,肝郁痰阻是高血壓伴焦慮的主要病機,虛證也占一定比例,故理氣化痰補虛是該病重要治法[14]。從肝、從痰、從虛論治眩暈伴郁證皆有七情不遂的病因,又屬于從郁論治的范疇。
3.1.1 從肝論治 《類證治裁》記載“木郁則化風,為眩。”木氣被郁,肝失疏泄,郁而化風致眩,氣機上逆,而致血壓升高[27]。張宇峰[28]用解郁平肝湯治療30例高血壓合并肝郁化火型焦慮癥,在有效改善患者焦慮癥狀的同時,使其血壓也控制在正常范圍,發現此方通過抑制血管運動中樞神經、阻滯交感神經,從而起降壓作用。有研究證實柴胡疏肝散加減可以明顯降低焦慮自評量表、降低血壓[29-30]。方中柴胡具有疏肝作用,常被用于治療和情緒相關疾病。現代藥理學研究證實柴胡中提取的總柴胡皂苷(Total Saikosaponins,TSS)具有抗焦慮作用[31],柴胡提取物及柴胡類方劑可調節中樞腎上腺素,使得血神經肽Y(Neuropeptide Y,NPY)、去甲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NE)水平下降[32]。LEE等[33]研究也發現柴胡提取物可能是通過中樞腎上腺素能機制發揮作用,顯著減少焦慮樣行為。從肝論治高血壓伴焦慮患者,能有效穩定患者血壓,緩解焦慮癥狀,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
3.1.2 從痰論治 張娜等[34]收取74例氣虛痰濁型高血壓患者,在拉西地平降壓治療基礎上加用赭決七味湯加減(代赭石、草決明、黃芪、五爪皮、白術、茯苓、法半夏、陳皮、竹茹、甘草),發現方中的草決明浸出液、黃芪提取物具有降壓作用,代赭石對中樞神經系統有鎮靜作用。諸藥合用,通過改善血管內皮功能達到降壓療效,同時能明顯改善患者的焦慮狀態,提高生命質量。研究發現用半夏白術天麻湯與溫膽湯加減治療痰濕壅盛型原發性高血壓能改善患者的血管內皮功能,促進血壓恢復正常,減少血壓波動,同時還能有效改善患者的頭暈、焦慮等臨床癥狀[35-37]。現代藥理研究發現溫膽湯加減方具有鎮靜、安神、抗驚厥的作用,在治療痰熱內擾型廣泛性焦慮方面取得較好療效[38]。張素香和周虹[39]研究發現用健脾化痰法治療痰濕中阻型高血壓,能有效改善患者眩暈、氣短、胸悶、頭痛等臨床癥狀,而健脾化痰法配合疏肝法應用于肝郁痰擾型廣泛性焦慮癥,可使患者焦慮癥狀得到明顯改善[40]。
3.1.3 從虛論治 顧寧教授認為,高血壓合并焦慮的病機應以脾腎之虛為本[41],故臨床可以固本培元、補益心脾之法辨證論治此病[42]。肖艷春[43]納入60例陰虛火旺型高血壓伴焦慮患者,在常規的降壓藥物基礎上加載酸棗仁湯加減治療,該方在酸棗仁湯基礎上加用滁菊、白蒺藜等藥疏肝解郁,方中的酸棗仁具有擴血管、安神的作用[44],能有效平穩控制血壓,改善心煩血虛的焦慮狀態。研究結果發現,此法降壓總有效率、漢密爾頓焦慮量表減分率均明顯高于對照組,漢密爾頓焦慮量表評分改善更明顯(P<0.05)。研究發現用平肝脈通片治療陰虛陽亢型高血壓伴焦慮患者能降低患者動態血壓水平及漢密爾頓焦慮量表評分,有效改善患者的焦慮狀態及臨床癥狀[45-46]。孫忠義[68]從腎氣虛角度出發,在抗高血壓治療基礎上,用安心湯聯用鹽酸帕羅西汀治療高血壓伴焦慮狀態患者,該方主要以淫羊藿、生黃芪、杜仲、槲寄生、懷牛膝、益智仁等藥組成,全方補腎益氣為主。結果顯示,該法不僅在改善高血壓伴焦慮狀態患者的焦慮狀況、中醫癥候方面均優于單獨使用鹽酸帕羅西汀,且此法的不良反應較少,還可以緩解用鹽酸帕羅西汀治療帶來的不良反應,可減毒增效。
中藥降壓療效與西藥比較,雖不如其速度快、作用強,但中藥的作用是多靶點的,并且能夠兼顧眩暈、焦慮等其他癥狀,在提高高血壓伴焦慮狀態患者的生命質量,保護靶器官方面有獨特的優勢。采用中醫方法治療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臨床效果良好,其具有療效穩定、不良反應少、療效高等優點,在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提高其生命質量方面具有積極意義。
3.2 非藥物治療
研究顯示[47],對高血壓伴焦慮患者給予藥物治療的基礎上結合中醫非藥物治療,包括針灸、中藥貼敷、音樂療法、運動干預等,同時進行心理干預,不僅能改善高血壓患者的焦慮情緒,還有利于血壓的控制;不但能提高降壓療效,減少患者的服藥劑量與藥物的不良反應,還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提高其生命質量,降低疾病進展的危險因素,減少并發癥的發生。
3.2.1 針刺 《靈樞·海論》云:“膻中者,為氣之海……前在于人迎。”氣血兼顧,標本同治,才能平秘陰陽。石學敏院士[43-44]在臨床治療高血壓時常選取人迎穴作為的主要穴位,利用針刺理血治本,調氣治標,其“活血散風”針刺法可通過改善焦慮抑郁狀態來達到降壓目的。孔莉等[45]將120例原發性高血壓伴焦慮狀態患者隨機分成2組,每組60例。對照組給予非洛地平緩釋片口服治療,觀察組在予以非洛地平緩釋片口服的基礎上加用針刺治療,以人迎穴為主穴,配以合谷、曲池、太沖、足三里等穴,以24 h動態血壓、漢密爾頓焦慮量表、焦慮自評量表為觀察指標,治療60 d后發現,針刺在降壓、緩解患者焦慮狀態方面均等取得一定療效。通過針刺人迎、太沖、足三里等穴位使氣血調和、平沖降逆,降低患者血清腎素、血管緊張素Ⅰ、醛固酮濃度,達到穩定血壓的目的,同時改善患者的壓力反射敏感性,有效改善其焦慮狀態[48-50]。林子舒[51]對原發性1、2級高血壓患者給予西藥聯合針刺調神法治療,本法注重臟腑、氣血同調,改善患者外周阻力、血流動力學狀態,通過調神,又使患者的焦慮狀態以及睡眠質量均得到改善。針灸作為中醫特色療法,具有綠色、安全、多層次調節等優點。
3.2.2 五行音樂療法 音樂治療學是一門集音樂、醫學、心理學為一體的綜合性應用學科[52],中醫的五行音樂療法也是情志干預法的一種。“音樂可以通人地而合神明”音樂療法是用音樂的陰陽屬性來平衡陰陽,使機體達到“陰平陽秘”的狀態[53]。
劉安梅[54]對26例高血壓合并焦慮抑郁的老年患者給予降壓藥聯合音樂療法治療,與25例僅使用降壓藥的對照組比較,研究發現,聯用音樂療法對患者的降壓作用及焦慮抑郁狀態的緩解療效顯著。張敏和欒美君[55]將200例高血壓患者隨機分為100例觀察組和100例對照組,對照組予以常規降壓治療,觀察組在此基礎上加用五行音樂進行治療,研究發現,觀察組收縮壓值、舒張壓值、焦慮自評量表評分均下降,且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五行音樂療法能改善患者的血管內皮功能及中樞神經遞質水平,從而起到降低血壓和改善患者焦慮狀態的作用[56],是一種安全、無創且具有成本效益的非藥物治療法[57]。
3.2.3 養生功法 我國傳統養生功法太極拳、五禽戲、易筋經、八段錦等是我國醫療體育的瑰寶,能夠調暢臟腑經絡功能,疏經通絡,降壓作用較為可靠。養生功法皆屬于有氧運動,能增強人體的心肺功能以及機體適應能力,醫療運動可使交感神經的驅動作用減弱,迷走神經張力增加,小動脈痙攣緩解,有效輔助藥物降低血壓,是高血壓的非藥物治療方法之一,又有一定的改善患者焦慮狀態的作用[58-61]。
王曉斌和葉鷺萍[62]選取100例伴焦慮狀態的原發性高血壓患者,隨機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50例。對照組予以常規治療,觀察組在此基礎上結合太極拳練習,干預3個月后發現太極拳運動可有效輔助調控高血壓伴焦慮患者的血壓水平及改善其焦慮狀態,提高生命質量。現代研究發現,長期習練八段錦、三線放松功可有效防止、減緩高血壓的發生,降低高血壓患者的血壓,在緩解焦慮方面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63-66]。PONTE等[67]對24例干預組予以正念冥想訓練,18例觀察組患者予以健康教育講座,學習健康知識。8周之后發現,接受正念冥想的患者在控制動態血壓方面有明顯益處,患者臨床測量的收縮壓、24 h收縮壓、靜息收縮壓和舒張壓值均較對照組低,且患者的焦慮狀態得到改善。
4 問題與展望
現代醫學模式正轉變為“生理—心理—社會”的醫學模式,此觀點與中醫學“形神合一”的整體觀念不謀而合。東漢時期的華佗曾云:“善醫者先醫其心,而后醫其身,其次則醫其病。”在多角度、多層次治療患者軀體癥狀的同時,還要重視精神心理的健康,對于雙心疾病患者,“先醫其心”進行心理干預,減輕心理負擔,再配合中藥、西藥治療,輔以針刺、導引、五行音樂療法等中醫特色療法,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方式來治療高血壓伴焦慮狀態患者,身心同治,能達到雙重治療的目的。
中醫藥治療高血壓伴焦慮狀態能有效改善其臨床癥狀,縮短療程,充分體現中醫藥治療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研究價值以及廣闊前景。同時也存在下列問題:1)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中醫病名、病因病機以及辨證缺乏統一認識,隨著現代飲食、生活方式的改變,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病因病機是否發生改變?2)臨床質量相對較低,大部分文獻未對隨機、盲法的方法進行闡述、說明,較少文獻對于中醫藥治療高血壓伴焦慮狀態的不良反應進行系統觀察,較少研究涉及多中心等,在今后的科研設計中有待改進。3)臨床證據等級有待提高,中醫藥是否能降壓、降壓幅度、焦慮狀態改善程度如何,降壓、改善焦慮的療效能否被指南所認可,4)缺乏長期隨訪,對靶器官損傷的監測及干預后評估,需開展大樣本、隨機、雙盲的更深層次的隨機對照試驗。
利益沖突聲明: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