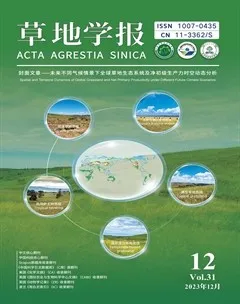放牧背景下短花針茅荒漠草原研究進展
康薩如拉,韓國棟,趙萌莉,張 霞,張燦浩,劉仰喬
(1.內(nèi)蒙古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草原與資源環(huán)境學(xué)院,草地資源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內(nèi)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2.內(nèi)蒙古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植物學(xué)國家級實驗教學(xué)示范中心,內(nèi)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內(nèi)蒙古荒漠草原是我國北方草原重要的組成部分,荒漠草原處在草原向荒漠過渡的地帶,是變異性最大,最脆弱的草地生態(tài)系統(tǒng)[1]。由于該區(qū)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嚴(yán)酷性和氣候的波動性,荒漠草原是易受外界干擾且對環(huán)境變化敏感的生態(tài)系統(tǒng)[2-3]。了解荒漠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和功能及其對外界環(huán)境的響應(yīng)是理解脆弱生態(tài)系統(tǒng)適應(yīng)的有效途徑。近年來,氣候的持續(xù)變化和過度的人類干擾,尤其過度放牧加劇了荒漠草原退化,使得荒漠草原生態(tài)質(zhì)量持續(xù)下降,退化問題日趨嚴(yán)重[4-5]。近20年,前人開展了一系列放牧利用狀態(tài)下荒漠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和功能的研究,并取得了諸多成果。本文總結(jié)了近20年相關(guān)研究的關(guān)鍵發(fā)現(xiàn),對放牧背景下的短花針茅(Stipabreviflora)荒漠草原研究進展及得到的相關(guān)結(jié)論進行了綜述。旨在探討荒漠草原區(qū)何種放牧利用方式及強度不僅可以提高家庭凈收入,啟動草原恢復(fù)進程,還能將草原保持在牧草質(zhì)量的臨界值以上的同時,可以實現(xiàn)更好的草原管理。
1 研究區(qū)分布及放牧概況
前人對放牧背景下短花針茅荒漠草原的研究區(qū)主要分布在寧夏鹽池縣草原資源生態(tài)監(jiān)測站和內(nèi)蒙古荒漠草原區(qū)。內(nèi)蒙古荒漠草原區(qū)的研究樣地主要分布在內(nèi)蒙古四子王旗短花針茅荒漠草原放牧試驗平臺(111°53′46″E,41°47′17″N)、內(nèi)蒙古蘇尼特右旗朱日和鎮(zhèn)(112°47′11.2″E,42°16′26.2″N)及內(nèi)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荒漠草原試驗區(qū)(106°41′~108°54′E,38°18′~40°11′N)。植被類型均為以短花針茅建群的荒漠草原。
四子王旗放牧實驗平臺是從2004年6月開始建立的放牧試驗基地,共設(shè)置了4個放牧強度:對照區(qū)(CK)、輕度(LG)、中度(MG)和重度放牧區(qū)(HG),每個處理設(shè)置3個重復(fù),共計12個小區(qū);鄂爾多斯市鄂托克旗荒漠草原研究樣地共劃分3個試驗區(qū):禁牧區(qū)(不放牧,2011年起禁牧的國家定位觀測點)、適度放牧區(qū)(載畜率為0.75只羊·hm-2,短期休牧點)和重度放牧區(qū)(載畜率為1.5只羊·hm-2,為自由放牧區(qū));而內(nèi)蒙古蘇尼特右旗朱日和鎮(zhèn)研究基地是結(jié)合無放牧、適度和重度3種放牧強度及禁牧、季節(jié)性休牧和輪牧等不同放牧制度的研究樣地。
2 不同放牧利用方式及強度下荒漠草原生態(tài)系統(tǒng)結(jié)構(gòu)和功能的變化
2.1 植物個體上的變化
2.1.1解剖結(jié)構(gòu)的變化 關(guān)于荒漠草原植物解剖結(jié)構(gòu)變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2個方面,首先是大的空間尺度上植物解剖結(jié)構(gòu)和氣候因子的關(guān)系[6]。康薩如拉等[7]對來自內(nèi)蒙古8個樣地的短花針茅葉片解剖結(jié)構(gòu)進行矢量化并分析了其與氣候因子之間的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短花針茅具有典型的旱生結(jié)構(gòu),如葉片卷曲、角質(zhì)層加厚,且葉片的卷曲度和葉片的高度相關(guān),位置越低葉片卷曲度越大[8]。且導(dǎo)致這種差異的主導(dǎo)因子并非水分而是熱量。與吸收、光合和蒸散等生理特性相關(guān)的維管組織類指標(biāo)出現(xiàn)了顯著的差異,且這些變化與年降水量和年平均氣溫密切相關(guān)[7]。這種葉片解剖結(jié)構(gòu)的變異和遺傳結(jié)構(gòu)之間不存在一致性,說明大尺度短花針茅的分布不存在地理隔離,其結(jié)構(gòu)的分化主要與氣候因子有關(guān)[7]。其次是小尺度固定樣地上的長期不同放牧強度下,分析荒漠草原幾種關(guān)鍵植物的營養(yǎng)器官解剖結(jié)構(gòu)的差異,發(fā)現(xiàn)C4植物解剖結(jié)構(gòu)隨長期放牧強度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與光合能力相關(guān)的結(jié)構(gòu),如花環(huán)結(jié)構(gòu)面積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具有明顯增加的趨勢,C3植物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保護組織和輸導(dǎo)組織,例如葉片厚度、角質(zhì)層厚度、表皮細(xì)胞面積顯著加厚,導(dǎo)管面積、韌皮部面積顯著增加等[8-10]。葉肉細(xì)胞面積、莖表皮細(xì)胞面積、木質(zhì)部厚度、導(dǎo)管壁厚度隨著放牧強度減小,這可能和植物的矮小化有關(guān)[8,10]。在放牧條件下植物的超微結(jié)構(gòu)也有相應(yīng)的變化,如葉肉細(xì)胞面積、細(xì)胞壁厚度、葉綠體面積、線粒體數(shù)量和大小逐漸減小,這可能是矮化的細(xì)胞學(xué)形成機制[10]。
2.1.2植物體內(nèi)各類物質(zhì)和元素的變化 牧草和動物在生長發(fā)育過程中,牧草營養(yǎng)元素和微量元素的缺乏和過剩,都是制約其產(chǎn)品產(chǎn)量和品質(zhì)的重要因素。研究發(fā)現(xiàn),適度放牧區(qū)優(yōu)勢牧草粗蛋白質(zhì)、粗脂肪、粗灰分、磷、鈣、鐵、鈉、鎂、硒、銅等營養(yǎng)元素和微量元素的含量均高于禁牧區(qū)和過度放牧區(qū),且禁牧區(qū)和重度放牧區(qū)牧草部分元素含量近持平或低于該地區(qū)安全含量標(biāo)準(zhǔn);適度放牧區(qū)優(yōu)勢植物粗纖維、中性洗滌纖維和酸性洗滌纖維的含量低于禁牧區(qū)和過度放牧區(qū)[11-12]。植物體內(nèi)的一些元素的變化還預(yù)示著植物自身生理活動的變化,如穩(wěn)定同位素δ13C值的變化可以指示植物對有機物質(zhì)的積累和資源利用效率,尤其對水分的利用效率。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荒漠草原多年生叢生禾草和根莖禾草的δ13C值顯著減小,而一二年生植物和灌木、半灌木的δ13C值顯著增加,表明多年生禾草類的水分利用效率隨放牧強度減小,而其他植物的水分利用效率逐漸提高[13]。也有分析短花針茅葉片δ13C值的研究發(fā)現(xiàn)短花針茅葉片δ13C值隨放牧強度的增大而顯著減小,表明短花針茅水分利用效率、有機物質(zhì)的積累和資源利用能力降低[13-15]。
從生態(tài)化學(xué)計量學(xué)的角度分析植物對放牧的響應(yīng)發(fā)現(xiàn),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優(yōu)勢植物短花針茅的葉干物質(zhì)含量、葉片C,N,P含量或C/N比未呈現(xiàn)顯著差異[16-17],但是在不同放牧強度背景下增加水氮添加試驗的時候,發(fā)現(xiàn)水分添加試驗?zāi)軌蝻@著引起不同處理下植物葉片干物質(zhì)含量、葉片N含量和葉片C/N比的差異[8,18],表明荒漠草原作為水分嚴(yán)重匱乏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水分輸入的多少更能決定植物的生長發(fā)育。而同樣是優(yōu)勢植物的無芒隱子草葉片C和C/N比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呈現(xiàn)顯著降低的趨勢,葉片N含量具有增加的趨勢[19]。還有研究分析了除優(yōu)勢植物之外的其他物種的生態(tài)化學(xué)計量學(xué),發(fā)現(xiàn)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一些多年生雜類草的N含量顯著降低,但是多年生禾草和一二年生植物的N含量卻顯著增加,而C和P含量及C,N,P之間的相互比值隨放牧強度的變化因不同植物而異[20],可見這不僅和不同放牧強度及其長期不同放牧強度下形成的土壤條件有關(guān),還和不同植物的生活型、生理特性及其不同環(huán)境下的復(fù)雜生存策略有關(guān)。
2.1.3植物內(nèi)源激素的變化 植物對牲畜的采食活動做出響應(yīng),如補償性生長或超補償性生長,而這種響應(yīng)活動是由植物體內(nèi)的各種激素決定的,因此植物內(nèi)源激素在不同放牧強度下的變化可以為植物的避牧性和耐牧性研究提供可靠的機理性解釋。但是因為內(nèi)源激素的含量及其變化往往收到溫度、水分的季節(jié)動態(tài)影響,因此這類研究的野外實施非常的困難[21]。研究發(fā)現(xiàn)放牧能夠顯著改變植物內(nèi)源激素的含量[22],例如顯著增加生長素(IAA)和細(xì)胞分裂素(CTK)的含量,導(dǎo)致重度放牧下中、小型株叢禾本科植物的大量分蘗和分蘗節(jié)的產(chǎn)生,但是當(dāng)生長素(IAA)過高也會抑制禾本科植物的分蘗數(shù)量。過度放牧下根的赤霉素、生長素和蕓苔素增加,說明過度放牧促進地下根系的生長;而莖和葉中蕓苔素含量顯著減小,說明蕓苔素的減小可能是矮小化形成的主要機制[10]。還有關(guān)于短花針茅內(nèi)源激素相關(guān)表達(dá)基因的研究發(fā)現(xiàn),放牧導(dǎo)致短花針茅防御型基因、響應(yīng)刺激類富集基因活躍[10,23],如茉莉酸、脫落酸表達(dá)量增加,乙烯、CTK表達(dá)量減少,葉綠體富集基因、氧化還原酶活性類基因表達(dá)顯著,代謝通路上差異表達(dá)基因富集注釋最多,如光合代謝、氧化磷酸化、蛋白酶、過氧化物酶、脂肪酸降解、Notch信號途徑等富集差異通路,說明牲畜對植物的直接采食和踐踏激發(fā)了植物的自我保護代謝[23],且適度放牧有助于增加種群遺傳多樣性,增進群體遺傳結(jié)構(gòu)分化。
2.1.4植物表型性狀變化 在放牧條件下植物耐牧性、避牧性研究的首要研究對象是植物表型特征的變化,因為矮小化、基叢擴展等植物避牧或耐牧策略很容易由外部的表型特征量化。學(xué)者們針對植物個體表型性狀在不同放牧強度和不同放牧利用方式下的變化進行了大量研究。荒漠草原植物表型性狀隨放牧強度的變化主要體現(xiàn)在優(yōu)勢植物高度、基蓋度、單株生物量下降[16-17,22,24],葉片長度、葉面積、比葉面積等直線下降[17,22]或呈現(xiàn)凸型單峰曲線,輕度放牧區(qū)達(dá)最高值[16],但是株叢數(shù)和株叢直徑卻增加[16,25-26]。優(yōu)勢禾本科植物分蘗節(jié)深度逐漸下降,分蘗數(shù)呈單峰趨勢,在輕度放牧區(qū)達(dá)到最大值[25]。短花針茅植物個體高度、干重、葉長、葉面積、葉干物質(zhì)含量、單株生物量顯著減小[14,18,22,25-26]、葉片數(shù)、營養(yǎng)和生殖枝高度及數(shù)量、營養(yǎng)器官中C,N,P含量及比值[14,27]、根系直徑、根尖數(shù)等均出現(xiàn)不同程度的變化[14,27],株叢徑或株叢蓋度呈現(xiàn)單峰趨勢,輕度放牧強度下最高[25]。對于短花針茅地下部分的研究發(fā)現(xiàn),短花針茅地下生物量顯著減小,根系深度明顯變淺[14]。還有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如C4植物無芒隱子草(Cleistogenessongorica)單葉面積、單葉重及單葉平均葉長均變小。隨著草原退化程度的加劇,無芒隱子草(C.songorica)葉寬度呈顯著減小趨勢[14]。放牧導(dǎo)致無芒隱子草葉長和葉面積減少,對植物生產(chǎn)功能產(chǎn)生巨大影響[14,25,28-29]。
植物表型特征之所以能夠隨不同放牧強度產(chǎn)生趨勢性變化主要是因為這些表型特征具有一定的可塑性。研究發(fā)現(xiàn),植物表型性狀的可塑性隨著放牧強度也會產(chǎn)生變化,即在特定放牧強度下植物表型性狀具有特定的變化趨勢,荒漠草原植物性狀中可塑性較高的有葉面積、植株高度、葉片長度和比葉面積[17,22],且重度放牧區(qū)植物可塑性最高[24]。比起其他植物,短花針茅的株高和株叢徑的表型可塑性較小,但短花針茅的地上生物量和分蘗數(shù)的表型可塑性更高,大株叢的可塑性比中小株叢更強,且隨著放牧強度分蘗數(shù)量提高[26],這可能是短花針茅通過無性繁殖來適應(yīng)高強度放牧的首要策略,且隨放牧強度增加的可塑性和變異性使其在過度放牧的荒漠草原成為建群種。也有研究發(fā)現(xiàn)短花針茅的表型性狀當(dāng)中,株叢徑、葉面積、莖長等指標(biāo)是較敏感的,而葉長、株高是惰性的,其可塑性較小[30]。這可能和所測短花針茅的年齡有關(guān)系,因為短花針茅的這些表型特征的變化會受到放牧強度和生長年齡的雙重影響[8,26]。
2.2 優(yōu)勢植物種群特征變化
荒漠草原植物較單一,少數(shù)幾種優(yōu)勢植物種群的變化可以揭示荒漠草原在放牧利用下的變化規(guī)律。研究證明,短花針茅種群密度隨放牧強度逐漸增加[25,28-29]或呈單峰趨勢,輕度放牧區(qū)最高[25];枝條密度隨放牧強度直線上升,隨月份變化呈單峰趨勢,六月達(dá)到最高值[28];種群高度直線下降,種群生物量呈單峰趨勢(凸形),輕度放牧區(qū)最高[25],種群生物量年動態(tài)也呈單峰趨勢(凹形),適度放牧區(qū)年動態(tài)最低,無放牧區(qū)最高[8];根據(jù)短花針茅株叢基徑大小將短花針茅分為5個年齡段,發(fā)現(xiàn)短花針茅的種群密度不僅和放牧強度有關(guān),還和株叢的年齡有關(guān)[8]。適度放牧區(qū)幼齡和成年短花針茅植株的密度明顯高于其他年齡段,重度放牧區(qū)幼齡期占據(jù)多數(shù),而無放牧區(qū)由老齡期和成熟期占優(yōu)勢[8]。短花針茅在放牧壓力下繁殖方式也有明顯的變化,如分蘗節(jié)數(shù)和種子產(chǎn)量在輕度放牧區(qū)最高,但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繁殖能力受到抑制,如分蘗節(jié)數(shù)、種子產(chǎn)量、種子密度及土壤種子庫逐漸減小,分蘗節(jié)深度逐漸下降[8,14,25,31-32],還有研究發(fā)現(xiàn)當(dāng)把短花針茅分成大、中、小3種株叢型的時候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結(jié)果,中、小型株叢在高強度放牧下分蘗顯著增加[17]。短花針茅的生殖高度隨放牧強度降低,但是生殖枝在整個植株當(dāng)中的權(quán)重在適度放牧區(qū)提高了82.99%,且放牧打破了可萌發(fā)種子的重量下限[8],短花針茅的生長速率、分蘗(無性繁殖)能力和有性生殖能力在輕度放牧區(qū)均顯著升高,而隨著載畜率的增大而顯著降低,說明輕度放牧(載畜率為0.91只羊·hm-2·0.5 a)是短花針茅種群的最適載畜率,也是其生長和繁殖的載畜率閾值。在長期的放牧脅迫下,短花針茅通過犧牲一些生長階段的個體、改變表型或提高較小年齡個體的種子產(chǎn)量來完成其生命周期,以維持繁殖體資源分配[32]。
對荒漠草原另一些優(yōu)勢植物種群研究發(fā)現(xiàn),無芒隱子草(C.songorica)種群在退化的荒漠草原上具有超補償性現(xiàn)象,但生長緩慢、再生能力較弱,被采食之后的再生能力主要依賴于根基部儲藏物質(zhì)的多少[33]。且無芒隱子草的蒸騰系數(shù)較高對水分比較敏感[33],種子產(chǎn)量隨放牧程度的加劇而顯著降低[34-35],無芒隱子草(C.songorica)種群密度在輕度放牧區(qū)較高,但隨著放牧強度的持續(xù)增加種群密度逐漸下降,單株枝條密度逐漸增加[28]。冷蒿種群多度隨著放牧強度直線下降,在重度放牧區(qū)下降率達(dá)到99.31%。但是枝條密度隨著放牧強度增加,種子產(chǎn)量逐漸減少[28,34]。
2.3 群落特征的變化
2.3.1物種組成與物種多樣性的變化 群落物種組成隨放牧強度的變化直接導(dǎo)致物種多樣性的變化。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群落中多年生根莖禾草呈下降趨勢,如羊草和米氏冰草(Agropyronmichnoi),從無放牧區(qū)的2%~3%逐漸下降,再從重度放牧群落中消失;一二年生草本從無放牧區(qū)的24%下降到重度放牧區(qū)的1%;灌木和半灌木的下降趨勢最為顯著,從29%下降到2%,如冷蒿(Artemisiafrigida)、木地膚(Kochiaprostrata)的比重逐漸降低,小葉錦雞兒(Caraganamicrophylla)、狹葉錦雞兒(Caraganastenophylla)、駱駝蓬(Kochiaprostrata)等逐漸從群落中消失;多年生雜類草呈單峰趨勢,從19%下降到10%,輕度放牧區(qū)比重最大達(dá)到20%,變化較明顯的為銀灰旋花(Convolvulusammannii)和阿爾泰狗娃花(Heteropappusaltaicus)[36];多年生叢生禾草的比重逐漸增加(29%上升到78%),其中短花針茅和無芒隱子草的比重上升最為顯著[37-40],克氏針茅(S.krylovii)和糙隱子草(Cleistogenessquarrosa)的比重整體呈減少趨勢[40]。群落變成了由少數(shù)植物占絕對優(yōu)勢的簡單群落[41]。
物種多樣性和功能群多樣性均隨著放牧強度顯著降低[37,39],如物種豐富度、Shannon-weiver指數(shù)、優(yōu)勢度指數(shù)、均勻度指數(shù)均顯著降低[42-45]。物種數(shù)從無放牧區(qū)平均24~26個物種降低到重度放牧區(qū)的平均19~20個物種[37-38],而每平米出現(xiàn)的物種數(shù)從平均8~10個物種降低到平均4~7.5個物種[39,46]。放牧強度是主要決定因子,其作用高于年份和氣候因子[37]。但有時土壤黏粒含量對物種豐富度變異的解釋率也較高[46]。總體上,物種多樣性隨著放牧強度的變化呈現(xiàn)先增加后減小的趨勢,和生產(chǎn)力的變化趨勢保持一致[47],可見適度利用可以實現(xiàn)生產(chǎn)與生態(tài)兼顧。
2.3.2群落數(shù)量特征的變化 群落特征可以通過高、蓋、密等群落數(shù)量特征來量化。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群落高度、生物量或地上凈生產(chǎn)力、蓋度等直線下降[48-52],群落密度也顯著降低,生物量在輕度、中度、重度放牧區(qū)較無放牧區(qū)分別下降27%,47%,62%[37],但這種變化也和每年的降水條件相關(guān),例如在風(fēng)水年,地上現(xiàn)存生物量隨著放牧強度直線下降,但在有些干旱年,輕度放牧區(qū)的現(xiàn)存生物量要比無放牧區(qū)高[53-54]。5-7月降水的變化能夠解釋地上現(xiàn)存量76%的變異[51]。植物多樣性的下降是影響地上生物量下降的另一個間接因素[45],當(dāng)把群落物種劃分為優(yōu)勢種和非優(yōu)勢種2種類型時發(fā)現(xiàn),群落地上生物量隨放牧強度的降低主要取決于非優(yōu)勢種的降低,而優(yōu)勢種的生物量隨放牧強度并沒有顯著的變化[39]。也有研究認(rèn)為地上地下生產(chǎn)力和物種多樣性顯著正相關(guān),但是物種多樣性是影響生產(chǎn)力的間接因子,放牧才是導(dǎo)致生產(chǎn)力變化的直接因子[39]。群落高度分別下降23%,59%,99%[37]。群落地下生物量呈T型分布,80%的地下生物量主要分布在0~20 cm深的土壤,且地下累計生物量隨著放牧強度顯著降低[49,53,55-56],但也有研究發(fā)現(xiàn)群落地下生物量沒有顯著變化[43]。而地下根系凈生長量隨放牧強度的變化和地下生物量的變化不一致,根系凈生長量呈凸性單峰趨勢,輕度放牧區(qū)根系凈生長量顯著高于無放牧區(qū)和其他2種高放牧強度區(qū)域[39]。凋落物蓋度[48,55,57]及生物量[48,55,58-59]逐漸減小,優(yōu)勢植物的生物量向地下權(quán)衡,且放牧強度越高,權(quán)衡值越大[55],地下/地上生物量的比值隨著放牧強度逐漸增加的變化也證明了這一點[39]。
2.3.3空間格局的變化 在群落空間結(jié)構(gòu)的分布上,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優(yōu)勢種群和群落的空間異質(zhì)性變化趨勢不一致[37,60]。如與對照相比,不同放牧強度均使短花針茅種群密度顯著增加,在較小的尺度上,無放牧區(qū)短花針茅的空間分布符合線性模型,但是放牧條件下符合指數(shù)模型。在尺度稍放大的時候,短花針茅空間分布由高斯模型轉(zhuǎn)變?yōu)橹笖?shù)模型[60],可見放牧尤其是重度放牧使短花針茅種群空間異質(zhì)性降低,使其分布更加均勻[61]。對無芒隱子草種群空間分布來看,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無芒隱子草的空間分布多重分形度逐漸增加,無放牧區(qū)的空間復(fù)雜性主要由母株繁殖能力、擴散能力和種群競爭能力決定,而重度放牧區(qū)的空間復(fù)雜性主要和家畜選擇性采食、隨機游走踐踏和種群本身的耐牧性相關(guān)[62-63]。研究認(rèn)為群落的空間異質(zhì)性隨放牧強度是顯著增加的[37],但是在荒漠草原上相反的研究結(jié)論占據(jù)多數(shù)[37,60-61],如禁牧區(qū)或無放牧區(qū)群落空間分布最復(fù)雜,異質(zhì)性較高,重度放牧區(qū)種群和群落趨于均勻,異質(zhì)性降低[64],群落空間格局從對照的聚集轉(zhuǎn)變?yōu)橹囟确拍羺^(qū)的均勻分布[65]。適度放牧下隨著空間尺度的增加短花針茅種群空間分布從集群分布逐漸轉(zhuǎn)變?yōu)殡S機分布,相反在重度放牧下隨尺度增加從隨機分布轉(zhuǎn)變?yōu)榧悍植糩8]。經(jīng)過對不同層次的對比發(fā)現(xiàn),不同物種的空間異質(zhì)性具有特異性,尤其短花針茅和無芒隱子草的空間異質(zhì)性高于群落空間異質(zhì)性[37],但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物種空間異質(zhì)性大于群落空間異質(zhì)性的物種數(shù)逐漸減少[66]。
2.4 種間關(guān)系
有研究探討了荒漠草原短花針和無芒隱子草2種優(yōu)勢植物之間的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在輕度放牧區(qū)2種植物的物種多度均有所提高,但是隨著放牧強度的繼續(xù)增加,無芒隱子草的物種多度持續(xù)降低,而短花針茅繼續(xù)增加。在整個放牧梯度下,2種植物的關(guān)系以無關(guān)聯(lián)或親和關(guān)系為主,對群落內(nèi)其他物種則以競爭關(guān)系為主[67-69]。但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由無放牧區(qū)的親和關(guān)系轉(zhuǎn)變?yōu)楦偁庩P(guān)系[46,69]。重度放牧使物種之間關(guān)聯(lián)減少[67],尤其降低物種之間的正關(guān)聯(lián),負(fù)關(guān)聯(lián)則有所增加[70]。對主要植物種群,自由放牧較劃區(qū)輪牧更能削弱倆倆物種間相互關(guān)聯(lián)程度,劃區(qū)輪牧較自由放牧更能保持種間關(guān)聯(lián)序的相對穩(wěn)定[70]。當(dāng)荒漠草原春季休牧后,無論放牧強度變化如何,正關(guān)聯(lián)種總數(shù)較對照均減少,但總體種間親和作用增加[71]。從群落整體來看,圍封和輕度放牧處理下植物群落整體呈負(fù)關(guān)聯(lián),負(fù)聯(lián)結(jié)種對占57.1%,表現(xiàn)為競爭關(guān)系,中度放牧和重度放牧處理下群落整體呈正關(guān)聯(lián),正聯(lián)結(jié)種對占85.7%,表現(xiàn)為親和關(guān)系[41,72]。群落物種間的關(guān)系不僅和放牧強度相關(guān),和降水條件也有密切的關(guān)系,降水的減少使荒漠草原物種間轉(zhuǎn)變?yōu)楦偁庩P(guān)系[41]。上述結(jié)論可以由物種的生態(tài)位變化來解釋。研究發(fā)現(xiàn),輕度放牧提高了短花針茅和無芒隱子的生態(tài)位寬度,降低了其他物種如冷蒿、木地膚及堿韭(Alliumpolyrhizum)的生態(tài)位寬度,且輕度放牧顯著降低了物種生態(tài)位重疊,而中度和重度放牧顯著提高生態(tài)位重疊率[67-68,73];與禁牧相比,自由放牧使建群種短花針茅和優(yōu)勢種無芒隱子草生態(tài)位變寬,而其他優(yōu)勢種生態(tài)位變窄[74]。種內(nèi)關(guān)系和上述種間關(guān)系不同,隨放牧強度的增加,短花針茅高密度分布區(qū)的競爭作用在加強,生態(tài)位寬度增加,空間分布均勻性增大,種群個體間的競爭強度增加[65,75-76]。
2.5 土壤理化性質(zhì)的變化
土壤物理性質(zhì)的分析發(fā)現(xiàn),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土壤硬度、土壤容重逐漸增加[58,77],而土壤滲透率、黏粒含量[58,78]、淺層(0~20 cm)土壤含水量[58,79-80]及土壤呼吸速率逐漸下降[79,81-83]。也有研究表明,土壤容重、含水量、土壤溫度對放牧強度不敏感[39,45],或土壤含水量逐漸增加[79]。無論是哪種植物,植物根部土壤含水量隨著放牧強度沒有明顯的規(guī)律性[84],可能原因是局部的植物基叢會形成局域范圍的陰影,且植物的根部有一定的持水性,導(dǎo)致根部土壤含水量和周圍土壤含水量有一定差異,抵消了放牧活動導(dǎo)致的植被變化及對土壤含水量的影響。土壤孔隙度逐漸減小[77]。土壤微團聚體上升,但是土壤團聚體穩(wěn)定性和大、小團聚體下降,且大團聚體對團聚體穩(wěn)定性具有正效應(yīng),微團聚體具有負(fù)效應(yīng)[85]。
土壤化學(xué)性質(zhì)隨放牧強度的變化較為復(fù)雜,不同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結(jié)論。如,部分研究得出土壤有機碳呈單峰趨勢,輕度放牧區(qū)最高,重度放牧區(qū)最低,且隨土層逐漸降低[77]。土壤有機質(zhì)隨土層深度逐漸減小,隨放牧強度無顯著變化[39,78,81,86]。根系有機碳含量顯著減少,土壤有機碳含量和有機碳儲量呈單峰趨勢[53,87]。土壤全氮隨土層深度逐漸減小,隨放牧強度無顯著變化[78,81,88]或呈單峰趨勢,輕度最高[86],速效氮呈單峰趨勢,輕度最高[77]。淺層(0~20 cm)土壤全磷逐漸減小[78]或無顯著變化[86],淺層(0~20 cm)土壤速效磷逐漸減小[78-79]或呈單峰趨勢,輕度放牧區(qū)最高[77]。土壤全鉀無顯著變化[79,86]或逐漸增加[81],表層土壤速效鉀逐漸增加,而深層土壤速效鉀逐漸減小[78],或無規(guī)律性變化[79]。土壤pH值隨放牧強度顯著增加[81]或無差異[79]。總的來講,土壤有機質(zhì)、土壤全效養(yǎng)分和速效養(yǎng)分隨放牧強度無一致的趨勢性變化,但均隨著土層深度逐漸減小[39]。進一步分析土壤化學(xué)計量學(xué)發(fā)現(xiàn),部分研究區(qū)域土壤N含量隨著放牧強度增加,C和P降低,導(dǎo)致土壤C/N比顯著下降[81,89],但也有研究表明土壤C/N比隨著放牧強度無顯著變化[90]。這種多樣化的結(jié)論可能和研究進行的年份和氣候條件相關(guān),尤其水分條件對荒漠草原的生態(tài)系統(tǒng)過程及功能尤為關(guān)鍵,如在水分條件較充足的年份土壤全效和速效養(yǎng)分之間具有一定的差異顯著性,但是在水分條件較貧乏的年份,不同放牧強度下的土壤各類養(yǎng)分之間就不存在差異[90]。且放牧年限也對土壤化學(xué)性質(zhì)有顯著的影響,如長期放牧顯著增加了土壤pH值、速效磷和速效鉀[79]。土壤腐殖質(zhì)中腐殖酸碳、胡敏酸和富咖酸含量顯著減少[78]。土壤氨化、硝化、礦化速率以負(fù)值為主,與土壤含水量和溫度呈正相關(guān),總體上圍封和適度放牧有利于土壤氮素礦化,圍封能夠促進土壤銨化,而放牧?xí)种仆寥冷@化[91]。
2.6 土壤風(fēng)蝕的變化
研究發(fā)現(xiàn),風(fēng)沙通量隨著放牧強度顯著增加,且生長季小于非生長季,生長季不同放牧強度區(qū)差異較大,非生長季無顯著差異;從風(fēng)沙流結(jié)構(gòu)來看,在生長季,放牧增加近地表含沙量,而非生長季影響含沙量的高度達(dá)到地表以上50 cm的距離;風(fēng)沙沉積物的營養(yǎng)成分隨著放牧強度減少;放牧增加了風(fēng)蝕強度,重度放牧區(qū)的風(fēng)蝕強度能夠達(dá)到對照區(qū)的5~6倍,是典型草原同等放牧強度的10倍;放牧也會提高物理結(jié)皮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土壤風(fēng)蝕程度;群落蓋度和輸沙量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52,57,92]。由此可見,放牧尤其家畜的采食導(dǎo)致的植被蓋度的降低是影響土壤風(fēng)蝕的主要因子,因此,增加冬春季保存枯落物量是防止或降低土壤風(fēng)蝕的有效辦法,荒漠草原冬春季保持不少于32.93 g·m-2的枯落物能夠有效保持固沙能力[93]。適度放牧草地流沙量比重度放牧降低了45.16%,且秋季重度放牧能增加草地流沙量,因此在秋季荒漠草原應(yīng)降低載畜率[93]。
2.7 土壤動物、微生物的變化
土壤各類線蟲種群在輕度放牧區(qū)達(dá)到最高,之后逐漸下降,在重度放牧區(qū)有些物種消失。同樣,各類線蟲多樣性指數(shù)在輕度放牧區(qū)最高,后逐漸降低,在重度放牧區(qū)最低[94];土壤動物類群數(shù)和個體數(shù)均隨放牧強度降低,其中中小型土壤動物類群和密度、大型土壤動物的密度、地面節(jié)肢動物類群數(shù)降低。中度和重度放牧降低了大型土壤動物的類群以及地面節(jié)肢動物的個體數(shù)。放牧改變了土壤動物的表聚性,使原對照區(qū)表層和深層土壤動物之間的差異消失[95]。對土壤微生物的研究發(fā)現(xiàn),隨著放牧強度的增加,荒漠草原0~5 cm土壤微生物顯著降低,與土壤養(yǎng)分含量、植物多樣性及群落生產(chǎn)力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和植物多樣性通過調(diào)節(jié)枯落物生物量提高有機質(zhì)的輸入有關(guān),且土壤微生物中的放線菌和細(xì)菌的互作關(guān)系是影響土壤可利用養(yǎng)分含量的主要原因。對土壤真菌的研究發(fā)現(xiàn),0~30 cm土壤的非根際真菌數(shù)量逐漸減小[96]或呈現(xiàn)單峰趨勢[97],輕度最高,重度最低。而優(yōu)勢植物根際土壤真菌總量因物種不同而不同,如短花針茅根際真菌隨著放牧強度逐漸降低,無芒隱子草根際真菌呈現(xiàn)單峰趨勢,冷蒿根際真菌沒有明顯的趨勢變化。復(fù)合根際土的真菌總量在輕度放牧區(qū)最高。總的來講,放牧降低了根際和非根際土壤中的真菌數(shù)量,而適度放牧能夠增加優(yōu)勢種短花針茅和無芒隱子草根際真菌數(shù)量的增加[96]。在禁牧、休牧、輪牧和自由放牧等不同利用方式下研究土壤真菌發(fā)現(xiàn)真菌侵染率在自由放牧區(qū)最高,而真菌多樣性和孢子密度均呈現(xiàn)休牧區(qū)優(yōu)于禁牧和自由放牧[97]。
2.8 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及穩(wěn)定性
從生態(tài)系統(tǒng)功能角度的研究集中于幾個方面,如生態(tài)系統(tǒng)生產(chǎn)力、碳儲量、碳交換、凋落物分解、生態(tài)系統(tǒng)呼吸、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wù)等。如生態(tài)系統(tǒng)地上生產(chǎn)力和地上地下含碳量均呈現(xiàn)單峰趨勢,輕度或適度放牧區(qū)達(dá)到最高,地下生產(chǎn)力、總初級生產(chǎn)力和植被總碳密度逐漸減小[53-54,98],地上植物有機碳儲量和凋落物有機碳儲量顯著減小,但生態(tài)系統(tǒng)有機碳儲量呈現(xiàn)單峰趨勢,輕度和中度放牧較高[99];生態(tài)系統(tǒng)呼吸、凈生態(tài)系統(tǒng)碳交換、總生態(tài)系統(tǒng)碳交換均顯著降低[54,98,100]。但是,生態(tài)系統(tǒng)碳交換的變化也和降水條件有關(guān),如在豐水年植物地上現(xiàn)存量隨放牧強度逐漸降低,但是在干旱年輕度放牧區(qū)的地上現(xiàn)存量往往最高,進而放牧和年份共同決定了生態(tài)系統(tǒng)凈碳交換、生態(tài)系統(tǒng)呼吸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總初級生產(chǎn)力的大小[98]。從凋落物分解速率來看,不同放牧強度對群落凋落物短期(135 d)、長期(870 d)分解影響極顯著,在短期分解過程中低C/N比有利于凋落物的快速分解。長期凋落物分解過程中,凋落物的分解主要和土壤微生物多樣性正相關(guān),和群落蓋度負(fù)相關(guān),凋落物前期分解受凋落物質(zhì)量影響,但較長時間的凋落物分解則與分解過程中接受到的太陽輻射量有關(guān)[101]。
也有研究從草產(chǎn)品、土壤侵蝕、涵養(yǎng)水源、CO2固定、O2釋放、營養(yǎng)物質(zhì)循環(huán)、廢棄物降解、多樣性與文化價值等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wù)來估測荒漠草原在長期不同放牧干擾下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wù)功能[86],并將其劃分為直接和間接2種類型,發(fā)現(xiàn)無放牧區(qū)的直接價值最高,輕度放牧區(qū)的間接價值最大。進而輕度放牧區(qū)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wù)總價值最高,之后呈下降趨勢,重度放牧區(qū)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服務(wù)總價值比無放牧樣地下降了18.70%。再有研究從優(yōu)勢種群、功能群和群落組織力的角度分析了長期不同放牧強度下的荒漠草原群落穩(wěn)定性,發(fā)現(xiàn)放牧對各層次組織力的影響劇烈,而降水相比放牧無顯著影響。放牧使群落組織力下降69%;除短花針茅、無芒隱子草等個別優(yōu)勢種群之外,多數(shù)物種的種群組織力下降[41,102]。放牧還使群落時間穩(wěn)定性、恢復(fù)力、抵抗力顯著下降[39,41,103],使物種異步性顯著下降[41]或輕度放牧使群落Gogron穩(wěn)定性[42]、生物量時間穩(wěn)定性[51]及物種異步性增加[39],使其高于無放牧區(qū)。從功能群時間穩(wěn)定性來看,放牧使多年生禾草的時間穩(wěn)定性增加,使灌木、半灌木和一二年生草本的時間穩(wěn)定性下降[41]。在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性指標(biāo)的影響因子中,物種多樣性是生態(tài)系統(tǒng)恢復(fù)力的重要調(diào)控因子,而物種異步性對時間穩(wěn)定性更加重要[39]。
2.9 牧民經(jīng)濟收入
對于沒有其他養(yǎng)分輸入方式的荒漠草原,過高的載畜率和過低的載畜率都不利于草地群落的正常演替[47]。分析綿羊體重指標(biāo)發(fā)現(xiàn),每年夏季和秋季以及總放牧期,綿羊體重均有所增加。但在整個放牧期內(nèi),草地ANPP和每只羊日體重增加量隨著載畜率增加而線性下降。在整個放牧季節(jié),每單位面積的最大綿羊產(chǎn)量出現(xiàn)在大約2 SE·hm-2150天的載畜率(SE為羊單位),但預(yù)計每只綿羊的個體收益在大約1 SE·hm-2之后會下降,可能是因為飼料限制。然而,為了實現(xiàn)穩(wěn)定的綿羊年產(chǎn)量,建議在大約0.77 SE·hm-2的條件下對荒漠草原進行5個月的放牧,牧食利用率控制在30%是最有益的[104]。較低的放牧率(約為150 SE·a·hm-2,既1 SE·a·hm-2150天)不僅提高植物群落物種組成,保持顯著的羔羊生長率,還能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44]。也有研究采取了冬季補飼并把生長季載畜率降低14.1%的新策略,發(fā)現(xiàn)該策略降低了34.14%的甲烷排放且增加了牧民15.85%的凈收入[105]。
3 未來研究方向和亟待解決的關(guān)鍵科學(xué)問題
從合理放牧而言,我們從學(xué)者們的工作得到的一個共性研究結(jié)論是輕度放牧對荒漠草原的地上地下各項生態(tài)指標(biāo)均有益。在內(nèi)蒙古和甘肅進行的一系列實驗、農(nóng)場示范和模型分析中一致的結(jié)果是,載畜率降低50%,不僅提高了家庭凈收入,還啟動了草原恢復(fù)進程,通過將草原保持在牧草質(zhì)量的臨界值以上,可以實現(xiàn)更好的草原管理。休牧和輪牧對荒漠草原的作用也符合有效保護荒漠草原的同時合理利用的初衷。混合放牧也是很好的利用荒漠草原的方法,能夠使植物多樣性有所提高,維持荒漠草原正常功能[106]。另一方面,草原的成功恢復(fù)還需要為牧民提供激勵和支持的政策,因為全面禁牧(通常為期5年)可能無法實現(xiàn)草原的恢復(fù),實現(xiàn)更好的草原狀態(tài)可能需要10~15年。
3.1 長期定位研究和不同地點數(shù)據(jù)整合
短期研究不能揭示植被長期變化趨勢及因果關(guān)系。長期過程隱含于“不可見的存在”,即生態(tài)過程中因果之間的滯后效應(yīng)。而單一研究結(jié)果缺乏景觀尺度上的代表性,常常隱含于“不可見的地點”,造成研究結(jié)果的不明確性[107]。因此,在秉持長期研究積累的基礎(chǔ)上,未來更應(yīng)該進行多地點、多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同步研究或整合研究,有效消除研究數(shù)據(jù)的“不可見的存在”和“不可見的地點”現(xiàn)象。
3.2 多層次、多營養(yǎng)級同時監(jiān)測
從文獻的研究對象發(fā)現(xiàn),無論研究內(nèi)容涉及地上還是地下,幾乎所有的文獻研究對象都是單一指標(biāo)或只停留于一個營養(yǎng)級。而我們知道生態(tài)系統(tǒng)是一個整體,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3個主要組成部分,生產(chǎn)者、消費者、分解者之間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且每個部分的變化都會引起另外任何一個部分的直接改變。而放牧生態(tài)學(xué)和其他自然生態(tài)學(xué)研究不同,牲畜作為主要的消費者,對生產(chǎn)者和分解者的活動有直接影響。且大多生態(tài)因子的變化具有尺度效應(yīng)。因此,多尺度、多層次、多營養(yǎng)級之間的整合研究是未來放牧生態(tài)學(xué)研究發(fā)展的必經(jīng)之路。
3.3 加大重視機理性研究
多數(shù)研究還只停留在表層現(xiàn)象的變化,如植被生產(chǎn)力、土壤理化性質(zhì)或某種物質(zhì)含量的增減,而關(guān)于這些現(xiàn)象的機理性探討還很少。而放牧可觸發(fā)一些植物的應(yīng)激性反應(yīng),導(dǎo)致一些激素類物質(zhì)的變化,而這些激素類的變化又進一步影響植物的生長和發(fā)育。因此,放牧?xí)鹬参镎w的響應(yīng),而植物的變化必然會影響地下土壤肥力,這又必然反饋到牲畜本身。然而,放牧對植物整個植株系統(tǒng)的生理生長作用的機理以及土壤-植物-動物之間的互作關(guān)系研究仍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