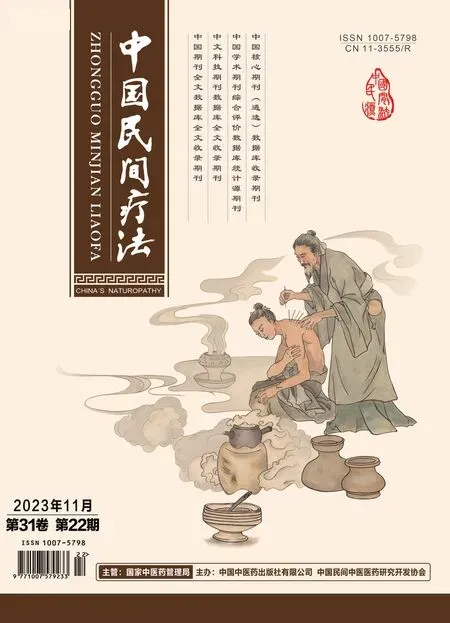基于臟腑相關理論從肝論治胃痞病
王洪江
(山東省諸城龍城中醫醫院,山東 諸城 262200)
胃痞病是常見的脾胃病,以上腹部痞滿塞滯、滿悶不舒為主要癥狀,可兼見胃部嘈雜、大便或干或稀的臨床表現。“痞”首見于《黃帝內經》,又稱為“痞滿”“痞塞”等。張景岳提出本病有實有虛,常表現為虛實夾雜。劉渡舟教授認為,胃病的發生與情志密切相關,肝在胃腸病中起到關鍵的調節作用,提出“肝胃同治”的觀點[1]。田德祿教授治療消化系統疾病時應用“從肝論治”思想,遵其師董建華教授“疏調肝木”之旨,衷中參西,每獲佳效[2]。可見,從肝論治胃痞病有理可循。本文基于臟腑相關理論,探討從肝論治胃痞病的思路。
1 肝與脾胃在生理病理上密切相關
1.1 臟腑相關 從臟腑相關角度上看,肝與脾胃關系密切。經絡方面,肝厥陰之脈循行環繞胃腑,故肝對脾胃有調節作用。五行方面,肝屬木,木曰曲直,肝氣具有木的延展舒暢、沖和通達之功;脾胃同居中焦,屬土,胃主受納,脾主運化。生克方面,肝木能克脾土,土為木之所勝,通過有序的克制和制約維持動態平衡。《黃帝內經》云“土得木而達”,若肝氣調暢,則脾胃之氣和順。葉天士認為,脾胃病根源在肝,為從肝論治脾胃病奠定基礎。徐景藩教授在治療腸易激綜合征時,強調以脾虛為本、肝郁為標,自擬抑肝扶脾方,方中白芍、防風發揮瀉肝與疏肝的作用,通過條達肝氣以利脾胃氣機運行,從而治療脾胃病[3]。周英信[4]提出脾胃病重在調肝,認為調肝運脾是化痰除濕之根本。由此可見,肝木與脾胃之土存在微妙的平衡關系,若肝木疏泄力量不及,脾土不得疏,則有壅滯之弊;若肝氣過旺,侵犯脾胃,則有脾胃嘈雜之亂。
1.2 氣血相連 從氣血生化上看,脾胃與肝相輔相成,肝、脾、胃的疏泄、運化、受納功能正常是維持機體正常生理功能的前提條件。肝藏血,氣血運行有賴于肝的疏泄,肝疏泄正常,氣血運行才能暢通無阻。脾胃功能正常也有賴于氣血的滋養,血行不暢,瘀血阻于胃絡,輕者脾胃氣血失養,導致胃痞,重者不通則痛,表現為胃痛,或氣不攝血,導致胃部出血,均會導致脾胃病進展。李乾構教授認為脾胃病當從氣血論治,肝失疏泄,導致氣郁不通,氣血凝滯不行而致胃痞病,使用入肝經的藥物能增強治療效果[5]。呂雄教授在《黃帝內經》“肝與氣血休戚相關”的基礎上,結合多年的臨床實踐,提出“氣血肝脾”理論,認為氣機壅滯至血瘀形成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間存在一個氣血病變混合共存的階段[6]。這也印證了肝脾、氣血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1.3 功能相互為用 肝對脾胃有調節作用,反之脾胃病變也會導致肝損傷。肝主疏泄可使脾胃健運,脾土散精的同時也能滋養肝木。若脾胃失健,則精氣不充,氣血不化,肝血無以充養,然肝體陰而用陽,肝陰不足,則肝木受邪,導致疾病進一步發展。姚乃禮教授在脾胃病的治療中重視調肝法的應用,認為肝、脾、胃在功能上相互為用,故治療上常以調養脾胃、疏肝解郁為主[7]。現代醫學研究表明,神經內分泌系統穩態失調與焦慮狀態有密切聯系,焦慮會使胃酸分泌增加或減少,破壞胃屏障功能,導致萎縮性胃炎發生[8]。藥理學研究發現,理氣藥能增強胃腸道運動及分泌功能,促進消化與吸收[9]。由此可見,肝、脾、胃在功能上相互影響、相互為用。
2 從“肝病傳脾”探討胃痞病的病因病機
2.1 臟腑失常,情志所因 情志異常是胃痞病發病的重要因素之一。王高峰等[10]對88例難治性胃食管反流病患者進行調查統計發現,約有一半以上的患者合并有焦慮與抑郁情緒。另有學者研究發現,心理應激刺激加重,會導致慢性萎縮性胃炎患者胃黏膜充血、水腫,反復刺激則病情逐漸加重,導致癌前病變[11]。情志發病,首先傷肝,肝為厥陰之脈,若肝疏泄失司,氣逆橫走,滯于本經,常見兩脅肋脹滿不適、少腹氣脹或脹痛等表現,皆因氣機郁滯而發脹,氣滯不通而為病[12]。其次,肝郁則中焦不通,脾不升,胃不降,發為胃痞。若情志抑郁,則人體氣機升降出入異常,影響肝疏泄之職,氣血津液失于常道,導致胃痞病發生。
2.2 疏泄失調,氣機壅滯 痞者,滿也,臨床主要表現為胃脘痞塞、脹滿不舒,其核心病機為氣機壅滯,而肝主疏泄,能調暢全身氣機。劉啟泉教授認為,氣機不暢是慢性萎縮性胃炎發病的主要原因[13]。氣滯濕阻導致胃部脹滿,氣機不暢導致血瘀,引起胃痛,氣不順降會發生噯氣,氣不宣通則飲食物不消化,氣機壅滯則病證由生。有學者認為,氣機疏泄失調、升降異常會打破體內微生態平衡,導致疾病發生[14]。各種原因導致的肝疏泄功能異常均會導致胃痞病發生,一方面表現為肝胃不和,肝疏泄失常易致氣機壅滯,導致食物壅滯中焦,釀生濕濁之邪,從而引起胃痞病;另一方面表現為肝旺乘脾,導致脾胃氣機逆亂,脾氣不升,胃氣不降,壅滯中焦,日久化火,灼傷胃絡。
2.3 氣血失和,遷延難愈 從宏觀上看,氣血不調是胃痞病發病的重要病機,其中血瘀為關鍵核心病機。唐旭東教授認為氣滯血瘀在慢性萎縮性胃炎疾病中起到重要作用,氣血不暢,脈絡瘀阻,夾濁為患,積于胃腑而致病[15]。鄭蕾蕾等[16]通過分析80例慢性胃炎合并焦慮患者的病例資料,發現大部分中醫證型分布中均兼有血瘀,氣滯血瘀貫穿疾病始終。血氣壅塞不通會導致胃痞病發生,輕者表現為胃部痞滿不適,重者表現為胃痛。肝主藏血與主疏泄功能保證血液的正常運行,血瘀證的發生與肝密切相關,氣機疏泄失調日久會導致脾胃氣血瘀滯,氣滯不行促使瘀血形成,導致胃痞病發生,甚者不通則痛,臨床常伴有胃痛。脾胃是氣血生化之源,肝主藏血,氣血不和會導致脾胃病發生、發展。從微觀上看,胃鏡作為中醫望診的延伸,當出現胃痛、反酸、胃灼熱、飲食物不下等癥狀時,鏡下可見胃黏膜粗糙、顆粒樣不平,局部充血、水腫,或伴有黃綠色反流液,肝硬化患者鏡下可見食管靜脈曲張,嚴重時可見靜脈破裂出血,出現吐血、黑便癥狀。提示肝與脾胃在氣血方面的緊密相關性。
3 從肝論治胃痞病的治法
胃痞病病位在胃,與肝、脾密切相關。肝為剛強之臟,以條達疏泄為貴。肝生理功能常健,脾胃之氣才能和降通順,反之則影響脾胃的升清降濁功能,升降失常則百病叢生,故治療上施加調肝之法,能起到既病防變的作用[17]。以下將從通降法與調氣血法加以論述。
3.1 胃痞壅滯,氣機不調,主用調和肝胃之法 胃痞病總因氣機壅滯不通而致,以滯為重點[18]。臨床上以肝胃不和、肝旺乘脾為主。根據癥狀的不同,治法上有疏肝和胃、清降肝胃、瀉肝補土之不同。
(1)疏肝氣,和脾胃 肝胃不和會有脘腹作脹,甚則脹痛的表現,常與情志變化相關。肝郁氣滯,氣塞不行,壅阻于中焦,出現脹滿。治當疏肝理氣,宣暢中焦氣機,上下無礙,伸其郁,導其滯,則脹消食進。常用辛香發散之品,既能理肝氣、疏肝郁,又能調理脾胃氣機[19]。代表方有四逆散、旋覆代赭湯、柴胡疏肝散等。田德祿教授善用張仲景《傷寒論》中的四逆散解氣機之郁閉、郁滯[2]。方取柴胡解郁之功,芍藥與柴胡配伍增強疏肝之用,枳實理氣機、和氣血,甘草益脾調中。該方臨床常用于治療胃痛、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脾胃病,療效顯著。白光教授認為,氣機升降失常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主要病機,臨床應用旋覆代赭湯治療時也常加入枳實、枳殼以降氣寬中、疏肝和胃,患者服藥后反流、胃灼熱癥狀基本消失,便秘癥狀亦有改善[20]。程琳[21]研究發現,以疏肝和胃法(柴胡疏肝散)治療肝胃不和型反流性食管炎,治愈率及總有效率均高于使用奧美拉唑治療的患者(P<0.05),而且在保護胃黏膜、緩解臨床癥狀方面的療效較奧美拉唑治療更好。
(2)瀉肝火,降胃氣 肝旺乘脾主要表現為脅肋脹痛,急躁易怒,反酸,胃灼熱,口中異味,大便黏膩不爽,舌質暗紅、苔黃膩,脈弦滑數。肝氣橫逆犯胃,脾胃升降功能異常,壅塞中焦而生痞滿。肝火郁滯,沖逆太過,木旺克土,則清氣遏而不升,濁氣逆而不降,肝胃郁熱,升降失常而胃脘脹痛,病屬木旺乘土之胃痛。治療當用抑肝扶脾之法,代表方有化肝煎。曹志群教授常用此方治療胃痛、痞滿、反酸,效果顯著,該方善解肝郁、平郁火[22]。周夢蝶[23]研究發現,相較于雷貝拉唑及硫糖鋁,中藥復方疏肝愈胃湯治療慢性平坦型糜爛性胃炎(肝胃不和兼濕熱證)療效更好,總有效率為91.9%。疏肝愈胃湯是由柴胡疏肝散合清中湯加減而成,前者能疏肝降氣、解郁清火,后者能降胃氣、祛濕熱,疏肝之品多屬燥性,易助陽生火,宜少量使用,清中焦之品易傷陽寒化,宜中病即止。
(3)瀉肝氣,補脾胃 四季脾旺不受邪,若脾氣旺盛,則不易被肝侵犯。若脾虛乘肝,則表現為脘腹隱隱作痛,常與情緒變化密切相關,時輕時重,或有腹痛作瀉,或脹痛、按之則舒等癥,其本為脾虛,肝氣乘虛而犯脾胃,治療以培土為主,益氣溫陽、疏肝行氣為輔,常用六君子湯加減。戴永生教授提倡運用“五行辨證”理論治療胃病,認為該病的病機在于脾土先虛,肝木不疏,橫逆犯脾,脾土失運而致病,故治療上選用六君子湯加減,逆肝木之性而瀉之,順脾胃之性而補之,每多奏效[24]。
3.2 痞滿兼痛,氣血同病,主調和氣血之法 胃痞病初起多見胃脘痞塞滿悶,觸之無形,痛或不痛,反復發作,日久不愈,病情加重后多兼灼痛或刺痛。胃是多氣多血之腑,當外邪侵襲后,容易引起功能紊亂,邪氣郁于其中,氣血必然受阻。董建華教授論治脾胃病時,重視氣血理論的臨床應用,常采用調氣和血、調血和氣之法治療[25]。
(1)疏肝絡,活氣血 肝主藏血,能運氣血,肝木條達,則血行流暢。若肝失疏泄,木氣推動無力,血液停滯不行,則會淤積形成瘀血,影響胃部氣血和暢,胃絡受阻,不通則痛。肝郁血瘀證表現為痛處固定,或大便色黑,甚或吐血等。治當疏肝理氣,調肝木條達之性,恢復脾胃升降功能,輔以活血之法,祛胃絡瘀血,通則不痛[26]。臨床常用丹參飲加減,方中丹參補氣活血化瘀,砂仁、檀香行氣止痛消痞。魏瑋教授重視益氣活血法在脾胃病中的應用,常用藥物有丹參、赤芍等[27]。藥理學研究發現,丹參素能清除潰瘍面的壞死組織,提高細胞再生能力,促進潰瘍面愈合[28];赤芍醇提取物能抗內毒素,發揮抗炎作用[29];半枝蓮可興奮家兔離體腸,促進胃腸平滑肌蠕動[30]。朱方石教授以活血化瘀為主要治法,創立活血化瘀抗萎方,研究顯示,活血化瘀抗萎方能增強胃黏膜防御能力,促進胃黏膜細胞修復,有效改善局部炎癥及胃黏膜萎縮和腸化生的病理狀態,抑制胃上皮內癌變進程[31]。
(2)柔肝體,養脾胃 肝為剛臟,體陰而用陽。肝體用協調的情況下,肝臟不易發病。若肝體不及,則相火肝風上竄,變癥蜂起,就會出現病態[32]。肝陰不足、脾胃失養則多表現為胸脅脹滿不舒、食少不饑,或胃脘痞脹、噫氣、大便不爽、失眠多夢等癥。治療以柔肝養陰為主,常用一貫煎合芍藥甘草湯加減。董麗[33]研究發現,一貫煎合芍藥甘草湯加減治療胃陰不足型慢性萎縮性胃炎的臨床療效優于單純西藥,能有效緩解患者癥狀,且復發率較低。研究發現,芍藥苷可通過調節細胞膜鈉鈣離子交換,舒張胃腸平滑肌細胞,緩解胃腸痙攣[34]。袁成業教授認為肝以柔為補,故臨證時常加大芍藥用量,通過柔肝體之法調整肝的疏泄功能,并自擬柔肝醒脾湯治療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慮抑郁狀態,能改善患者的胃腸動力,促進排空,保護胃黏膜[35]。
4 小結
從肝論治胃痞病臨床應用廣泛,有不少醫家重視肝與脾胃之間的關系,情緒因素可導致多系統疾病發生,尤其是脾胃系統疾病,如胃食管反流病、腸易激綜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等,同時從肝論治也是中醫“整體觀”“辨證論治”理念的體現,但是從肝論治脾胃病尚未形成系統的理論。如何在臨證時作出準確的判斷可能是臨床醫師遇到的最大問題。對于此種情況,一方面須加強對名老中醫學術思想的傳承,在跟診學習過程中鍛煉個人的中醫思維;另一方面須多讀經典、多臨床,通過學習經典理論,將理論知識應用于實踐中,從而更好地深入挖掘中醫藥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