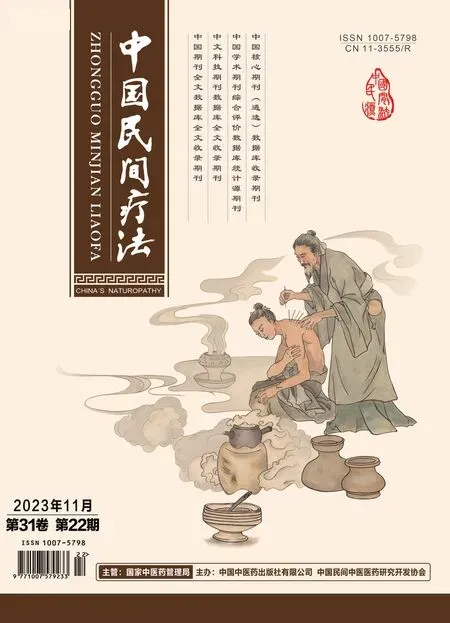中醫藥防疫方法進展※
付菲菲,李玉霞,馬思淼
(1.甘肅中醫藥大學,甘肅 蘭州 730000;2.甘肅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甘肅 蘭州 730000)
疫病與西醫的傳染病基本對應。疫病主要屬于“溫病”范疇,是一類傳染性強、傳播快、癥狀類似、病死率高的疾病。傳染病是指由微生物感染人體后產生的有傳染性、在一定條件下可造成流行的疾病。中醫古籍對疫病的相關記載較多,如疫癘、瘟疫等,具體以病因命名的名稱有傷寒、溫病、春溫、冬溫、濕溫、暑疫、風溫等,以自然災害特征定義的名稱有荒疫、饑疫、旱疫等。中醫藥對于疫病的防治主要體現在降低病理性損害、防止疫病惡化、改善癥狀體征、促進預后與康復、防止疫病復發等方面[1]。《素問·刺法論》言:“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癥狀相似。”疫病有“疫”“癘”之分,兩者發病的條件有所不同,但防治方法基本相同。《素問·刺法論》言:“于是疫之與癘,既是上下剛柔之名也,窮歸一體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總其諸位失守,故只歸五行而統之也。”疫病的防治可從五行屬性入手。有學者認為,論治疫病可從固護正氣、避其毒氣、針刺防治、五氣護體法、三法防疫方面入手[2]。
1 疫病的病因病機
《黃帝內經》提出運氣周期與疫病的發生時間有密切聯系。《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記載:“辰戌之紀也……初之氣……民乃厲,溫病乃作。”“卯酉之紀也……二之氣……厲大至,民善暴死……終之氣……其病溫。”“寅申之紀也……初之氣……溫病乃起。”“丑未之紀也……二之氣……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子午之紀也……五之氣……其病溫。”“巳亥之紀也……終之氣……其病溫厲。”由此可見,在初之氣、二之氣、五之氣、終之氣幾個時間段易發生疫病,運氣變化與疫病發生的關系密切。陳金紅等[3]認為,六氣之司天在泉不遷正與不退位,間氣升降不前,年天干剛柔失守,導致“氣交失守”,引發疫病;剛柔失守是“三年化疫”的前提,而“三年化疫”即指在氣候發生異常的第2年或第3年可能會出現嚴重的疫情,并且氣候異常之年的歲運與病性有關。疫病屬于外感病,而發病關鍵是外邪之氣與人體正氣的消長。《靈樞·百病始生》指出“兩虛相得,乃客其形”,提示外感邪氣與機體正虛是外感發病的重要因素。六氣之風、寒、暑、濕、燥、火失常,發為六淫,損傷人體。人體正氣的強弱與多種因素相關,譬如先天稟賦、飲食、情志、地域、時間等。總的來說,正氣強則不易患病,正氣虛則易患病。古人對疫病病因病機闡述比較詳細,主要集中在運氣失常與人體自身的正氣不足。
從西醫角度出發,傳染病主要是因感染相關病原體導致人體的免疫功能受損,從而引起一系列相關癥狀。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就是因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而導致人體發生以呼吸系統癥狀為主的傳染性疾病。王亮等[4]從腎虛與血瘀的角度出發,探討重型與危重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的病因病機,認為腎虛患者多伴有肺虛,血瘀患者多出現低氧血癥、凝血功能障礙及免疫反應失調,男性患者多有激素水平異常,且會影響生育功能。屈杰等[5]基于《傷寒論》闡述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病因病機,認為該病初起多屬太陽病,濕熱證可以從少陽論治,危重癥多屬少陰病。王冬等[6]根據清·王燕昌《王氏醫存》探究疫病的總病機,認為該病具有“水弱火強”“三焦傳變”“伏熱內發傳變”的傳變規律,且有夾病、夾證的特點。熊必丹等[7]發現老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病機可歸于濕、熱、毒、瘀、虛,且虛與瘀更明顯。
2 防疫方法
2.1 內治法 在歷代的防疫工作中,中藥湯劑及中成藥均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根據辨證論治原則,針對不同證型的疫病給予相應的方藥。屬于溫病范疇的疫病,應用清熱解毒藥物治療較多,如金銀花、蒲公英、連翹、白頭翁、野菊花、板藍根等。疫病多夾濕邪,其發病與濕濁、濕熱、寒濕之邪密切相關。吳鞠通認為:“疫為穢濁之邪,自口鼻入里,循經傳腑,每多變化。”脾喜燥惡濕,而濕邪喜犯脾胃,導致脾不運化;濕邪重濁黏膩,易阻滯氣機,加之兼夾他邪而致病情復雜。芳香藥物氣味辛香,性溫可通,而辛能行氣,香能通氣,故芳香藥物有效成分經口鼻吸入人體,外走肌表,內達臟腑,可調暢氣機,固護正氣,提高人體免疫力[8]。常用于防疫的芳香之藥有郁金、降香、蒼術、厚樸、白豆蔻、砂仁、佩蘭、藿香、草果、丁香、石菖蒲等。徐大椿認為:“香者氣之正,正氣盛則除邪辟穢也。”《本草綱目》強調:“中氣不運,皆屬于脾,故中焦氣滯宜芳香,以脾胃喜芳香也。”“芳香之氣助脾胃。”《藥品化義》記載:“香氣入脾。”“香能通氣,能主散,能醒脾陰,能透心氣,能和合五臟。”《臨證指南醫案》提出:“夫疫為穢濁之氣,古人所以飲芳香,采蘭草,以襲芬芳之氣者,重滌穢也。”現代藥理學研究表明,芳香藥物具有抑菌、抗菌、緩解疼痛、改善負面情緒的作用[9-11]。2010年,甘肅省舟曲特大泥石流災害發生災后疫情。馮蕾等[12]將496例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自愿服用中藥(腹瀉方及感冒方由甘肅省名老中醫劉東漢教授提供),對照組不服用中藥,干預20 d后,治療組淋巴細胞亞群和血常規指標均明顯優于對照組。兩方均使用芳香藥物,如藿香、白豆蔻仁、麩炒蒼術、厚樸。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發生,很多中醫家投身疫情防控工作中,對于該病的病因有不同的觀點,主要集中在寒、溫燥、濕。上海市2022年春季發生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以奧密克戎變異株為主)疫病屬于中醫“濕毒疫”范疇,治療應以清熱解毒、化濕毒、祛瘀毒為主,根據無癥狀感染、輕型/普通型、重癥/危重癥分別予以中藥湯劑、中成藥、中醫非藥物療法[13]。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防治過程中,很多醫家根據患者的居住環境及飲食習慣等創制多種經驗方,并取得顯著的療效。如在吉林省防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過程中,吉林省中醫藥救治專家組成員認為此次疫病屬中醫“寒濕肺疫病”范疇,在發病的不同時期予以不同的治療方案:外感早期予以荊防敗毒散或神術散加減治療;外感遷延期邪郁肌表,用柴葛解肌湯合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合白虎湯加減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初期,寒濕疫毒束表,濕濁痹阻肺絡,方用小青龍湯合平胃散加減;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中期,熱毒痹肺,方用白虎湯合清營湯加減;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重癥期,脾胃虛冷,疫毒化火,方用附子理中湯加味;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重危期,內閉外脫,方用參附湯送服安宮牛黃丸或蘇合香丸;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恢復期,方用陽和湯合附子理中湯加減[14]。治療后,所有患者癥狀均好轉,臨床療效佳。另外,戈佳磊等[15]在疫情防治過程中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兒恢復期主要表現為肺脾氣虛,選用培土生金法的代表方劑參苓白術散療效佳。方邦江等[16]從《瘟疫論》治療疫病的角度出發,并借鑒國醫大師的經驗,提出化濕透表泄毒和清熱利濕泄毒的表里雙解之法,應用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防治療效顯著。從各醫家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用藥思路及治療效果可以發現,清熱解毒藥與化濕藥為主要配伍藥物,對溫邪與濕邪致病的效果較好。
2.2 外治法
(1)芳香防疫 芳香防疫之法古已有之,并為后世沿用。用于防治疫病的芳香藥物主要作用有芳香化濁、辟穢防疫、透邪解表、開宣毛竅、醒脾理胃、理氣化濕、開竅醒神、活血通經等[17]。用于芳香防疫的方法眾多,主要有中藥熏蒸、佩戴中藥香囊等。①中藥熏蒸療法。該法主要作用為辟穢解毒以凈化空氣,驅蟲滅害以切斷傳染源及傳播途徑,化濕醒脾以提高免疫力,開竅解郁以安神定志[18]。常用中藥有礦物類和植物類,礦物類有雄黃、雌黃、朱砂、礬石,其中雄黃、朱砂等具有一定毒性,可殺蟲滅毒。植物類有艾葉、蒼術、皂莢、白術等,其中艾葉、蒼術氣味芳香雄厚,能除惡氣辟穢,故應用較為廣泛[19]。研究發現,在兒科病房中采用蒼術、桉葉及艾葉熏蒸法對空氣消毒的效果佳[20]。中藥熏蒸方法多種多樣、成本低、安全有效,適合在人員密度大、易污染的環境中使用。②佩戴中藥香囊。該法在我國的應用歷史悠久,通過佩戴芳香藥物,經口鼻吸入,達疏通臟腑經絡之效,發揮辟穢濁、防治疾病的作用[21]。芳香藥物可以提高機體的免疫力,也具有一定的殺菌及抗病毒作用。張晉等[21]總結中藥香囊辟瘟囊在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中的應用情況,發現辟瘟囊可針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核心病機“濕、熱、毒、瘀、虛”發揮作用,臨床將辟瘟囊中的6種藥物(羌活、大黃、柴胡、蒼術、細辛、吳茱萸)研細末或粗粉裝入香囊中佩戴,或開發成滴鼻劑、香薰劑、沐浴劑、噴霧劑等,能提高便捷性、依從性。唐維我等[22]研究發現,防疫香囊藥物中有防疫功效的成分主要是揮發性物質,如石菖蒲、細辛中的細辛腦。吳潔雁等[23]分析提示防疫香囊可能通過多種活性化合物作用于多靶點,促進抗病毒細胞的信號轉導,提高機體免疫功能,發揮防疫作用。
中藥熏蒸與中藥香囊的作用機制相似而又不同,相似之處可總結為“香者氣之正,正氣盛,則自能除邪辟移也”(《神農本草經百種錄》)。不同之處在于,中藥熏蒸是通過在密閉空間中焚燒中藥,使芳香類中藥揮發的氣味彌漫于空氣之中,以起到驅蟲祛邪、辟穢化濁等作用;中藥香囊是通過佩戴芳香之藥,使揮發的氣味經口鼻、皮膚腠理、經絡腧穴等途徑調節人體的氣血經絡,幫助機體達到陰平陽秘的狀態。
(2)針刺法 針刺法應用于防疫首見于《黃帝內經》。《黃帝內經·素問》針對運氣變化,采用針刺法補不足、瀉有余,其中針對“氣交失守”最嚴重的剛柔失守所致疫癘,從五行屬性出發,補瀉兼施,“太過取之,不及資之”。龔亞斌等[24]采用針刺法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33例,以合谷、內關、列缺、足三里、曲池、太沖為主穴,利用平補平瀉法,每次單側針刺穴位,雙側交替,隔日治療1次,治療效果佳。侍鑫杰等[25]在負壓病房內運用管針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42例,針刺合谷、內關、足三里、太沖、曲池、列缺,施以平補平瀉法,留針30 min,經連續治療12 d后,患者胸悶、胸痛、乏力等癥狀均得到明顯改善。
(3)艾灸法 艾灸是將燃燒的艾葉(艾絨)放置于患處,通過熱量傳導刺激體表穴位,以促進人體的自我調節,達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古人用艾灸防疫的方法主要通過點燃艾葉,利用艾煙對空氣進行消毒,達到防疫效果,或通過艾灸人體的強壯穴位,如足三里、氣海、關元、百會等,扶助人體正氣。《黃帝內經》提及“針所不為,灸之所宜”,《醫學入門》指出“凡病針之不到,藥之不及,必須灸之”。艾灸能有效改善患者呼吸道癥狀,提高免疫力、緩解緊張情緒,可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預防、治療和康復中發揮不同的作用[26]。《中國針灸學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針灸干預的指導意見(第1版)》建議對疑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患者予以艾灸足三里、氣海、關元,調節免疫力;對輕型、普通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艾灸合谷、太沖、足三里、神闕以改善患者癥狀,縮短病程,舒緩患者情緒;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恢復期患者,艾灸大椎、肺俞、膈俞、足三里、孔最以恢復肺脾功能,增強人體正氣[27]。
3 小結
本文通過分析中醫藥防疫的發展情況發現,中醫藥防疫有效且有獨特的防治優勢,但也存在很多不足,防疫范圍還需繼續擴大。在傳統的中醫防疫手段基礎上,應該加強中藥的藥理研究、制劑研究,發掘有效的特色療法,把中醫藥防疫與現代科學研究緊密聯系起來,發揮中醫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