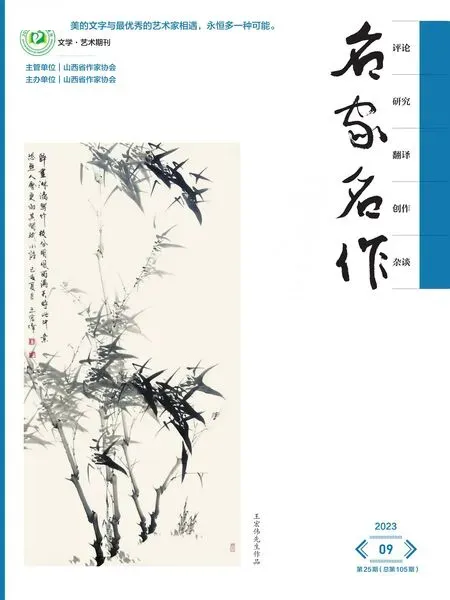淺談《儒林外史》中的商人形象及其社會文化因素
趙 彤
一、文獻綜述
通過計量可視化分析,近二十年關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向:(1)對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分析,如杜少卿、匡超人、范進等,或者分析主要群體的共同特質,如士大夫知識分子群體、女性群體、和尚群體;(2)對作品所反映的科舉制度的討論以及對名利尊卑觀念的分析和批判;(3)研究作品中的諷刺藝術與寫作手法;(4)將作品與其他明清小說進行對比,分析其中所反映的社會現象。
以《儒林外史》和“群體”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發現,大多數文章是分析科舉制度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小人物形象與和尚群體形象,例如《論〈儒林外史〉中文人群體的科舉情結》《〈儒林外史〉小人物群體的敘事意義》《〈儒林外史〉中僧人群像的世俗化特征》等,關于商人群像的研究相對較少。
堯育飛的《〈儒林外史〉徽商群像的建構策略》通過描寫名士和官僚兩大階層的碰撞,將徽商豪橫而卑賤的兩面性呈現給讀者,徽商群像得以立體呈現,通過分析建構策略,側面反映了明清士商關系的變化;李娜的《從〈儒林外史〉解析士商關系及其成因》表現出士依附于商,士商滲透、融合、結親與聯姻等關系,融洽中不乏對立,對研究明清時期士商關系以及《儒林外史》中的商人形象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王娟娟的《程夢星和〈儒林外史〉中的商人形象莊濯江》通過吳敬梓與程夢星之間的聯系,具體反映了莊濯江這個小說人物與程夢星這個現實人物之間的關系,對于揭露明清時期儒商這一特殊商人群體有極大的借鑒意義,對具體分析商人形象有重要的指導作用;馬佳麗和杜升強的《〈儒林外史〉中的商人及吳敬梓的價值取向》深入分析了商人形象的類型和作家對于商人群體的價值取向,對《儒林外史》中的商人形象做了初步整理。
綜上所述,當前對于《儒林外史》中商人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討原文中的商人形象,以及商人與知識分子之間的交集,而對于這些形象背后文化因素的分析相對較少或較為分散。筆者認為,對于商人這個特殊群體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形象層面,而應該分析作品中促使商人行為產生的社會文化因素以及作者對這一群體的態度,多角度了解《儒林外史》中的商人群體。
二、《儒林外史》中的商人形象
商人形象雖然不是作者的主要寫作對象,卻是全書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明清時期,士農工商的階級劃分仍然很明顯,時人普遍看不起商人,認為商人滿身銅臭。在《儒林外史》中也不乏典型的商人形象,他們有的一心為財,有的追逐文人風流,有的貪婪成性且勾結官府。《儒林外史》為我們展現了一類特殊的商人形象。
(一)正經老實、善良熱心的儒商
生活在儒學主導的社會,商人不僅做著正經的生意,還盡其所有地幫助他人。在小說中第一個出現的商人形象是周進的姐夫金有余,他看到周進六十多歲還在追求功名,就勸慰他不要再執著于讀書求功名:“人生世上,難得的是這碗現成飯,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幾時?”①吳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作者通過金有余的論述,似乎是在向封建社會所有的老秀才發問:難道真的要一直執著于功名嗎?金有余還為周進謀了一個差事。但由于知識分子高于一切階級的思想根深蒂固,周進仍沒有放棄求功名的念頭,幾次昏死在貢院。書中最讓人感動的是當那些商人看到周進昏死幾回之后,一致同意湊了二百兩銀子讓周進再次應考。士農工商,世間百態,在《儒林外史》中既能看到高高在上的“士”鉤心斗角,也能看到最被鄙夷的“商”仗義疏財、成人之美。
莊濯江,敬重文人,樂善好施,重視友情,在吳敬梓筆下的士人眼里亦非等閑之輩,得到了全書中商人的最高評價,是典型的儒商形象,“曾開過兩個典當,轉徙經營,又自致數萬金”,并且“平日極是好友孰倫,他尊人治喪,不曾要同胞兄弟出過一個錢,俱是他一人獨任;多少老朋友死了無所歸的,他就殯葬他,又及尊先君當年的訓,最是敬重文人,留戀古跡”。
除此之外,小說中出現的牛老爹以及隔壁卜老爹都是最老實本分的小商人形象,他們認真做好自己的小本生意,甚至結為親家,卜老爹在牛老爹死后,無條件地幫助牛浦郎,最后因老友的死傷心而亡。他們之間的情誼真摯、溫暖。他們的出現也成為《儒林外史》中為數不多的暖流,他們之間純粹的交往和奸商與知識分子之間虛偽勢利的往來形成鮮明的對比,進一步增強了作品的諷刺意味。
(二)喜好詩書、追求文人聲譽的偽商
商人重利向來為世人公認,但在《儒林外史》中還有這樣一類偽商,他們雖為商人,卻不屑于商人之事。商人階層賈而好儒,更多是源于對自己社會地位低的不滿,因此,他們將自己包裝成士人模樣,希望以此滿足自己內心的空虛。這一類的商人大多不問賬目,愛好詩書,喜歡追逐文人名譽與素質,自詡有幾分才氣,但驕傲自滿,且開口閉口就是自己與哪位大詩人論詩。
作品中的楊執中就是這一類商人的典型。楊執中“雖是生意出身,一切賬目,卻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閑游,在店里時,也只是垂簾看書”②吳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最終他只能在鹽務記賬,卻在賬上出了問題,多虧婁家兩位公子才被救出。雖然楊執中在經濟上多有耍賴,但毫無疑問,他還是略有幾分才氣的。而開頭巾店的景蘭江就不一樣了,他自詡杭州各處詩選上都刻過他的詩,且已“二十余年了”,景蘭江與人交談時口出狂言,說魯老先生是他的詩友,卻不知魯老先生最恨詩詞,眾多虛偽可笑之舉看似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可最終不過惹人取笑。
(三)貪財逐利、賄賂官府的奸商
在《儒林外史》中同樣擁有古代小說中最常見的奸商形象,根據行為的不同,又可以將他們分為兩類:
一類是裝仁善、真盜賊的商人。作為牛老爹的孫子,牛浦郎先是為了讀詩而偷錢買書,這姑且只是追求文人風流罷了,但他后來甚至偷牛布衣給老和尚的詩稿來讀,更可惡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竟不顧自己與牛布衣的年齡差距,冒名頂替牛布衣和各種官員來往,輕視且辱罵收留他的卜家兄弟。一個身居貧賤還沒能爬上去的人,就已經表現出對下層平民的深深藐視,世界上難道還有比這更卑鄙、更無恥的事嗎?雖然在這本書中只有他一個人盜取他人身份,但他的行為已經讓人對其他商人產生懷疑,是否他們也曾想過冒名頂替詩人呢?
一類是追求社會地位、賄賂官府的商人。這類商人往往擁有豐厚的家底,希望通過結交官府來提高自己的地位,尤以徽商最為典型。徽商一方面需要名士的人際關系幫忙打點官府;另一方面需要名士的聲譽來附庸風雅,提高社會地位。雖然徽商在名士身上花了很多錢,但仍無法掌握名士,甚至名士將其視為呆笨者,冷嘲熱諷。《儒林外史》通過徽商與名士之間的對話,構建出徽商豪橫、強勢、精明的形象。但在與官員交往時,又不難看出徽商脆弱和卑微的態度。鹽商萬雪齋有幾十萬家私,每頓要吃冬蟲夏草,富甲一方,但仍不被上層人尊重。萬雪齋原來只是程明卿家的一個家客,所以即使他現在家財萬貫,但是在那個社會官員的眼里,他“到底還是程家的奴才”③吳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萬雪齋娶了某翰林的女兒,想盡辦法與官府結私。大商人們不僅結交官府,還極力賄賂在上層社會有名望的知識分子。小說第35 回里,莊尚志被天子詔見后回了臺兒莊,“只見岸上有二十多乘齊整轎子歇在岸上,都是兩淮總商來侯莊征君的”④吳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四)一心為財的純商
《儒林外史》中還有一群只想賺錢的純商,他們是最純粹的商人,比如胡屠夫。胡屠夫在范進中舉之前,對范進肆意辱罵,不肯借錢給范進考進士,嫌棄范進花他的錢。而當范進中舉之后,前后轉換判若兩人,遇人就講范進是文曲星下凡,但歸根到底,胡屠夫的態度轉變只是因為范進中舉后就可以做官,不僅不用再花他的錢了,還可以幫襯他。
這類商人在《儒林外史》中所占筆墨不多,但卻深刻反映了明清商品經濟繁榮的社會里小商人的生活狀態,讓讀者對商人群體有了更清晰、更完整的認識。
三、《儒林外史》背后的社會文化因素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價《儒林外史》:“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⑤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6。《儒林外史》中的很多形象都可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原型,吳敬梓之所以塑造了這么多不同類型的商人形象,必然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有關。
(一)政治因素
從以上的商人分類中可以發現,除了純商,其余商人形象都與知識分子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這也與當時的社會階級劃分有關。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傳統的“士農工商”四民觀念深入人心。長久以來,士與商一尊一卑,猶如兩個界限分明的陣營,無形中構筑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高墻。①李娜: 《從〈儒林外史〉解析士商關系及其成因》,《黃山學院學報》2016 年第4 期,第46-50 頁。受“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知識分子在封建社會顯示出無與倫比的優越感,而商人由于身份問題無法參與科舉,逐漸產生自卑感。
隋唐時期,科舉制明確規定商人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宋朝開國以后實行重文輕武的國策,規定商人及其子弟可以入學讀書,也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考中可以做官,商業貿易是朝廷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從此商人受到尊重,地位有所提高。明朝商人后代不僅可以參加科舉考試,政府還為流動性很強的商人提供了參加科舉的便利——給予他們與其他流寓人員同樣可以在異地寄籍暫居或附籍的權利。清代沒有不許商人參加科舉考試的規定,清代商人不僅參加科舉,捐官的也有很多。②李娜: 《從〈儒林外史〉解析士商關系及其成因》,《黃山學院學報》2016 年第4 期,第46-50 頁。
雖然明清時期朝廷放開了科舉范圍,但幾千年來“抑商”的思想早已滲透進每一個人的心里。在社會倫理上,人們仍然看不起商人,對于商人滿身銅臭充滿鄙夷。因此,商人只能通過名士、官府來提高自己的社會聲譽,從而導致從明朝中后期開始出現官商勾結現象。
(二)社會環境因素
首先,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雇傭關系出現,中國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社會上逐漸出現了富甲一方的商人,優厚的經濟條件讓他們開始追求社會地位的提升,傳統的士農工商的排序開始松動,士商關系在此時開始緩和。作為現代主義小說的《儒林外史》,其中莊濯江形象的存在也表明,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士商之間的隔膜正在逐漸消解,出現了一群不再單純依靠父輩財富盡享富貴榮華,而是享受風雅生活的溫文爾雅的儒商。《儒林外史》一改明清小說只寫奸詐商人的傳統,體現了商人形象的多樣性。
其次,區域經濟高度發達,江南以及長江中上游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商品流通加快,出現了以地域劃分的商人群體,由此也出現了《儒林外史》中最重要的商人群體——徽商。徽商的生活方式、官商依附的形式都為《儒林外史》的寫作提供了現實基礎。
最后,在《儒林外史》中士與商交往密切,互相取利的現象層出不窮。由于商品經濟發展,不事生產的士人生活緊迫,難以為生,很多士人迫于生計棄儒從商。而商人為了附庸風雅或提高自己的社會聲譽,大多追求名士風流,賈而好儒。士商依附極大地改變了傳統儒家無私為公的思想,是對當時社會倫理和道德的重新建構。在《儒林外史》中也很好地體現了這一社會現象,體現了當時復雜的社會環境,很好地闡釋了吳敬梓對這種畸形的社會士商關系的無奈。
(三)作者的態度
商人,由于骨子里的“重利”而被統治者劃分為最下等的一類人。在古代小說中,商人形象極為少見,就算出現也大多是反面形象。在《儒林外史》中也不乏這一類商人,如楊執中、萬雪齋等。他們也許行為不端,但本質上都是為了改變自己低下的商人地位。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不僅描繪了很多奸商形象,也塑造了一些熱心善良,為了幫助他人不惜傾家蕩產的儒商形象。在吳敬梓的筆下,商人的好壞從不是靠身份來界定的,他是中國古代少有的對部分商人表示肯定的作家,他讓讀者相信商人也不一定都是老奸巨猾的形象。正是吳敬梓這種不以儒家道德劃分階級的思想,才沒有在主觀上將知識分子捧上高臺,將商人打入塵埃,而是將所有人放在經濟發達的社會里,真實地描繪眾生相,這才讓我們在這本書中看到了不一樣的商人形象。
四、結語
《儒林外史》中的商人形象是社會眾生相中最具世俗氣的一部分,雖然部分商人形象讓人生恨,但不可否認,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的種種行為深刻地反映了商品經濟繁榮的社會下道德倫理觀念的滯后,以及社會等級松動所帶來的陣痛。通過對不同類型的商人的描寫,作者在無形中對商人與商人、商人與知識分子進行了對比,更加反映出作品對黑暗社會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