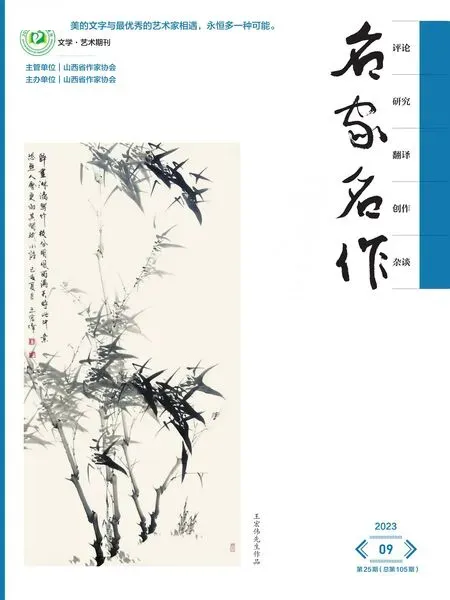消費社會理論下的《毛毛》解讀
李文馨
《毛毛》是米切爾·恩德于1973 年創(chuàng)作的一部兒童幻想小說。這部小說耗費了恩德六年的時間,作品一經出版,便大獲成功,深受德國兒童的喜愛,并在此后十幾年間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世界各地掀起熱潮。
最優(yōu)秀的兒童文學作品,往往不僅僅是面向青少年讀者的作品。《毛毛》不僅有吸引青少年讀者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和大膽的幻想,還包含著作者對人類生存狀態(tài)和社會的反思,以及對改善社會現狀的思考。恩德用細膩的筆觸和大膽的幻想,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對工業(yè)社會中人的時間觀進行了深刻的諷刺。
本文以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為理論依據,對《毛毛》中體現的工業(yè)社會下人際關系與時間的異化進行解讀。《毛毛》通過書寫灰先生對人類社會的侵蝕,以及小女孩毛毛與灰先生智斗的過程,體現了工業(yè)社會下主流時間觀的扭曲與異化,并最終提出解決方案——重塑時間觀。
一、物質的豐盛與人際關系的異化
豐盛是后工業(yè)社會中最普遍的現象之一。科技進步下機械化生產的普及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大多數人不再受困于溫飽問題。百貨商店中大量堆積的貨物昭示著這一點,人們進行購物這一活動后,貨架上消失的不過是總量的一小部分。“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1]琳瑯滿目的物品充斥在人們的視野中,供人們選擇。除了物的數量在增加,物存在的方式同過去相比也有所改變。物不再是以零散的方式存在,而是更多地以整套的形式出現,例如成套的衣服、化妝品和家具。這些成套的物品大多數時候以看似雜亂無章的形式出現,成為鏈條式的存在。物品的組合會對消費者進行誘導與心理暗示——成套的就是高級的、更好的。
《毛毛》中灰先生引誘毛毛的方式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灰先生將精致的布娃娃放到毛毛生活的露天劇場附近,誘使毛毛撿到后,又登門推銷布娃娃的妙處。布娃娃不斷重復著“我想要更多的東西”,毛毛不解其意,灰先生這樣解釋道:她需要許多衣服,比如漂亮的晚禮服。灰先生將一件又一件衣服從后備廂中扯出來,在毛毛面前堆成了一座小山,供她挑選。接著,灰先生又將口紅、粉盒、帽子、香水、玩具等一系列物品擺在毛毛面前,聲稱這才是與布娃娃玩耍的正確方式。灰先生說道:“這很簡單,人們必須有越來越多的東西,這樣才永遠不會感到無聊。”最后,灰先生又拿出一個男性布娃娃交給毛毛。當感到無趣時,就再讓布娃娃交新的朋友,新的朋友又會有他們的男朋友和女朋友,這樣就永遠也不會感到無聊了。
灰先生的手段十分高明。他給予毛毛的不僅僅是“足夠”,而是“太多”,一件漂亮的晚禮服遠遠不夠,布娃娃還需要不同種類、不同場合下合適的衣服。“你不是一下得到,而是要一個一個得到。”正如同消費者在進行消費時,很難一次將一整套的商品搬回家中。或許是因為財力有限,或許在幾年之后同一系列又出現了新的商品,資本總有辦法將消費者引入無窮的黑洞中去。在這樣的社會中,連朋友和戀人都可以成為一種商品——感到無聊時,只要交新的朋友或者戀人,得到新的刺激便好。灰先生的把戲沒能在毛毛身上得逞,但卻誘騙了絕大多數的孩子。大多數人顯然沒有抵抗誘惑的能力,即使知道灰先生的花言巧語是圈套,卻身不由己。虛榮心、攀比、盲目從眾心理,讓人在消費主義的泥淖中越陷越深。
物質豐盛的另一個表現是個性化的喪失。工業(yè)生產抹消了商品與商品之間的差別,甚至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無論是流水線上的商品,還是工人的勞動,甚至連服務行業(yè)都有統(tǒng)一的標準。
吉吉曾經以擅長講故事而受到在露天圓形劇場附近玩耍的孩子們的喜愛。在灰先生的誘騙下,他將自己擅長講故事的優(yōu)勢作為賣點,開始在銀幕上活躍。但是,離開了劇場和朋友們以后,吉吉的故事變得越來越乏味、單調,只能不停地改編過去的故事,即使如此,吉吉的故事還是深受朋友的歡迎。觀眾對故事的藝術魅力或真正的內核并不關心,他們僅僅將吉吉的故事當作一種商品消費,商品并不需要個性,只要依然擁有價值,自然會有人買單。
“當人們只能從消費之中獲得安寧感與存在感時,消費本身便不再是一個被動的接受過程。”[2]當毛毛的朋友們全部被灰先生的花言巧語蠱惑后,他們也偶爾會回憶起與毛毛一同在露天劇場玩耍時的快樂時光。毛毛回來后,他們也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接待了毛毛。但是,正如吉吉所說:“我已經不能自主了,想回也回不去了,我已經不再是吉吉了。”看似更加理想的生存環(huán)境使吉吉等人無法放棄現在的生活,強大的慣性推動著他們在消費社會中隨波逐流。
灰先生入侵后的世界,可以說正是消費社會的真實寫照。人們的生活更加富足體面,不再需要憂心于溫飽問題,最開始時,大部分人也對生存現狀十分滿意。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漸漸變得麻木,人際關系發(fā)生異化,連生命本身都變得毫無意義。而這一現狀產生的根本原因,正是灰先生奪走了大家的時間。
二、時間的扭曲與物質化傾向
《毛毛》的故事是圍繞著時間這一主題寫就的。灰先生為了生存竊取人們的時間,制成香煙,并靠吸食時間香煙維持生命。毛毛在時間管理者侯拉師傅那里見到了時間的原始形態(tài)——在水面上盛開的時間花,并最終用時間花拯救了整個城市。
灰先生的游說聽起來十分誘人:
如果您五年之內不把您存的時間取走,那我們就再付給您同樣多的時間。您的財產將每五年翻一番,懂了嗎?十年之后,就是您原來數目的四倍了,十五年以后則是原來的八倍。您可以依此類推。假如您二十年前就開始每天節(jié)省兩個小時,那么您到六十二歲時,即四十年以后,就會有原來數目二百五十六倍的時間供您使用。這個數目將是二百六十九億一千零七十二萬秒。[3]
時間在灰先生的嘴中擁有了金錢的特質——可以儲蓄、可以增值,在有需要的時候隨時可以提取出來。當然,灰先生的承諾是無法兌現的。在人們將時間交到灰先生手上的一瞬間,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再屬于自己了,而這只是灰先生的陷阱的第一步。“為把勞動者引向商品時間的‘自由’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身份,先決條件就是對他們時間的暴力征用。”[4]當人的自由時間被征用后,下一步便是走向同質化,成為工業(yè)流水線上的一件為資本創(chuàng)造價值的商品。弗西先生在聽完灰先生的勸說后,將老母親送入了養(yǎng)老院,不再與達利婭見面,鸚鵡也被拿到市場上賣掉。為了以最高的效率完成工作,他不再與顧客閑聊,原本接待一位顧客的時間現在可以接待三位。可是,省下來的時間似乎也并沒有如灰先生所說的那樣回到弗西先生的手中。時間似乎真的變成了金錢,將時間節(jié)省下來的人們似乎變得更加富裕了,可是他們卻無法享受自己的財富,只是一天又一天地為了節(jié)省時間而努力工作。他們忘記了灰先生的來訪,甚至連自己為什么要節(jié)省時間都已經忘記了。而事實上,正如故事中所提到的那樣,節(jié)省下來的時間一去不復返了,隨著節(jié)省下來的時間越來越多,人們能夠握在自己手中的時間反而越來越少了。
“生命的異化,不僅體現在勞動時間上,還表現為閑暇時間或曰自由時間的異化。”[5]自由時間是與勞動時間相對的、可以被個體支配的時間,可是事實上,在消費社會中,不僅勞動時間成為納入社會體系中的商品,連自由時間也很難掌控在勞動者自己手中。
在毛毛從侯拉師傅那里返回現實世界后,這樣的情況更加嚴重。
“現在你們到底要去哪兒?”毛毛想知道。
“去上游戲課。”弗蘭科回答,“我們在那兒學習怎么玩。”
“玩什么?”毛毛問。
“今天我們玩帶孔的紙牌。”保羅解釋說,“這種東西很有用,但必須特別用心。”
……
“玩得高興嗎?”毛毛懷疑地問。
“問題不在于好不好玩。”瑪麗亞膽怯地說,“不許這樣看問題。”
“那問題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保羅回答道:“問題在于這種游戲對將來有好處。”[6]
灰先生認為,孩子是最難攻陷的,因為孩子不在乎功名利祿,攀比心沒有大人那樣強烈,因此誘騙大人的話術在孩子身上并不適用。但是孩子也有弱點,那便是無法違抗大人的命令。灰先生先對大人進行洗腦,宣傳孩子們原本的游戲是浪費時間的觀點,再讓大人對孩子們施加命令,最終,孩子們全部被送到了兒童之家里,學習如何玩游戲。在消費社會中,游戲這項原本單純的娛樂活動也被納入了資本體系中。大人不允許孩子玩“浪費時間”的游戲,游戲的評判標準變?yōu)椤笆欠駥碛泻锰帯薄S螒蛎髅魇呛⒆拥奶煨裕瑓s需要有人來教孩子們玩,用一系列的規(guī)則來束縛孩子們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
在消費社會中,個體看似掌握了時間的主動權,人們可以自由支配工作之余的時間,但事實上,自由時間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2)不要將飄窗開在兒童房,飄窗窗臺低矮,兒童有可能爬上窗臺易發(fā)生意外給飄窗。國家標準《住宅設計規(guī)范》明確規(guī)定:外窗窗臺距室內樓地面低于0.9米時應采取防護措施,飄窗需加上安全防護欄[2],且不能隨便拆除,七層以上需采用安全玻璃以保證其安全性。
三、解決方案:重塑時間觀
《毛毛》的故事不僅是對現實社會的簡單影射,還給現代社會的種種弊病提出了解決方案。毛毛最終靠著自己的勇氣與智慧消滅了灰先生,使整個城市重新回到原本的軌道。在與灰先生戰(zhàn)斗之前,毛毛首先經歷的便是與烏龜卡西歐佩亞一起躲避灰先生們的追捕。文中這樣描述道:“盡管烏龜現在爬得比剛才還慢,但他們在這里前進得卻更快了。”在最終決戰(zhàn)前,毛毛催促卡西歐佩亞能不能快一點,它卻回答:“越慢越快。”
在康德的先驗時間理論中,時間作為一種純粹的主觀感性觀念被確認。“時間是直觀在我們里面發(fā)生的主觀條件,時間是先于對象,可以被先天直觀到的內直觀形式。”[7]換言之,時間是一種主觀維度,只有經過個體內心的確認后,才會發(fā)揮效力。因此,“越慢越快”也就能解釋得通了。雖然毛毛和卡西歐佩亞的行動變得更加遲緩,但是他們內心的時間并沒有變慢,可以行動的時間反而增多了。
在侯拉師傅那里,“時間是什么”這個問題的答案更加顯而易見。為了幫助毛毛更好地理解時間的概念,侯拉師傅給毛毛出了一個謎語:
家有三兄弟,
住在一屋里,
相貌雖不同,
區(qū)分卻不易,
乍看他們都差不離。
老二不在家,剛剛出門去。
只有老三家里坐。
老三排行雖然小,
至關重要不可少。
因為老大變老二,
生出這位三老弟。
你想盯住看其一,
總是看到他兄弟。
現在能否告訴我:
他們是一還是倆?
或者一個也不是?
他們都叫啥名字?
你若猜出這個謎,
將認識三個統(tǒng)治者。
他們三個皆強大,
治國齊心又協力,
兄弟仨人合為一,
王國就是他們自己![8]
毛毛深入思考過后,解出了侯拉師傅的謎題。老大是過去,老二是未來,老三是現在。時間是三兄弟所在的王國,世界是他們住的房子。過去、現在、未來是時間的三個重要維度,三者既互相獨立,又可以互相轉換。過去和未來借由現在這個維度得到確認,但它們又并非從屬于現在。現在是個體存在的維度,過去是已經發(fā)生的,而未來是即將發(fā)生的,時間的維度實際上是一種經驗性的顯像。
隨后,侯拉師傅又帶領毛毛來到了時間的發(fā)源地。一朵朵美麗的花在水面上盛開,在凋零后,又緊接著誕生新的、更加美麗的花朵。這就是時間的本來面目,在這里,“時間就是金錢”被徹底否定,侯拉師傅想教給毛毛的是另一句話——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原本是沒有實體的存在,但是在故事中卻化作花朵的形式呈現在毛毛面前。凋謝的花朵代表過去,盛開的花朵代表現在,含苞欲放的花朵代表未來。時間花的美麗給毛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此以后,這朵花也盛開在她的心中。每當毛毛對戰(zhàn)勝灰先生喪失信心時,時間花就會出現在她的心中,激勵著她。最終,她成功將被灰先生奪走的時間花返還到人們的心中,城市又恢復了原本的生機與活力。
“時間這種直觀形式,不能獨立地通過感官給予我們,除了經驗性的顯像之外,時間的實在性就蕩然無存了。”[9]毛毛在侯拉師傅處所見到的一系列與時間相關的物品,無論是恒星鐘和世界鐘,還是時間花,其本質都需要個體在心中重新確認時間觀念后才能運行。毛毛在經歷了一系列奇特的歷險后,雖然對時間的概念還有些懵懵懂懂,可是時間花已經出現在了她的心中。隨后,她將時間花還給大家的行為,也是幫助城市中的人們對時間維度進行再確認。時間花最終在人們的心中生根發(fā)芽,在所有人都能夠確認自己內心深處生命的共鳴后,灰先生的詭計也就不攻自破了。
恩德在揭露現代社會人類精神危機的同時,也保留了優(yōu)秀兒童文學的特質:質樸、純真和最原始的游戲性。他將一個個抽象而難以理解的概念具象化,使故事雖然有深刻的哲思,讀來卻也不覺得晦澀。在揭露了冷冰冰的現實后,他的作品給讀者帶來的并非絕望,而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帶給讀者生命最原始的美好與感動。它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將“時間就是生命”這一概念教給年輕的讀者,同時也喚醒了成人讀者早已麻木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