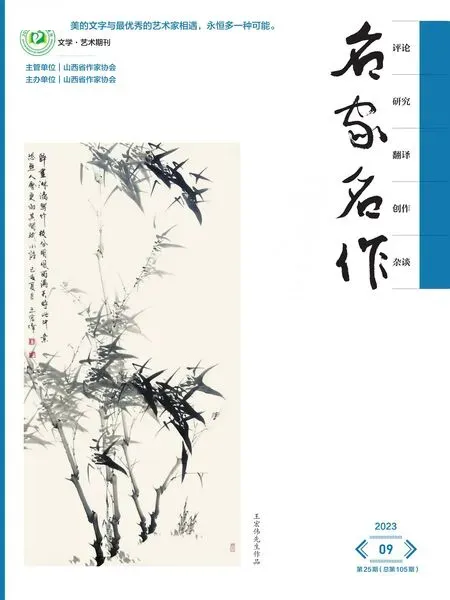馬華作家小黑微型小說研究
——以《微笑菩薩》《安德魯的SMS》《會飛的螞蟻》為例
陳 娟
從20 世紀20 年代開始,大量中國文人南渡東南亞地區并從事文學活動,這些南下文人是當時華人文學的核心創作群體。在這些文人中,有人傳播五四啟蒙文學,有人關注華校教育,有人用自己的文學作品啟發和影響華人,有人積極提攜有潛力的文人。二戰后到東南亞各國獨立、建國,東南亞作家經歷了從“僑民”到“國民”的身份轉變。直到20 世紀90 年代,很多本土華人作家崛起,且創作成績傲人。馬華作家小黑正是這個時代的華人作家之一。其創作的文學作品類型多樣、題材豐富,多次獲得各大文學獎項。本文擬在心理文化理論下分析小黑的三部微型小說中的人物心理和行為。
一、小黑及其三部微型小說作品《微笑菩薩》《安德魯的SMS》《會飛的螞蟻》
小黑,原名陳奇杰,祖籍廣東潮陽,1951 年生于馬來西亞。馬華文壇知名作家,1969 年開始發表作品,曾獲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小說獎、鄉青小說推薦獎、花綜小說推薦獎、楊升橋美國萬元馬華文學創作獎等多項文學獎,著有小說集《黑》《白山黑水》《尋人啟事》《結束的旅程》等,散文集《抬望眼》《大樹要開花》等。小黑也有多篇微型小說作品,本文選取其中《微笑菩薩》《安德魯的SMS》和《會飛的螞蟻》三篇以親情為主題的微型小說。三部作品中,小黑以簡潔的筆觸,生動地描繪了母子、父女、爺孫代際間的祈愿、期望和傳承:母親為了兒子的前程燒香禮佛行善;父親殷切地渴望女兒完成自己成為醫生的夢想,因擔心女兒壓力太大而轉變觀念;爺孫之間思想的碰撞,認知的傳承。小說雖然簡短,但結構緊密、情節巧妙,引人思考。
二、小黑三部微型小說作品分析
(一) 小黑微型小說作品中的家庭關系
《微笑菩薩》中,小黑筆下的秀蘭具有典型的母親特征:秀蘭的生活中兒子修文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多年來,秀蘭堅持每天燒香禮佛,“白瓷的菩薩塑像都漸漸給香火熏黃了”“拜了108 次”“注意菩薩的神情”“看見菩薩的笑容,她的心放下來”,修文中學最后一年獲得政府獎學金,赴英國深造。帶修文去面試的早上,秀蘭“起得特別早”“在菩薩跟前默禱了不知多少遍”,在修文接受考官提問的時候,秀蘭不停地默誦佛經……以上細節描寫,生動地還原了修文在秀蘭生命中的重要性。她不辭辛勞下跪、起身,數十年如一日燒香拜佛,費盡心思“觀察”“揣摩”菩薩神情,只為求得兒子健康、平安、學業有成。修文赴英深造的七年來,“秀蘭非常積極參與佛教會的慈善功德。菩薩保佑,讓她的孩子出人頭地,將來的子孫們就有更好的保障”,簡單兩句話,生動地刻畫了家庭中代際關系的主導地位。貫穿小說的主線就是母親秀蘭為兒子向菩薩祈禱,文中還提及為“子孫們”,就是沒有提及為自己或者夫妻祈福,整個家庭的核心就是兒子的健康、平安、學業、事業。家庭成員的關系以代際關系為主軸,其他關系被弱化到從未提及。秀蘭在印度貧民區齷齪的環境里樂此不疲地布施,積極參與各種慈善功德,都是懷著殷殷期盼在為子孫們鋪路,這也反映了秀蘭的觀念里對“代際關系”的強調和強化。
《安德魯的SMS》主要講述父親安德魯與女兒杰吉的故事。在這個家庭中,家庭成員間的談話內容、家庭里大家討論的話題都與女兒杰吉學醫科相關。文中安德魯與妻子的交流有兩處:一處是安德魯錄下跟女兒聊天的SMS,回家給太太看,“女人瞄了一眼,慢吞吞地說:你可不要給孩子太大壓力了。”另一處是:“早餐桌上,女人邊抹面包邊說:你讀報紙了嗎?好可憐啊。進不了首選的科系,為什么要輕生呢?安德魯瞪了她一眼:說一點快樂的,可以嗎?”可見夫妻兩人相處的十幾個小時內,互動話題都是關于女兒的學業,沒有夫妻之間的示愛,全部圍繞女兒的學業。這完全符合家庭中親子關系占主軸,夫妻關系因占優勢的親子關系而做出修正,讓位于親子關系的規律。
(二) 小黑微型小說作品中的信用借貸交換關系
《微笑菩薩》中,秀蘭與“菩薩”之間的關系,不失為一種受信用借貸型交換關系影響的人神關系:許愿與還愿。人向神明提出一些要求并承諾如何回報,如:“神明在上,請保佑我這筆生意順順利利,如若應驗我為您塑金身。”這種許愿和還愿明顯帶有信用借貸型交換的性質。秀蘭多年禮佛,祈求“菩薩”保佑她兒子:她許愿兒子康復,兒子第二天就舒緩了,她還愿:堅定信佛,堅持燒香拜佛;她祈禱兒子學業有成,兒子獲得政府獎學金,赴英深造,她還愿:虔誠、積極地參與各種佛教會的慈善活動;她祈愿菩薩護佑兒子出人頭地,將來子孫有更好的保障,兒子漸漸走上了平坦大道,她還愿:即便在齷齪的環境里做布施也很樂意。這許許多多的許愿與還愿之間,祈愿人秀蘭似乎與“菩薩”之間達成了某種默契:所愿之事朝向祈愿之人的預期發展,就是神明在保佑,祈愿之人就需要還愿,即加倍信任神明,遵照神明的指引做事。另外,所愿之事與遵照神明的指引做事兩者之間是非等價的:首先,兩者無法估價;其次,這里面還有祈愿人的情感投入;這就與信用借貸交換的非等價性完全吻合。還愿,即祈愿人為償還神明而遵照神明指引做事,這里的事情就因身份、地位等因素而異,凸顯了信用借貸交換的非限定性。
誠然,客觀世界中任何事物的發展必然都會遵循發展的客觀規律,斷然不會只是因許愿而使所愿之事成真,這種“許愿”只是身為家庭主婦的母親對兒子的殷切期盼,是一種內心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僅此而已;兒子清楚母親對自己的拳拳之心,日常生活中感知到母親望子成龍的期望,這些或許也是他努力學習的動因之一;抑或在他對未來發展沒有明確規劃的年少時期,母親的期望(兒子將來能成為一名醫生)為他指明了發展方向。小說中,“菩薩”是秀蘭掩沒在日常瑣碎中的愿望宣之于口的媒介,也是作家借口向讀者傳遞信息的渠道。借此,全篇秀蘭與修文母子二人雖然沒有任何對話卻全然不影響母子的溝通,作家也完美地實現了十余年的生活故事的講述。
《會飛的螞蟻》中,住在鄉下的退休教師永和計劃著接待來鄉下住幾天的孫子阿boy 去游山玩水,去看大自然如何孕育美好生命。爺爺花時間、花心思提供各種場地、條件,他的預期使孫子阿boy 從冰冷的知識學習中逃離開,與大自然交融,感受自然,體驗生命。所以當阿boy 在永和的帶領下觸摸溪水、跳入小溪玩水,與爺爺一起抓魚、釣魚時,阿boy 的所有玩耍都已經回報了永和,達成了他的預期。另外,永和的計劃與阿boy的回報,并不是同時發生的,回報有時間上的延遲,正是信用借貸交換的非同時性。在永和把一個蚯蚓撕成兩段作魚餌釣魚的時候,當阿boy 得知蚯蚓不會死而且還會變成兩只時,他說想要有兩個爺爺,一個住在這里,一個跟他回去,天天陪他玩耍。這個回饋是超出永和預期的,也是直接的增量回報,完美體現了信用借貸交換鼓勵增量回報的特點。
(三) 小黑微型小說作品中的抑制型情感控制機制
《安德魯的SMS》中父女二人用短信溝通,父親根據女兒的回復,結合從妻子處的反饋、自己的見聞,不斷調整語言表達,其實質是在時刻根據外部的反饋調整自己的情感。小說一開始就已經給讀者交代清楚安德魯的背景:年輕時夢想成為醫生,奈何讀醫科費用太高,家庭承擔不起,輾轉中成了一個書商。他辛苦經營,經濟條件尚可。一直努力培養女兒想讓她成為一名醫生,這就是安德魯的人生目標。在安德魯看來“讀書而已,很難嗎?”,而且已經為女兒籌劃好一切:讀書環境又好,又沒有經濟方面的后顧之憂。在安德魯的眼里,女兒讀醫科這件事情已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女兒勤奮努力,考出好成績。安德魯最強烈的情感(他的人生目標)就是渴盼女兒順利讀醫科并成為醫生。在遇到第一次外界情況(外部沖擊:女兒杰吉有三科沒考好)時,行為者安德魯對自己最強烈的情感做出調適:沒有表示失望和不滿,仍督促女兒堅定信念。在出現第二次外部情況(外部評價:妻子輕描淡寫提醒他女兒會有壓力)時,行為者安德魯對外部評價出現敏感反應,并對后續行為做出調整——鼓勵并寬慰女兒,說沒考好只是“一時的挫折、延遲一下”。應對第三次外部情況(外部沖擊:女兒沒有回復SMS+報紙報道年輕人因沒能進入首選科系而輕生+女兒隔天回復說太累了)時,行為者安德魯抑制自己最強烈的情感,調整“人生目標”,轉換態度:告訴女兒“可以轉系”,自己“沒有異議”。在遇到最后一次外部情況(外部沖擊:親眼見到一位青年因車禍橫躺在地面,猜不出生死)時,行為者安德魯將最強烈的情感渠道化為對女兒的關愛,不再執著于讓女兒學醫科這件事情。他推掉與老友的高爾夫之約,籌劃著帶上女兒愛吃的東西去探望她。
(四) 小黑微型小說作品中的自我認知
《會飛的螞蟻》中對自我認知的形成有生動的描寫。永和給孫子阿boy 展示自己用活蟋蟀、小青蛙或者小魚蝦喂養的碩大美麗的金龍魚時,阿boy 卻有一點焦慮。因為阿boy 在為那些小魚小蝦擔心,在小孩子的眼里,碩大的金龍魚嘴巴一張開,小魚小蝦就沒地方躲,也不清楚小魚小蝦還會不會出來。阿boy 還在認知自我、建立自我認知的年紀。故事里的阿boy,于他而言,有意義的人就是爺爺永和;物質就是他從小溪里抓回來的小魚。當他看到碩大的金龍魚吞掉小魚時會不安、焦慮,他可能已經朦朦朧朧感知到小生命的消逝,可是又不了解生命的周期和自然世界中小動物的各種生存險境。因為掛念小魚們,第二天一大早阿boy 就去看魚缸里的小魚,發現又有一些小魚被金龍魚吃掉后,就不愿再與爺爺去捉小魚回來了。至此,阿boy 已經漸漸對生命有了初步的認知:小魚會被大魚吃掉,生命逝去了就沒有了。
親子一體化,簡單來講就是父母更多的是把孩子當成是父母身體的一部分或生命的延續,而沒有把孩子當成一個獨立的有各種欲望、要求和感受的生命個體。中華文化有“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說法。父母對子女的“過度保護”是親子一體化在生活中的表現。孩子入學、挑選專業、找工作、買房、生子……都是父母一手操辦。《安德魯的SMS》完美地展示了親子一體化:父親對女兒的“過度保護”。女兒杰吉選專業這件事情直接就是父親一手操辦。小說中父親安德魯眼看女兒長大了,馬上送她進學院專修生物,向醫科的道路前進。女兒杰吉一直以來非常清楚父親安德魯想有個當醫生的女兒,不單只是杰吉,安德魯身邊的家人朋友都知道安德魯的這個“人生目標”。所以她的專業從來就不用“選”,是早已設定好的,無論她擅長與否、喜愛與否。
《微笑菩薩》中兒子修文一路按照秀蘭的意愿發展,雖然小說中只透過秀蘭向菩薩祈禱來展現作為母親對兒子學業和人生的規劃,但修文求學、工作的人生軌跡也的確是沿著秀蘭祈盼的方向發展。秀蘭一直把修文的事情視作頭等重要的事情,這也映射了親子一體化。
三、小黑三部微型小說中的人物關系:自我與他者的相遇
對于修文、杰吉和阿boy 而言,他們自己的學業、對世界的認知、人生走向到底是“自我”的探索和實現,還是“他者”(母親、父親、爺爺)夢想的延續或歷經世事后的領悟?他們會沖破“他者”的烏托邦,憑借自己吸收的陽光雨露生根發芽茁壯成長,還是會迫于長輩的權威不得不一步步遵照其指引走向“他者”的夢想?這是由來已久的難題,也是現代家庭教育中普遍需要面對的問題。從事教育工作的小黑關注年輕人的發展,在書寫中呈現了 “自我”與“他者”的相遇。
四、結語
分析馬華作家小黑的三部微型小說作品《微笑菩薩》《安德魯的SMS》《會飛的螞蟻》主人公的心理和行為發現:在家庭關系方面,秀蘭、安德魯都是以家庭為核心,家庭中親子關系占主導地位;在交換模式方面,無論秀蘭與菩薩之間的人神關系,抑或是阿boy 對永和的情感回饋,都完美詮釋了信用借貸交換關系;從情感控制機制分析,父親安德魯在面臨“自己的人生夢想”與女兒的健康成長出現矛盾時,一步步調適自己的情感,完全符合抑制性情感控制機制;著眼自我認知,阿boy 自我認知的形成和安德魯、秀蘭的親子一體化都生動地體現了互依型自我。同時,也引人深思:在親子關系中當“自我”與“他者”相遇時,我們該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