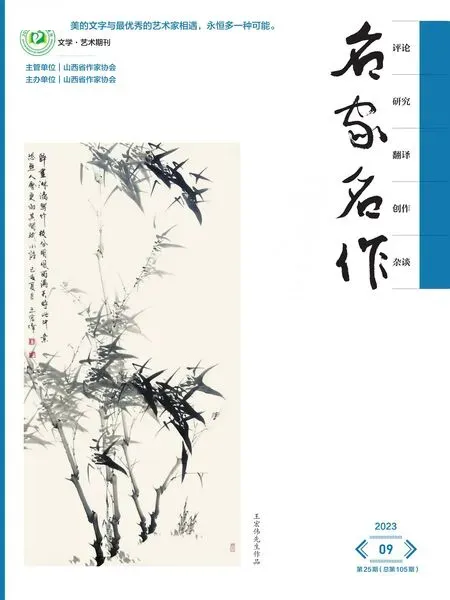對志賀直哉“調和”之路形成過程的研究
——以志賀直哉作品中的“死亡”為線索
孫 可
志賀直哉以白樺派代表作家之一而聞名,活躍于日本大正、昭和時期。他的代表作有《在城崎》《學徒的神》《和解》《暗夜行路》等。其中《在城崎》被公認為日本私小說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在文學界擁有重要的地位。志賀直哉在《在城崎》中通過對蜜蜂、老鼠、蠑螈三個小動物死亡的描寫,表達了自己療養時期對于死亡的感悟。《在城崎》讓大正時期的教養主義在文學界開始流行,同時也開創了調和型私小說(又被稱為心境小說)這一新類型。有關死亡的描寫在志賀直哉的小說中并不少見,本文嘗試從志賀直哉幾部作品中對死亡的刻畫及思考,解析志賀文學調和之路的形成。
一、對死亡的恐懼與反抗
《為了祖母》與《某個早晨》《母親的死與新的母親》都為志賀直哉自身生活的早期作品,三部作品中都包含一個人面對親人即將去世和去世后的復雜情感。其中《為了祖母》里對死亡的心理活動描寫最為豐富,可以說在志賀早期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高橋敏夫(1987)認為《為了祖母》是一個對正在衰弱、崩壞的內部導入來自外部否定的契機,然后為了確保內部的穩定,將外部契機排除的故事。從小說開頭的部分可以看出,祖母是“我”的依靠,祖母病倒后,“我”對祖母的死亡產生恐懼,就是高橋所說的來自外部的危機。《為了祖母》中在祖父病逝十五分鐘內,患了白化病的殯儀館員工“羊白頭”就趕到現場,高橋認為他是虛構的外部契機。在文中,他“經常揣著兩手在路上晃晃悠悠地走動。在我看來,那就像饑餓的肉食動物在搜尋獵物一般”。祖母感冒病危后,“我一定會拼命盯著房間里黑暗的角落,在那里,其實并不能看到羊白頭那灰色的眼睛,但我卻臆想著——并且盡量——用盡全力緊緊盯著那眼睛”。我認為羊白頭這個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死亡,在祖母痊愈,“我”準備帶祖母到鵠沼休養時,路過殯儀館門前沒有看到準備辦喪事,“‘說不定是羊白頭死了!’——僅僅只是猜想就讓我胸中悸動不已。……從后面望著前方車里微微露出的矮小的祖母那戴了頭巾的腦袋,我很想怒吼一聲‘看啊’,但極力克制住了。”“羊白頭確實是死了。——關于這件事的含義我絲毫沒有懷疑。”從文中“我”強烈的情感中可以看出人們對戰勝死亡的喜悅。根據高橋的理論,“我”與祖母同屬內部整體,而死亡是外部因素,因此《為了祖母》表現出的是“我”與死亡的對峙,即自我與外部的強烈對立。
二、對死亡的勝利
《范的犯罪》是志賀直哉虛構的作品,靈感來源于一位親戚的遭遇,那位親戚因妻子出軌而自殺,作者試圖在小說中表現出相反的結局。在虛構的情節中,也強烈反映出作者本人的心境。下岡友加(2010)認為,《范的犯罪》通過種種手法讓讀者代入范某的視角,講述范某從壓抑中解放的故事。現實中親戚因沒能擺脫被背叛的心境而自殺,所以志賀直哉很可能想要將范塑造成一個戰勝壓抑的具有強烈自我主義的角色。
范某的助手回答法官對夫妻兩人品行的詢問時答道:“她是個正派的人”“他倆待人都極為和善”。法官問范某:“你此前絲毫沒有愛過你的妻子嗎?”范某回答:“從結婚那天起直到孩子出生時,我曾經真心愛著她。”法官問妻子是否愛著范某時,妻子回答“不愛”。“我越發覺得,這樣瞻前顧后,成天愁眉苦臉,又不敢正視自己內心的愿望,對無比厭惡的事也沒有勇氣拒絕,這半死不活、窩窩囊囊的日子都是與妻子的關系害的。對自己的未來我看不到一絲光亮。但自己心里還燃燒著尋找光亮的愿望,我要讓它燃盡,妨礙這種燃燒的正是我與妻子的關系。而那團火總也不熄滅,還在那里冒著煙勉強地燃燒著。那種不快和煎熬簡直就要讓自己中毒,徹底中毒時自己就死了。雖然現在活著卻成了死人。”從以上描述可以推測出,文中范某的妻子形象來自現實里親戚的妻子,但除了真正意義上的“妻子”,也象征著范某無法自我原諒的一面,范某與“妻子”都是“正派”且“極為和善”的,彼此都無法愛對方,說明兩者有同一性。下岡也在論文中說到,使整個“從壓抑中解放”的故事更加堅固地完結的“裝置”,就是法官的“無罪”判決。“我想著,終于殺了她。”“此話怎講?是故意為之的意思嗎?”“是的。無意間做了仿佛是故意的事。”“我突然興奮起來,興奮到坐立難安的程度。我感到無比愉快,甚至有種想要大喊大叫的沖動。”“對現在的我來說,被判無罪就是一切。我絕不斷言這是過失所致,另一方面,我也絕不會說這是故意所為。”“‘可是你對妻子的死,絲毫沒有感到悲傷嗎?’……‘完全沒有。即使是從前對妻子萬般憎惡時,也想象不到自己竟然能以如此快活的心情談論她的死’……法官感到內心涌起了莫名的亢奮。他立刻拿起了筆,接著當場寫下了‘無罪’二字。”以上法官對范某下達無罪的描述,看上去是不符合常理的,范某殺害了妻子是不爭的事實,而他殺人后的態度是過失還是故意又模棱兩可,卻使法官亢奮地給出“無罪”判決,這就說明了《范的犯罪》并不是真實地記錄針對范某殺妻的審判,而是通過范某的直白,講述了其戰勝自己壓抑面的故事。
在《范的犯罪》中,妻子的死亡同樣代表勝利,是自己與自己過失的斗爭的勝利,對范某“殺死”了自己過失的一面并感到無比愉快的“無罪”判決,是志賀直哉表達戰勝過去的強烈自我意識,但是范某本人的糾結與痛苦同時也是志賀本人的夢魘。近代文學研究者紅野敏郎評價《范的犯罪》為“志賀文學初期自我擴張的巔峰之作”,而《在城崎:志賀直哉短篇小說集》譯者吳菲評論:“這種與周遭激烈對峙的心態,在作者經過數年的沉默與掙扎之后,才找到通往自我調和的出口。”
三、死亡的答案
《在城崎》作為志賀直哉最知名的作品,一直是志賀文學研究中的熱門,而圍繞《在城崎》中三種動物:蜜蜂、老鼠、蠑螈的死的解讀不計其數。山田伸代(2017)在《志賀直哉の『城の崎にて』をよむ:靜かなる生と死》中闡述了對《在城崎》中生與死的理解。山田認為蜜蜂的死對于志賀來說是“獨自一人的、孤獨的、寂靜的”,“只我一人,連個說話的對象也沒有”,此時“我”假設了如果因電車事故而死,“現在大約已仰躺在青山墓地的土里了。……身畔是祖父和母親的尸骸,且相互之間已沒有任何交涉。”這里志賀提到了祖父和母親,志賀其他作品里對兩人的描寫,《為了祖母》里寫祖父“是個很有本事的人,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很了不起。祖父是整個家族的頂梁柱,對祖母而言幾乎就是一個偶像”,可以看出祖父是一個被包括作者在內的所有人所敬佩的存在,并且《為了祖母》中的“我”第一次對“羊白頭”產生敵意就是因為祖父的死,那樣有本事、健壯、被人所敬佩的祖父一死去,病態的“羊白頭”仿佛等候多時,令“我”感到可疑,仿佛覺得他在期待著別人的死。而在《母親的死與新的母親》中,“我”的生母在病逝時,志賀通過幾個側面描寫使讀者感受到當時的悲傷,比如“大家都議論說,潮汐退去的時候,人也會隨之逝去。聽了這個說法,我跑去母親最初養病的房間,一個人撲在那里哭泣。學仆進來安慰,我問他:‘退潮是幾點鐘?’學仆回答:‘再過大約一個小時。’我想,母親再過一個小時就會死嗎?‘再過一個小時就會死嗎?’不知為何那之后也時常回憶起當時曾這樣想過”。不難看出,在志賀早期的作品里,親人的死令人悲傷,尤其是《為了祖母》里的祖父,即使有本事、身體健康,在死亡面前也是無力的,這使當時的“我”對“羊白頭”、對死亡的對抗意識開始覺醒,并在早期作品中逐漸達到巔峰。《在城崎》里則是說到,如有閃失,自己可能已經和祖父、生母一樣死去了。因電車事故受傷時,志賀說“如果發展成脊椎骨瘍難保不會變成致命傷”,在此擔憂下,此刻志賀的心態已經發生了變化,開始思考死亡的本質,“雖然凄涼,但這想法并未令自己感到多么恐懼,總有一天將會如此。……總是不知不覺地把‘總有一天’當作遙遠未來的事,而現在卻越發感到那真的是不知何時。……奇特的是,我心里一片寧靜。我心中對死亡產生了某種親近感”,就像《母親的死與新的母親》里所說,“‘再過一個小時就會死嗎?’不知為何那之后也時常回憶起當時曾這樣想過”。而《在城崎》中作者對蜜蜂的描寫,真實地說明了這一過程。《在城崎》中也提到之前寫的《范的犯罪》,并說:“作品主要描寫了范的心情,但現在,我感覺自己更想以范妻的心情為主,描寫她被殺后在墳墓中的那種靜謐。”上文我分析《范的犯罪》中的范某與妻子的對立可能象征著對立的自我與自我斗爭的勝利,而《在城崎》中作者產生了與彼時不同的想法,死亡如此接近,無論是勝利的范某,還是身死的祖父、生母、范妻,等待眾生的最后都是靜謐。
對于老鼠的死,“老鼠為了不被殘殺,雖身負死期已至的命運,依然竭盡全力四處奔逃的情景奇特地刻印在腦海里。我感到凄慘且心生厭倦。我想那才是真實的。”而后又通過描寫自己受傷時就醫的情形,表達真正面臨死亡時的反應,這是人之常情,訴說自己與前文認為死亡很“靜謐”“親切”不同。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志賀也許認為老鼠的死是還沒有認識到死亡本質的階段,所以“感到心生厭倦”,就像當初還無法和解的自我的掙扎。之后的登山及蠑螈之死的部分,就像眾多研究中得出的結論,志賀感受到生命的無常,生與死的間隔如此之近,用一句“它們并非兩個極端”作為《在城崎》思考的結束。
《在城崎》與志賀直哉之前的作品比起來,是一篇頗為溫和的小說,文中充滿了動與靜的對比,勞碌的蜜蜂、掙扎的老鼠、被砸中時躍起的蠑螈,它們是動的,而無論是以自然的方式死去,還是以意外的方式死去,它們最后都歸于寧靜。對登山時桑葉隨風抖動的部分的解釋是《在城崎》研究的難題,一直眾說紛紜。志賀在《創作余談》中多次解釋了寫這段的緣由,其中在《生命》(《在城崎》的初稿)中的解釋較為合理,他說:“由于其方向和植物葉柄軟硬程度的緣故,只有那片葉子才可以感覺到其他物體所感覺不到的微弱的風。這就好比時鐘的秒針精密地不停跳動一樣。其他物體也能感受到的那種程度的風刮起來的時候,這片葉子反而會停止抖動。”(肖書文,2006)但就像《范的犯罪》中對殺人行為宣判“無罪”的不合理一樣,這里也不必過分追求物理學上的合理性,不妨從文藝的角度去解讀。在登山時,拐過幾個彎后,“景物都顯得蒼白,空氣涼颼颼的,‘寂靜’反而讓我有種心神不寧的感覺。”如果把“靜”與死亡聯系起來,可以解讀為還沒感悟時對死亡的不安,而那片桑葉先在風中翻動,其他樹葉隨風而動時它卻停止不動,是代表了生前的動到死亡的靜的變化,“我”因為觀看了忙碌的蜜蜂融入泥土的過程,所以說“自己應該明白其中緣由”。
總之,在《在城崎》中,死亡代表無常、寧靜、和諧、萬物的最終歸宿,也是和自己命運的和解,正如孟子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四、結語
志賀直哉因《在城崎》《暗夜行路》等作品被稱為心境小說的代表作家,但他的心境歷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從早期作品中與死亡的對立,到被稱為心境小說的作品中對死亡靜謐、糾結、無常的認識,是逐漸發展的。在動蕩的昭和時期,人們即使生活還算安定,也會經歷眾多變故,尤其是以自己的生活為模板進行創作的作家。日本近代史上眾多私小說作家為了創作出別具一格的作品,大多過著不同尋常的生活。志賀直哉的心境小說也被稱為“調和型”私小說,與之相對的是“破滅型”私小說,代表作家是太宰治。太宰治最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以厭世著稱的芥川龍之介同樣也是自殺,志賀直哉與兩位作家都有所交集,芥川龍之介死后,志賀直哉在《沓掛にて—芥川君の事—》中提到,芥川說自己不是適合寫小說的人,志賀回道:“誰都有那樣的時候,就那樣接受不也挺好的嗎?抱著冬眠一樣的心情休息一兩年試試如何,以我的經驗,那之后就能寫出來了。”
白樺派文豪們經常因為出身較好而遭受非議。包括太宰治在內的許多人評價志賀直哉的作品不夠接近平民,芥川龍之介在《文蕓的な、余りに文蕓的な》里評價志賀直哉,“也許是像神一樣活著的人物”。志賀本人的一生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他經歷過和父親的不和與決裂、電車事故、自己的兩個孩子死去,但他沒有像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最終破滅,而是對抗死亡、理解死亡并自我和解地活著,就像成為佛一樣的神明,但這一切也是有一定的過程的,志賀直哉最終也在暗夜的路中找到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