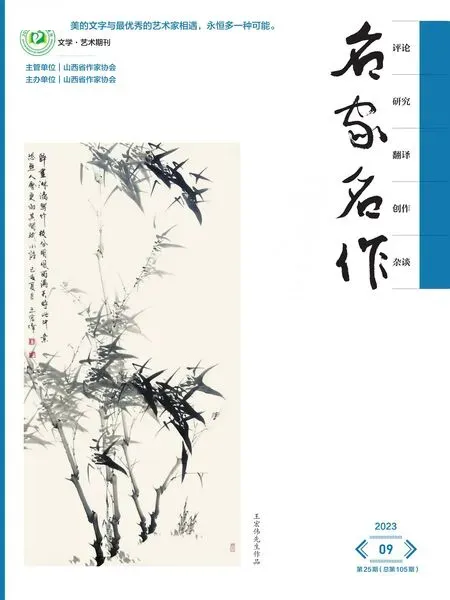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格非的創作
王 昭
1986 年,格非以卓然的先鋒姿態邁向文壇,用獨有的詩性語言和智性思考編織著小說敘事的旗幟。實際上,格非的創作經歷了曲變,這與當時的特定歷史文化語境有著密切關聯。因此,除了從作品維度研究格非的小說,從讀者接受的角度進行分析也是不可回避的。
一、打破期待視野的先鋒敘事
在姚斯看來,“‘期待視野’顯然指一個超主體系統或期待結構,一個所指系統或一個假設的個人可能賦予任一本文的思維定向”,換言之,在讀者閱讀作品之前,基于自身的閱讀經驗形成一種定向思維,這種思維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讀者對作品的預設和判斷。當這種視野建立之后,作品中的語言符號和情節構思會使得讀者與作品之間產生一定的審美距離,通常情況下,陌生化的敘事往往會更加吸引讀者積極地參與到作者所建構的想象世界中,不斷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雖然這種距離并不能成為判斷作品好壞的唯一標準,但卻可以激活作品中的技巧,并賦予文本意義。在格非的《褐色鳥群》中,故事的結尾又有一個女人來到“我”的公寓,可她卻不再是此前的“棋”,那么“棋”究竟是否真實存在過呢?“我”的記憶又是否可靠?這在作品中是無法找到答案的,讀者從這個缺口處對記憶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不知不覺進入一個不見盡頭的迷宮,并不斷觸發其中的回憶機關,“我”向“棋”回憶著與棕色短靴女人的故事,而之后面對新的訪客,“我”又開始在回憶中尋找“棋”存在過的印記,一個回憶里套著一個回憶,循環往復,無始無終。這種敘事技巧打破了傳統的完整線性敘事的閱讀經驗,指引讀者從故事中轉向對現實存在的拷問,作品也由此完成了從生產到接受的本文建立過程。
期待視野的形成不僅會受到個體閱讀經驗的影響,群體的意識形態還會與讀者建立彼此引導的機制。某段時期的主流文學是一面可以折射出當時歷史語境的鏡子。20 世紀80 年代是中國當代文學在經歷了跌宕與緊張之后的探索活躍階段,初期的總結歷史經驗、邁向新發展成為社會的整體風向,此時的 “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是人們對過去追根溯源、療愈創傷的載體;而到了中后期,國家工作重心向經濟轉移,再加上此時一些外來思潮文化的涌入,各種西方文學作品與理論美學蔚然成風,在新的語境下,人們開始追問本質,并重新審視歷史。此時,以格非為代表的作家們勇當先鋒,用各種新奇的形式技巧開拓著讀者的接受視野,為先鋒文學在八九十年代的茁壯生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環境。
1986 年,22 歲的劉勇在《中國》第二期上發表了《追憶烏攸先生》,此時他還未采用“格非”作為筆名,之后,《迷舟》《褐色鳥群》《青黃》等作品接踵而至。回看格非此時的創作,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文本的先鋒色彩,循環交替的敘事圈套、神秘莫測的夢境書寫、引人遐想的空缺敘事等,從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這些技巧恰恰是讀者可以和作品保持平衡的一種中介。《迷舟》在一開始就向讀者設置了一個革命戰爭的歷史背景,卻沒有朝著傳統革命敘事的方向發展,沒有宏大的戰爭場面和激情的精神對話,小說以“蕭旅長”的返鄉為開端,悶熱的天氣、焦躁的情欲以及神秘的暗示,使整個故事氤氳在一種迷霧氛圍中,撲朔迷離,危機四伏,而一切的謎底都終結在警衛員的六聲槍響之中。小說中的一些特定符號指引著讀者的理解方向,瞎子的卦語、王二嬸的眼神、警衛員的身份等,但讀者并非只是被動地跟隨作品的腳步,最后的空白讓讀者陷于思考的旋渦,蕭旅長去榆關究竟是為了見杏還是為了向兄長傳遞情報?空缺的出現讓讀者感受到了革命歷史的另一面——隱秘性,從而瓦解了對歷史的宏偉想象。
由此可見,特殊的接受語境為先鋒創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格非在敘事技巧上的實踐打破了20 世紀80 年代讀者的期待視野,作品中形式與意義的先鋒性得到整合,奠定了他的創作在當代文學史上極具變革性的地位。
二、拉近審美距離的現實探索
站在文學史的角度回看先鋒文學,新穎的形式技巧的確對當代文學的發展起到了前瞻引領的作用,但其中也存在無法回避的問題,那就是短時間內對西方的歷時性文學成果的接受,似乎早已注定會是曇花一現的命運。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先鋒作家在短暫的光芒四射之后逐漸落幕,他們面臨著共同的寫作困境:如何擺脫形式的影子而重建文學的現實性?“失去形式的遮掩,‘先鋒派’小說不僅在思想意識方面顯得平淡無奇,同時,更重要的在于,他們回避現實的寫作不能不說是一個致命的局限。”隨著先鋒文學的敘事技巧被廣泛地接受與認同,它的獨特魅力也隨之消殞,當這種敘事形式不再具有陌生感,一些形而上的思考就顯得有些空洞晦澀,作品與讀者之間便會產生疏離感。倘若繼續將技巧作為指南,那只會走到創作的“死胡同”中去。于是,回歸現實便成為重新聯結作品與讀者溝通的紐扣,在這種境況下,格非開始扭轉文學創作的方向,他的思考命題由“怎么寫”變為了“寫什么”。
1995 年,《欲望的旗幟》的出版可以明顯展露出格非向現實回歸的意緒。故事以一場學術會議展開,其間受到了各種突發事件的干擾:賈蘭坡教授自殺、宋子衿精神分裂、贊助商被捕等,一場嚴肅的學術報告變成了一出荒誕不經的鬧劇。“事實上,它只是一把刻度尺。”格非用這部作品來丈量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廢墟。對比此前的創作,雖然小說中依然生發出對個體存在的哲學思考,但格非儼然已將鏡頭轉向人們的欲望訴求和精神困境等一些現實問題。除此之外,他的形式先鋒也有所收斂,對技巧的使用更加配合內容的表述,這樣的改變重新拉近作品與讀者之間的審美距離,形成新的本文“召喚結構”。這個概念是由伊瑟爾提出的,他認為一部作品的創作結束并不僅僅是真正完結,只有當讀者完成閱讀接受,并挖掘或賦予作品意義,這才能稱得上是一部完整的“本文”,在這個過程中,作品會設置一些“召喚結構”來引導讀者的理解,規避主觀的偏差與誤讀,在作品中往往表現為“隱喻讀者的塑造”“結構策略的安排”“否定引起的空白”等。
首先,隱喻讀者指的是作家在創作時構想出的一個非現實的讀者,他能夠“深深植根于本文的結構中”,理解作家的創作意圖,并對之后現實讀者的閱讀起到引導作用。格非此前的先鋒作品使用了較多的形式策略,再加上高蹈性的哲思,導致作品的接受范圍受限,這是由于其中的隱喻讀者與現實讀者產生了落差。而《欲望的旗幟》調整了隱喻讀者的身份,縮小了與現實讀者之間的距離,并在作品中將知識分子拉下神壇。小說中,賈蘭坡教授主體分裂,一個是懷揣敬仰的哲學信徒,一個則是出軌、引誘女學生的變態;現實讀者透過隱喻讀者的眼睛窺探知識分子的矛盾掙扎,探尋當代人的精神病癥所在。其次,在作品結構策略的安排上,格非將人的欲望作為小說的中心內涵,學術會議、愛情選擇、信仰分歧等統統淪為精神廢墟的背景,張末與曾山想借愛情慰藉彼此無處安放的靈魂,卻發現這并不會緩解心靈的孤獨,在離開曾山后,鄒元標的追求讓張末陷入道德與欲望的掙扎之中,格非通過背景——主體的策略安排不斷矯正讀者的閱讀感受:在張末感情迷惘的背后,是升起的欲望旗幟在作祟。當然,除了對現實主題的觸碰,作品中的空缺依舊會指向對存在哲學的思考,賈蘭坡的死因成謎,宋子衿的話難辨真假,慧能院長與師母的關系令人匪夷所思……讀者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向現實發出詰問,但最后也只能進入對個體本質的無解狀態。
格非通過自己的探索,填補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溝壑。先鋒文學在20 世紀90 年代之后很難激起大的浪花,格非也在此擱筆將近十年,但之后的再度回歸卻開拓了讀者接收的新海域。
三、實現精神凈化的烏托邦想象
“烏托邦”是指那些脫離現實糟粕卻永遠無法企及的美好想象,它的建立既是對現實問題的直指與逃離,更是對至高境界的仰望與追求。在格非停筆的十年中,人們經歷了生活時代的變革和精神際遇的挑戰,20 世紀90 年代之后的文化接受語境更加青睞于市場資本運營的節奏與模式,鋪天蓋地的媒體信息覆蓋著人們的思想領域,許多文學作品逐漸模糊了與社會新聞之間的界限,“當下的很多作家跟公眾意識之間沒有距離,而是統一的,所以迫切需要來自外部的力量‘入侵’進來”。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一經發表,就成為這種外部力量的支持,此后《望春風》的出現更是持續了這種外部力量的干預,在“故鄉已死”的普遍認者的期待視野中重構鄉村詩學,還原美好的鄉村圖景,在現代人的精神廢墟上建造烏托邦,由此,讀者再次面臨挑戰,作品的形式策略與精神意向發生嬗變,二者之間互相成就,凝結出更為成熟完滿的現實書寫,并為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尋找救贖路徑,此時的讀者以舊的視野迎接新的創作,進而生發出新的視野想象,完成視野交融。
《望春風》以第一人稱的成長視角呈現出儒里趙村四十年的時代變遷。格非曾談道:“我可以從敘事口吻、人稱視角來體現它的‘成長性’,這種成長性會隨主人公年齡閱歷的變化而出現。”小說中,兒時的“我”在儒里趙村與父親相依為命,而父親死后“我”受到村里人的照顧,感受到的是儒里趙村的善良與淳厚;成年后的“我”久經世故,在南京的生活一塌糊涂,重回故土卻滿目瘡痍,昔人已去,物是人非。讀者跟隨小說的語言基調體味“我”由年少懵懂到飽經滄桑的變化,其閱讀視點在這一過程中開始出現轉變,由人物視點向敘事視點轉移,讀者將儒里趙村由敘事背景拉至閱讀視野前方,并無限地放大,而“我”則成為整幅蕭條畫面的一部分。這種閱讀視點的游移是讀者在接受過程中表現自我感覺的一種方式,讀者透過“我”的眼睛,看到儒里趙村由古樸寧靜變為劫灰滿目,焦雨山房、罌粟花園、老福奶奶家的籬笆院,最后都化為溫柔卻哀傷的春風;儒里趙村經歷了時代變遷,政權讓位于資本,代際關系發生斷裂,傳統道德人性走向衰弱,讀者由主人公的悲劇感嘆轉為對故鄉的沉湎。
然而,格非不忍再給生活于苦難中的人們增添絕望,因此,“《望春風》里我想讓悲劇性的人物散發出一些肯定性的力量”。在故事的結尾,趙伯渝與春琴重回便通庵,過著聽雪種菜、打井燒柴的原始鄉村生活,雖然現時的幸福隨時面臨著坍塌的危險,但是片刻的擁有于“我”而言,已是無比的滿足。在格非看來,《望春風》的結局不能完全算作普通意義上的烏托邦,因為趙伯渝與春琴的確實現了與世隔絕、相濡以沫的生活狀態,但由于這種生活又存在不真實的特征,便只是給讀者營造了一種烏托邦的氛圍。讀者在接受過程中會在作品與現實之間來回穿梭,既能進入主人公的悲歡離合之中,又能保持自我意識,在跳出起伏的情緒之后進行獨立思考,從烏托邦的想象中找到現實的答案,進而完成自我的更新與凈化。當代社會中,人們在與自然、自我、他人的交往中存在著難以彌合的裂痕,并追索著個體存在的本質,這種彷徨、焦慮在格非的烏托邦書寫中似乎獲得了一些安慰,這也是小說的最大意義所在,那就是對自然美與人性美的肯定與追逐,對精神家園的重建。
格非在十年擱筆后再度回歸,借用中國古典敘事的傳統書寫人文關懷,對形式技巧的熟稔使用使得作品與讀者之間產生高度的契合,推動著格非的創作邁向新的階段。
四、結語
綜上所述,從接受美學的角度重新梳理格非的創作,其中對技巧策略的使用,引導著讀者的理解方向和角度,并推動著讀者不斷地追問與探尋,從而使作品的哲學內涵得以生成。而讀者在接受過程中不斷調整與作品之間的距離,主動走入作家的敘事圈套,觸發作品中的形式按鈕,使作品的審美價值與意義得以彰顯,在敘事想象中更新對生活的理解,完成精神凈化。在整個過程中,讀者與作品相輔相成,共同確立了格非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特殊地位——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