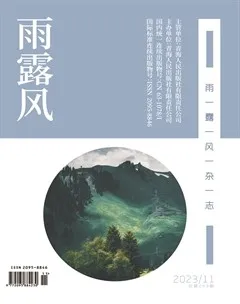論施蟄存小說中的鄉土文化
20世紀30年代,施蟄存作為新感覺派的代表人物,以出色的心理分析小說被人們熟知。本文另辟蹊徑轉而重點關注其筆下“都市異鄉人”,分析這一群體的鄉村經歷與都市生存狀態,生動地展現豐富的鄉土文化、繁華都市下對鄉土的企慕以及城鄉碰撞之后的鄉土展現。
施蟄存出生于書香門第的江南小鎮,作為新感覺派的中堅人物,他有著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為了生活,奔赴聲色犬馬的大都市,現代都市文明與傳統鄉野文化發生了碰撞。大都市是金錢統治的世界,人與人之間的陌生關系、唯利是圖的生存哲學強烈地沖擊著傳統文化,游離于都市之外的異鄉人施蟄存展開了對鄉土的回望與追尋。
一、都市異鄉人的鄉土回望
都市異鄉者是突入城市的“異質”,城市是他們一代甚至幾代人的異鄉,而鄉村也不再能安妥他們被城市文明招安的靈魂。他們遭遇了空前的文化身份認同困境,在自愿與非自愿、自然與非自然地接受著身份的異化。本質性的一個“異”字恰切地顯示了這一介入沖突和掙扎的精神歷程。面對大都市,他們始終無法融入其中,但現代都市的魔力又無法讓他們回到淳樸的鄉鎮,造成了都市異鄉人城與鄉二元對立的文化心理。通過描寫鄉土實現精神還鄉的施蟄存,將鄉土情結推向頂峰,通過對曾經故土生活的回憶來描寫鄉鎮純粹的風情、風俗、風景,展開對故土的回望,傳達對精神桃花園的尋覓與憧憬。這種鄉土情結使他在作品中執著追求人生信仰與生命的價值,贊頌著鄉土之上自由的生命與淳樸的人性。
(一)淳樸溫情的鄉野倫理
旅居上海的施蟄存曾寫道:“假如有一天能使我在生活上有一點夢想的話,我只想到靜穆的鄉村中去生活,看一點書,種一點蔬菜,仰事俯育之資粗具,不必在都市為生活掙扎,這就滿足了。”[1]他如此醉心于鄉鎮,在其正式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上元燈》中,以秀逸安詳之筆展示了家鄉杭州、松江和蘇州的風土人情,把那里的江河、小屋、茶樓、私人小院一一陳列,采用奧格登和瑞恰茲提出的語義三角理論,通過飾品來寄托情思感受。書香人家書齋秀房中擺放的書畫、燈扇等一些極為常見常用的物品,卻寄托著極為樸實真摯的感情。翻開第一篇就是一幅“輕羅小扇撲流螢”的美妙動態。寫道兒時玩伴兼暗戀對象在園中賞月,用團扇來捕捉螢火蟲的情景。一把茜色輕紗的團扇,呈現出兒時純真美好的友誼,以及少男少女兩小無猜懵懂的初戀故事。一把扇子寄托多少美好的溫情與遐想,抒寫了江南水鄉詩意般的桃花園生活。
《上元燈》中,在張燈結彩的元宵燈節,“我”換上嶄新的皮袍去見她,純真的她卻心直口快地說:“這新袍怪刺眼的,還是舊的好。”隨后她表兄強行拿走了本該送給“我”的“玉樓春”,“我”郁郁寡歡。可第二日,她卻把一架更精致的青紗彩燈送給了我。盡管在她母親的偏袒下富貴而庸俗的表兄獲得向她求婚的先機,但她也只管按自己的心意來:“由他們去,我總是拒絕。”她以精心制作的彩燈相贈,向“我”表明愛意,含蓄委婉不失大體又帶有詩意。以一盞彩燈向我們傳遞兩小無猜的純真感情,別有一番風趣。這里,可以將少女精心制作的古典雅致的彩燈與都市中絢麗多變的霓虹燈作比較,將鄉鎮中的團扇與都市里的電扇、鵝毛扇相對照,雖然這些舊物已經沒人使用了,但它們古風悠悠,有著纖塵不染的真情,承載著多少美好與純真。以至作者從內心呼喊:“天啊!能夠再讓我重演青春的浪漫故事嗎?”
《漁人何長慶》里一個遠離喧囂的小鎮有著古老美麗的傳說,有四季豐富的時蔬,有種類繁多的海鮮,也有鎮上人的閑言碎語,16歲的何長慶也因流言遠離了云大伯而自立門戶。他勤勞能干,把生活過得有模有樣。當他知道自己喜歡的菊貞與青年私奔到上海后,他郁悶了一天,又像往常一樣工作了。只是到鎮上去的時候,他時時留心著菊貞的消息。當聽聞菊貞的遭遇時,他毅然決然把菊貞接回家中,盡管鄉人還會議論他,但他成了當地最大的漁戶,兒子也開始到魚攤上照料生意了。小說沒有揭示何長慶的苦與酸,總是尋覓那掩藏其中的生命的光芒,給人溫暖和希望。人物心靈在這個淳樸的小鎮中得到凈化,作者以此呼喚人們皈依自然,贊美淳樸的世風民情。小說透視了古樸的鄉村文化和奢華的都市文化的異同優劣,作家顯然趨向于對鄉村的歸同,只有在鄉鎮才能找回最初的自己。
(二)理想的人物形象
鄉鎮是施蟄存精神的桃花源,那里不僅有淳樸的民風,還有天真可愛的村民。施蟄存是一個具有典型中國傳統人格的作家,出身書香門第,早年舊學的熏陶,給他后來的生活與文學作品都留下了濃郁的古典風韻。川端康成在《純真的聲音》中寫道:“如果少女的聲音是純真的聲音,那么少女的形體可以就是純真的形體了吧。既然有純真的聲音,又有純真的形體,就應該有所謂的純真精神。”[2]施蟄存的鄉鎮抒寫中幾乎都有著這樣一個純真的少女。她們生活在鄉村,天真純樸,固守著善良。這類少女身上時刻散發著江南小鎮優雅古典的美。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下身邊的人、物、景轉眼即逝,感覺淡了,心麻木了。大都市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使得都市異鄉人每當想起小時候的鄰居玩伴,天真可愛的少女,心里不免得到一份溫馨的安慰。所以塑造了一些理想中的完美女性。讀施蟄存這類小說使我想起了榮格曾提出的“阿尼瑪”形象,她是男子心中的永恒女性形象,類似于夢中情人。
《舊夢》中“我”的玩伴及初戀對象芷芳,不僅美麗的容顏讓我心動,去鬼屋冒險時被石頭絆倒時的勇敢也讓我難以忘懷。《上元燈》中“她”表哥搶走本該送給我的“玉樓春”之后,為了安撫我的失落,“她”把更為精致的輕紗燈送給了我。在我換上更昂貴的新袍子去找她時,直爽的她卻說“新的太扎眼,還是舊的好”,可見她的質樸。筆下的“她”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溫婉而有才華,這樣完美的女子怎能不令人心動。《扇》中官珍一雙發光的眸,曼妙的身姿近乎完美。還不取笑不會說普通話的“我”,當知道我偷走了她的扇時,為了給我面子她把扇送給了我。這個純真善良的少女使我心里至今依然有一種莫名的感動。施蟄存作品中這些純真的鄉鎮少女,是來自鄉鎮、生活在城市的不如意男子心中的“阿尼瑪”,也是對于平淡小鎮的向往的另一種表達。
二、都市文明下鄉土夢的破滅
著名學者趙園說:“濃厚的鄉土情結致使現代作家難以由城市生活形態、由大工業生產的宏偉氣象來發現美,難以由不和諧中發現更具現代意識的美感。”[3]施蟄存作為來自鄉鎮的都市作家,在情感上依賴鄉土小鎮,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他清醒地看到了鄉村不美好的一面,思想封閉生活艱辛,人與人之間不信任。作者的理想鄉土夢到這里已經破碎,他開始從理想的鄉土中回歸往昔的精神桃花源,已經無法承載自己游離的靈魂。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如夢中的白鷗,再也回不來。這一階段,他心平氣和地展現現實的鄉土。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年輕的才子如何向往書籍帶來的精彩世界,他的不斷追尋甚至美夢竟成現實;可是在現代生活經驗的映照下,這些具體化了的美夢只能帶來失望和痛苦。
(一)返鄉—夢醒的失落
小說中涉及一系列來自鄉鎮,去城市生活,又回到鄉村的人物。他們經歷鄉鎮生活與都市文化,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時空距離使他們永遠不可能回到過去。所以他們的返鄉注定是惆悵失落的。施蟄存的鄉土夢是由追尋到失落的過程。《桃園》中“我”為了追尋鄉間的可愛之風來到碩果累累的桃園,又甜又大的黃桃、毫不吝嗇的桃園主人甚是讓我滿意。但意外的是桃園的主人卻是中學時很有天分的同學盧世貽。殘酷的生活使他屈服于封建等級,甘愿淪為一個種植人,卑微地叫我一聲“老爺”。無情的時光把兩個童年伙伴變成路人。《舊夢》中“我”帶著對美好初戀的期待再次回到兒時生活的蘇州小鎮,然而時光無情,美麗可愛的芷芳變成了一個愁容滿面的憔悴婦人,抽上鴉片的芷芳,再也不是兒時的“她”了。見證兒時感情的小鉛兵還在,但卻淪為芷芳可憐孩子的玩物。面對眼前的舊人舊物,時光改變的不僅是人的外表,更是人的內心,男女之情已蕩然無存。對芷芳的期待是“我”對家鄉風土人物的懷念。但是當我沿著兒時的足跡尋找時,卻失望地發現一切已經面目全非了。正如作者所寫,“實在也只如枯萎落的曇花,飛逝的翠鳥;當一瞬間的絢爛,徒然供追憶時的惆悵”。《閔秋日記事》中“我”來到鄉間野與一個美貌的女子四次偶遇,不禁產生情愫戀上她的淳樸和善良,但她的身份卻又給了我重重的一擊,又一個美夢破滅。
此外施蟄存在作品中還直接表現了都市對鄉村的沖擊。《上海來的客人》中“我”的鄰居明芳姐姐被“幽默紳士”的上海人吸引,當大家認為有情人終成眷屬,明芳姐姐過上了城里人幸福的日子時,卻聽到了這樣的消息:“誘惑人的惡魔遍布在世界上,即便在鄉村里他也會尋來,真是人不能防備呢。”[4]作為施蟄存精神桃花源的鄉鎮,現在已不是純潔不可侵犯的了。在現代化進程中,社會自身的發展與西方文明已經改變了原先明凈的土壤。作者心中的鄉鎮與眼前的鄉鎮交織,那個淳美和諧的小鎮已無處可尋。
榮格說:“人之所以抓住兒童時代的理想境界不放,正是表現出對命運之神的反叛,對周圍一切企圖吞噬我們的力量的反抗。”[5]施蟄存的反抗就是不動聲色地逃離。小說《魔道》《旅社》《夜叉》等作品充分展示了對都市的恐懼,企圖逃離,但又無法逃脫。小說中那些憧憬鄉村、想要治愈都市病的人兒,回到了鄉鎮仍然疑神疑鬼,無法擺脫恐懼幻想,且病情更加嚴重了。就像《魔道》中的魔鬼一樣,無論主人走到哪都無法擺脫他;《旅社》中丁先生對鄉鎮旅社的潛意識想象帶給他無數個無眠之夜;《夜叉》中主人公將鄉間一普通女子想象成夜叉,人格分裂,又提心吊膽地回到城市。這些都市異鄉人鄉土治療的失敗,也暗示他們已成為無法真正進入鄉鎮的陌路人。他們滿懷希望地返鄉,但鄉村早已物是人非,故土桃花源已無處可尋,處處是陌生,處處是失落。都市病在鄉鎮愈演愈烈,此時的鄉村已經不再純美和諧。它和都市一樣,也讓人惶惑不安,只想逃離。對于施蟄存來說,城與鄉不再對立。它們同樣都充滿了陌生和恐懼,往昔的桃花源再無法帶來心靈的寧靜。施蟄存揭開江南鄉鎮溫情脈脈的面紗,他的鄉土美夢已經醒來,起而代之的是永遠無法逃脫的陌生和惶恐。
(二)理性的鄉土展現
施蟄存從都市人的返鄉來側面展現鄉土夢的破碎。這讓他再次關注鄉鎮,近距離審視現實中的鄉土。在其后期的小說創造中,他理性客觀地展現鄉土,從正面寫出了鄉土夢幻的失落和精神桃花源的消失。
《汽車路》中關林因征地給的錢被自己一次賭博輸光,所以對這新修的公路有些氣憤,經常做些小動作。后來公路修通了,汽車開來了,在一次車禍中他因幫忙得到了六角錢,他因此看到了商機,不顧別人的生命安危,破壞公路,最后鋃鐺入獄。妻子變賣了所有家當才把他換出來,他們家又變得一窮二白。這個小說中顯示出作者對鄉村愚昧落后觀念行為的批判。以地為生的鄉民為了一點小利不再珍惜土地,想致富卻不用腦子,而是賣掉土地,吃喝玩樂。鄉間的人們不再淳樸,善良,勇敢,而是鼠目寸光,自私自利,過一天算一天,他們的麻木讓人觸目驚心。
施蟄存后期的創作中鄉土失去了詩意的光環,他不再是一片文明的凈土,現實中的鄉村同樣存在著爾虞我詐、貧富懸殊以及驚人的愚昧無知。作者直面鄉村的慘淡,赤裸裸地呈現。在經歷都市異鄉人的返鄉后,從對鄉土的企慕過渡到對鄉土的白描,否定對鄉鎮的幻想。“凡是成功的鄉土作家都是地域性故土的逃離者,只有當他們進入城市文化圈后,具備了良好的藝術素養、深邃的思想境界、科學的思辨能力,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鄉村文化的真實狀態。”施蟄存從鄉鎮走到都市,又走回鄉鎮,經歷城鄉文化的碰撞之后,他沒有沉溺于對鄉土牧歌的幻想,不再用鄉土來對抗城市,他已經清楚地看到,現實中的鄉土無法超越都市精神文化。
三、結語
施蟄存在其小說中不僅將可愛的鄉民、淳樸的鄉間民俗展現得淋漓盡致,并且把現代都市文明沖擊下鄉村逐漸瓦解、鄉間封閉愚昧的現狀赤裸裸地暴露。從精神上對桃花源的追尋到鄉土夢幻的破滅,我們看到鄉土貫穿他的整個創作,一切重新回到原點,作為一個精神的流浪者,通過其對鄉土的展現向我們昭示他的迷茫與失落,展現著20世紀30年代城鄉交織下人們的生存狀態與文化心理。
作者簡介:過娜平(1978—),女,漢族,河南許昌人,普洱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注釋:
〔1〕牛亞博.施蟄存筆下的城與鄉[J].華北水利水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4(2):139
〔2〕謝大光.旋律的奧秘[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4.
〔3〕王繼志.模式的超越——沈從文鄉土小說的特異性[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Z1):32-40.
〔4〕施蟄存.十年創作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5〕傅軍.施蜇存都市小說敘事的二元結構解析[J].文教資料,2008(34):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