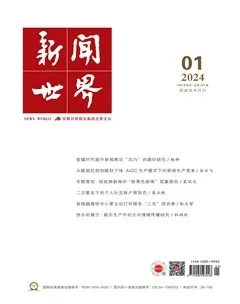田園治愈劇《去有風的地方》與鄉村振興題材的創新融合
范妍君
【摘? ?要】《去有風的地方》將鄉村振興與田園治愈電視劇融合,在藝術形式創新表達、畫面構建詩意美學、劇情正視關鍵問題等方面開拓了思路,平衡了電視劇的娛樂性和鄉村振興題材的嚴肅性,實現了田園牧歌式悠閑情調和創業號角式激越旋律之間的奇特對話,豐富了當代鄉村振興題材影視劇集創作的可能性。本文從電視劇的理念融合、內容呈現、表達手法和傳播效果四個方面進行解讀。
【關鍵詞】鄉村振興;田園治愈劇;去有風的地方;創新融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懈奮斗。[1]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等新型元素逐漸成為電視劇文化傳播的新方向。自2020年開始,以《山海情》《山河錦繡》等作品為代表,一批以改變農村村容村貌為背景,幫助農民擺脫精神與物質貧困為底色的藝術作品從現實題材電視劇中脫穎而出,實現文化傳播助力鄉村振興。湖南衛視田園治愈劇《去有風的地方》于2023年1月3日在湖南衛視、芒果TV雙平臺首播,講述了北京五星級酒店前廳部經理許紅豆為排解抑郁心情到云苗村散心,邂逅放棄高薪回鄉興業的同齡人謝之遙,開啟了與周圍樸實真誠的鄉村勞動者群體的故事。該劇將田園治愈風與鄉村振興的時代主題相結合,通過文藝作品與地域文化的深度綁定,呈現出淳樸的民風民俗和社會主義新農村風貌。據數據統計,《去有風的地方》微博主話題閱讀量195億,抖音話題播放量103億,豆瓣評分8.4分,并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點贊好評。本文擬從電視劇的理念融合、內容呈現、表達手法和傳播效果四個方面進行解讀。
一、理念融合:田園治愈劇與鄉村振興題材的創新融合
(一)鄉村振興題材藝術層面的創新性發展
縱觀鄉村振興題材劇的影像譜系,現存作品的目光多投向新舊農居的生態變遷、扶貧案例的典型表達與破除藩籬的真知實干。[2]鄉村振興題材影視作品要想得到繁榮發展,就應在藝術層面進行創新。[3]《去有風的地方》作為湖南衛視在“三農”領域的新嘗試,不同于傳統鄉村題材劇聚焦家庭倫理的“守望”情感圖式,而是將基調劃定為大理田園牧歌般的充滿溫情的鄉土生活,奏響了田園治愈和鄉村創業相交融的旋律,更新了鄉村振興題材藝術層面創作的情感取向、價值導向與審美風向。
在情感取向層面,《去有風的地方》以“治愈”作為主線,全劇40集內容用日常化敘事、生活流風格和情感的在場牽動人心,上演了客居云苗村的青年們苦辣酸甜的心靈之旅,從“早晚要離開”的游客轉變為“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參與者,用充滿溫度的表達詮釋了青年的成長和選擇,通過藝術手段創新性地展現了云苗村發展致富的歷程,闡揚出“變革敘事”與新農村圖景交融下的戲劇張力、情感濃度與生命質感。
在價值導向層面,該劇以“留在都市打拼還是回家鄉創業”這一價值議題作為中心線索,將青年人返鄉創業和農村地區人民的生活境遇與情感軌跡共同植入故事脈絡。劇情將重點聚焦于歸來者,以真情實感講述返鄉興業的故事,打破了過去說教灌輸,正面強推鄉村振興的影視劇作風。一方面實現了電視劇題材與時代同頻共振,講好鄉村振興背景下的鄉村故事;另一方面將以往作品“守望相助”的底層思維轉換為成長寫照的心靈階梯,凸顯了鄉村振興進程中的青春力量與創業故事,實現了田園牧歌式悠閑情調和創業號角式激越旋律之間的奇特對話,探索出鄉村振興題材劇發展的多種可能。
在審美導向層面,《去有風的地方》將鏡頭對準廣袤的云南鄉村,用詩意化的表達手法展現溫情恬靜的當代鄉村生活,在以山林河湖為依托形成的鄉村空間中生產出不同于城市快節奏的日常。審美層面的創新讓整部劇與以往鄉村振興題材劇中鄉野的“黃土原色”大相徑庭,巧妙地展現出鄉村的“現代元素”和詩情畫意下蒼山洱海的靈秀,具備偶像劇的浪漫、風光片的質感和生活流的煙火氣,打破了以往鄉村振興題材影視作品的受眾群體囿于特定圈子,無法形成多圈層轟動效應的現狀,不僅受到農民群體的喜愛,還吸引了更多年齡層觀眾的共同關注。
可以看出,《去有風的地方》印證了藝術層面的創新發展,成為文藝作品助力鄉村振興的典范之作,是一部思想性、藝術性相統一的標桿之作,也為鄉村振興的主流表達開創了新的創作方法論。
(二)在影像中描畫新農村的生態圖景
長期以來,寫實是鄉村振興題材劇創作特征鮮明的美學標簽,用深刻的筆觸描繪鄉村變遷的進程,嶄新的村容村貌已成為鄉村建設的重要符號。《去有風的地方》立足詩意性建構的邏輯,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中國鄉土文化的熟悉和親切,為后續鄉村振興題材的創新帶來了可借鑒的美學價值。
《去有風的地方》在視聽造型上下足功夫,大量的長鏡頭手法錄攝云苗村的真實環境,對現代鄉村的真實樣貌進行還原,劇中拍攝場景均為云南真實場景,對于大理至美自然風光、淳樸風土人情以及魅力非遺文化都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如雙廊古鎮、沙溪古鎮、喜洲古鎮的美景,茶馬古道的飲茶歷史,劍川木雕、白族刺繡的非遺傳承。同時,全劇以極具地域和民族風格的建筑、服飾和美食為畫面增添別具一格的情調,巧妙地做到了鄉土元素與當下審美的結合,通過重塑鄉村社會景觀改變觀眾對農村落后貧窮的刻板印象。
在展現農村生活條件極大改善的同時,亦刻畫出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從封閉到開放、從保守到創新的轉變。新型電商經營模式貫穿全劇,帶動整個云苗村旅游業的發展,村民鳳姨成為網店的幕后客服,寶瓶嬸成為電商的打包員,村子發展后青年勞動力回鄉再就業等,均體現出村民緊跟時代步伐,開啟產業新模式的進步生活方式,生動詮釋了新時代農民對于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勾勒出當代農民在奮斗中成長的新精神風貌。
對于鄉村振興題材來說,立足鄉村文化與鄉村景觀,表現農居生活的“精神”與“風貌”,更能凝聚廣大觀眾的審美心理和文化記憶。
二、內容呈現:多元性與整體性的情節架構
(一)多元性的主體構成
面對“鄉村振興”這樣的命題,當下的鄉村振興題材電視劇偏好于塑造扁平化、臉譜化的形象,著重表現主角人格成長過程中的精神能量。而《去有風的地方》堅持新視角,取材于鄉村振興中的典型人物,如駐村干部、返鄉青年、農村村民等共同構成熒屏群象,顯現出高辨識度的多元化特征,通過不同的敘事線索聯通與交融各個人物群體的行為,使得不同的“意義場”產生共振共鳴的力量,能夠讓觀眾從中感受人物形象的動態發展。
1.返鄉青年的“逆城市化”追求
《去有風的地方》堅持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小切口,展現出了一幅有為青年奮力建設家鄉的鄉村振興圖景。謝之遙放棄北京高薪工作回鄉創業,推廣非遺解決文化斷層困境,將家鄉的特色帶出大山;曉春大學畢業回鄉跟隨大哥創業,幫助家鄉開啟網絡營銷。當代年輕人一步步打破陳舊保守思想,將媒介邏輯嵌入到鄉村的日常生活當中,進而發揮媒介傳播效能,通過拍攝宣傳片、主播推廣、網絡帶貨等助力產業發展和基礎建設,在美麗鄉村新圖景的打造中追逐自己的理想。
除了返鄉青年,本劇還聚焦夢想在鄉村振興建設中落地生根的故事,許紅豆用她多年的酒店從業經驗幫助村民提升服務意識、幫助小鎮提高旅游業的管理意識,為云苗村的鄉村振興帶來了更多的可能。以返鄉青年為主體的情節巧妙結合形成鄉村振興敘事的“因”與“果”,在助力村子發展的同時,從側面印證作品主旨:高樓大廈和高山流水都撐得起年輕人的夢想,熱火朝天的鄉村建設也可實現年輕人的人生選擇,由此延伸出時代巨變的鮮活注腳,構成鄉村振興的發展新圖景。
2.基層干部形象的年輕化表達
鄉村的建設與發展離不開村干部的正確引導,《去有風的地方》在對村干部的形象塑造上仍選擇年輕人[4],以大學生村官黃欣欣為代表,人物有想法和激情,立志幫助村民致富發財,塑造出新時代青年懷揣地方情懷或回報家鄉的新形象。
作為年輕的大學生村官,黃欣欣面對村里繁雜瑣碎的大小事,她認真負責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真實地體現出年輕干部在鄉村工作的不易,讓觀眾感受到基層干部在致力于鄉村發展事業時的激情與蓬勃的生命力。在探析基層干部內心的過程中,對其情緒進行了深入刻畫:為了工作與男友異地分居,住在破敗漏雨的房子中無處抱怨,以及和前來拍攝的師姐傾訴煩惱等,繪就出一個生動鮮活的基層干部立體形象,增強了電視劇的藝術性,做到了正視基層工作“繁雜”與“激情”的關系。
3.普通村民眾生相的多角度闡釋
《去有風的地方》并未將視線一味置于主角身上,而是通過捕捉村民的種種生活細節,勾勒出樸實、鮮活的村民群像,感受人與人之間綿密醇厚的情感溫度。
為了獲得關注度,一些影視作品刻意放大了農民的一些特質,許多農村形象甚至有了刻板化符號。[5]《去有風的地方》則徹底打破了這種人物形象上的束縛,人物性格不再是單一的,而是多面的,通過對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講述將筆墨、鏡頭對焦更細節的部分,用完整的故事鏈打開每個人物內心的世界。例如劇中阿桂嬸作為在有風小院打掃衛生的阿姨,一口地道的馬普,穿著特色的民族服裝,打破了影視作品中往往挑選外貌形象俱佳的人物擔當村民角色的慣例。對其性格的設計就是一個嘴上不饒人、喜歡到處瞎顯擺,生活中明明被自己兒女嫌棄,卻始終不愿承認的農村婦女形象。但阿桂嬸仍然是刀子嘴豆腐心的熱心村民,在鳳姨老伴遭病時拋下恩怨驅車送友,在馬爺找不到人生道路束手無策時,給予他再次前行的勇氣。
通過文藝作品與地域文化的深度綁定,在巧妙的劇情設計和別具一格的方言臺詞中,塑造了符合現實的村民形象,讓觀眾對劇中的人物、情節產生親近感和認同感。
(二)整體性的情景關聯
鄉村振興題材必須依賴客觀、真實的鄉村環境,才能更好地引發、激勵、放大體驗過程與效果,達到吸引觀眾的目的。[6]村莊空間是鄉村振興題材劇主題的直接承載與最基本的表征圖式。《去有風的地方》為在鋼筋水泥的城市叢林中生活的人們營造了一個寧靜、悠閑、恬淡的桃花源,謝之遙深耕鄉村“生態、生產、生活、文化”等要素,合理使用閑置資源,分別以有風小館、非遺作坊、有風小院為中心,構建起經營、參觀、民宿的三個空間,村莊場景的意象與蘊涵中國文化寓意的視覺符號相勾連,彰顯出云苗村本地的風土人情、鄉音鄉情、民間藝術等人文景觀。
茶館極具中式傳統特色,濃厚的文化氣息見證了一個地域的生活發展、文化變遷。劇中的有風小館在此基礎上“創新化”,以桌椅上的扎染、牛肝菌薄餅、穿著民族服裝的阿嬤等極具云南特色的符號,勾勒出當地質樸的民風和地域文化,是鄉村生態生活的重要表征。
扎染坊、刺繡坊和木雕坊作為云南當地特色,非遺傳承的刺繡、扎染和木雕技藝是極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文化符號,既承載著厚重的歷史,又飽含著時間的沉淀,劇情不僅向觀眾推介民間手工藝品,還挖掘每個非遺傳承人背后的故事,既展現了云苗村的民間藝術,又表達了云苗村人的精神追求。
“有風小院”則聚焦當地房屋特色和生活方式,還原了每天忙碌的城市人最渴望的田園生活,緩慢的節奏和簡單的敘事風格,療愈了從城市來的青年身心,滿足了快節奏生活下的人們對于慢生活的向往。
劇中構建起的三個空間將民俗文化作為地域原生態意象的外顯符號,在電視劇中的使用有著接軌現代語境的功能性意義,現代鄉村中“慢生活”使城市生活者的身心得到放松,緩解他們的壓力。
三、表達手法:深入現實肌理的敘事風格
(一)交織并進成長,引發身份認同與情感共鳴
《去有風的地方》在劇情中鑄造出交織并進的成長模式,不僅能為觀眾帶來美好的觀感,還能成為改變個人生活感知與觸達的“體驗”。
一是“成長”的向心力。有著不同人生經歷,但共同追求“自愈”的年輕人群體,完成從個人主觀能動性塑造到實現一個群體的成長過程,達到內部帶動與互助的統一集合。許紅豆因摯友離世逃避療傷,娜娜因網絡暴力遠走他鄉,胡有魚在追夢路上不被家人理解,作家大麥逃避原生家庭壓力、馬丘山多次創業失敗沉浸式打坐……打造出逃離城市、來到鄉村凈化心靈的都市打工人群像,以多樣的視角講述不同角色構建起的真實故事,以極強的現實觀照性建構起觀眾情感認同的橋梁,在他人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獲得身份認同,在療愈成功的案例里找到精神寄托完成擬態人際關系下的情感共振。
二是“他者”的引領力。“他者”作為精神寄托者,在一次次合作或矛盾化解中實現多者交互性地成長。娜娜作為網暴的受害者,選擇逃避現實留在云苗村做咖啡小妹,由于云苗村的快速發展被挖出曾經的故事。在所有人得知娜娜的過去后,全員開啟了“他者”鼓勵模式,幫助娜娜重整旗鼓。娜娜的自我治愈和價值找尋的過程,使觀眾既可以獲得心理宣泄和情感撫慰,又為其面對未來生活提供了有效激勵。
不同的角色,通過劇情的發展解開心結,交織并進成長模式,揭示了心理治愈的有效方法不是逃到遠離塵囂的桃源仙境,而是要以主動進取的姿態,開創生活新境界,這與鄉村振興的理念不謀而合。
(二)強化戲劇沖突,聚焦農村變革的關鍵性問題
鄉村振興題材在展現農村變革進程時難免會觸及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與問題。《去有風的地方》敢于觸碰農村改革矛盾問題,將保護傳統文化,關懷留守兒童這些主題融入其中,并加以故事化敘述。劇中村民都很淳樸,但生活在半與世隔絕的地方則很容易與現代化社會脫節,木雕坊的學徒謝曉夏與“有風小院”中的人們逆行,疲于鄉村的單調簡單,他向往著繁華多樣的上海,只身前往最后卻遭遇詐騙。
同時,劇情對準空心村的問題,從十年前謝之遙就是留守兒童,到如今虎子的爸媽因為賺不到錢,被迫留下虎子與爺爺奶奶獨自前往昆明打工賺錢,點明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問題亟待解決。除去家中老人、小孩需要照顧,承載著文化和鄉愁的記憶被淡忘,祖輩賴以生存的山水被荒廢。
遭遇詐騙、留守兒童等都是《去有風的地方》中著力反映的深刻的現實議題,而好的作品就應該作為好的向導,引發社會對農村問題的關注。《去有風的地方》在劇情設置上巧妙地將鄉村振興、保護傳統文化、關愛留守兒童、網絡暴力等現實問題融入劇中都市人的情感世界,很好地踐行了主流媒體的責任擔當。
四、傳播效果:切實激發鄉村振興
近年來,爆款影視劇帶火景點及取景地的現象屢見不鮮。武漢大學鐘晟道認為:“影視劇之所以能夠帶火相應旅游目的地或景點,其中最重要的機制是游客可以在現實場景中實現情感的投射。影視劇的現實場景有一種獨特的空間喚醒機制,能夠喚醒游客觀影過程中形成的情感記憶,進而形成豐富的情感體驗。”。
該劇在前期宣傳上摒棄了部分電視劇主打明星內容的做法,而是堅守鄉村振興主題、展演藏在山里的“桃花源”,傳播了一場“風”里飄來的鄉村振興韻意。《去有風的地方》讓觀眾產生“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之感,劇中極具地域特色和民族風格的建筑、服飾、美食,為故事的發生創造了極具詩意的展現空間,木雕、扎染等具有示范性、影響力的非遺文化展現地域特色,加上那首反復出現的極具云南特色的搖籃曲,給人帶來田園牧歌般的輕松愉快,讓觀眾多角度認識了大理,進而愛上大理,以助力當地旅游業復蘇。依托“有風”流量,電視劇主拍攝地大理市鳳陽邑村目前已成了大理文旅“網紅”打卡地,劇中扎染坊開啟線下體驗模式,讓游客擁有了與劇中演員同樣的沉浸式體驗,從而了解非遺文化,感受非遺魅力,助力美麗鄉村“破土飄香”,這也喚醒更多觀眾親身實踐的意愿。中國鄉村開始呈現出新的價值,成為能讓久居城市的人獲得“治愈”的地方,大理在這方面體現得尤其明顯。
《去有風的地方》,以山水田園,古風民情,返璞歸真的影像,讓我們堅定鄉村振興信心,從而使電視劇的意義和影響更為深遠,實現了“治愈心靈”和“鄉村振興”的雙向奔赴,實現了鄉村振興與影視產業的融合,打開了文旅互動、文旅融合的新思路。
五、結語
娓娓講述暖心故事,生動展現自然風光、人文風情與歷史積淀。《去有風的地方》將鄉村振興與田園治愈電視劇融合,創作者不落窠臼地把田園治愈過程放到鄉村振興的號角下去描繪,在藝術形式創新表達、畫面構建詩意美學、劇情正視關鍵問題等方面開拓了思路。精準把握當代都市人的心理癥候與共同渴望,以文藝創作助力鄉村振興,勾勒了一幅當代年輕人扎根基層、建設鄉村的生動畫卷,帶動了云南當地文旅經濟發展,為鄉村振興題材文藝創作探索出新路徑。
注釋:
[1]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懈奮斗[N].人民日報,2022-10-29.
[2]趙博文.當下農村題材電視劇的主題嬗變與路徑突圍[J].電視研究,2022(12):107-110.
[3][5]黃霞.鄉村振興題材影視的新變與反思——以電視劇《花繁葉茂》為例[J].電影評介,2022(08):73-76.
[4]黃堯.鄉村振興視域下鄉村題材電視劇《花繁葉茂》的多重解讀[J].西部廣播電視,2022,43(20):124-126.
[6]柏林,邵振奇.慢綜藝與鄉村振興創新融合策略探究——以湖南衛視《云上的小店》為例[J].電視研究,2022(07):39-41.
(作者:同濟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