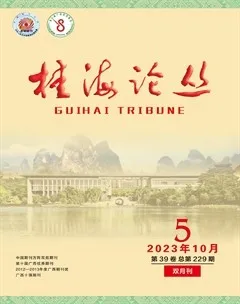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邏輯及其跨越時空的喻示
黎學軍
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體思想在新時代的理論與實踐呈現。恩格斯在1875年給倍倍爾的信中提及的共同體(Gemeinwesen)的中文對譯詞“公社”抑或英文對譯詞的“團體”(Community)之主要義項均可解讀為有自身時空維度的、有某種關系連接的且能喻示未來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基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理解并結合時代精神推導出來的概念,貫穿其全部理論與實踐的邏輯就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產關系。時空維度的表征就是關系時時處處都在場,即在縱向維度的時間連續性上,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關系有階級關系、發展(人民解放)關系兩個階段,分別對應著階級對立社會、無階級對立社會;在空間的地理位置上其體現為存在于人類社會各階段、各子空間。由時空坐標出發,人類命運共同體連通著人類歷史與未來,勾勒了各國普遍交往的全球化圖景。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關系邏輯;生產關系
中圖分類號:D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1494(2023)05-0025-06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人工智能的認識論制約問題研究”(23BZX125)。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正在孕育成長,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全球命運與共、休戚相關。”[1]人類命運共同體是與恩格斯在1875年寫給倍倍爾的信中提及的“Gemeinwesen”[2]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新提法,習近平總書記上述重要論斷揭示了貫穿人類命運共同體全時空的關系邏輯:各個國家、各個地區之間時刻處在經濟、政治、生態等紛繁復雜的關系之中,其中最重要的一種關系就是生產關系。
生產關系作為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與相互聯系,體現著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的經濟利益。這是一個人們身處其中而不自知的關系網絡,每個人都是這個關系網絡中的一個點。從動態過程來說,生產關系由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的各種關系構成,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中與他人和社會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聯系。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內部是如此,全世界范圍內也同樣是如此。全部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構成了社會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業革命開啟了全球經濟互通互聯的時代,生產力的飛躍發展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聯系發生了根本性轉變,企業的生產不再只著眼于本地區的消費市場而是放眼世界范圍內的消費市場。這一歷史浪潮或快或慢地改變著世界的整體面貌,這樣的改變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筆下早已被清晰地描繪出來。從生產關系入手并通過對其的分析,有助于尋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關系邏輯并從中得出跨越時空的諭示。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關系”
所有類型的共同體歸根結底都是關系共同體。因為人是由自身與肉體以及更廣泛的自然界、特別是和他人的內在關系構成的[3]。從馬克思主義理論視角來看,無論是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差序格局抑或以家國情懷為紐帶形成的民族共同體,歸根結底都是以生產關系為紐帶形成的關系共同體。
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關系歸根結底就是一種生產關系,階級關系由其而起,生產力發展也得益于與其相得益彰的互動。較早提出共同體概念的斐迪南·滕尼斯認為,共同體是一種基于親屬關系和鄰里關系分享民俗與文化的一群自然人,就像是村落和村莊農民,是更加緊密、更加具有凝聚力的社會實體[4]。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斐迪南·滕尼斯的說法與《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的“勞動創造財富”等試圖掩蓋階級對立的語句描述性質是一樣的,因為其既不反映生產關系也不反映階級關系。馬克思指出,勞動只是一種勞動力的表現,“只有一個人一開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5]的時候,他的勞動才是財富的源泉。這里就涉及人與物質資料的關系,在階級對立環境下其可轉為人與人的階級關系。在階級對立初期、無階級對立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適配的關系推動著生產力的發展。
生產關系是人與人最基本的關系,共同體整個內部結構也取決于“自己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6]68。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引入了生產關系概念并將其作為全部社會關系的基石,他指出:“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6]142
列寧認為:“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7]這個定義明確了人群劃分的主要標準是人與物的關系,正是由于人與物的不同權屬,人們才得以將人群區分為兩大共同體。階級首先是一個實體,如果從另一個視角看,它又是依據某種相同的關系集結而成。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階級的內涵也會有所不同。從關系角度來看,形成階級的關系牽涉非常廣泛,其超越了直接生產過程并時時處處彌漫在“各個特殊的生產、占有單位”[8]。湯普森高度重視關系定義階級的重要性,認為階級是一種因人與人相互關系而發生的一種實體[9]。
生產力發展是一種關系的轉換,這里表示的是其與生產關系適配度的調整。就其社會主義地理空間意義上說,它代表著人民解放,而人民解放就是指一種從人被物規定的種種束縛關系中釋放從而獲得自由的意思。在德語文本里,Befreien是一個多義項詞,陳望道引用了其中“釋放”的義項并用古已有之的中文詞“解放”對譯之,這也是受到了李大釗文稿影響的緣故。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談及“解放”時主要的義項是“無產階級解放”或“人類解放”,這也是我國長期使用“解放”這個詞的基本義項。就資本主義地理空間意義上說,生產力發展也意味著生產力擺脫已不適配的生產關系從而獲得進展的一種關系。
總之,生產關系圍繞著生產力發展來建構自身形態,并通過全時空途徑滲透到人類社會的所有方面、層面、階段,進而或快或慢地引起了一切社會關系的變更。在此意義上,生產關系是諸多社會關系中最根本的一個關系,因此,它也成為了貫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顯性邏輯。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間維度
“跨越時空”指的是某種觀點或學說基于自身的理論特性進而被后人從各種維度上進行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跨越時空的喻示要基于自身的時空維度,從時間縱軸看是從階級對立社會到無階級對立社會的歷程,這是一條無斷點的直線。
近年來,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諸流派聚焦馬克思主義概念的形式研究,“共產主義”“人”“歷史”“解放”等二元對立(Dualismus)問題成為理論聚焦點。質疑者如保羅·麥克勞克林、安德熱·斯托因斯基、阿蘭·巴迪歐等,在他們眼里,馬克思主義概念都有自身的時間與空間限制,或者只適用于當下,或者只具有信仰的屬性。
馬克思主義概念并非中間有斷點(Breakpoint)的邏輯結構。生發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成長于社會主義發展中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具有的現實性,意味著它內蘊著歷史與未來。在時間坐標軸內,其是一條介于時間與永恒之間的連續直線。其形其神如同黑格爾辯證法所展示的情況一樣:每個當前之中,都有永恒在場[10]。
就人類實踐的視角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一個連續的運動。在此意義上,人們不能將共產主義視為一種只有未來才有的東西,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11]又如《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6]306就其概念結構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整體,我們也僅僅是因為邏輯分析才區分為“階級對立”“無階級對立”兩個片段。
社會上任何一個領域都存在著人以群分的現象且產生了一些論述。《荷馬史詩》中有將人群歸類的描述,比如先知、醫者、木匠、詩人歸屬于“工作者”一類[12],塔西佗《編年史》中也有類似記載[13]。自古希臘的瑟秀斯以財產關系將人群分為三個共同體開始,努瑪、李啟紐斯、梭倫、塞爾維烏斯、吉丁斯、勒蓬等人都嘗試過以財產、技術、職業、類群意識、群體精神[14]等關系來將社會人群劃分為不同的共同體[15]。可以看到,上述學者認為,社會可分為不同的共同體,劃分的依據主要是人與人之間達成的共識關系。階級意識的產生同樣源于關系,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圖景里,人類社會伴隨著分工的日益精細而產生了私人與社會共同利益的矛盾,而這種矛盾普遍表現為公私利益之間的沖突與碰撞,且其首先是作為“彼此有了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現實之中”[6]84。正是因為分工的發展,部落之間、部落內部為保護屬于公共利益的剩余產品而產生了不同共同體之間的爭端,這就是以人與物之關系即階級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共同體的發端。隨后,伴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整個人類社會范圍內階級關系共同體的分化組合也隨之變化。第一次社會大分工催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裂,產生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兩個共同體;第二次大分工以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導致以職業關系為紐帶的新類型共同體的產生;第三次大分工創造了“一個不再從事生產而只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16]166。
當人類歷史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之后,人類社會階級發展的最精彩部分出現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抗。當資本家和雇傭工人在貨幣資本與勞動力中互相對立時,雙方的對抗就已經存在了。“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17]。正是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人建構了龐大的對象世界,并在這個建構過程中,他們認識了對象世界和自身的階級意識日益集聚,爾后其必然走向社會變革的道路。人群為經濟利益而斗爭,斗爭形成階級意識,階級意識引導社會革命的發生。由此可見,階級是解開自由何以實現之謎的鑰匙。
恩格斯指出:“社會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6]17在政治斗爭、階級斗爭、經濟解放的鏈條中,經濟解放是歸根結底的,人民解放是為了生活資料的生產及其分配方式。在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階段,人民解放進入了以經濟解放為主要內容的階段,這也是迄今為止我們對人民解放的主流或主要方面的理解。
進入到這個階段之后,生產關系也仍然是聯結人與人、人與社會的最重要的關系紐帶,以我國經濟建設為例簡要說明之。隨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8]的發表,改革開放這一新的時代精神自上而下迅速傳遍了中國大地。鄧小平同志為此曾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19]發展一詞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鄧小平同志對我國社會生活、對理論研究的期許。解放和人民解放也由此獲得了新的內涵,經濟建設成為人民解放的時代內涵,提升社會生產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之間的適配度是人民解放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進入新時代之后,人民解放有了新的含義:經濟高質量發展及其成果更均衡分配給人民。習近平總書記在2012年就明確指出:“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20]新的生產力建構了為自身服務的生產關系,新生產關系又使得共同體呈現出新的氣象。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空間維度
從空間橫軸看,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生產力發展處處皆是的樣態。人類社會像一幅紛繁復雜的圖畫,但貫穿其中的必然是種種人與人的關系。馬克思曾指出,人類大分工引起了城鄉分離、第一產業與其他產業日益分離,同時導致了具體工種的差異。血緣、地域、技能的高低等關系與不同系列的諸多生產關系又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在“交往比較發達的條件下,同樣的情況也會在各民族間的相互關系中出現”[6]68。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6]291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作用下形成的世界市場中,人們將逐漸分化為兩大階級,而且只有兩種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兩個對立著的階級在此消彼長的斗爭之后,無產階級因自身先進性而勝出,社會經濟形態進入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在此必然的歷史進程中,人的一切社會屬性均從屬于階級屬性。
階級是馬克思世界主義理論①的根基,當馬克思說到階級的時候,他說的就是“世界主義”,二者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解讀世界主義者眾多,我們這里是根據一種世界主義的得以成立的最核心的理論特質來研究,諸如宇宙、理性、人權、文化、語言、公平,等等,馬克思世界主義的理論特質就是階級。我們按照列寧的定義來理解階級。民族是指一群住在一定領土范圍內的,有著共同文化心理認同的人,民族主義則意味著對民族和民族國家的忠誠超越于其他任何對象[21]。在此限定范圍內,我們將馬克思的這句話及其所代表的意思稱之為階級的世界主義——一種傳承了歐洲歷代世界主義傳統,以反資本的邏輯展開的、以階級斗爭為內驅力的、認為世界終將因此而走向一體化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論。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所說:“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而各個人的世界歷史性存在,也就是與世界歷史直接相聯系的各個人的存在。”[6]87
德國學者亞當·米勒認為,國家一詞可作為“社會”“社會生活”“世俗生活”“世俗存在”等等的同義語使用[22]。在德國百科全書派學者謝德樂那里,民族(Nation)一詞亦常以“人民”的意義出現。有時,民族一詞也會用來指稱社會中的某個“階級”(estate, stand, ordo)或社會團體(Gesellschaft, societas)[23]。在此意義上,“工人沒有祖國”在字面上可解釋為“工人沒有世俗存在”“工人沒有領土”“工人沒有政權”。歸納起來看,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這句話大約有以下三種意義。
其一,地域角度的理解。無產階級無國籍,全世界只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環境,除此再無其他。至于為何要忘記國籍,因為資產階級聯盟同樣是沒有國籍。在《關于波蘭的演說》中,馬克思談道:“一個國家里在資產階級各個成員之間雖然存在著競爭和沖突,但資產階級卻總是聯合起來并且建立兄弟聯盟以反對本國的無產者;同樣,各國的資產者雖然在世界市場上互相沖突和競爭,但總是聯合起來并且建立兄弟聯盟以反對各國的無產者。”[6]308又如,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指出:“工人不是屬于某一個資本家,而是屬于整個資本家階級。”[6]337既然資本家是一整塊的,顯然覺悟起來的工人階級也應該是一整塊的。工人階級如何不分國籍地聯合起來呢?顯然并不需要孔多塞極力推薦的世界語言作為黏合劑[24],只需要具有共同的被壓迫感即可。正如恩格斯在《關于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歷史》中所指出:“單靠那種認識到階級地位的共同性為基礎的團結感,就足以使一切國家和操各種語言的工人建立同樣的偉大無產階級政黨并使它保持團結。”[16]209
其二,屬性角度的理解。無產階級無民族、性別、宗教等一切屬性,只有階級的屬性,民族性包含于階級性之中。首先,因為大機器的使用,使得勞動的差別越來越小,從而使得“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生活狀況也越來越趨于一致”[6]281。其次,資本的肆虐摧毀了某國無產階級之所以是某國民族的那些原因。“現代的工業勞動,現代的資本壓迫,無論在英國或法國,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是一樣的,都使無產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6]283并且,“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的實現和世界市場的建立,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趨于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無產階級的統治將使它們更快地消失。聯合的行動,至少是各文明國家的聯合的行動,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人對人的剝削一消滅,民族對民族的剝削就會隨之消滅。民族內部的階級對立一消失,民族之間的敵對關系就會隨之消失。”[6]291馬克思認為,民族的狹隘性與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當各個被壓迫的成員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者之后,他們就不會再堅持自身的民族性了。再次,有階級壓迫,連性別在社會意義上的差異都消失了:“現代工業越發達,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擠。對工人階級來說,性別和年齡的差別再沒有什么社會意義了。他們都只是勞動工具,不過因為年齡和性別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費用罷了。”[6]279-280最后,連宗教性都一概沒有,恩格斯在《論原始基督教的歷史》中也曾說過:“既沒有后世基督教的教義,也沒有后世基督教的倫理,但是卻有正在進行一場對全世界的斗爭以及這一斗爭必將勝利的感覺,有斗爭的渴望和勝利的信心,這種渴望和信心在現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經完全喪失,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只存在于社會的另一極——社會主義者方面。”[16]468-469
其三,執政權角度的理解。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觀點,“工人沒有祖國”是指工人應該把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看作是壓迫他們的機器[24]。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不取得執政權,就沒有屬于自己的國家。而“共產主義只有作為占統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時發生的行動,在經驗上才是可能的”[6]86。所以,“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6]89。全世界工人階級應該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數國同時發起無產階級革命并奪取資產階級的政權,然后再將幾國聯合為一個整體[25]。
從以上的文本分析出發,馬克思階級世界主義的特點可簡略歸納如下:首先,階級性。日益增長的世界市場將會事實上逐漸消除民族之間的差異,即使有差異也是轉瞬即逝。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中,許多民族將會完全消失,被融入較大的民族;另一方面,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是一種分散工人注意力的工具,只有當其有助于社會主義轉變時,民族主義才能得到支持。其次,普適性。從城邦世界主義,到各種有理論內核的世界主義,包括馬克思的階級世界主義,雖然諸世界主義的內涵及其研究域變化很大,但將世界聯結為一體的夢想始終未變。雖然階級世界主義與別的世界主義迥然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堅持自己觀點具有普適性。資本主義轉變的總體進程將會產生一個單一的、同質的世界,產生某種所有國家都不得不遵循的統一性。整個人類正走向某種單一的世界文化,最終目標是某種同質同構的人類共同體。
四、結語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科學的概念且其對人類社會有著長久的喻示。《共產黨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6]307的吶喊為建立最高級的共同體(Gemeinwesen)指明了方向,也為當下各類型共同體的交流鋪墊了理論的依據。
以生產關系為基本關系的共同體形式時時處處普遍存在著。馬克思更強調的是人的社會本質,即只要人類社會還必須依靠生產來維持自身的生存,生產關系將一直存在,從而以生產關系為基本關系的共同體形式將一直存在且一定是某種人群共同體的最基礎關系。
我們也必須按照唯物辯證法去分析和理解已存在的不同國家、民族、關系的共同體之間的交融。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關系就是“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26],也即生產力的發展可以成為全世界各國聯結在一起并形成一個共同體的紐帶,不同的關系共同體之間存在著求同存異的可能性和現實需要。
注釋:
①“世界主義”(cosmospolis)與“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總是“糾纏不清”的,“世界主義”尊重多元文化,強調各民族國家可以跨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加強團結,與“民族主義”相對;“普世主義”相信萬物背后有普遍的本體或不變的原則,與“多元文化”相對。二者的共同點是,都強調“一”的重要。
參考文獻:
[1]習近平.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415.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3.
[3]JOHN. B, COBB. JR. Postmodernism and Publicpolicy[M]. New 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121.
[4]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張巍卓,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76.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列寧.列寧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8]艾倫·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對資本主義:重建歷史唯物主義[M].呂薇洲,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96.
[9]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卷[M].錢乘旦,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前言1-2.
[10]莊振華.黑格爾的歷史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75.
[1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9.
[12]荷馬.荷馬史詩[M].陳中梅,譯.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6:譯本序19.
[13]塔西佗.編年史:上[M].王以鑄,崔妙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7.
[14]鮑桑葵.關于國家的哲學理論[M].汪淑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77.
[15]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M].楊東莼,等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211-265.
[1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1.
[18]本報特約評論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N].光明日報,1978-05-11(1).
[19]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3.
[20]習近平.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22.
[21]CARLTON J HAYES.Essays on Nationalism[M].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8:5-6.
[22]里亞·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M].王春華,祖國霞,魏萬磊,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430.
[23]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M].李金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
[24]湯伯杞.如何理解《共產黨宣言》中“工人沒有祖國”的論述[J].河北學刊,1994(5):108-112.
[25]安苗,火勝.“工人沒有祖國”原理的國際主義本質[J].教學與研究,1964(4):60-63+59.
[26]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433.
責任編輯陸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