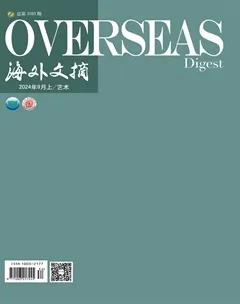從《邶風(fēng)》《鄘風(fēng)》《衛(wèi)風(fēng)》探古淇水衛(wèi)地的植物文化
《邶風(fēng)》《鄘風(fēng)》《衛(wèi)風(fēng)》是《詩經(jīng)》收錄的衛(wèi)地民歌,反映了古淇水衛(wèi)地居民的真實生活。三風(fēng)中提到植物33種,探討這些植物蘊(yùn)含的文化內(nèi)涵可以了解古淇水衛(wèi)地居民的生產(chǎn)生活、民風(fēng)社俗,理解中原文化的深厚積淀、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源遠(yuǎn)流長。
1 朦朧狀態(tài)的環(huán)境文化
自然環(huán)境是人類生存發(fā)展的物質(zhì)基礎(chǔ),環(huán)境文化是表征人與自然相互關(guān)系的歷史范疇,是對人類如何認(rèn)識自然、處理人與自然關(guān)系的集中反映,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chǎn)物。《邶風(fēng)》《鄘風(fēng)》《衛(wèi)風(fēng)》提到的植物共33種,構(gòu)成了古淇水地區(qū)繁盛的植物世界,也顯示了生產(chǎn)力發(fā)展水平有限、人類處于朦朧狀態(tài)的先秦時代環(huán)境文化,反映了人們對于自然的改造。
觀賞植物:《衛(wèi)風(fēng)·淇奧》中有“綠竹猗猗”“綠竹青青”“綠竹如簀”,描繪了大片的竹林。全詩以“綠竹”起興,借綠竹的挺拔、青翠、濃密來贊頌君子的高風(fēng)亮節(jié),可見古淇水衛(wèi)地居民很早就將竹作為觀賞植物,懂得欣賞植物所蘊(yùn)含的美了。
經(jīng)濟(jì)作物:《邶風(fēng)·氓》中有“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描繪了桑田。詩中的女主人公養(yǎng)蠶栽桑。可見這個時期的人們,已經(jīng)開始種植桑這種經(jīng)濟(jì)作物。
糧食作物或食用作物:《鄘風(fēng)·桑中》有“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麥?zhǔn)且荒晟蚨晟荼局参铮墒旌罂捎脕砟ッ娣郏部梢杂脕碇铺腔蜥劸疲俏覈狈街匾募Z食作物。可見,古淇水衛(wèi)地居民很早就有種植麥作糧食作物的歷史。《鄘風(fēng)·載馳》中也有“我行其野,芃芃其麥”。
除此之外,古淇水衛(wèi)地居民還采葛制衣、采藥治疾、采菜以食、伐樹制舟建屋,田間地頭一片忙碌,盡情享受大自然的饋贈。古淇水衛(wèi)地居民種植糧食作物、經(jīng)濟(jì)作物、觀賞植物的活動是“自然人化”的過程,同時也是“人類進(jìn)化”的過程,顯示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天人合一”的景象,正是古代朦朧狀態(tài)的環(huán)境文化的體現(xiàn)。
2 原始樸素的情感文化
情感文化是指一個社群或文化中對于情感表達(dá)、體驗、管理的共同認(rèn)知、態(tài)度和行為方式。古淇水植物種類多、數(shù)量大,生生不息,不僅具有提供衣食住行的物質(zhì)功能,也具有讓古人表達(dá)情感的文化功能。
2.1 贊美之情
先秦是中華民族逐漸走向統(tǒng)一的時期,諸侯國之間的烽煙讓人們渴望和平安定,自然就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賢相、能臣良將身上。《衛(wèi)風(fēng)·淇奧》中有“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用竹子比喻君子有節(jié)、品德高雅。《毛詩序》:“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guī)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這里的武公,是衛(wèi)武公衛(wèi)和,衛(wèi)國的第十一任國君,在位半個多世紀(jì)。在位期間,百姓和睦安定。史傳記載武公晚年九十多歲了,還寬容別人的批評,接受別人的勸諫,廉潔從政,很受尊敬,人們因此作了這首《衛(wèi)風(fēng)·淇奧》來贊美他。從此武公成為中國詩歌文化里第一位奇男子,而詩歌中的青青翠竹,成為中國文化里君子的象征。
《衛(wèi)風(fēng)·碩人》把贊美送給姜莊夫人。詩中有“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lǐng)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意思是姜莊夫人的手指纖纖如嫩荑,皮膚白皙如凝脂,美麗脖頸像蝤蠐,牙如瓠籽白又齊,額角豐滿眉細(xì)長,嫣然一笑動人心,秋波一轉(zhuǎn)攝人魂。這里的“荑”“瓠”都是植物。明眸皓齒、皮膚白皙是古人判斷美人的標(biāo)準(zhǔn),這種審美在中國延續(xù)千年至今。《衛(wèi)風(fēng)·碩人》開創(chuàng)了千古題詠美人作品的先河。清人對這首詩做出了評價,方玉潤:“千古頌美人者,無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語”[1];姚際恒甚至說:“千古頌美人者,無出其右,是為絕唱。[2]”
2.2 愛戀之情
愛情是人類自古以來一個共同的主題。男女主人公相戀、相會往往以美好的植物相贈,以示愛意。《邶風(fēng)·靜女》中一位恬靜的姑娘與相愛的男子在城邊約會,“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這里的“荑”,不是普通植物。朱熹曰:“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意思是初生之茅名為“荑”,白而柔。可見古淇水衛(wèi)地居民很早就會用植物表達(dá)愛戀之情,且在挑選植物時十分上心,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用來傳情達(dá)意。《衛(wèi)風(fēng)·木瓜》中的“投我以木瓜”“投我以木李”“投我以木桃”,都是男女戀愛相贈的禮物。最后一句“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正是男女主人公堅貞于愛情的誓言。
2.3 寄托憂思
古淇水衛(wèi)地居民還常常借植物表達(dá)思念、消除憂愁。風(fēng)光秀麗的淇水是衛(wèi)國人的游樂之地,當(dāng)他們遠(yuǎn)居異鄉(xiāng)思念故國時,淇水就化成抒懷唱詠的重要文化符號。《衛(wèi)風(fēng)·竹竿》講的是拿竹制的魚竿在淇水邊垂釣的女子對出嫁前生活的回憶,全詩以樂寫哀,表達(dá)思家不得歸的惆悵。詩中特意強(qiáng)調(diào)竹子制作的魚竿(“籊籊竹竿”)、松木制作的舟、檜木制作的漿(“檜楫松舟”),就是因為它們都是家鄉(xiāng)的物產(chǎn)。《衛(wèi)風(fēng)·伯兮》另有“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蓬,即飛蓬,又名蓬草。蓬草枯萎后,其莖斷裂,在風(fēng)的吹拂下四散而飛,故稱飛蓬。《禮記正義》:蓬,御亂之草。女為悅己者容。丈夫東征未歸,女子以飛蓬的形狀指代自己頭發(fā)凌亂,突出因思夫而憔悴枯槁,表達(dá)對丈夫的思念之情,飛蓬自此具有憂思懷人的內(nèi)涵。
《邶風(fēng)》《鄘風(fēng)》《衛(wèi)風(fēng)》中借植物寄托的憂思,不僅局限于個人情愛,還上升到家國。《鄘風(fēng)·載馳》作于衛(wèi)文公元年(公元前659年)。據(jù)《左傳·閔公二年》記載:“冬十二月,狄人伐衛(wèi),衛(wèi)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zhàn),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及狄人戰(zhàn)于滎澤,衛(wèi)師敗績。”當(dāng)衛(wèi)國被狄人占領(lǐng)以后,許穆夫人心急如焚,星夜兼程趕到曹邑,吊唁祖國的危亡,寫下了這首詩。這首詩也是《詩經(jīng)》中少見的可以考其作者的詩。《鄘風(fēng)·載馳》中“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抒寫了許穆夫人對故國的“善懷”,刻畫了一個心情沉重的詩人形象。
3 源遠(yuǎn)流長的社俗文化
3.1 祭祀祈福
《邶風(fēng)》《鄘風(fēng)》《衛(wèi)風(fēng)》屬于《國風(fēng)》。國風(fēng)是采自各地的民歌,反映的是百姓日常生產(chǎn)生活,內(nèi)容樸素真實。先秦生產(chǎn)力相對較低,種類繁多的植物成為百姓衣食住行的主要來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基礎(chǔ),同時也與人們祭祀祈福等民俗傳統(tǒng)緊密相連。
古時人類對自然現(xiàn)象認(rèn)識有限,因此對各種自然力產(chǎn)生敬畏和崇拜心理,為求吉避禍,實現(xiàn)人神天地和諧共生,祭祀作為人神溝通的手段產(chǎn)生了。《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3]”意思是國家的政治大事只有兩件,一是軍事活動,二是祭祀活動。可見祭祀在先秦時期人民心中的重要地位。事實上,在先秦社會,祭祀活動已成為社會生活難以分割的組成部分,已融入當(dāng)時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遍觀《詩經(jīng)》,大量與祭祀活動密切相關(guān)的植物,已成為其中帶有特定象征意義的審美對象。《鄘風(fēng)·定之方中》中“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的榛樹和栗樹;《邶風(fēng)·谷風(fēng)》中“采葑采菲”的葑、菲等都是祭祀用品。可見,古淇水衛(wèi)地植物的文化內(nèi)涵。
祭祀既是重要的國家政治制度又是民間習(xí)俗,能夠強(qiáng)化群體凝聚力,使人們在共同信仰和儀式中產(chǎn)生共同體精神和文化認(rèn)同感。
3.2 植物崇拜
桑樹被視為太陽和生命的代表,寓意是生命力的頑強(qiáng)和永生。桑樹崇拜可以追溯到商代初年,商代的神祠設(shè)在桑林,商湯曾經(jīng)在桑林禱告求雨。聞一多先生在《釋桑》中認(rèn)為桑即桑社,是祭祀社神的地方。從古史傳說來看,桑林與民俗活動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其中的活動主要有兩類,一是男女在桑林中幽會,祭高媒之神(即生育之神),以求子。二是在桑林中進(jìn)行祭天求雨活動。求子是為了子孫繁衍,求雨是為了糧食豐收。
《鄘風(fēng)·桑中》有“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描寫男子夢想與自己心儀的少女在桑中幽會。《邶風(fēng)·氓》有“桑之未落,其葉沃若”,用桑葉的季節(jié)變化比喻自己容顏的老去。兩首詩用繁茂的桑樹來隱喻擁有生育力的年輕男女,說明了古時桑樹崇拜的風(fēng)俗。原始的植物崇拜是古人對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敬,它以相對固定的儀式和觀念,維系著個人對社會的群體認(rèn)同感,使個體具有群體歸屬感,發(fā)揮著凝聚社會的作用。
3.3 孝道文化
中國最早的一部解釋詞義的著作《爾雅》對“孝”下的定義是:“善事父母為孝”。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的解釋:“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即“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角的形體,和“子”字組合而成的一個會意字。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孝”的古文字形與“善事父母”之義是吻合的,因而孝是子女對父母慈愛的一種回報。
《邶風(fēng)·凱風(fēng)》有“凱風(fēng)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fēng)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無令人。”此處的凱風(fēng)指南風(fēng),即夏天的風(fēng),比喻母親。棘心指酸棗樹的嫩芽,代指母親未長大的孩子。棘薪指長大的酸棗樹,可以作薪柴使用,喻指母親撫養(yǎng)七子長大成人。然而她付出了這么多,作為詩人的“我”卻沒有成為有德的“令人”。全詩委婉地表達(dá)出孝子反躬自責(zé)之心。《邶風(fēng)·凱風(fēng)》是一首蘊(yùn)含中國傳統(tǒng)“孝”文化的詩歌,體現(xiàn)了七子對母親一片殷切的孝心。宋代蘇軾在為胡完夫母親周夫人所作的挽詞中,還有“凱風(fēng)吹盡棘有薪”這種從此詩直接化用而來的詩句,可見“孝”作為中華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傳延。今天,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孝文化強(qiáng)調(diào)良知與責(zé)任并存,是個人品德修養(yǎng)的基石,是凝聚社會、塑造文化、報效祖國的強(qiáng)大推動力。
4 結(jié)語
草木有心,古人通過草木認(rèn)識天地自然、理解社會人情、創(chuàng)造禮樂文明,形成中國強(qiáng)大的發(fā)源型文化的根基。古今相連,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的今人通過了解淇水兩岸植物的前世今生,看到了淇水文化歷經(jīng)千年歲月洗禮的源遠(yuǎn)流長。它們的鮮活存在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chǎn),是中原文化深厚沉淀的象征,也是匯成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大江大河的涓涓細(xì)流。■
引用
[1] 方玉潤.《詩經(jīng)》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
[2](清)姚際恒.《詩經(jīng)》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8.
[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09.
本文系2023年度鶴壁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校本課題社科類重點課題:淇河文化地理(2023-SKZD-003)的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李雪梅(1972—),女,河南鶴壁人,碩士,副教授,就職于河南鶴壁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