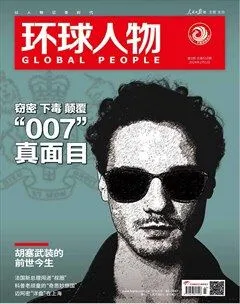孟子的氣與勢
陳正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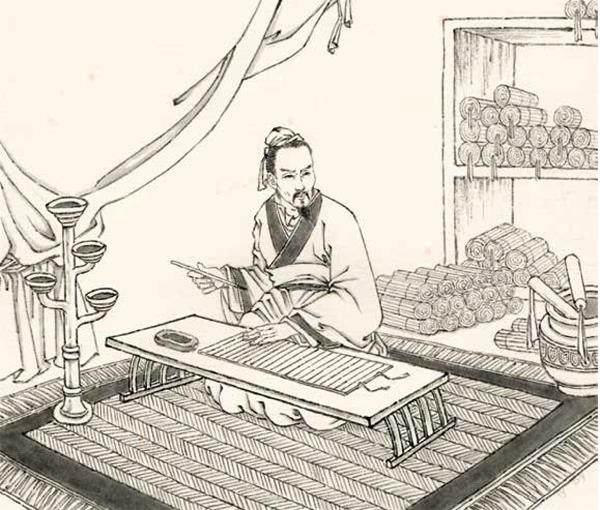
孟子對孔子的基本價值取向既有繼承,也有推進和提升。(馮濤 / 繪)

陳正宏
說起孟子,今天的我們很容易把他跟孔子連在一塊兒,孔孟仿佛是兄弟的感覺。其實兩人雖然在儒家系統里都是數一數二的人物,生活的時代卻相差大約兩百年,雖然都算是周王朝,孔子東奔西走的時代是春秋,孟子則已經到戰國了。
關于孟子的生平,現存真正早期的文獻其實很少。比較靠譜的,只有《史記》的《孟子荀卿列傳》里的孟子傳記部分。這篇孟子傳,總共只有137個字,連孟子的名字都沒記(今天我們知道孟子名軻,是據給《孟子》作注解的東漢學者趙岐的記錄)。而這137個字中,還有40個字是寫秦用商鞅、富國強兵之類歷史背景的。剩下的97個字里,寫孟子實際生平的,只有三點:第一,他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子思的再傳弟子;第二,他到齊國和魏國推銷自己的政治理論,都不受最高當局待見;第三,之所以不受待見,是因為當時各國都忙著合縱連橫,以打勝仗為最高目標,而孟子卻還在宣傳他堅守的三代道德,不合潮流了。所以最后,他只好跟自己的學生一起,做沒有國家資助的自選項目,寫成了《孟子》七篇。
這七篇《孟子》,后來被各分上下,逐步演變,就成了今天我們見到的通行的十四卷本《孟子》。和記錄孔子金句的《論語》相比,它字數上已經翻倍,形式上也多了戰國時代流行的策士論事的精密邏輯和激情說理。但直到唐中葉,《孟子》至多只能算是《論語》的影子。我們看20世紀以來的考古發掘,像河北定州中山懷王劉修墓、江西南昌海昏侯劉賀墓,那樣高規格的西漢諸侯王墓葬里,都一再出土竹木簡本的《論語》,就可知兩千年前《論語》就紅了。反觀《孟子》,雖在東漢班固主纂的《漢書》里記錄了西漢官方典藏有其書,但唐以前《孟子》的書本實物,無論是簡帛還是紙本,到今天好像一片半葉都沒有傳下來。
所以合乎邏輯的推論就是,孟子和《孟子》的地位后來那么高,歷史上一定發生過一次或多次時來運轉的突變。事實也的確如此。這些突變之中,數唐宋兩代接力而行的“孟子升格運動”最為著名:以唐代著名文學家韓愈為先鋒,詩人皮日休為策應,宋代大學者朱熹進一步推舉,孟子在儒家名流的序列里,第一次被抬升至僅次于“至圣”孔夫子的“亞圣”地位;《孟子》一書,最終也跟《論語》一樣名列經部經典。這場運動自有其復雜的歷史背景,這里無法細說。但透過《孟子》一書,看看其中所言能跟《論語》比肩甚至超越的東西,大概就能理解唐宋以后的讀書人,何以對孟子抱有如此高的熱情。
首先是孟子對孔子的基本價值取向有不少繼承。像他在《盡心上》篇里說的“君子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前面說的是行孝悌,中間說的是成君子,最后說的是做導師,都精準地踏在孔子的原有路徑上。
當然也有推進和提升。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他對于個人立身處世提出了比孔子更嚴格的標準。他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離婁下》)這里的“大人”,與孔子所說的“君子”近似,而形象更顯高大。葆有赤子之心的“大人”,在孟子看來,做人的底線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盡心上》)。更高一級則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有意思的是,孟子還進一步為他心目中的大丈夫們設定了種種極端的情境,比如《告子下》篇里那段以“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為開頭的話,由于被收入現代中學教科書里,是今日讀者再熟悉不過的。而對于期待成大事的大丈夫們必須施以那樣煉獄般的考驗,背后的理據,是因為對于負有責任的君臣和士大夫而言,“生于憂患,死于安樂”。也正因此,在最棘手的生死問題上,孟子在《告子上》篇中進一步把“義”提高到一個無以復加的位置: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生取義,意味著把道義的堅守和理想的實現,看得比個人肉身的存在更寶貴、更重要。這樣的理念,作為一個人面對生死抉擇時的一種不二決斷,出現在距今兩千三百年前禮崩樂壞、詐偽層出的戰國時代,不能不說是一種異數。但它在中國后來漫長的歷史中,尤其是歷次反抗外來入侵者的戰爭中,成為千千萬萬烈士奮不顧身的精神來源和行動指南,又說明這一理念在中國人心目中的真實分量。儒家的形象,在孟子的努力下,因此也由相對文弱的文質彬彬的君子,上升為不乏英雄氣概的大丈夫了。
說到英雄氣概,就不能不提孟子在自述修為境界時說過的一句名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在《公孫丑上》篇中,當弟子以“何謂浩然之氣”相問時,孟子還作了一大段解說,中心意思是這股“氣”,是與“義”和“道”相互配合而存在的,當你用正義去培養它,它就會充塞于天地之間。“氣”從一種自然的生態,演變為中國人文精神里一個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應該就是從孟子這里開始的。所謂“人活一口氣”“做人要爭氣”,形容一位正派人經常用“一身正氣”這樣的詞,諸如此類的說法,追溯上去,直接的源頭就是孟子的“浩然之氣”。而作為精神氣質外化的“浩然之氣”,從中國人的普遍意識里說,其實就是對于正義的一種持續不懈的追求和堅守。
舍生取義,意味著把道義的堅守和理想的實現,看得比個人肉身的存在更寶貴、更重要。儒家的形象,在孟子的努力下,因此也由相對文弱的文質彬彬的君子,上升為不乏英雄氣概的大丈夫了。
此外,與“氣”相關,在孟子筆下落墨不多卻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勢”。所謂“勢”,就是情勢、趨勢和潮流。《孟子》里直接出現“勢”這個字的地方,只有很少幾處,但像“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公孫丑上》)之類的話,已經透露出孟子是比孔子更懂得用言語運勢甚至造勢的人。我們看書里,他不時給跟他聊天的對方挖坑,即使對方是一國之君,聊天聊到“王顧左右而言他”也不管,就知道這孟夫子對于辯論上的乘勢追擊,是如何地偏愛。但其實在他的內心,對人性的了解是相當透徹的。他教學生識人,說聽人講話的時候,要“觀其眸子”,也就是注意看對方的眼睛,因為對方的心事,在眼睛里是藏不住的,即是一例。
而以對人性的透徹理解為基礎,加上對“勢”的把握,成就了孟子的另一種顯著的能耐,就是推己及人的功夫。推己及人,在孔子那里,說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與我的邊界感十分明晰;孟子則跨出邊界,更富熱忱,強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用同理心把最大多數的群眾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所以與孔子比較強調個人的學養不同,孟子更多看到的,是作為群體的人的力量,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孫丑下》),要實現“人和”,靠的就不單是讀書人個人的修養了。當然,這方面孟子走得最遠的,是在《盡心下》篇里提出的如下論斷——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在傳統中國語境里,敢說這樣的話,是足夠驚世駭俗了。
驚世駭俗,當然逃不過命運起伏的宿命。即便借了唐宋以后科舉考試必考題那般有利的“勢”,孟子和《孟子》一書,在14世紀之后依然命運坎坷。據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讀了《孟子》,很不舒服,揚言這老頭要是活在我大明朝,絕沒有好結果。而有確證的史實,是這位出身貧寒的明太祖下令刪除了《孟子》里八十五條“詞氣之間抑揚太過”的違礙文字,刊成《孟子節文》一書下發全國,下令:“自今八十五條之內,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并把孟子配享孔廟的地位也取消了。而那讓朱元璋不悅被刪除的文字中,就有上述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實,孟子說的中心意思,脫去君君臣臣的舊外套,不就和我們今天用現代語言表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非常接近了嗎?
史載當時一位擔任刑部尚書、名叫錢唐的高官,公然反對朱元璋貶低孟子,面對幾乎送命的危險處境,錢尚書帶著棺材上朝,聲稱:“臣為孟軻死,死有余榮!”神奇的是,錢氏這股得自孟子的浩然之氣,最后不僅讓朱元璋沒敢痛下殺手,還間接地迫使官方恢復了孟子在孔廟配享的地位。而到了今天,明初刻本《孟子節文》已非常罕見,未經刪節的《孟子》全本,卻是家喻戶曉的大眾讀物了。